- 3
- +143
专访|《在路上》译者陶跃庆:凯鲁亚克及其燃烧的时代
“我一生都喜欢跟在令我感兴趣的人身后,那些有点疯狂的人,疯狂地生活,疯狂地表达,疯狂地渴望被救赎,同时渴望一切,不知疲倦,不落俗套,他们不停地燃烧,燃烧,就像惊人的能连射迸发的黄色烟火筒,如蜘蛛穿过星际,在天空中央你会看见蓝色的中心光点砰地爆裂,所有人都不禁惊呼。”
出版于1957年的凯鲁亚克的自传性小说《在路上》从诞生之时就充满了传奇性,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这部小说是凯鲁亚卡伴随爵士乐、烈酒、药物,在一卷30米长的打字机纸上一口气写完的,这一片没有断句的密密麻麻的文字是凯鲁亚克燃烧的激情,当时三十多岁的凯鲁亚克或许没有想到,在第一部分第九章偶然出现的“垮掉的一代”这个词语后来经评论家们的提炼被用以概括一个时代的青年人的精神气质,凯鲁亚克从来不是一个社会理论家,而《在路上》却极大程度地介入美国人的精神构建与日常生活。因为高度指向青年的精神世界,《在路上》能够摆脱时空的负累,甚至能够脱离文本,读者不必按部就班地从前言、目录开始阅读,随便翻开一章都能看到凯鲁亚克们自由到近乎癫狂的生活,他们纵情于一切美好的事情,毫无目的地漫游。

杰克·凯鲁亚克于1969年去世,今年他的所有作品都已进入公版期,各家出版社纷纷推出最新版的《在路上》。从上世纪60年代凯鲁亚克进入中国的视野迄今,由出版社们牵头,《在路上》再次掀起被读者关注的小高潮。最近,澎湃新闻专访了《在路上》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陶跃庆。
中国大陆对凯鲁亚克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凯鲁亚克是被概括在“垮掉的一代”之中被提及,且中国当时对“垮掉的一代”以及凯鲁亚克的批评都带有阶级意识,认为文中的人物都是堕落腐朽的。196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在路上》的中文节译本,译者署为石荣(黄雨石、施咸荣合译)。这个节译本是“内部参考书”,这个节译本又被称作“黄皮书”,在地下青年中传播,给当时“文革”中被压抑的青年人以极大的震撼。
后来被称为是“文学的黄金时代”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于《在路上》和垮掉的一代变得非常宽容,到90年代,对凯鲁亚克作品的翻译也开始了新的局面。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陶跃庆、何晓丽的译本《在路上》是继之前石荣的节译本后中文世界的第一个正式出版的全译本。
陶跃庆在谈起《在路上》翻译的缘起时说:“我是学英美文学的,我很清楚在西方世界《在路上》的价值,它直接引发了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文化,我当时看的《光荣与梦想》、《伊甸园之门》中都提到了‘垮掉的一代’,鲍勃·迪伦也说这本书对他有强烈的启发作用。其次,《在路上》和当时还年轻的我的心态是共鸣的。我们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我们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觉得我们未来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我们所理解的‘垮掉’这两个字,是青春的激情和勇气,以及一种独立面对社会的个性的心态。”

由此,陶跃庆在第一次读到《在路上》时就获得一种强烈的精神的感召,并起念希望将这本书翻译到中国。1988年,陶跃庆通过同学联系了漓江出版社的编辑沈东子,并很快得到沈东子老师的答复,于是陶跃庆和师姐何晓丽很快将试译的稿子寄到了漓江出版社。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沈东子便同意让他们二人翻译全本的《在路上》,这让当时还是学生的陶跃庆非常激动。
我们就从八九十年代时中国的青年人的状态与对《在路上》的接受开始聊起。
【对话】
“自发式写作”与持续五年的修改
澎湃新闻:您提到1980年代的大学生们没有将“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很负面的群体来理解,而是看到了他们自由又积极的一面,这是否和八十年代的整个文化环境相关?
陶跃庆:是的,大家觉得那个年代非常开明、有活力、非常激情。对于《在路上》,我们这些大学生从没有觉得这部书写的是沉沦,也没有从其中看到颓废。
我特别想总结一下1980年代大学生的特点。第一,我们特别有使命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都认为,我们以后一定会是这个社会的中坚,一定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我们非常的开放,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在你面前,所有的窗户都是打开的,你可以看见任何东西,可以思考任何问题;第三,我们也很独立,这种独立性是指我要有我的想法,我要去思考我能够思考的问题,我愿意为我的想法去学习、去努力、去说服别人。
澎湃新闻:从市场和读者接受的情况来看,在当时的语境中,介绍《在路上》这样一部作品的社会反响是怎样的?
陶跃庆:《在路上》的出版是1990年12月,我拿到稿费是1991年3月。这本书的反响我几乎不知道。首先是我当时已经参加工作了,离开了文学,而且是在政府机关工作,所以跟文学圈相对就有隔阂,不是特别敏感和了解。第二个原因是1990年开始,整个文化界相对比较沉寂,那个时候几乎没有比较大的文学思潮。1980年代是隔一两年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文学思潮出现。进入1990年代,我们很少看到有比较明显的文学现象,文学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开始逐渐降低。大家都开始经商,文学的作用以及发挥的能量越来越小。
第三个原因是当时的出版业和媒体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这么重要一本书的出版,好像没有什么宣传。但是,这本书的影响还是很大,我看到这本书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印了三次,大概印刷了几万册,之后因为版权的问题不能再接着印了。

当时这本书的封面设计非常香艳,特别符合90年代初地摊文学的封面设计,大家一看就觉得吸引眼球,很多人会希望去尝试一下那种生活。而且,对于许多读者而言,“垮掉的一代”应该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封面我觉得非常符合当时典型的对《在路上》的想象、对美国的想象,包括对“垮掉的一代”的想象。
事实上,凯鲁亚克描写的这些人物、情节跟封面的这几幅画其实是比较贴切的。这样的封面可能让人觉得它不像一个经典的、严肃的出版物,当时中国刚刚打开窗口,对于西方文化的想象往往是直观的、甚至是字面的,看不到、也不了解背后的文化。但无论如何,《在路上》中文版出版之后,这部经典之作也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
澎湃新闻:我看到一个材料讲凯鲁亚克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没有断句的,就是一大篇的文字。您最开始看到的英文本是什么样子的?也是没有断句吗?
陶跃庆:凯鲁亚克在1949年时就开始酝酿写这本书,他在1850年代初的时候,把所有的打印纸粘在一起,然后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打字机上不停写作。他几乎是没有断句,一气呵成地把文字给打出来,所以当时大家都说他是“自发式写作”。
“自发式写作”很真实地记录了他所能记住的原始状态的生活,他把他的生活基本上很忠实地写下来了。但是之后在出版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几乎看到这本书的出版社都认为这本书不堪一读,并且在诲淫诲盗。
在出版社的压力下,凯鲁亚克开始不断修改,把中间所有让出版社认为不适的内容几乎全部删掉。许多人可能想不到,这本书里连一句“fuck”都没有,最多的是“damn”,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让你看了之后感到不适的地方,包括一些性的描写都比较隐晦。从1952年他把书稿正式交给出版社开始,一直到1957年正式出版,这几年间他一直在对书稿进行删改。在正式出版前,出版社还让他书中写到的人物原型每人都要签一份保证书。因为他书中写到的人物基本都是他的朋友,虽然改了名字,但是人物原型非常容易辨认。因此出版社要求这些人物原型必须签名放弃索赔,放弃与出版社发生可能的诉讼。
而且,出版社又请来律师仔细审查全书,删除了所有可能会引起诉讼、或者出版之后会引起查封的段落与文字。当时美国的出版文化有很强的法律约束,并非我们所想象的可以随便描写滥交、吸毒等内容。后来有人说我第一版译的是删节本,把里面那些内容都过滤掉了。我根本不会过滤或删改原书的内容,而且以我当时那个年纪,根本不会有意过滤这些东西,因为这是一本名著,既然能正式出版,我们又有什么不能翻译的呢?所以,他怎么写,我们就怎么翻,根本不会去过滤、删节什么。这本书现在这样,是美国自身出版的要求,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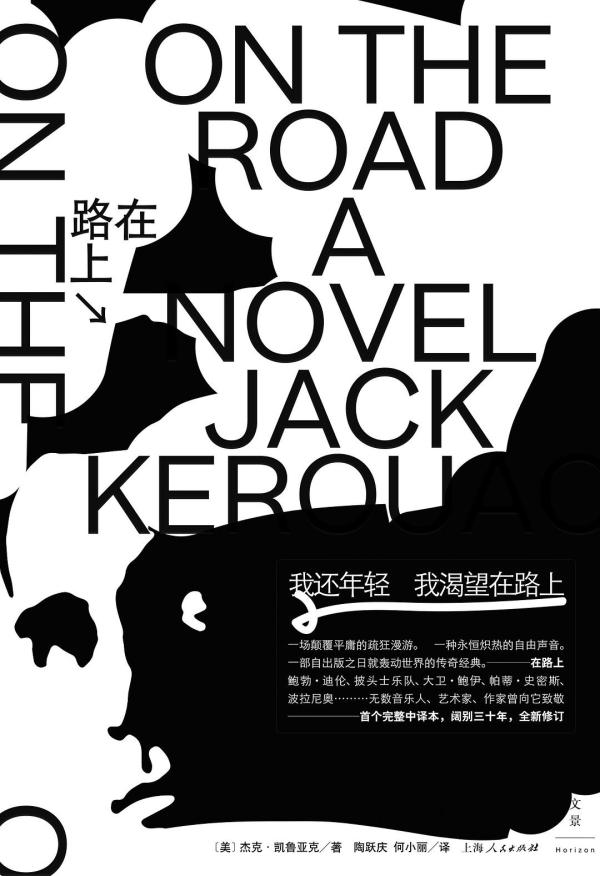
“你每看一个片段都能感受到整本书的情绪,那种激情、无所顾忌、放纵的感觉”
澎湃新闻:作家有时会介绍自己的翻译策略,是尽量贴合中国的语境还是尽量贴合在英文中的样貌。对于您而言,您当时翻译的时候是怎么想着去呈现这个作品?
陶跃庆:在1988年翻译的时候,我和何晓丽商量过,我们的原则是尽量忠实原著,他怎么写我就怎么翻,包括句式。因为英文的句式和我们的不一样,有时候会有倒装、或者强调的重点不一样、或者有语法上的一些问题,跟我们的阅读习惯不太一样。我们尽量会照原著的状态来写。
事实上《在路上》这本书的文学性不是很强,没有那么多文学上的问题,几乎都是平铺直叙地叙述,很少有描述性的东西。国外的作品确实有许多地方对翻译是个考验,比如幽默,如果作品中有幽默的东西对我们的翻译来说就会造成很大困扰,因为幽默与文化、人群、语言、环境等等有很大关系,作为翻译者,有时很难把握幽默的点在哪里、梗在哪里。好在《在路上》并没有太多翻译的难点,你只要把他的情绪、他的状态写出来就行,因为凯鲁亚克是一口气写出来的,所以他给你一种生活一直在推进、一直往前走的感觉。你只要按照他的思路和语言,照实翻译出来就行。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够非常传神地翻译这部作品,跟我们年轻热情的心态有关,我们跟作者和作品有一种共振的感觉,能够感受到作者与人物的神态与语言,仿佛那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这本书不用从头看到尾,没有必要一页一页看,你随便翻开一页看一页是没有问题的,你每看一个片段都能感受到整本书的情绪,那种激情、无所顾忌、放纵的感觉,这本书永远在给你加油、在给人们的生活增加不一样的色彩。你可能生活很平淡,你晚上躺在床上可能会觉得很压抑、很疲劳,这个时候你可以随便翻开这本书,突然就会发现这本书让你放下了所有负担、没有任何的哀痛和伤感,书里的每个人都那么阳光、那么激情,你在生活中遭遇的所有困难、所有问题,在这本书面前全部都不再存在,他只要你跟着他一起在路上往前走。

澎湃新闻:这也是《在路上》最让人精神振奋的地方:虽然凯鲁亚克们在流浪中比较拮据,但是这本书里面没有一句埋怨。您怎样去看待这本书里反映的生活状态和中国的生活状态?
陶跃庆:他们是在离经叛道但却不是有意识地在离经叛道,反而那就是我选择的一条道路,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不是在跟谁比较也不是在跟谁较量,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1980年代也是这样的,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我既然选择了就努力往前走,遇到一些难题那就克服呗。我们习惯了用二分法或用二元论的方法去读作品,自然不自然就会觉得它跟你不一样,它就是有问题。实际上社会本来就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应该得到尊重,那有什么问题呢?恰恰我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集中在某几条路上的时候,其他的路都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我觉得对现在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我没有必要一定要去上大学、或者说所有的才干都集中在金融业、或者都要去挣钱。当整个社会逼着你或者说你没有能力、没有勇气去选择的时候,我觉得不是社会有问题就是个人有问题。但是正常的社会是允许每一个人做出不一样的、独立的选择。
澎湃新闻:如您所说,《在路上》阅读的时候就像是日记一样,随便翻开一章都是完整的历险和一气呵成的故事。那我们怎么去认定它,这是一个文学作品还是自传性质的作品?
陶跃庆:我其实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怎么认定某种文学是有一个固定的框架、或者某一个小说有固定的模本。我觉得一个文学作品之所以有它的成功之处,显然基本的文学构架是完整的,比如说有人物、有塑造、有情节、有结构。最重要的是它能够唤起你的共情,在情感上、在理性上能够让你有更多共鸣感。第三是你能够透过它理性地看到一些东西。我觉得文学作品只要有类似这样的内容就可以。至于是不是意识流、是不是没有情节、或者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非常写实的。这种写实性到什么程度呢,后来有人专门把凯鲁亚克的生活和小说作了对照,在对照的过程中就发现《在路上》所有的原型、所有的情节都跟他当时的生活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这本书的自传性质非常强,几乎可以当作自传看。但是由于后来的修改,这本书已经跳出了原有的人物原型,变成了一种我们所认定的文化的代表。所以这本书的价值就跳出了自传本身的状态。包括说玛格丽特写《情人》的时候也是自传。为什么那本书会成为经典?它所有的细节越真实、越详尽,反而我们阅读起来越像文学。我觉得不在于说真实性或原型性的接近有多少,包括虚构的成分有多少,这个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从中有共鸣、或者能够透视它获得更多的内容,这是我们判定一个文学作品的标准。
澎湃新闻:我觉得大家很在意去分辨这一点,也是很想看一下当时的社会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陶跃庆:其实我觉得第一像你说的可能想看到社会的真实,社会真实就是他描写的;第二是大家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反常态的、反常规的、隐秘的东西。但是首先,美国的出版物有非常严格的法律上的界定,第二它也有社会文化的限制,并不是每个人随便写什么东西都可以作为正式出版物出版的,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给予我们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包括后来美国五六十年代一些反战文化之所以源头能够找到《在路上》也是基于此。并不是说它激发了大家在性解放上的一些内容、或者它激发了大家反战,其实只是它的精神上让大家意识到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在路上》和“垮掉的一代”开启了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垮掉的一代”这个词和这个流派?
陶跃庆:一说到“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们是反叛社会的,是被社会抛弃的,或者是流落于社会边缘的,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都与主流社会相隔遥远。事实上,我觉得凯鲁亚克笔下的Beat应该两个含义。首先它是音乐上的节奏。凯鲁亚克生活的时代,美国非常流行pop音乐和布鲁斯音乐,音乐一直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在书中无数次写到音乐,写到地下音乐会,写到当时的流行乐手,他们认为自己是在pop音乐和布鲁斯音乐的节奏中长大的。第二个就是他们是非常跳动的一代、活跃的一代,并不是沉默的一代,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所以Beat Generation被翻译成“垮掉的一代”并不准确,但如今这个词在中国已经约定俗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没必要去改换另一个词汇。但无论如何,这个词汇以及这个流派的作品讲述的是他们独特的生活,也是他们独特的精神状态,他们在别人不在意的地方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自己渴望的生活。他们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他们更愿意独立去选择。这也就是他们的作品能够影响整个美国五六十年代的重要原因。
应该说,“垮掉的一代”开启和塑造了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化,这部作品开创了美国文学新的传统。它不同于麦克维尔、欧·亨利、福克纳、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等作家,而是将自己的生活凝固成文学新的形式。这样的自发式写作的方式,在美国当代文学中也非常普遍,《裸者与死者》、《洛丽塔》等等作品中,都能看到这一写作方式的影响。
纽约有一条酒吧街,是Beat Generation作家过去经常聚会的地方,金斯伯格的《嚎叫》就是在这条街上第一次发表的。现在这里依然是美国文学界朝拜的圣地,许多作家都会在这里聚集、交流,他们的身上依然有“垮掉的一代”的影子。鲍勃·迪伦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就证明了“垮掉的一代”这一文学流派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澎湃新闻:我在第三部分第二章看到他描写黑人,说白人世界所给予的所有东西都不如黑人世界能够这么得令人心醉神迷。大家也经常会拿这个描述来探讨他那个时代对于黑人的态度,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这其实只是一种诗性的想象,并不是那一代人理解黑人的真实。我觉得这是大家非要去讨论这本书有多少层面是真实的一个原因。
陶跃庆:你说的这个段落是他当时在丹佛看到了一个场景后的感想。当时他特别失落,刚刚经历过一次狂放的交往之后,回到丹佛,度过了一段安安静静地生活。这种安静让他有一种错觉,他开始审视自己和他们的生活,突然感到他们的奔波与丹佛安静的生活反差如此之大,所以忽然有了一种渴望安定的冲动。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内心,虽然他当时觉得黑人的生活非常稳定,非常像他渴望的那种生活。但他内心实际上并不希望自己也这样生活。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对摇滚乐、布鲁斯以及pop音乐的认可。这本书涉及到几乎所有那个年代最重要的pop或者布鲁斯音乐的音乐家,而且这些音乐家绝大部分都是黑人,所以凯鲁亚克觉得黑人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意义,让他觉得有一种原始的、内在的、神灵的东西,他对黑人有一种崇拜感,这种崇拜感在美国的文化中非常强烈。我觉得当时对黑人的理解其实更多的是表现在文化上,至于生活上黑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涉及。我们知道,一直到60年代,美国南部黑人的地位还是非常低下的,所以才有马丁·路德·金。所以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过于纠结、并且用意识形态的眼光去看这本书。那其实是一种误读。这本书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年轻人的勇气与激情、无所顾忌、独立的选择、没有任何负担,甚至连社会批判都没有。他强调的是个人和自我,是自我的独立性。
澎湃新闻:您理解的《在路上》在哪些层面上影响了之后的美国社会?
陶跃庆:我觉得《在路上》和“垮掉的一代”启发了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每次战争之后往往会有一个安定期,二次大战后,大家都非常痛苦,社会也非常撕裂,整个社会希望能够安定下来,所以四五十年代美国的社会氛围是相对稳定和安静的。然而这种安定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比较沉闷,所以很多个人的选择就与社会产生了对立。凯鲁亚克以个人的方式跟当时社会主流的氛围产生了碰撞和抵触,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是凯鲁亚克写《在路上》的时候,美国文化当中的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以布鲁斯音乐为代表的、来自底层的文化,成为整个文化的一种突破。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化和精神就是继承了“垮掉的一代”以及布鲁斯音乐的精神,出现了像鲍勃·迪伦这样的代表性歌手。鲍勃·迪伦之所以成为60年代反战文化、流行文化的代表,就是因为他汲取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养分,也让当时的美国文化有了多样的选择。
应该说,二十世纪前叶的美国文化更多传承了欧洲文学的传统,海明威、马克·吐温等等,他们身上有着明显的欧洲文化的影子。但是“垮掉的一代”和《在路上》一下子把这些过去的传统打破了,开创了一条新路,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类别。美国文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文化,包括美国“迷茫的一代”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生活的,所以美国的文化以前更多的是汲取欧洲文化的营养。但是《在路上》第一次从美国本土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它是完全从本土上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并且滋养了以后的美国文化。所以“垮掉的一代”和《在路上》在美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 伊朗港口大爆炸
- 伊朗外长: 美伊谈判进展良好
- 俄罗斯准备与乌克兰谈判

- 美团:外卖柜始终对全行业外卖小哥开放,更不会限制某平台外卖订单
- 商务部等6部门:放宽离境退税商店备案条件

- 中国的前乒乓球名将,2025年4月,当选中国乒乓球协会新任主席
- “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的简称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