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叙诡笔记|古代笔记中的“名侦探苍蝇”
又到了苍蝇滋扰世间的时节了。欧阳修在《憎苍蝇赋》里曾作此痛骂:“尔形至渺,尔欲易盈,杯盂残沥,砧几余腥,所希杪忽,过则难胜。苦何求而不足,乃终日而营营?逐气寻香,无处不到,顷刻而集,谁相告报?其在物也虽微,其为害也至要……”意思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玩意儿,天天成群结队聚集在一起追腥逐臭、玷污食物,真是可恶至极!
但也正是苍蝇,在我国古代刑侦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帮助人们破获了很多奇案,成为不少古代笔记和法医学典籍中提及的“名侦探”。今天的这篇“叙诡笔记”,咱们就来说说这些故事。
一、苍蝇乃是鬼所变
很多动物,古代和今天的认识大不相同,比如蝙蝠,今人以为其乃种种病毒的载体和传播者,而古代则因其名字中的“蝠”与“福”同音,所以将它视为吉祥的化身,在很多装饰物上都镌刻或刺绣上它的模样。但苍蝇可不一样,从来就没有人当它是个好东西,而且中医很早就从疾病预防的角度,认识到其传播病毒的危害:“搬运污物,传布恶疾,甚为危险。”
明代学者谢肇淛在笔记《五杂俎》中说:“京师多蝇。蝇最痴顽,无毒牙利嘴,而其搅人尤甚,至于无处可避,无物可辟。且变芳馨为臭腐,浣净素为缁秽,驱而复来,死而复生……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蝇与鼠耳。蝇以痴,鼠以黠。其害物,则鼠过于蝇;其扰人,则蝇过于鼠。故防鼠难于防虎,驱蝇难于驱蛇。”在这段话里,谢肇淛认为苍蝇和老鼠一样,都是既小又奸,卑鄙无赖的坏蛋。

其实,不仅京城的苍蝇多,由于古代卫生条件很差,全国各地都受此物危害。清代笔记《亦复如是》中记载,广东有谚语说:“广东蚊子惠州蝇。”惠州有一种树名叫“苍蝇树”,“其树忽臃肿如瘿疣,久之坼开,蝇满其中,见风四散。”据说增城县城外有两株这种树,导致城里面的大街上“蝇甚多,望之似铺荞麦于地者然”。《清稗类钞》里还记载青海有一种苍蝇,“多毒,以其常集于腐臭之动物上也,凡饮食中有蝇点者,隔宿变绿色,误吞之,若触瘴毒。”简直就像生化武器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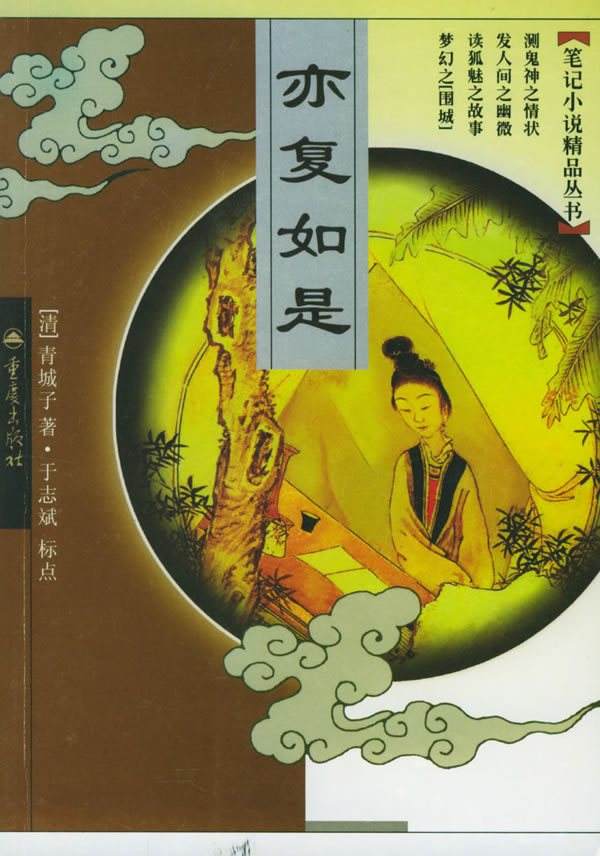
也许正是因为苍蝇传播病毒,在古代医学不昌的情况下容易引发恶疾,是故在古代笔记里,有作者将其与死亡联系起来,清代大学者袁枚就是其中之一。《子不语》中多次写到,苍蝇其实就是鬼变的。“徽州状元戴有祺,与友夜醉,玩月出城,步回龙桥上”,正好有个穿着蓝衣服的人持伞从西乡来,见到戴有祺,欲前不前。戴有祺疑他为贼,上前询问,蓝衣人说自己是差役,要进城去拿人。戴有祺立刻驳斥道:“你说谎!从来都是城里派差役到城外去拿人,哪里有城外派差役到城里拿人之理?”蓝衣人没办法,只好说自己乃是阴间的鬼役,奉了阎王的命令到城里勾魂。戴有祺问他有无牌票,鬼役说有,拿出来呈验,戴有祺见牌票上第三个人是自己的表兄,暗下决心要救之。“乃放之行,而坚坐桥上待之。”四更天,鬼役回来了,戴有祺迎上去问:“人可拿到了?”鬼役说拿到了,戴有祺问在哪里?鬼役说在自己的伞上。“戴视之,有线缚五苍蝇在焉,嘶嘶有声,戴大笑,取而放之。”鬼役气得不行,可是按照“规矩”,凡是在阳间做官或考取功名者,阴间不能轻犯,戴有祺是状元,一个鬼役万万得罪不起,只好踉跄而去。戴有祺回到家,到表兄处探问,家人说:“你表兄病了很久了,三更突然死去,四更天不知怎么又活过来了……”
还有一则故事说,江宁有个姓饶的女人,“当阴司差役之事”,就是兼职在阴间当鬼役,而每次“工作”时都是昏睡不醒。“一日者,饶氏睡两日夜方醒;醒后满身流汗,口呿喘不已。”其嫂问她怎么回事,她说:“邻妇某氏,凶恶难捉,我奉了阎王的命令去捉拿她,她却与我斗了多时,最后我解下裹脚布才算把她手脚捆住。”嫂子问那人现在在哪里?饶氏说就绑在窗外梧桐树上。嫂子前往梧桐树处细细查看,“见无别物,只头发拴一苍蝇”。

二、苍蝇化身名侦探
人死化蝇,以蝇为鬼,当是对其深恶痛绝者的杜撰,但苍蝇能为“死鬼”伸冤,却是在古代笔记和法医学典籍中多有记载之事。
宋代法学家郑克在《折狱龟鉴》中曾经记载过两起靠着苍蝇破案的故事。

其一曰:扬州刺史庄遵曾经在郡內巡视,忽然听到路边传来女人的哭声,“惧而不哀”。庄遵掀开车帘一看,原来是那女人的丈夫死了,正待下葬。他立刻停车询问其夫的死因,女人回答说是“遭火烧死”,而尸体也确实是全身焦黑的过火模样。庄遵却不着急,让吏役们守着那具尸体,片刻“乃有蝇集于首”!庄遵立刻拨开死者的头发查看——得铁钉焉!“因知此妇与人共杀其夫也。”另一案与此案相似,讲的是唐朝政治家韩滉在润州当刺史时,于万岁楼宴请宾朋,忽然听到楼下有办丧事的声音,也是一家的丈夫突然去世,死因乃是病死。韩滉检验尸体,通过聚集在尸体头部的青蝇亦发现从头顶插入的铁钉,“果妇私邻人,醉其夫而钉杀之也”。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苍蝇破案”,还要算是南宋著名法医宋慈于《洗冤集录》中详细记录的一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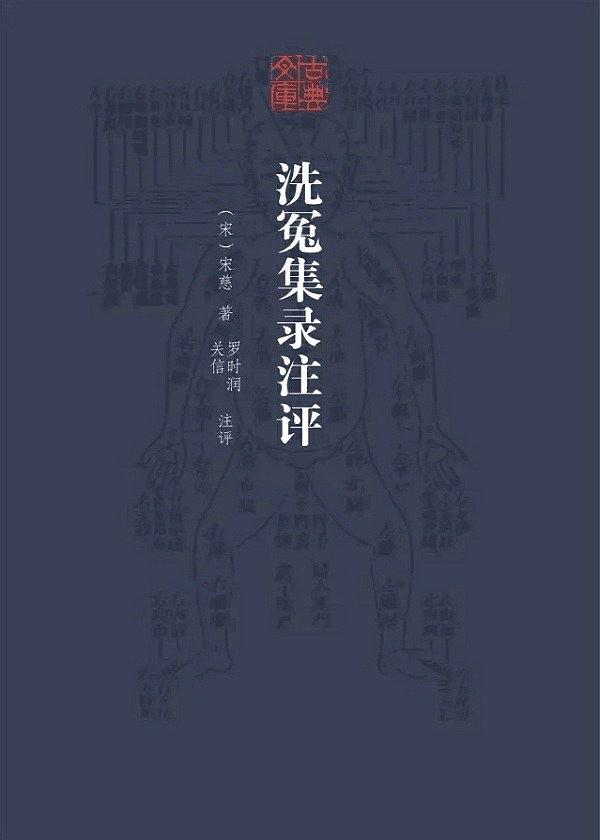
有一个人被杀,尸体遗弃在路边。一开始官府怀疑是强盗把他杀害的,但是经过点检,发现他身上的财物并没有丢失,而且“遍身镰刀砍伤十余处”。负责侦查的官员说:“假如此人系强盗所杀,那么完事应该抢走他的财物,可是没有,更何况伤口这么多,更像是凶手与死者有深仇大恨,必欲置其于死地。”于是他将死者的妻子找来问:“你丈夫最近与什么人结下冤雠?”其妻回答说:“我丈夫为人宽厚,从来与人不结仇,只是最近有个同村的某甲向他借钱,我丈夫不肯借,某甲曾经口出恶言,但是按理说也不至于真的要杀我丈夫啊!”官员立刻下令,让整个村子的所有人家都把家中的镰刀拿来呈验,“如有隐藏,必是杀人贼,我当直接抓捕之”!居民们赶紧将家中镰刀尽数拿出,一下子凑了七八十把。这时正是盛夏暑天,官员让把所有的刀放在庭院的地上,“内有镰刀一张,蝇子飞集”。官员立刻指着问这是谁的镰刀,有个人出来承认——正是那个向死者借债不成的某甲。官员吩咐左右将他拿下,某甲却拒不认罪,官员指着布满苍蝇的镰刀厉声说:“众人镰刀无蝇子,今汝杀人,血腥气犹在,蝇子集聚,岂可隐耶?”左右围观审案者都失声叹服,而某甲者也只好叩首服罪。
这个案子表明,早在宋代,我国的法医学家就已经对苍蝇和气味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现代法医昆虫学研究表明:苍蝇的嗅觉感受器长得很特别,不仅分布在口周围的触角上,而且还大量分布在脚上。每个嗅觉感受器都是一个小空腔,与外界大气相通,里面含有上百个神经细胞,因此它们的嗅觉极为灵敏,特别是对血腥气味。而且当一只苍蝇吸吮腥味后,还会释放出一种招引同类的特殊气味物质,使苍蝇群集而至,并且越聚越多——前面三起案子,通过苍蝇的聚集发现伤口和辨识凶器,道理正在于此。
清代学者胡文炳在《折狱龟鉴补》中还记载了一个案件:有个商人被强盗杀死,仔细调查了很久也找不到凶手,县令严责捕役,让他们务必在期限内将凶手捉拿归案。众捕役们万不得已,只好集资聘请一位退休的老捕帮忙缉访。这一日,老捕坐在河边的茶社里饮茶,见河中一条船经过,老捕立刻站起身说:“杀人凶手就在那艘船上!”捕役们扣押了那条船,一番审讯,船主果然承认了自己杀人越货的罪行。县令和众捕役们都不知道老捕何以能这样“精准”地破案,老捕说:“我看那条船的船尾挂着一条新洗的绸被,上面聚满了青蝇。凡是沾染了血液的丝绸布匹,无论怎么洗,只能洗去血迹,不能彻底洗掉血腥气。绸被本是人盖,上面所沾十有八九是人血。何况那船主就算再有钱,洗被子时怎么会不拆被面,而将整条被子在水中洗濯呢,想必是死者之血已经渗入被里之故,其为盗之明证,一望可知。”诸捕役顿时拜服。
三、数万苍蝇猛扑面
不过,不管苍蝇怎么有利于破案,也不会招人待见,其令人厌恶之处,既在其脏,更在其乱,有它们飞舞的地方,令人顿起不洁之感。
《清稗类钞》记载,学者李铁君很爱干净,“入夏,即洁治一室,常下帘坐”。本想静心读书,谁知苍蝇总是飞进屋子来,到处嗡嗡,而且它们经常落在砚台里,染了墨汁又满室乱撞,搞得书房里到处墨迹斑斑,尤其是珍贵的图书上,宛如甩了无数墨点一般。李铁君气得不行,“如见恶人,亟起治之”,然而想要扑打它们却难之有难,只能苦笑说:“此物之黠,举世无偶也!”
清代学者汤用中在《翼駉稗编》里更写过苍蝇对扑打它们的人实施的一次“恐怖袭击”。宋代政治家钱文敏的夫人有洁癖,“尤恶蝇,每至夏令,日课婢媪扑杀之,习惯已数十年”。这一天她早晨起来,梳洗完毕,正在静坐,突然一抬头,“见梁间灯钩上蝇集如毬”,竟达数万之多!钱夫人不禁毛骨悚然,正要喊叫下人们搭梯子登到房梁上驱杀之,那些苍蝇嗷然扑下,遮盖在她的脸上,“钻耳穴鼻皆满”。家人们惊恐万状,整整半天时间才将这些苍蝇赶走,从此钱夫人看到苍蝇就吓得浑身发抖,“杀机顿息”。
还有更奇葩的,见之于清代学者乐钧所著之《耳食录》:有个人特别讨厌苍蝇,每天拿着根棍子,见到苍蝇就打,有一天恰好有几只苍蝇落到他父亲的头上,“大怒,槌之,父脑裂死,而蝇飞去”,结果他被有司以弑父论罪。为了驱蝇居然一下子闹出两条人命,真是太可悲了。

由此可见,驱蝇在古代是人人头疼之事,但自古难处见高人:清代著名戏曲家沈起凤在笔记《谐铎》里写他的叔父沈鸣皋,曾任直隶保定府太守,他治政严苛,有能吏之名。他的门下有一宾客名叫熊子静,此人相貌非常丑陋,“不甚识字,饮食高卧外,兀然独坐,绝不与外人通款洽”,总之是个很孤高也很奇怪的人。他在沈鸣皋的府邸住了半年,临别那天,沈鸣皋摆筵相送,他说:“我这半年在吃穿用上多多仰仗,今天要告别了,想表演一出奇技请你观赏。”沈鸣皋便“召幕下客共观之”。时值大暑,“堂中苍蝇数百万头,飞者,集者,缘颈扑面者,嗡嗡扰扰,如撒沙抛豆”,熊子静从袖子里拿出一双筷子,“随飞随夹,无一失者,尽纳入左袖中”。满堂观看的人们都很惊讶,熊子静却“谈笑赴主人饯筵”。吃完饭,他打开衣袖说:“你不扰我,我不捉你,速去!速去!”须臾间,流星万点,纷然四散,而堂中绝无一蝇。沈鸣皋才知道此人实乃高士,馈赠金银加以挽留,熊子静不肯接受,反而劝告沈鸣皋说:“愿你治政,就像我治蝇一般,有收有放,则一郡获福多矣!”言罢即扬长而去。
虽然不知道沈鸣皋治政到底有哪些苛察之处,但以治蝇比喻,终究不妥。蝇乃害物,岂能随意“放生”?中国古代对政治治理总是崇拜一团和气,而抵触严格执法,以为那是缺乏宽仁之心。事实上司法所用,只论罪与非罪,不论老虎苍蝇。近年来的反腐风暴已经一再证明,虎豹豺狼、城狐社鼠,对国家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必须除恶务尽,绝不能姑息养奸。就算是比喻吧,假如今天真的有熊子静这种人,于大庭广众之下放走百万只苍蝇,恐怕是少不得挨老百姓一顿暴揍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