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三合村街口

小城故事摄影作品/张灿枫
三合村街口
文/张乃述
三合村街口是片街头广场,是“城中村”三合村的生活中心。在这里尽显小人物种种生存状貌,它混杂着尚未消尽的乡土气息与越来越浓郁的时代风貌。
三合村街口是片街头广场,街面约有十几亩地。你站在街口向北望,整个街衢呈“Y”字形,像只高脚杯,泛着烟然青晖。而游乐园高高的摩天轮映衬在大青山下,口衔街尾的屋脊飞檐,粼粼转动,那整个街衢就似一条扶摇天际的苍龙,一个活着的童话世界。
我打小就知道大青山下有个三合村,我好奇地问母亲,为什么叫“三合村”呢?母亲说,因为那个村只住着三户人家。我说,住在天边,不怕狼吃吗?在我小时候的想象里,三合村仿佛就在遥远的天边,那里有令人神往的原野与林莽。
直到五十年后,因了“乔迁新居”,才有幸走近三合村。只是,原野与大林莽早已逝去,三合村已经变成了一处乡镇,参差错落的街衢,却还渗透着我儿时似曾享受过的市井俚俗,还残留弥漫着一抹久违了的乡土气息。
三合村广场是我平时最喜欢去的地方。它是一个热闹的所在,人烟聚集,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间剧情也在这里上演。“打场子”便是其中之一。
有一天傍晚,在三合村酒杯式街口广场上,有人打了一个场子。场子很大,周围闪烁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两只巨大的音箱八字摆开,中间是声控设备,声控设备后面的暗影里站着两女一男:三人中间的那个女子年龄稍长,三十多岁,剪发头,肤色很白,还算好看,拄着亮晶晶的双拐,穿着上红下黑的丝质衣裤,手里拿着一个麦克风,像是主持。站在她两边的一男一女,显然很年轻,那个后生个子很高,他正在一展歌喉,歌声不是很美。他身边那个小姑娘梳着两根小辫子,端妍清纯亭亭玉立,暗夜掩饰不住她姣好的脸庞。两个人都戴着大大的墨镜。大黑天里为什么还要戴墨镜呢?这让我很是不解。后来看到场地当中的小募捐箱和声控设备前面挂着的彩绘条幅,才恍然大悟。那条幅上写着一行大字:三人行残疾人艺术团。
“好!”场面上有人在喝彩,那个秀气的年轻姑娘正在唱一首十分好听的歌。歌声很美也很甜,音色醇厚清润,她唱歌的时候,面带微笑,样子温柔可人。三个人中数她唱得最好,也最吸引人。这种感觉越发使你猜想着你面前这个姑娘摘了墨镜是不是会更美?
围观的人中不时有“桥头部队(农民工)”走进场子经过那片很大的空地,把零钱放进小慈善箱里。不知为什么,大凡上前放钱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都显得很拘谨羞涩,那种不自然的样子倒像是他们在接受施舍。于是有人就让自己的小孩进去放钱。也有放了钱走人的,那都是些大男人。每有人助捐,站在中间的那个拄双拐的女子就拿起麦克风,说,谢谢。那个美丽的姑娘在美丽的夜色中唱着美丽的歌,一曲终了,又唱一曲,唱完了,拄双拐的女子就接着来上一段承上启下的串场词,然后她就亮起民歌嗓子唱起歌,歌喉还可以。我注意到,一有人上前放钱,她就把麦克风换在左手,接着用右手碰碰坐在她旁边休息的盲姑娘,盲姑娘就对着手中的麦克风微笑着说,谢谢。我发现盲姑娘好像始终在微笑,像是从心里自然流出来的,没有痕迹。那微笑深深地流淌在我的脑海里,荡起微澜。
夜色渐浓,曲终人散。终于等到“残疾人艺术团”演出散场。我见有人围拢过去,也跟脚走到那位盲姑娘身后。盲姑娘还坐在小板凳上。我把目光越过她的头顶和前额极想从上面看到她的眼睛,然而未能如愿。这时,一个“愣货”对盲姑娘说,你能不能摘下眼镜让我们看看?盲姑娘一点没生气,依然微笑着说,摘了,很难看,怕把您吓着。拄着双拐的女子不愿意了,抢白道,天地良心,谁还糟践自己?那个盲后生没好气道,爱咋想咋想。盲姑娘说,我是农村人,家里穷,小时候害眼病,没钱看,耽误了。拄着双拐的女子指指盲后生说,他的眼睛让毒气熏了,还能看见一点。我这两条腿每天站好几个小时,疼得不得了,回家全凭他给按摩呢。有人问道,你是几级?女子道,这条四级这条二级。那人道,我是三级,经过国家鉴定的。我这才看见,说话的那人也拄着一只亮晶晶的拐杖。这时有人说,你们应该找残联。女子说,我们靠自己,自力更生。
这时一辆破旧的中巴开过来,停在道边。司机大汉走过来也不说话,忙着收拾家当。盲后生和盲姑娘闻声上前,抬起一只足有一米多高的大音箱,往车前摸索着走,只见有人上去帮忙。
有人见了车说,嗨,还有车呢。拄双拐的女子说,我们吃住都在车上。我想,显然是大篷车了。
大篷车在夜色中拐了个弯终于走了,大篷车上同样有彩喷:“自强自立”“三人行残疾人艺术团”。我想起了吉普赛人。是的,他们显然超越了“乞讨”的范畴,他们甚至想活得更好,他们努力活着尽力活着,完全靠自己。
我曾经在维多利闹市看见一个紫面皮壮士,光着膀子,满身肌肉,叉开双腿,两脚踏住大理石地面,一根胳膊粗的绳索从脖子后面绕到胸前,打结成枷锁状,尔后又像树根似的伸向地面。他左手卡在腰间,右手握着一根丈八木棍直杵天地。在他的脚下,铺着一张彩喷书写大纸。他说他是个行者,他渴望把自己的苦旅写成大书好与世人分享。看着他的造型,我觉得他更像一种行为艺术。
这倒勾起我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那是一个盛夏的中午,我和几个等着揽活的“桥头部队”在三合村街口一家门脸前的阴影里纳凉,只见一个身材高大束发留须的布衣道人走进阴凉,靠墙坐了下来。他把一只钵就势放在面前,他看也不看我们,就那么旁若无人地坐在我们旁边。“桥头部队”并不在意,依旧有说有笑,可我却怦然心动。我暗自窥视眼前这个道人,虽不面善,却似有几分仙风道骨。我站起来像是漫不经心地走过去,掏出十元钱,十分随意地把钱放进钵里,那道人依旧面无表情,视而不见,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我知道,乞讨就丢了尊严。壮士与道人用一种文化粉饰包装了乞讨,乞讨而不伸手,似乎就保留了尊严的底线。可我很快又知道,也不尽然。
这天中午,我刚出小区,就听见三合村街口一个稚嫩的童音随着麦克风飘了过来,夏日的中午,只有烈日和燥热,而这个天籁般的童音一洗炙热的烦躁,恰似一袭清风拂过心间。我循声而去,一眼看到那个唱着天籁的小孩,却令我心中咯噔一下,满是凄凉。只见一家三口,两个大人几乎是匍匐在地,只有那个年纪大约五六岁的小男孩坐在父母前面,手里拿着一只麦克风在奶声奶气地唱着儿歌,尽管有时跑调儿,然而依然不失天国里的声音。令人奇怪的是,竟无人围观。可孩子依然唱得纯真唱得一丝不苟,唱到高音处,孩子就歪倒身子半跪着,空着的那只手杵在地上,梗着脖子往高处拔音,白皙的小脸都憋红了,脖子上的青筋也暴绽出来。
没有一个听众,孩子唱给谁呢?是唱给天国吗?还是唱给他身边匍匐着的一对“父母”。这时我才开始注意他们。“母亲”是个瞎子,眼球瘪了,眼眶深深凹陷进去,不知为什么她穿着一身土黄色的僧衣,她趴累了就直起身来坐在自己跪着的后脚跟上。“父亲”却未皈依佛门,然而他完全是巴黎圣母院丑陋的阿西莫多相貌,他的脸被烧得疙里疙瘩歪歪扭扭,一只耳朵烧得贴住了耳孔,两只手烧成了肉疙瘩,只有右手还残留着两根抽搐得像鸡爪子一般的拇指和食指,僵硬得勉强能捏起散落在地上的零钱。
我环顾四周,才发现,沿着街口广场周遭的商铺门前,都远远地站着商家或是过往的人们。坐北朝南的街口像一只高脚的酒杯盛满正在中天的烈日,烈日想流泻出去烧毁这个世界。不时有人远远地走过来,把零钱放进这个家庭面前的搪瓷饭盆里,然后匆匆离去。我上前赶紧放下本是买切面的钱也准备离开。
孩子唱完了最后一首歌,“父母”终于直起身来,盘坐在地上。“父亲”从孩子的手里收走麦克风,孩子站起来顽皮地笑笑,张开两臂原地转了一圈,顺手帮助“父亲”整理东西,完全是漫不经心的样子。我睁大眼睛企图看见这个家庭的顶梁柱、这个正需要父母呵护、可父母反倒需要他来养活的、本该上幼儿园的孩子,这个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得意,我还想看见孩子向父母撒娇、嚷嚷着“饿了”的难看的小脸,我甚至想看见孩子埋怨父母如此不利索如此难看的不屑的神情,然而我错了,孩子依旧很乖,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情。
当一切收拾停当,我看见“父亲”站起来脱去干净的还算八成新的黑色半袖T恤,露出了像我在维多利广场看见的那条壮汉一样健硕的古铜色身躯,然后把黑色半袖T恤叠好放进背包中,又顺手从一只小塑料桶中提出一件旧了的豆绿色长袖汗衫,穿在身上,接着把一尺多高的功放音箱背在身上。显然,那件黑色的半袖T恤,是“父亲”的演出服,是“父亲”乃至整个家庭的门面,一如富豪的奔驰悍马。
这时,只见一家人整理好行装,准备走了。我看见孩子往后靠了一下,我以为他想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哪怕只一会儿,当一抹温馨就要浮上我的心头的时候,却戛然而止:父亲先行一步,开拔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母亲的一只手搭在了儿子的肩上,脚也就挪动起来,这一系列默契的动作可能已成机械式的习惯。我目送这一家三口离开了三合村街口,不知道他们的下一站将在何处停留。
后来我知道,三合村是青城不可小视的大村之一,包括外地的许多小剧团凡来青城,必到三合村演出。
那年中秋,三合村在街口广场搭了个大戏台,一个乡间剧团演出“狸猫换太子”。这是晋剧的传统剧目。演员们重彩敷陈把你引入豪奢的皇宫生活,诸等角色唱得不错,我尤其对那个“皇帝”感兴趣,待他下场,我也像村民们那样好奇地绕到戏台后面,想一睹演员的风采。我用手扒开幕布间的一条缝隙,我看见“皇帝”坐在一把椅子上,身上还穿着龙袍,长靴却脱去了,他可能累了,伸直了腿,把脚担在一只板凳上,靠着椅背休息,让我吃惊的是,我最先看到的竟是他的一只深蓝色的袜子后跟磨破了,是因为赶路匆忙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没有针线?那个破洞烂得很大很大,露出的后脚跟如同一颗山药蛋。我忽然想到,身边有个女人或是母亲该多好。从此,奢华的龙袍和破旧的袜子,就时不时地在我眼前晃动。这是一个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那两年,戏剧跌入低谷,大剧团都举步维艰,何况乡间剧团。
高脚杯式街衢之于三合村一如青城的“中山路”那般热闹。酒杯式或饭碗样街口是三合村重要的“政治”中心和文化广场。到了夏日,在黄昏的安逸和冲动里,有人就提着琴鼓丝弦随意在广场的某一片空地上,拉开架式搭起“台”来开锣唱戏自娱自乐。这里会吹拉弹唱的人很多,随便叫几个人就能打起场子。有唱晋剧的,大多唱二人台。乡间的二人台,时有荤的,人们听了会哄堂大笑。我细细听来,其实那些荤的,并不下流,既恰到好处又不失幽默和智慧。
搭起台子来,如果还缺唱的,乐手们就先一个接一个地演奏曲牌,夜幕渐渐降临,悠扬的琴声勾魂般弥漫开来,自然围观的人也渐渐多起来,这往往也是人们相互问候的时候。听见了琴声,就有人来唱,甚至有农民工骑着自行车摩托车,打工归来,路过,拐个弯,下车走进场子,亮开嗓子来上一段,不过瘾再来一段,赢得掌声之后,一溜烟扬长而去。
这天,夜色已晚,可三合村街口依旧琴音袅袅,我走上前去,一眼看见赵师傅在场子当中扯起嗓子正在唱晋剧“打焦赞”中的花脸“焦赞”,唱得不错。一则唱完,赵师傅在叫好声中不无自得地走出场子,他好像在寻找什么人,就一眼看见了我。我说,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吃饭?他说,过把瘾就回。他转而问我,你们咵咵也喜欢晋剧?我说,晋剧也当国粹,生末旦丑都不错,有些叙事段尤其是苦段子,唱得宛转悠扬如泣如诉,让人剜肠刮肚,只是花脸黑头的唱腔有些“刨躁”。“刨躁”是本地方言,有点暗喻“性压抑”。赵师傅听了哈哈大笑。我说,营生挺好?他说,近日个没甚营生。我说,还能揭开锅吧?他说,觉察。“觉察”是乌盟方言,含义很广,只可意会,大意是“将就”“可以”,里面有一种感觉生活的无奈?却又自豪?乐观?或是信心?“觉察”在这里有种精神向上的动感,你好像能看得见。
说着,赵师傅走到一个街头烤鸭大排档前买烤鸭,大布棚子下面,立着三只巨大的装奶罐般的移动式烤炉,年轻的烤鸭师傅,手里操着一把大刀一把小刀,在麻利地剁着案板上的烤鸭,说话间,那小师傅,早已一刀把鸭尖切下来并刮向一边,赵师傅见了,伸手抓过鸭尖放进嘴里,有滋有味地说,鸭屁股也是肉啊。
是耶,是耶。我哈哈大笑。赵师傅并不尴尬,他也跟着笑。
我说,十年前,我的女儿师范大学毕业,我和女儿住在天津拖拉机厂招待所等待分配,就常常到后面也是这么一个裤裆街上的菜市场去买吃食。一日,我们在一个卖熟鸡的地摊上正准备买很便宜的鸡小肘,一位大哥走过来,问小老板,你是哪的?安徽的。安徽的鸡几个屁股?小老板不解地回答,一个屁股。只见天津大哥一挥手把装着一只鸡的塑料袋啪的一下摔在小推车的案板上,怒道,你妈妈的,你看介(这)是几个屁股?说着,天津大哥回过头对我们说,介还了得,一只鸡里掖着四个屁股,介不欺负人嘛。
说完了,我和赵师傅还有烤鸭师傅就哄堂大笑起来。我学着天津话说,介是真事,我忘也忘不掉。我也忘不掉,禽流感的时候,我看见赵师傅竟买了一大兜鸡蛋,我说,你不怕死么?他说,操,禽流感不就是过去的鸡瘟么,有球甚可怕的,前些时鸡蛋贵咱吃不起,现在便宜了,咱不吃谁吃?这时候,赵师傅提着切好的烤鸭准备回家。我说:“显见你这生活还觉察。”赵师傅说:“我儿子早就嚷反着要吃烤鸭,我一直没给买,今日个挣上钱了就潇洒一回。”这时候,一个人走过来喊道:“赵哥走哇。”我回头看去顿然惊愕道:“这不是……”赵师傅笑笑说:“是我兄弟。”我说:“好。是兄弟就好。把苦分给他一点,自己不就少受一点么?!”“是了,是了。唔哈哈哈。”我们都笑。这么笑着,赵师傅与那个人就相随着骑上停放在不远处的平板车,往街衢深处骑去,临走,赵师傅回过头对我说,“遇见活儿您老给搭照一下。”
我望着他们的背影渐远渐逝,想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和好的呢?因为我曾亲眼看见赵师傅把他的这位兄弟打倒在地。想来是穷苦人之间也没有多大的仇恨,恼得快,好也得快。
说起来我和赵师傅的友谊颇富戏剧性。那是我第一天到润宇装饰城采买装修材料,刚到润宇西大门就遇到一场战争:就见三四个人追打一个人,打倒了,爬起来,逃窜,再追打,再打倒,再爬起来,再逃窜,那场面犹如兽斗,打得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围观的人也随着潮来潮去,直到那个人被打得鼻青脸肿满面是血,像大虾一样佝偻着身子躺在地上为止,只见他张开双手护住自己的脸和头,为首追打的那个人就势弯腰跨在他身上,一手按住他的额头,道:“让你日粗!让你动手打人!”被打倒在地的那个人嘴里一个劲地讨饶,“不敢了!再不敢了!”这时有人劝解道:“这小子初来乍到,不懂规矩,算了算了。”那人这才直起身道:“球也恋不成混下满家人,日你妈的。”说着与他的同伙走了。我打听到,这个外来仔抢了人家的活儿。当时我认定那个为首打人者是地头蛇是恶棍。
后来我才知道,能够跑马的润宇装饰城之所以场面不乱,是因为形成了一个潜规则:拉活儿的板儿爷们按“先来后到”的规矩,逐渐把润宇这块大蛋糕分割成无数块领地,各自在自己的地盘上揽活儿,井水不犯河水。
这一日,我看好了一家装饰材料,不巧恰是那天打群架那伙人的地盘,而那个头儿就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形影不离,而且上赶着讨好我,我爱搭不理,没好脸也没好话,他却全然不去理会,其他几个伙计流露出一点不痛快,远远的嘟囔着:赵哥,算了,操,离了鸡蛋还不做槽子糕了。赵哥并不恼,依旧跟在我屁股后面转。我心想,操,下三烂,那日的威风哪去了?跟球要饭的有什么区别,还称王称霸!
我终于没买,我又跑了好几家甚至西龙王庙和南昭君坟都去过了,还是喜欢润宇那一家。好几天过去了,眼看要停工了,只好去那一家,也必须面对赵师傅。
正是七月流火的季节,下午三点,满世界太阳,大地企图把人们烧烤成人肉串。赵师傅和他的一个伙计为我各拉着一车沉重的装饰材料慢慢地“爬”行,我们小区有一大段上坡路,赵师傅爬到车下,调节了一下车链子,然后像纤夫般拉着绳套,头几乎杵在地上,两只死劲攥在车辕上的大手青筋暴绽,脖子梗得俨然是一只拓荒的牛,他哈哈地喘着粗气,看着自己大粒大粒的汗珠子掉在地上摔成八瓣,他耕犁着自己的汗水缓缓地向前挪移。我一下子心疼起赵师傅来,就赶紧帮他推车,他憋红着脸苦笑了一下,困难地说:“不用不用,球,受苦人,不受苦,喝西北风?”他坚持不让我推车,我也只好依他。也就是在那一刻,我一扫前嫌,摒弃了先前对他的成见。
那天晚上,我远远望着赵师傅蹬着平板车在夜空下使劲扭背脊的粗犷与憨态,不禁觉察到“还觉察”。
夜色渐浓,三合村的“桥头部队”,披着满天星斗,在灯光怒放的酒杯式街口,欢乐地在笑声中洗去一天的疲惫,准备迎接明天的生活。
作者简介:张乃述,北京人,长于呼和浩特。写小说也写散文随笔,小说曾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文学“索龙嘎(彩虹)”奖。
本文选自《向度》2020年第一期(春夏卷)总第2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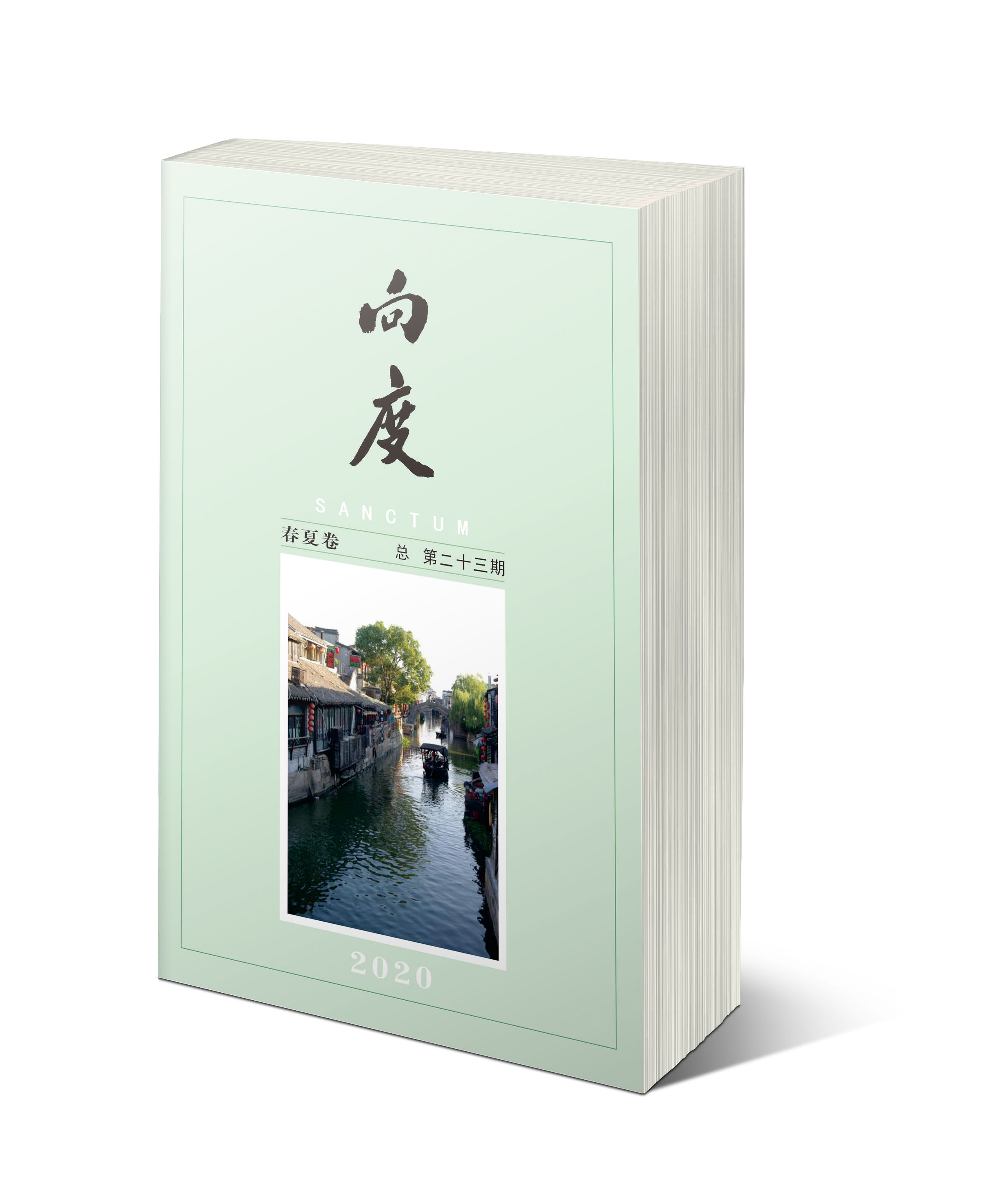
《向度》2020春夏卷(总第23期)2020年6月出版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