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姜鸣谈晚清历史现场的探访与写作

长期身处学院之外、各类事务缠身的姜鸣,一直坚持着对晚清史的研究和写作,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从最早的《龙旗飘扬的舰队》到“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在最新出版的《却将谈笑洗苍凉》中,他将对历史现场的探访与历史文献的研读融为一体,通过不断地重访晚清史现场,既深化了自身的历史认知,也增添了文字的趣味和厚度。在此次访谈之中,姜鸣对相关情况做了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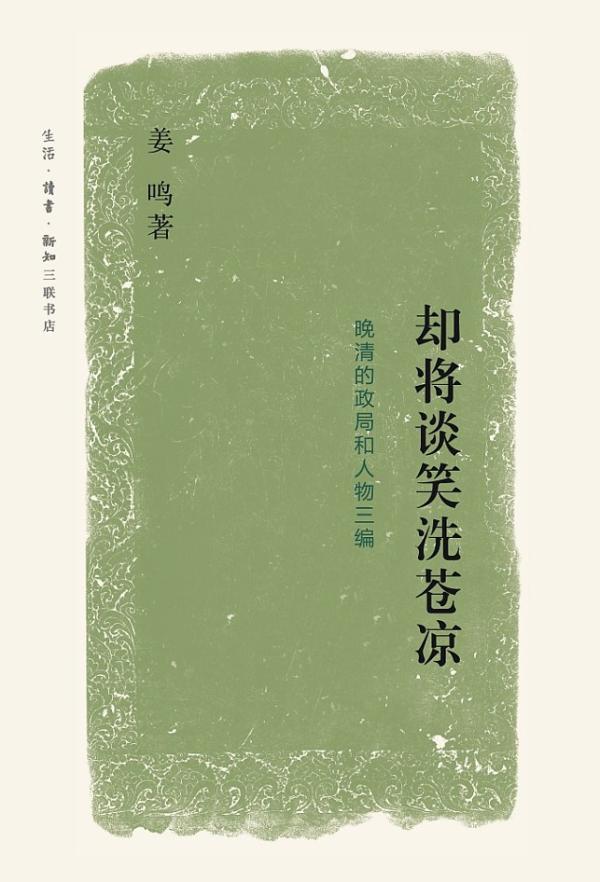
想先从您的书名谈起。这是“晚清政局和人物”系列的第三部,第一部名为《天公不语对枯棋》,第二部名为《秋风宝剑孤臣泪》,到了这一部,您起名为《却将谈笑洗苍凉》,用意何在?
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是陈宝琛的诗,出自《感春》;“秋风宝剑孤臣泪”,是李鸿章的绝笔诗;而“却将谈笑洗苍凉”还是陈宝琛的诗,出自《沪上晤篑斋三宿留别》:“却将谈笑洗苍凉,三夜分明梦一场。记取吴淞灯里别。不须寒雨忆洪塘。”这是1898年陈宝琛在上海遇见张佩纶,写给他的三首诗中的一首。他们1885年2月福州乌龙江金山寺分别,再次老友相逢,都已离开政治舞台十多年,朝局变得更不堪了。我很喜欢陈宝琛的诗,觉得写得真好,譬如《感春》四首其二“阿母欢娱众女狂,十年养就满庭芳”,他怎么能提炼出这样精彩传神的诗句来?对那些讨好慈禧的大臣真是讽刺入骨。“天公不语对枯棋”“却将谈笑洗苍凉”,都是对晚清走到穷途末路的喟叹,也能概括我自己对当时政局的感想。
您很注重将阅读史料和实地调查相结合,曾经奔赴云南、缅甸、张家口、伦敦等地,感受历史现场的氛围,您能具体谈谈是如何现场探访的吗?
姜鸣:对历史研究来说,仅仅埋头阅读文献,与阅读文献之后,赶赴历史现场进行田野调查,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有些历史现场多次前往,每次都会获得新的认识。比如马嘉理事件相关地点我就去了三次。我从中感受到十九世纪英国人对地缘政治的深刻认识,以及布局全球的战略设想。在完成了中国东南沿海五口通商之后,他们一直想要寻找新的通道,能够从缅北进入云南,这样就能够从后方进入中国广袤的腹地了。通过马嘉理事件,英国人找出了一条路:从印度洋的安达曼海口到达缅甸,从仰光坐蒸汽轮船上溯伊洛瓦底江直抵八莫,再从八莫进入云南腾冲。

在“马嘉理事件发生地”横碑前
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理解英国人的战略意图,但是法国人是看得很清楚的。马嘉理事件后,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清政府被迫同意英国人可以从缅甸进入云南。因为当时云南交通极不发达,英国人选择按兵不动,没有立刻将这条道路打通。而法国人呢?1885年清政府取得镇南关大捷以后,乘胜求和,与法国人签订《中法新约》,放弃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此后,法国筹划从越南境内修建通往云南的滇越铁路,从越南海防修到河内、老街,过红河就是中国云南的河口,然后抵达昆明。铁路途经蒙自,有一条通往个旧的岔路,转运锡矿。英国人没想到,自己利用马嘉理事件跟中国人博弈,第一个将印度支那和云南连接起来的竟然成了法国人。当然,抗战爆发以后,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再次成为中国战场连接世界的战略通道。

滇越铁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过一些重要事件。1915年底,袁世凯准备称帝,蔡锷逃离北京,从天津跑到日本,再去香港,坐船到达越南海防,最终经河口回到昆明,发动护国运动,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1938年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师生从长沙撤退,许多著名教授也是沿这条路线转移,经香港、河内、河口、蒙自,辗转到昆明办学,这就是著名的西南联大。

今年4月,我去蒙自、河口现场走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自碧色寨的车站,这个车站也出现在电影《芳华》的结尾,这里经历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个不怎么发达的小村镇,却有法国风情的酒吧。碧色寨是从蒙自到个旧的中转点。法国人修的滇越铁路轨距只有一米,比普通轨道要窄很多,叫“米轨”。从蒙自去个旧的个碧石铁路,是云南士绅争取到路权后自己修的,轨距六十厘米,叫“寸轨”。而碧色寨就是寸轨和米轨的交接处,货物要在此地卸下再装车。这就带来了民国初年中越边境上这个偏僻小镇的繁荣,外商在这里投资开洋行,随着蒙自开放,清政府1889年在此还设立了云南第一个海关。如果不亲身到现场走一走,很难对这一系列历史事件有切身的体会。
您前面提到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对地缘政治的战略构想,能结合您对历史现场的探访展开讲讲吗?
姜鸣:一百多年前,英国的政治家、探险家、博物学家、传教士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事情,都服务于大英帝国的海外商业利益。譬如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驻印当局想渗透西藏,对藏发动战争,其中在江孜打了一百天左右,最后英军占领了拉萨,十三世达赖被迫逃走。我去年去了亚东,春丕河谷是英军当年入侵西藏的第一个地点。实地走访之后,对晚清时英军为何从这里入侵,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地缘政治,英印当局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觊觎和在西藏、云南边境的各种谋划,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英、俄两国在帕米尔地区的争夺等等,有了更为直观感性的认识。
当然,前面所说都是很宏大的。就具体生活方式而言,去历史现场探访给了我更多有意思的发现。我去过藏东芒康县的盐井乡,这个地方井盐资源很丰富。一千三百年前,格萨尔王和纳西土司为争夺盐田资源在这里发生过羌岭之战。盐井乡位于澜沧江峡谷,没有平地晒盐,当地民众在两岸陡峭的山坡上,一层一层垒起了晒盐的木头平台,仿佛梯田,一望无尽。西藏人为了吃盐,只能这样土法生产。这些场景让我产生震撼和联想。我们沿海地区吃海盐,内陆地区有的是吃井盐,也有的是将海盐运输过去,这对当地的民众生活和历史走向会有怎样的影响?在我研究晚清大历史的时候,它可以成为一个有趣的片段。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想无非就是这样,历史研究和旅行都是我的兴趣所在,多走动,多了解,就会觉得历史是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生动有趣的。
那么,在踏访历史现场的过程当中,您获得了哪些研究和写作的灵感呢?
姜鸣:先举一个例子。现在人们谈到云南近代史上的传教士,常常强调他们在当地设立很多教堂,譬如云南丙中洛的重丁教堂,然后通过传教,给少数民族带去了医疗、教育、文字和某些农作物。不少人谈到约瑟夫·洛克博士,会说他向全世界介绍云南。而这些说法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从人类文明传播的角度来看,民众将信仰的一种宗教转变为另外一种宗教,这个过程常常是艰巨而痛苦的,那么,在云南,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滇北和西藏交接处有很多雪山,当地民众称之为“神山”。从天主教角度来看,这是绝不可能的,只有信仰藏传佛教或者云南本土宗教(也就是“本教”),才会有“神山”的想法。藏传佛教在当地有一千几百年的传播史,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当地经常发生反洋教、烧教堂的现象。那么,天主教是如何在这里一步步取得成功,而藏传佛教和本教又是如何一步步败退的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读过外国旅行家的云南游记,譬如莫理循1894年去过昆明,他提到外国传教士在那里传教多年,“还没有男性皈依者,只有两个有希望的试探者”,传教士只能为孩子的小保姆施洗。他是站在英籍澳大利亚人的角度去看传教士的。事实上,传教士对如何发展信徒有一套严格的流程和考核标准,他们会通过种种方式来巧妙地向民众传教,同时又会严格地审视民众的信仰。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传教才发生突破。
我研究北洋海军史的时候,也发现过类似材料,写过文章,收在《秋风宝剑孤臣泪》中。李鸿章的姨太太莫氏,患病后中医无法医治,从伦敦来天津的传教医生马根济给她治好了,从此西医受到李鸿章的重视,每年予以资助,还帮马根济把诊所扩建成施医养病院,天津人称作“总督医院”。从传教士的角度看,认为给总督夫人治病成功,得到资助,扩建医院,是传教的成果。而从李鸿章的角度看,这只是借洋医生之手为民众行善,并不是资助教会。大家的角度并不一样。1881年,中国留美幼童被召回,李鸿章为了安置他们,接受马根济等人建议,在医院隙地创办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堂,安排八名幼童去继续读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清华创始人的唐国安。在马根济看来,开设医学堂也是传教方式,这些孩子都是教会的助手。而李鸿章则在奏折里说,需要为北洋海军培养随舰军医。马根济医生去世之后,关于医院的归属产生了争执,过去双方默契的窗户纸被捅破,结果是重新划分成两家医院。
所以,我在云南看到当地教堂之后,对晚清史产生了更广泛的思考。虽然宗教不是我的研究重点,却有助于我去关注其他一些问题。譬如宋子文的父亲是个牧师,到了他这一代人,为什么会突然发家,成为所谓“高等华人”。这个发家过程,伴随着与洋人深入接触的过程。你弄清楚宋家与洋人做生意的时候如何得到第一桶金,你才能够想象上海这个城市在近代如何发展。
胡文辉在一篇书评中说,“民国以来治近代史者,有一显一隐两大流别:显者是主流,是学院派,隐者是潜流,是掌故派”,而您“是兼有学院派和掌故派两种作风的”。对此您怎么看?
姜鸣:史学历来有文野之分。所谓掌故,也就是稗官野史,一个王朝结束后,野史会大量涌现,有些也写得很深、很有趣味。清末民初的笔记著作,有的是大官僚的后人追忆,讲述家族的往事,有的是把自己听别人讲的故事再讲一遍。不少掌故是道听途说,真假难以辨别,可贵之处在于提供了许多当事人的角度和丰富细节。这些都是需要研读的基础材料,但是严肃的研究不能基于掌故和回忆。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更多的是利用“官书”,例如奏折、诏书、档案等,另外则是当事人的书信、日记,而不是时隔多年的回忆。
像高阳这种谙熟掌故的文人的作品,我历来是很喜欢的。但是这种写作方式的一大问题,就是在史料选择和辨别方面,常常基于一条记载,就展开猜测推理。譬如,关于“甲申易枢”,高阳有个著名论断,孙毓汶是罪魁祸首,是他一手策划用醇王替代恭王,依据是《翁同龢日记》里提到,“济宁电线皆断”,并由此得出结论:孙毓汶与醇王有密电往来(孙毓汶是山东济宁人,当时用其籍贯来代指)。我找到当时《申报》上对电报线修复的报道,就把整个猜想推翻了。我还利用新公布的孙毓汶档案,对他在“甲申易枢”后奉旨去外地查案的行踪进行了梳理。当然不能苛责高阳,非得要求他去翻《申报》、读档案,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严肃的历史研究与掌故家小说家写作的区别。
话说回来,我之所以被认为有掌故派的趣味,我想可能是因为两点。
第一点,是我2015年在《上海书评》发表的一篇关于芭芭拉·塔奇曼的书评里说到的,历史一定要写得好看,“无法表达的历史一无是处”。
这个问题,当年在美国就发生过争议:一本历史书写得好看,这到底是通俗读物还是历史?塔奇曼援引原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韦布的观点,历史学家在写作和沟通中有三个层次:“有话要讲”“话值得讲”“自己比别人更会讲”。塔奇曼发挥说,写作必须和阅读的愿望形影不离。作者必须看到读者坐在他的书桌对面,必须搜肠刮肚地寻章摘句,传递他希望读者看到的画面,唤起他希望读者感到的情绪。非此不能写出生动鲜活的东西。作家的文字生于书页,也死于书页。
在我看来,除了写给专业读者看的论文之外,大多数历史著作不应满足于论文体、学院腔,要追求时代的气息和丰富的细节,追求写得好看。因为历史本来就是绚丽多彩的。同时,专业上也要毫不逊色,能够提出、解决疑难问题。我大学刚毕业时读过《光荣与梦想》,至今印象深刻,觉得这是好看的历史著作。历史怎么能写得好看,对史学工作者是一个挑战。我自己一直在努力尝试,从《秋风宝剑孤臣泪》开始,我就坚持用散文体写作,但是资料要有扎实的依据和审慎的考证,出处全部加注释,在报刊、网络上发表时删去,但是结集出书时保留,一来备忘,二来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方便。读书的时候,沈渭滨老师特别强调这方面的训练,我也由此养成了做资料长编的癖好。现在回看《天公不语对枯棋》,就会发现一小部分的引文出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所以我后来写文章,全部做好注释。

第二点,我特别关注书信、日记等个人资料的使用,从中寻找写作题材和突破。我曾经开玩笑说,大部分的旧信札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日常安排和社交应酬的“断烂朝报”,没什么意思,现在都被当成书法册页,一拍卖就是多少万元,但对史学研究意义不大。想在信件里找出史料,需要特定的条件,如果我跟你天天见面,就不会写信,能面谈就面谈,只是在信中约好见面时间地点。而我整理的《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却很特别。在光绪六年至十年这段时间,沈桂芬去世,李鸿藻上位,在军机处握有很大权力。李鸿藻是“清流”后台,张佩纶是“清流”代表,对中国政治有很多想法,其中之一就是引用能干的人才。李鸿章在办洋务,又是首席大学士、北洋大臣,而张佩纶父亲张印塘与李鸿章是世交,“清流”利用这层关系去接近李鸿章,张佩纶一直向李鸿章提供内幕消息,为李出谋划策。李鸿章欣赏张佩纶的才华,也愿意搭建政治关系。偏偏他们又在京津两地,两个政治家只能不断地用文字来交流对时局的看法,这批信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又比如,我在《上海书评》写过一篇《1880年民间专家组会诊慈禧太后》,在慈禧太后生病的时候,发生了著名的“庚辰午门案”,慈禧派太监给她妹妹、醇王福晋送中秋食物,因敬事房事前未曾知会,被午门卫兵拦住,双方发生冲突,慈禧非要杀卫兵以泄愤。事情后经陈宝琛、张之洞上奏得以化解。“掌故派”前辈徐一士在《一士谈荟》中做过详述。我从当年征召的民间医生薛宝田的《北行日记》中,读到9月14日吉林将军进呈了两支极好的老山参,15日,专家组医生安排慈禧太后服用。16日午门案发生的时候,恰恰是她吃人参后“精神顿健”,并表示“吉林人参颇有效,仍照用”的同一天,这样就为本来病歪歪的慈禧太后,怎么突然之间亢奋起来,寻找到了因果联系。这个细节也是多年研究晚清史的学者未曾关注的。当然,把信札、日记提供的史料与重要事件准确地联系起来,要有大量阅读和梳理史料的基本功。
现在到了网络时代,检索信息的条件更方便了,能够轻易看到很多过去很难获得的材料,自然更能获得灵感。
这让我想到了近年来颇为流行的“e考据”研究方法,能请您谈谈怎么利用网络来获取研究材料的吗?
姜鸣:我也还在探索之中。我的研究方法完全不拘泥于形式。比如,我写《天上的彗星和人间的政治》那篇文章时,突发奇想,光绪年间的中国人对彗星有很多政治上的恐惧,外国人是怎么看的呢?是否有保留下来的图文资料?我去eBay网站上搜索,居然找到两幅当年彗星在欧洲上空飞过的图片,而且画得很好。为了研究李鸿章曾经赞美过的“保卫尔”牛肉汁,我也在eBay上找到大量当年的广告招贴画,并且在淘宝网上买到现在的产品,和形形色色的“李鬼”假货。这就是e考据的方便之处,当然,前提是你要有丰富的想象力。

ebay上出售的早期广告:在所有火车站,十分钟就能喝到一杯“保卫尔”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