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别骗自己了,听书不等于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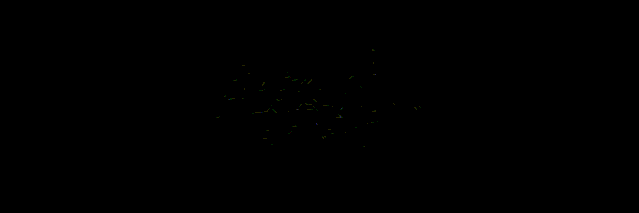

听书≠读书
不是什么书都适合听
1986年,金色的八十年代刚刚过半,路遥从陕北的群山和煤矿中走来,抖一抖尘土,捧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但迎接这本心血之作的,却是文学编辑冷淡的评价:“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慢,就是啰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
小说出版以后,也没有激起什么水花——在先锋文学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路遥过时的现实主义写法似乎已经没什么市场了。
而这时《平凡的世界》还没有写完,如果收到的总是低评价,很难想象路遥将以怎样的心情为这部小说结尾。

作家路遥
转机来自广播电台。
1987年,《平凡的世界》确定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出。节目开播的时候,路遥还在创作之中,电台录第一部用的是出版版本,第二部用出版社样书,第三本直接用了路遥的手稿。

柳青的《创业史》曾引发巨大反响,
也给了路遥很多启发。
孙少平和孙少安的故事随着电波传遍全国,这部长篇小说由文字转化为声音,覆盖数亿人的清晨和黄昏。
电视普及之前,电台是国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也填充了大多数闲暇时光,在那个时代,像《平凡的世界》一样被声音成就的文字并不在少数。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电台崛起,“听书”作为一种阅读方式,也大有复兴的势头,甚至有人断言,最终取代纸质书的将不是电子阅读,而是网络电台。
可是时间拨回到三十多年前,即便是格外感谢广播电台的知遇,一次次“面对那台收音机庄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的路遥,会同意他的读者只去听而不去看吗?

听书会取代纸质书阅读么?

听书年代
无论是否愿意,你都不得不承认,一个属于“听书党”的阅读时代已经到来。
根据上个月底公布的第十七次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愿意阅读纸质书的中国人只有36.7%,而仅仅一年之前,这个数字还是38.4%。剩下的一大半人,除了喜欢电子阅读,还喜欢听书。
过去这一年,有超过三成的国人养成了听书的习惯。2018年,成年人听书率还是26.0%,2019年,这个数字就已经超过了30%。统计结果与我们的日常观感也相吻合:
公园里,健身大爷腰上别的小音箱里播放《三侠五义》;地铁里,上班族用耳机隔绝世界,罗振宇和村上春树交替出现;写字楼里的白领,早就把热播剧集的原著小说听过一遍;多少人在早晚高峰拥堵的车流里,把一直没时间看的《明朝那些事儿》听完……

用高度口语化的语言讲述《明史》,《明朝那些事儿》无疑是适合“听”完的。
和成年人比起来,未成年的人的听书比例更高,达到了34.7%,对于相当一部分00后读者而言,“书是用来听的”可能已经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认知。
随着听众基数迅速扩张,越来越多的资本也瞄准了这个新兴市场——你能想到的任何热门小说、经典著作、成功学秘籍、心灵鸡汤,基本都能找到有声版。
对比看书,听书的优势总结起来很简单:便携、轻松、随时随地。

书籍有了越来越多的载体。
即便轻薄如Kindle,也总要在背包里占一方空间,有声书则只需要一部手机。
和埋头苦读相比,听书在接受上相对轻松,完全可以作为日常生活的“背景音”,一边通勤、做家务、炒菜,一边就能把一本书听完,很容易带来利用碎片时间的成就感。
还有不少人觉得,有声书不费眼睛,甚至不费脑子,可以作为日常消遣。
但听书最大的问题,也恰恰在来自这份“惬意”。

袁枚的《随园食单》,只有读才能品到美食的味道。
清代的袁枚用《黄生借书说》一文劝勉青年黄允修读书时,曾下过这样一个判断:“书非借不能读也。”
为什么借来的书才能读好呢?
因为“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借书者担心主人索要,所以才能读得既快又认真。
反观那些藏书丰富的富贵之家,则“姑俟异日观”,一日推一日,永远也没有读完的一天。
和古人相比,现代人阅读的成本已经很低,而有声书又将这种成本几乎压缩为零——不用购买书籍或阅读设备,不用腾出单独的一段时间,甚至都不用聚精会神。
这种唾手可得的惬意,在降低阅读门槛的同时,也消解了阅读这一行为本身的严肃性。被念出来的作品成了易于消化的流食,久而久之,读者自然也失去了啃硬骨头的兴致和能力。

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与法国作家卡里埃尔《别想摆脱书》里谈到,纸质书是完美的发明,没有其他载体比“纸质书”更适合用来实现书的用途,包括电影、收音机、电视、电脑乃至各类电子阅读器的发明,都无法取代纸质书,反而愈加证明了纸质书的价值。

什么书适合听?
八十年代初,北京,听广播是无数家庭晚饭时的保留节目。每天傍晚,家家户户打开收音机时,总有一个青年骑车穿行在首都的街巷里,听着不同的窗口飘出自己的声音。
这个有点自恋的家伙就是王刚,他播讲的评书《夜幕下的哈尔滨》当时正风靡大江南北。这部讲述地下党与日寇斗智斗勇的小说,经王刚改编后格外成功,评书版的影响力甚至远远高于原著。
那个年代,因为广播而走红的作品还不止这一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早就设置了《长篇连播》节目,《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等名作,在出版之初就被改编成了有声版本。

《白鹿原》很早就被录制成有声书。
陈忠实曾经在文章中回忆,一次在老家遇到一个农民,对方恰好是《白鹿原》的听众,一见面就抓起陈忠实的手,大声讨论起作品来。在陈忠实看来,当时广播剧对普通人的优势,和有声书对当代人的优势是相似的:
“广播电视连播长篇小说,恰是进入社会各个角落读者心中的最便捷的途径,比文本阅读还要方便……乡村人多在炕头或者地头上听,城里人在城墙根下散步时,手里端着收音机听得有滋有味。”
不过,并不是所有作品都适合以有声版的形式传播,那些叙事性较弱、思辨性较强的文本,注定是缺少听众的。
仍以《平凡的世界》为例,路遥写完第一部书的1986年,格非正在谋划自己的成名作《迷舟》,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尚未动笔,苏童凭借《1934年的逃亡》跻身文坛,莫言的《红高粱》刊登在《人民文学》上,引发轰动……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成名作家,在当时几乎都将目光投向一浪接着一浪的欧洲文学浪潮和奇诡艳丽的南美文学。

先锋派的作品读起来尚且晦涩,更不要说只靠听了。
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精神分析、意识流、魔幻主义,在一大批“先锋”作品的映衬下,《平凡的世界》恰是最适合朗读的那一部。
《平凡的世界》那些贴近生活的情节,只要稍微加上一些音效,就很容易变成受欢迎的“广播剧”。但如果非要把先锋文学也制成广播剧,传播效果可想而知。
说到底,文本转化成声音,很大程度上是作品面对传播度的一种妥协,即便录制再用心、制作再精良,都很难完全地还原原作。
比如1984年,《夜幕下的哈尔滨》被拍成电视剧,王刚在其中饰演了说书人的角色:每到关键情节衔接处,这位现代打扮的角色就会跳出剧情,给观众念上一段旁白。这种对故事过于直白的处理方式,在当年还受到过一些争议。

用现代的电视剧制作手法看,插入这样一个说书人角色多少有些突兀,李少红导演在新版《红楼梦》中使用了太多旁白,就已经引起相当多的非议。

读纸质书,
是读者参与作品的方式
过去漫长的历史中,阅读都更像是一种特权,只有少数既识文断字,又有闲暇和财富的阶层,才能读到真正的书,大部分人接触文字的方式,主要是声音。
在中世纪欧洲,吟游诗人背着弦乐器走街串巷,传递那些由历史和传说交织而成的故事,他们自己也成为“活书本”一样的存在。
在东方,戏曲话本是中国小说的源头之一,《阿Q正传》中的江南农民,终其一生都不识字,却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如数家珍。
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中,揭竿而起的华北农民,在衣着、语言、行动等诸多方面,都喜欢对照戏剧舞台上的做派——因为那些唱腔、念白,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最主要的知识来源。

阿Q临终前,还想学着戏曲里的人物唱上两句。/ 电影《阿Q正传》
老舍的名作《茶馆》里,也设置了大傻杨这样一个说书人的角色,用中式曲艺实现了戏剧上的“间离效果”。
“大傻杨,打竹板儿,一来来到大茶馆儿。大茶馆,老裕泰,生意兴隆真不赖……”每一幕的间隙,都有大傻杨的一段快板书,就像旧时代的曲艺艺人,替读者归纳情节。
无论戏曲、评书、快板,还是今天的有声书,听书从一开始就具备通俗色彩,也就多多少少牺牲了读者解读文本的自主权。
一部作品被朗读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演绎,不可能不掺入二次创作的成分,而阅读的节奏、顺序、语调、详略都不完全为自己所掌握,读者也自然而然退化为听众。

老舍作品《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成电影后也很出色,但新技术无疑会影响阅读体验,正如一位读者所言,“读的时候眼前都是范伟的脸”。
以北大教授孔庆东的散文《想念父》为例,文中描述山东籍的祖父因为担心死后不能土葬,执意要从哈尔滨回老家。老人流着泪对儿媳妇倾诉,满口山东腔:
“东儿他妈,我不能在哈拉滨老啊,我要是在哈拉滨老,那个畜牲就把我烧成灰儿,冒青烟儿啦。我还是回关里家老吧。”
这段文字,在录制时应该用普通话读还是方言读呢?如果用普通话,会不会让原文失色?用方言读的话,录制者的语调够不够地道?
而在直接看书的读者那里,这统统不成为问题,无论懂不懂方言,每个人都能在自己心中,以更妥帖的方式重构文字。
另外,中国文学历来有“炼字”的传统,讲究一字千钧,甚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种对语言的极致追求,让词汇的排布本身成为一种视觉艺术,不亲眼看两遍是没法体会的。

阿城的文字经得起反复品味。
阿城的散文《溜索》被收入语文课本,语言极富张力:
“一个精瘦短小的汉子站起来,走到索前,从索头扯出一个竹子折的角框,只一跃,腿已入套……他腰上还牵一根绳,一端在索头,另一端如带一缕黑烟,弯弯划过峡谷。一只大鹰在瘦小汉子身下十余丈处移来移去,翅膀尖上几根羽毛在风中抖。”
这些短促精炼的动词镶嵌在字句中,只是匆匆忙忙地听上一遍,很难捕捉到它们的神韵。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本著作在无数读者心中也有无数个版本,我们所听到的有声书,则基本剔除了这种解读空间,就像从阅读时代退回到游吟诗人时代,只剩下单向度的宣讲。

《读书的少女》,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的油画。

听书拯救了谁?
网络电台的复兴,让线上书场一下子涌入许多听众和创作者,泥沙俱下之中,作品质量难免参差不齐。
不妨去听听大大小小有声书平台上的明清小说,有几个能把常见的“唱喏”一词读对?
更何况声音相较于文字,本就更加模糊,如果只靠听书,《儒林外史》里的yan监生到底姓严,姓闫还是姓颜呢?大概听完一本书都搞不清楚。
阅读的节奏也是由阅读者自己掌控的。
苏东坡提出过著名的“八面受敌”法,也就是一本书反复阅读,每次阅读都有不同的关注点:
“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
每一次阅读的速度和仔细程度都不尽相同的,这一点听书显然很难实现。更重要的,是伴随反复揣摩而产生的思考。

毕飞宇在《小说课》里解读林冲如何“走”上梁山,展示了《水浒传》除了过一把听故事的瘾之外,有更高的文学价值。
《水浒传》里,刚刚和林冲相识的鲁智深,看到朋友的妻子被调戏,马上“提着铁禅杖,引着那二三十个破落户,大踏步抢入庙来”,准备帮林冲打架。
之后林冲发配,在野猪林险些遇害,也多亏了鲁智深跟随相助:“你五更里出门时,洒家先投奔这林子里来。”林冲一路上被押送的衙役百般刁难折磨,鲁智深都在暗中看到,但脾气火爆的花和尚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急着出手:
“夜间听得那厮两个做神做鬼,把滚汤赚了你脚。那时俺便要杀这两个撮鸟,却被客店里人多,恐防救了。洒家见这厮们不怀好心,越放你不下。”
寥寥几百字,前后对照,鲁智深义薄云天、粗中有细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两处细节读起来不过短短两分钟,如果只是为了了解情节而听书,很大概率错过仔细品读的机会。

《水浒传》以塑造人物见长,读一遍可以看故事,再读几遍,每个人物都值得玩味。
当然,每个人所读的书不同,对阅读的定义也不同,不是所有作品都适合听,更不是所有作品都值得看,如果用闲暇时间听听网络爽文,当然无可厚非——但这样的作品,显然不在我们所讨论的“阅读”之列中。
例如最近热播的《鬼吹灯》,原著以情节取胜,不失为网络小说中的佳品,听一听也无妨。但对于真正爱书的人来说,一本好书摆在面前,不由眼及心地读一读,简直是对作者的辜负。
上文提到的黄允修客死异乡,临终前嘱托家人把自己葬在袁枚的随园之侧:“生执一经为弟子,死营孤冢傍先生。”这种读者和作者因阅读而构建的联系,显然不可能出现在说书先生和听众之间。

张大春在《小说稗类》里分析小说的修辞、政治、动作、速度、腔调、方言等,这些意味不一定都能“听”出来。
说白了,有声书更像是摆在超市货架上的矿泉水,便宜、解渴、老少咸宜,利用空余时间听听故事解解闷,当然没问题,但把听书当成真正的读书,指望用矿泉水来代替茶和酒的滋味,那是万万不能的。
不过话说回来,大众娱乐时代,太多人只想喝水也只懂得喝水,那就另当别论了。

✎本期编辑 | 萧奉
图一 | 《X-Men 2》
欢迎分享到朋友圈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