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布加勒斯特:《策兰诗选》
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第三周 第三天
布加勒斯特 保罗·策兰 《诗选》

像卡夫卡一样,保罗·策兰出生在一个双重少数族群,切尔诺维兹(Cernăuți/Czernowicz)的说德语的犹太人社区,此地位于短命的罗马尼亚王国东端。这个王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匈帝国解体后分离出来的一部分。像卡夫卡一样,策兰对格外陌生的希伯来和意第绪文化传统有着浓厚的兴趣。还是像卡夫卡一样,他使用德语写作,归属于德国文学传统,尽管他还会其他族群的多种语言(卡夫卡会捷克语,策兰会俄语和罗马尼亚语)。
1930年代,当策兰还是一个学生,渴望成为诗人的时候,他发现了卡夫卡,那是1938年他动身前往法国学医之前。1939年,学医失败之后,他回到切尔诺维兹,开始学习文学,直到纳粹入侵完全改变了他所在社群的生活。他的父母在1942年6月开始流亡。父亲在集中营里死于斑疹伤寒,母亲被枪杀。他们的死令策兰非常悲痛,他因未能劝说父母与他一起躲藏而一直被愧疚所折磨。不久策兰自己也被捕,他在集中营度过了一年半,直到俄国人于1944年赶走了纳粹。1945-1947年策兰在布加勒斯特住了两年,在此期间,他把卡夫卡的一些小说和寓言翻译成罗马尼亚文,那时卡夫卡才刚刚开始为人所知。1947年12月30日,国王米哈伊一世被迫退位,共产党在苏俄的支持下掌握政权,罗马尼亚变为罗马尼亚共和国。策兰搬往巴黎,在那里度过了此后的生涯,他以翻译为业,并很快让自己的诗歌有了更高的影响力。
正如他的译者约翰·费尔斯蒂纳(John Felstiner)所说,策兰的创作可以用卡夫卡对自身写作困境的陈述来准确形容。卡夫卡对友人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说:“德语犹太作家,持续地挣扎于三种不可能之中:不去写作之不可能,用德语写作之不可能,用不同方式写作之不可能,而我们还能加上第四种不可能:去写作之全然不可能。”在战争年代策兰写下了《死亡赋格》,这是以诗歌形式来回应大屠杀的最早的一首,也依旧是最有名的一首。曾翻译过卡夫卡的普利莫·莱维说:“我把这首诗带在身体里,如同病毒”: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在傍晚喝它
我们在正午喝在早上喝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
我们在空中掘一个墓那里不拥挤……
这首诗以死亡结尾:“来自德国的大师”打死一个女人:
他用子弹射你他射得很准
住在那屋子里的男人你的金发玛格丽特
他派出他的狼狗扑向我们他赠给我们一个空中的坟墓
他玩着蟒蛇做着美梦死亡是一位从德国来的大师
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
你的灰色头发苏拉米斯
(王家新、芮虎译)
在这里,策兰被杀害的母亲弗里茨(Fritzi)获得了两次重生,作为歌德《浮士德》中被背叛的女主人公,和作为《雅歌》中的新娘。《雅歌》是对许多犹太艺术家来说引起持久共鸣的圣诗。其实我的高祖父利奥波德也用它写过一首圣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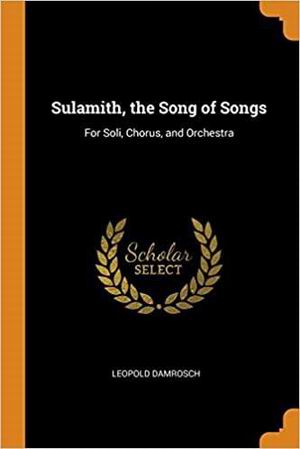
近年来,伟大的当代艺术家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把策兰诗歌结尾的对句作为两幅荒凉的画的题目,画里的金发与带刺铁丝相缠绕。他时常回到策兰寻找灵感,在他的画《黑雪花》里(题目也取自策兰),一本用铅丝做成的书伫立在一片孤寂的风景中。

在策兰后期的作品中,他不断削减诗句,接近沉默的境界。这些诗可以与萨缪尔·贝克特(Samul Beckett)的晚期作品相比较,又更接近他的朋友奈丽·萨克斯(Nelly Sachs)那被痛苦缠绕的诗歌。纳粹掌权之后,萨克斯与母亲一起逃往瑞典,她写作战时创伤的诗歌让她赢得了1966年的诺贝尔奖。她在1959年给策兰的信中写道:“在巴黎与斯德哥尔摩之间划过痛苦与平静的子午线。”
第二年,策兰在接受另一个重要文学荣誉毕希纳奖(Büchner Prize)时,发表了题为《子午线》的获奖演说。他把诗歌形容为“一个反词(counter-word),一个切断了那根‘线’的词,一个拒绝向‘历史’的闲荡者和游行的骏马卑躬屈膝的词,它是一个自由的行为。它是一个步伐”。在一首献给萨克斯的诗《苏黎世,鹳屋》(1963)中,他回忆起他们多年通信后终于在苏黎世相遇的那次交谈:
我们言及“太多”,也
言及“太少”。说起过“你”
和“非你”,谈论过
澄明中的混浊,谈论过
犹太人的事情,也谈论过
你的上帝。
……
说到你的上帝,我
反对它,我
让我曾经有过的一颗心
去期待:
期待
它那至高无上,发出垂死声音的
怨尤之语——
(孟明译)
策兰晚期的诗,就像萨克斯的那样,剥离一切的赤裸着,却又有无尽的回声:
那羊角号之地
在闪光的深处
空经文,
火炬那么高
在时间洞中:
听深处
用你的嘴。
在这里策兰创造的词“空经文”(Leertext)转换自“教经文”(Lehrtext),特指圣经学习。
或许对策兰晚期诗歌最好的解读是他妻子所画的插图,吉赛尔·策兰-莱特朗奇(Gisèle Celan Lestrange)是一位版画家,这是他们1965年的书《水晶呼吸》里的蚀刻画:

策兰越来越被抑郁症折磨,他数次住进医院,1970年,五十岁的策兰自沉于塞纳河。然而直到最后,他的诗依旧明亮。1958年,当他获得一个文学奖时,策兰说在经过战争的恐怖之后,“唯有一样东西仍可触及,在所有丧失中仍亲近而踏实:语言。是的,语言。尽管发生了一切,它仍旧抵御着丧失。但它必须穿越没有答案的自身,穿越可怖的宁静,穿越千万种谋杀言辞中的黑暗。它穿越了。关于发生了什么,它没给我任何词,但它已穿越。穿越了并能重新浮现,因这一切而变得更加丰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