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丨蔡洁皓:不仅要把患儿的病治好,还要关注孩子与父母的关系
原创 唐晔 晔问仁医
人 物 介 绍
蔡洁皓,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传染感染科主治医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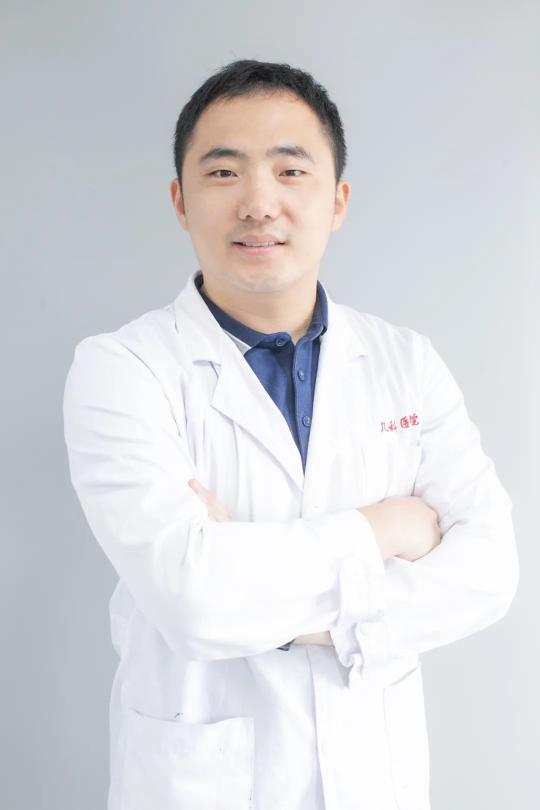
与他的聊天,很轻松。
他刚从战疫前线回来,已经洗净了铠甲上的征尘,以后的日子,但愿岁月静好,江河无声。
事实上,他的战疫分两个阶段,一场在本院,另一场,在公卫中心,他的病人也分两拨,一拨是本土病人,另一拨是输入性病人。
不过,他觉得在公卫中心,得到了人生的洗礼和顿悟,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在他担任儿科医疗队队长的一个多月,他演好了自己的角色,在这一行人中,他是率队的将领,在医院领导面前,他是冲锋的勇卒。大兵小将,正适合这位年轻的主治医师。
他终于送走了最后一个新冠患儿,大家闹着要送他礼物,他说,你们好好的,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他知道,这辈子与他们不会再相见,就这些消失在人海,相互挂念,相互回忆,直到相忘于江湖,真的挺好。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他是个最有耐心的父亲,最近在和女儿一起阅读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的《父与子》。他说,重读这部作品,对他这一辈80后的人来说,已经带上了符号的色彩,重温起来,就具备了双重的意义:怀旧与思念。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找回当年那颗单纯的心。”
我当然也读过这些漫画,那位肥胖、谢顶、平凡无奇的父亲,是多么可爱的人啊,我总是想,在这个冷眼如针和充满反讽的时代,在这个幽默越来越冷、越来越黑的时代,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眼里再也流露不出那种充满爱意和智慧的眼神?
我告诉了他我的感受,阅读这部漫画,展颜之余总觉得眼眶发胀,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是的,我相信,每一个读《父与子》的成年男人,都会不由自主想起童年,想起曾经如山一样给我们保护,如今却垂垂老去的父亲。我甚至意识到,父亲当年的强壮往往是由信念,而不是肉体来支撑;他的轻描淡写,往往是精疲力竭时,咬紧牙关的不露声色。
“是的,一个成年男人,只有当他读懂了自己的父亲的时候,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男人;只有当他自己成为了父亲的时候,才真正算得上一个男人。”他说道。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的是父与子,也是长大成人的必由之路。情感也罢,职业也罢,大抵如此。做人是这样,行医也这样。
最后,我们怀念了一下《父与子》的作者,伟大的德国漫画家卜劳恩:他出生于1903年,原名埃里西·奥赛尔,幼年随家人迁居卜劳恩市,后以该市名称为笔名。1934年到1937年,他创作了不朽名作《父与子》。1944年,因纳粹迫害自杀身亡。他本人于1931年拥有了可爱的儿子克里斯蒂安,成为父亲——那一年,他28岁。

冲锋号吹响了
唐晔:蔡医生,请回顾一下您何时进入战疫模式的?
蔡洁皓:好的。1月19日当晚送来第一例新冠患儿的时候,我正好在急诊排班。当时我有一种预感,冲锋号已经吹响,战斗拉开大幕,我很有可能被调回我们的主战场——感染科病房。那一阵医院的氛围很凝重,果然,两天之后,领导正式通知我,调回来参战。于是,21日我回到了病房。
唐晔:当时的心情如何呢?
蔡洁皓: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是激动,作为一个感染科的医生,能捞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仗打,总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笑),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么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有了用武之地,特别在国家、城市、单位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能够担当起来;而另一方面是犹豫,并不是考虑自己的风险,而是因为,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老大6岁了,老二才5个月,一旦家里人因我受到感染,我将难以面对我的亲人。
好在,犹豫很快就打消了,一方面是因为这次战疫,我们的院感防护特别扎实到位,令人安心;另一方面,上了战场,和战友们朝夕相处,穿上全套防护设备进入病房,眼睛里只有患儿,一切担心犹疑都抛在脑后了。从1月21日到3月23日,两个月零两天的时间,迎来了我们第一阶段的胜利。
唐晔:这两个月,主要的压力来自哪里呢?
蔡洁皓:主要的压力有两个。第一,病情是未知的。就像面对一个陌生人,不知道这仗该怎么打,说它是冠状病毒,表现还不一样,无论是传染性还是致病性,致死率,都不一样,在未知面前,很是棘手;第二,病人的数量是未知的。就怕一下子病人全来了,人满为患,无处收治,压力就会空前巨大。
我记得,1月下旬到1月底,包括整个春节,我整天焦头烂额,一方面是临床,另一方面是参与制定各种预案——万一患儿大群涌来,该送到哪里去,要有一套相应的预案,还要参与制定一线工作流程的细化,比如送样标本——哪天采样,谁放标本,放在哪里,谁来取样,何时出结果,如何反馈到临床,等等,牵扯到多部门协调,必须照章办事,以免挂一漏万。
唐晔:听说还发表了文章?
蔡洁皓:是的。我们的病例来的相对较早,所以就想把诊治的体会写成文章,早点告诉大家,让同行看看我们做了什么,遇到了不至于那么恐慌。我和曾玫主任一起写,2月初,这篇文章就投给《中华儿科》杂志发表了,当时文章很受欢迎,浏览量很快就攀升到该杂志全部文章阅读排行的第二位。接着我们又写了一篇英文的文章,发表在国际感染界里一本著名的期刊上。
唐晔:第一阶段的战疫,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蔡洁皓:每个患儿都是个体化救治,总体来讲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并没有重症,这点让我们欣慰。而且,从疾病的认识来讲,危机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更耐心地认识它,这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唐晔:到第一阶段快收工,也就是病房即将清零的时候,是怎样的感受?
蔡洁皓:早中期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晚上要加班,等核酸检测报告,写各种流程,甚至会熬个通宵都不知疲劳。而3月下旬即将清零的时候,开始关注自己,发现还挺累的(笑),想着仗打完了,可以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了,很开心。不过,还没来得及得意忘形,第二阶段的战斗又打响了。

唐晔:我知道,您授命率队支援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 ,说说接到任务的情况?
蔡洁皓:3月23日下午5点,我在市疾控中心,接到了医务科主任电话,有点突然。说实话,对这种突然的使命,已经比较习惯了,已经没有两个月前那种激动与忐忑,而更多了一份自信和从容,和家人匆匆告了别,7点钟就坐上了去金山的汽车。这是儿科医院派去支援公卫中心的第一支队伍,5个人,我是其中唯一一位医生,其余四位是护士,我是这支医疗队的队长。
唐晔:您这次出征的任务是什么,到了公卫中心,又发生了什么呢?
蔡洁皓:整建制接管公卫中心的儿科,这是我们的任务。刚到的时候,就4例患儿,一个医生肯定是足够的,后来就越来越多,于是,我们院领导就决定派出第二批医疗队队员。3月27日,第二批队员到位了,我们组成了一个16人的医疗队。
唐晔:作为队长,您遇到的难点是什么,又是如何解决呢?
蔡洁皓:第一,电脑系统程序不同,这个困难马上可以克服,多操作几次熟练一下就行了;第二,病房布局不同。这就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面对。比如,缓冲区、清洁区、污染区、半污染区等等,要非常熟悉,一旦走错,就可能造成污染。我刚到的几天,亲自走了几遍,摸索出一套心得,新队员来了以后,经过培训,很快都熟悉了;
第三,用药不同。儿科医院有很多院内制剂,到了公卫中心以后,没有这种药物,即使有,剂型、规格也不同。我们向本院领导反映了情况,医院很支持,想方设法把儿童的专属药物送来了公卫中心;
第四,面对患儿的突然间增多,给了我们医疗队沉重的压力。因为不知道后面是否还会源源不断,而患儿越多,有可能就出现重症病例。我们和公卫中心的领导也一直在做预案,好在,有惊无险,所有的预案都没有用上;
第五,也是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医务人员的防护,因为流程不一样,就怕防护中间出了问题,稍一闪失,医务人员就有被感染的危险。这是零容忍的,一旦发生,我会惭愧一辈子。我和同去的一位护士长,对整个医护人员进行反复培训,好在,几乎所有人都参加过第一阶段儿科医院的战疫,都有较好的防护基础,这一关,大伙儿顺利通过了。
唐晔:第二阶段的患儿比较特殊,在治疗和护理上,又遇到怎样的情况呢?
蔡洁皓:因为有不少是外籍患儿,沟通交流是一个难题,有些孩子并不说英语,说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或者其他语种,我们就找了一种专业翻译器,临时抱佛脚解决问题。此外,还有生活习惯。有的患儿有种族习惯,或者宗教信仰,还得照顾好他的特殊饮食,在多部门的协调和帮助下,大家搞了一个小程序,扫二维码点单,他爱吃什么,能吃什么,自主操作,一目了然。

唐晔:这次您要带一个团队打仗,必须有自己的领导力,说说您的感触?
蔡洁皓:一个多月在另一个战场,带兵也是头一次,的确成长很快。在之前,我是一个普通的主治医生,许多能力是欠缺的,而这一次领兵打仗,让我感到自豪,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现在回过头来看,真的是进步很多,以前只要把我的病人管好就行了,现在不仅要管好病人,管理好一个病区,还有管理好同事,把大家完完整整、安安全全带回家。
唐晔:听说您部署了一些必要的管理工作?
蔡洁皓:是的,首先是严格的考勤制度,加强纪律性。当然,我会以身作则;第二,排班时尽量两三个同事一起上班,互相有个照应,不让一个人落单;第三,加强院感的培训,培训一次还不行,多次演练模拟;第四,大家在外隔离很久,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会孤单,会想念家人,会出现各种焦虑和失眠。我们请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医生,陈俊主任,给我们上了一堂讲座。就讲“疫情下如何做到心理评估和处理”,解决了许多心理困惑,真的很管用。
唐晔:作为这支医疗队的大家长,其实您也很年轻,您对那段时间很难忘吧?
蔡洁皓:是的,其实大家也都很年轻,都合得来。有人过生日,我们就组织生日会,切蛋糕,偶尔还会玩一下“狼人杀”,当然,一定会控制时间,绝不影响别人。
唐晔:临床上,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病例呢?
蔡洁皓:我们在公卫中心的工作模式中,有个疑难病例的专家会诊制度,几乎每天都会和儿科医院曾玫主任等,连线会诊。印象较深的有一个患儿,影像显示肺炎相对比较重,连续1周多一直发烧,持续高热,经过专家组会诊,还有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重转轻,最后终于痊愈出院。还有一个患儿,经过治疗,看上去已经活蹦乱跳,但就是很久很久出不了院——核酸检测始终都是阳性的,漫长的等待,看着周围的孩子都出院了,对这个孩子来讲,是极大的煎熬,甚至偷偷哭过几次。所以,我们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每天都会多次到孩子的病床,同这个孩子说说话,安抚一番,让她破涕为笑。当然,最后检测还是转阴了。
唐晔:您跟患儿沟通,他们会跟您说些什么吗?
蔡洁皓:每个孩子都不同。有的外向,有的内向,有的是话唠,拉住你不放,一聊聊半天,想走都走不成(笑),有的是闷葫芦,问两句答一句……所以,不同患儿有不同的沟通方式。
唐晔:面对新冠患儿,对临床医生来说,有没有哪项工作是最具风险的呢?
蔡洁皓:采鼻拭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讨论下来,觉得还是要医生去采,一方面风险很高,另一方面,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此外,还涉及到一个语言交流的问题——很多都是外籍患儿,要同孩子沟通,也要和家长解释。过程很艰难,每次采完,都是鸡飞狗跳。有的孩子死活不让医生靠近,哭声响彻了整个楼层。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没有太多的育儿经验,只能硬着头皮,以家长作后援,想尽一切办法对付这些孩子,如果表现好,会给个小礼物作为奖励。总之,要保证质量,顺利完成任务。
4有感触,更有感动
唐晔:经过此疫,您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蔡洁皓:原先看问题,可能只是关注临床那个点,现在的思路会更宽广一些,这就是人文吧。比如,不光是要把患儿的病治好,还要关注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有些家长当孩子一生病,就变得非常焦虑、急躁,甚至会打骂孩子。这时候,我们就会去做家长的工作,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再比如,我以前管好自己就够了,现在要考虑同事们的感受,这样做是对我自己好,还是对所有人都好。
这次战疫,还让我看到了生命的活力。就像有一句话说的,爱笑的人运气总不会差,从孩子的身上就看到了,他们的精力是很旺盛的,痊愈之后活力四射那种感觉,真是美好。看到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我就想,这份工作是极有价值的,你想做的事,正是你热爱的事,那就追随内心去做,会有不断的激情在燃烧。
唐晔:有感触,更有感动吧?
蔡洁皓:其实有很多的感动,有一家武汉来沪的,一共八口人,其中七口人感染,两个孩子住在儿科病房。老人已经上呼吸机了,病得很厉害,年轻的还比较稳定。这一家人抱成团,心非常齐,从不互相抱怨,而是相互鼓励,不离不弃。最后他们都顺利地出院,当全家人再相逢抱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劫后余生的团聚,悲喜交加的释放,让在场的人都泪流满面。还是那句话,为了他们,我们付出再多,都是值得。
再说一个感动,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受到孩子们的小礼物,比如卡片,孩子们很敏感,会觉得我们儿科医生真心关注他们,真的会对他们好。有个大女孩,才艺出众,会花样滑冰,会舞蹈,还会做手工。她出院后,给我们每个医护人员都做了一件手工小礼物,礼物目前还在路上,比较神秘(笑)。其实,将来也没有什么机会再可以见面了,希望就这样消失在人海,大家互相挂念,互相回忆就好了,我希望他们都好好的。
唐晔:你现在已经回到正常的状态,解除隔离回家,有没有特别激动?
蔡洁皓:对,一走两个月了。我的大女儿哭了好几回,她送了我一面自己做的小旗,上面写:我有一个医生爸爸,很自豪。
唐晔:您是共产党员,能不能感受到在这场战疫中,党性的力量呢?
蔡洁皓:是的。党性是使命感,也是试金石。在关键时候突出先进性,共产党员挺身而出的那一刻,让我觉得很光荣。
唐晔:回到医院以后,最想做的是什么?
蔡洁皓:回归到我最初的工作状态,做好临床和科研工作,要想对病人好,光做临床是不够的,还要把科研做起来,让更多人受益。
唐晔:在生活方面,有什么最想做的事情?
蔡洁皓:和家人在一起,多陪女儿玩玩。以前老想着带孩子要去这里旅游、那里旅游,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最好的长情,就是陪伴。我每个晚上会和她讲故事,分闭眼故事和睁眼故事。睁眼故事,最近在讲德国漫画大师卜劳恩的《父与子》,闭眼故事,那就搜肠刮肚,挖空心思编故事,讲大概半个小时,她就睡着了。
唐晔:当初考医科大学是出于什么想法呢?
蔡洁皓:我母亲是护士,她虽然工作很忙,但我觉得她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一直愿意从事一些对社会、对人类有贡献的职业,能体现真正的价值,如今我找到了这种价值,这就是医者仁心,救死扶伤。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