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这段故事搁置了半个多世纪,她是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
编者按:伊迪丝·汉恩是在奥地利快乐成长的犹太女孩,她梦想成为大法官,却在纳粹入侵那天早早结束了自己的青春。亲朋离散,家族崩毁,伊迪丝被迫前往劳动营从事极不人道的体力活动,并不得不隐姓埋名,在德国人中周旋生存。
当伊迪丝遇到一个喜欢她的“纯种雅利安”男人,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因为渴望爱情,还是活下去的本能,让她同意与他步入婚姻。与纳粹军官结婚,真的能拯救自己吗?还是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当年的细弱声音
过了一段时间,洋葱买不到了。我从勃兰登堡市立医院红十字会的护士同事之间的谈话中听到,元首需要洋葱制造毒气征服我们的敌人。不过,我当时——那是1943年5月——觉得倘若能吃到一颗洋葱,第三帝国的公民会很愿意放弃享受毒死敌人的快感。
那时,我在外籍工人和战俘病房做护理。我的工作包括给所有病人泡茶,把泡好的茶水装在小推车里送到他们病床前。递给他们时,我尽量露出笑容,用愉快的声音说声“日安”。
一日,我推着空茶杯回到厨房洗刷,撞见一位资深的护士在切一颗洋葱。她是一名军官的妻子,来自汉堡。我似乎听见她名叫希尔德。她对我说,这颗洋葱是给自己吃的,当作午餐。她神情慌张,观察着我的脸色,看我是否看破了她的谎言。
我露出空洞的眼神,以及我的招牌式傻笑,自顾自去洗茶杯,装作全然不知这位护士为了一名重伤病危的苏联战俘,特地在黑市上买来洋葱,要让他在最后日子里尝到渴望已久的味道。这两桩事——买洋葱和友善对待苏联人——无论哪一桩都会让她进监狱。
跟那些胆敢违抗希特勒的德国人一样,这位来自汉堡的护士是罕见的例外。在我们医院里,更常见的是医护人员偷窃外籍病号的食物,带给家人或自己吃。你要理解,这些护士都不是来自进步家庭、受过教育、怀抱神圣使命来看护病弱者的女性。她们大多是来自普鲁士东部的农家女孩,生来注定在田地里、谷场上劳作。倘要逃脱这个命运,她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做护理是其中一条出路。她们在纳粹时代成长,接受纳粹宣传鼓动。她们真心相信,自己作为北欧“雅利安人”,属于高人一等的人种。她们觉得医院里这些苏联人、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波兰人,是为了给她们做苦力而生到这个世上。从这些低等生物那里偷一碗汤不是罪过,反而是极合法的行为。
我估计勃兰登堡大概拘有一万多名外籍战俘。他们都在欧宝汽车制造厂、阿拉多飞机制造厂,还有其他一些工厂做工。我们医院里的战俘,大多是在工业事故中受伤。在打造第三帝国的经济之时,他们被金属锻压机轧烂了手,被燃烧的锻铁炉烧伤,被腐蚀性的化学制品泼溅。他们属于被奴役的民族,自己的国家被征服,束手无助。他们被运走,离别了父母、妻子、儿女;他们渴望家园。我不敢看他们的面孔,害怕看到自己——我自己的恐惧,我自己的孤苦。
在医院里,每一种服务都单独设于专用的楼房。我们护理人员在一幢楼里进餐,一幢楼里洗衣,一幢楼里处理整形外科病员,一幢楼里处理传染性疾病患者。无论何种伤病,外籍工人与德国病人都被严格地加以隔离。我们听说,曾经有一整幢楼配给患斑疹伤寒的外籍病人,据传这种疾病源自被病菌感染的水。在我们这座美丽的历史古城,拥有如同神来之笔的不朽的协奏曲,我们的水源清洁,食物由政府谨慎地审查、定量配给,他们如何感染这种病,绝不是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女孩能想明白的。很多同事认定,这些外国人自己招致这种病,因为他们腌臜的生活习惯。这些护士竟能自欺到如此的地步,绝不承认病菌源自苦力工人被迫接受的不堪的生存条件。
你要知道,我并不是护士,而是护士助理,仅受过做粗活的训练。我给无法进食的病人喂食,掸去床头柜的灰尘,清洗橡胶手套。我们用的不是你现在所见的那种轻薄的白手套,使用一次就丢弃;我们的橡胶手套很厚,很耐用。洗干净后,我得给手套内衬撒粉末,方便再次佩戴。有时,我也调配一剂黑色膏药,抹在绷带上,做成敷布来缓减病人的风湿痛。我的工作大概就这些,再往医疗方面的事情,我就做不了。有一次,我被调去协助输血。他们用虹吸管将一名病人的血抽进一只碗里,再将碗内的血液抽吸到另一病人的血管里。我的任务是搅动碗内的血液,以免凝固。搅着搅着,我便觉得反胃,跑出手术室。他们议论道:“格蕾特这个小傻帽,维也纳来的小姑娘,没受过什么教育,跟清洁工没两样,能指望她有什么出息?让她去给在机器里剁了自己手指的外国人喂食吧。”
我总是祈祷病人不要在我值班时去世。上天肯定听见了,因为战俘们都在我轮班之后才死。
我尽量友善地对待他们,努力跟法国人说法语,缓解他们对家乡的思念。兴许我笑得太灿烂,因为8 月的一个早晨,护士长对我说,我被观察到以过于友好的态度对待外国人,所以要把我调往妇产科。
你瞧,告密者无处不在。正因为如此,那位触犯禁令买洋葱给苏联病人的护士看到我时惶恐得不知所措。你看,我只是个小傻帽,玛格丽特,方便起见,被缩称为格蕾特。我只是奥地利来的、没受过教育的、20岁的护士助理罢了。就连我也可能是盖世太保或党卫队的眼线。
1943年秋初,我被调到妇产科不久后,医院来了一位重要的实业家,一辆救护车专门从柏林将他送来。这位病人患中风,需要安宁、无干扰的疗养。盟军自1 月以来不断轰炸柏林,因此,他的家人和朋友认为,他在勃兰登堡会康复得更快些。因为这里天上不掉炸弹,医护人员无须处理轰炸后的伤残者,从而他能得到更精心的护理。或许是因为我最年轻,最没技术,也没有缺我不行的地方,我就被调离新生儿,派去看护这位病人。
这份工作并不是很愉快。他半身瘫痪,上厕所需要搀扶,需要一小口一小口地喂食,并且总要为他洗澡,帮他在床上翻身,按摩他萎软的肌肉。
我不跟未婚夫维纳详细地描述这位新病人,因为我觉得这会触动他的野心,然后他就会开始钻营,企图利用我与这位重要人物的密切关系谋求一些好处。维纳总是处处想谋取好处。他的经验让他知道,在第三帝国,晋升所依靠的是关系,而不是天赋和才能。朋友在高位,亲戚有权势,自己才有发达的机会。维纳原是油漆匠,他很有想象力,颇具天赋。在纳粹政府之前,除了失业和游荡,他的天赋不曾给他带来任何东西。他曾经在雨季里露宿森林。但后来生活好转,他加入纳粹党,在阿拉多飞机制造厂涂料部门当主管,手下管理很多外籍工人。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国防军的军官、我忠诚的丈夫。但他没有放下野心——仍然没有,维纳是不会轻易放下野心的。他时刻警惕着,观风寻隙,寻觅路子爬上那个位子,在那里他终于收获自以为应得的回报。维纳很浮躁、冲动,总是梦想着成功。我若将这位重要病人的背景悉数告诉他,他就会开始幻想。所以,我跟他仅提起一些事情,但不多。
当这位病人收到武器装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本人送来的鲜花之时,我终于明白护士们如此殷切地将这份工作分派给我的原因。看护职位显要的党员简直是行险。倘若床上便盆摔落,或者水杯泼溅,都可能让你大难临头。为他翻身之时,我可曾翻得太快?为他洗澡之时,我可曾搓得太粗暴?汤水是否太烫、太凉、太咸?可怎么办。还有——天哪——他若再次中风发作,可怎么好?如果他在我看护时死掉呢?
历数种种可能犯下的错,我心内慌恐,悉力将每一件事做得恰好。于是,这位实业家自然认为我工作很在行。一天,我给他洗澡时,他说:“玛格丽特护士,你是一名出色的工人。虽然年纪轻,你必定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经验。”
我用细弱的声音答道:“哦,没有的,先生。我刚从学校出来。我只是做好她们教会我的事。”
“那么,你之前从未看护过中风患者……”
“没有,先生。”
“真让人意外啊。”
他每天恢复一点点,他的声音渐渐地不再那么含糊。他必定对自己的康复有了信心,因为他的情绪变得很好。
有一次,我给他按摩双脚时,他说:“跟我说,玛格丽特护士,勃兰登堡的居民怎么看待这场战争?”
“哦,我不晓得,先生。”
“但你肯定听见人们议论……我对民众的意见很感兴趣。人们怎么看待肉类配给政策?”
“都挺满意的。”
“他们怎么看待来自意大利的新闻?”
我能承认自己知道盟军登陆的消息吗?我敢吗?我敢不承认吗?“我们都相信英国人最终会被我们打败,先生。”
“你男朋友有在东部前线的熟人吗?这些士兵的家信里写了什么?”
“哦,先生,男人们可不写打仗的事,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们担心,还有他们也怕不小心泄露重要军情,敌人有可能截取邮件,那么战友们都会有危险。”
“你可曾听说苏联人是生番,吃人肉?你可曾听说他们吃自己的小孩?”
“听说过,先生。”
“那么,你相信吗?”
我决定冒一下险:“有人相信的,先生。可我琢磨着,要是苏联人吃自己的小孩,那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苏联人了。”
他笑了起来。他的眼神亲切、风趣,举止温和。他甚至让我觉得有点像我的外祖父。外祖父患中风时,我也照顾了他多年……那么多年前的事,那是另一个人生。在这位显要的实业家面前,我渐渐地放松了一些警惕。
“护士,你说,元首如何才能使他的人民幸福?你怎么想?”
“我的未婚夫说,元首爱德国人民如同爱妻子,所以他自己没有妻子,以便能够尽全力让我们幸福。那么,如果您能见到他,先生,兴许您能告诉元首,如果他能给我们派发一些洋葱,我们会非常非常幸福的。”
他听了觉得很有趣,说道:“你是我的良药,玛格丽特。你很直率、善良,有真正的德国女性的灵魂。跟我说,你的未婚夫在前线吗?”
“还没有,先生。他有专长,所以他的工作是为空军部队准备航空器。”
“啊,很好,很好,”他说道,“我的几个儿子也是很不错的年轻人。他们眼下也工作得很出色。”他给我看一张儿子们的合照,都高大英俊,身穿制服。他们已经在纳粹党内身居要职,是重要人物。他很为他们骄傲。
我说道:“你若有亲戚做教皇,自己就能轻易做大主教。”
他遽然收敛夸耀的口吻,细细地打量着我,说道:“我看你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姑娘。我看你实则是很聪明的女人。你是在哪里接受的教育?”
我的胃一阵紧揪,喉咙突然干燥。
“我奶奶常说这句话,”我一面说着,一面为他翻身,开始擦背,“好像是我们家流传的一句老话。”
“我回柏林时,准备带上你,指定你为我的私人护理。我会跟你的上司说的。”
“哦。那可太好了,先生。可是,我和未婚夫打算很快就结婚,所以您看,我不能离开勃兰登堡——两地分居不太好!可是,还是很谢谢您,先生!谢谢您,这是我的荣幸!无上的荣幸!”
到了换班时刻,我向他道晚安,走出病房,只觉浑身寒战,腿脚颤抖。我搨了一身汗,渗透了衣服。我对换班的同事解释说,是因为帮病人运动他健壮的四肢而出汗的。而实际上,这是因为我险些被拆穿了伪装。哪怕仅仅流露丝毫细微的智力——引用一句奥地利普通女孩不可能学到的文学或历史——简直如同男子的割礼,足以将我的真实身份暴露无遗。
我和维纳住在城东阿多拉飞机制造厂工人宿舍区。回家的路上,我一遍遍地告诫自己,往后要更加谨慎,深藏所有流露智力的迹象,保持空洞的目光,紧闭嘴巴。
1943年10月,红十字会护理分队派给我一份殊荣。勃兰登堡市政府组织群众集会,每个工人组织须派遣一名代表。不知为何缘故,资深的护士俱无法出席,所以我被派遣为护理分队代表。我揣测她们不愿参加庆典,是因为听说德军在苏联、北非、意大利溃败(虽然我不晓得她们如何得知这些消息,鉴于德国电台不报道真实的战事,况且,大家都知道偷听苏联电台、英国广播电台、美国之音或者瑞士的贝罗明斯特电台,其罪状几乎等于叛国)。
维纳很为我骄傲。我能想象他如何跟阿多拉的同事吹嘘:“我们家格蕾特是祖国真正的爱国者!她们当然都会选她,毫无疑问。”我的维纳,真有幽默感,对于生活里这些小小的反讽“别具慧眼”。
为了这个重大的节日,我慎重地穿戴起来。我穿上红十字会护士制服,将单调的棕色头发梳成自然朴素的发型,不用发夹、不搽发油,不夹发卷。我不用化妆品,也不佩戴首饰,只戴了一枚细小的金戒指。戒指镶嵌一丁点钻石,是父亲在我16岁生日时送的。我个子矮,不到一米五。那时候,我的身材还好看,但我穿上宽松的白色长袜和围裙掩盖身材。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可不想在公共场合引人注视。让人看着顺眼,是的;干净,是的。但最重要的是,朴素,不招人注意。
结果,这次集会却不同于往年的场面。没有喧闹的鼓声、震耳的行军曲,不见漂亮帅气的年轻人身穿制服、手挥小旗。这次集会有一个指定目的,就是涤荡去年冬天斯大林格勒战役溃败后在德国弥漫的战败情绪。8月里,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被委任为内政部长,受命行使这项职责:“重振德国必胜的信念!”一个又一个演讲者鼓舞我们积极、更积极地工作,支持英勇的前线战士,因为我们若战败,纳粹上台前几乎每个德国人都曾经历的可怕的贫穷就会卷土重来,我们就会失业。我们若吃腻了每晚不变的烩汤——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宣称,在这个进入“全面战争”的国家,以这么一道菜为晚餐,最适合体现国民自我牺牲的精神——那就应该提醒自己,战胜之后,我们会像国王一般享受盛宴,喝真咖啡,吃细白面和整个鸡蛋烘焙的金黄面包。我们被告知,我们须尽一切努力,在工作上跟进生产效率,揭举我们怀疑包藏异心的人,尤其是偷听敌人电台、“极度渲染”德军在北非和意大利战败消息的人。
“天哪!”我想着,“他们开始担心了。”
自视为“世界的主子”的纳粹开始动摇了,开始颤抖了。我觉得头昏眼花,无法喘息。我的脑中不自觉地浮现一支老歌。
嘘,我想道,唱太早了。嘘。
那天夜里,我和维纳将收音机调到英国广播电台。我祈祷德军前线失利的消息意味着战争即将结束,意味着我很快就能放下伪装。
但我不敢跟人说我的希望,连维纳也不说。我藏起喜悦,让声音微弱,让自己不起眼。形如不在。沉默。这些是我当时养成的习惯,浩劫存活者称我们所经历的这段时间为“潜艇”(U-boat)。我是纳粹死亡机器之下的犹太逃犯,匿伏在第三帝国的心脏。
多年后,我与弗雷德·比尔结婚,安全地在英国生活,我卸脱这些习惯。现在弗雷德去世了,我也老了,不能控制记忆的冲击,又重拾起这些习惯。我坐在这里,像现在这样,和你一起坐在这家我最喜欢的咖啡馆,对着内坦亚城的广场,靠着大海,在以色列土地上,然后,熟人过来寒暄,说道:“我说,比尔女士,战时在德国与纳粹党员一起生活,假装自己是雅利安人,隐藏真实身份,随时怕被揭穿,那是怎样的感觉?”我的嗓音就变得细弱,惘惘然,无所适从。我答道:“哦,我不晓得呢。我想我不记得了。”我的目光开始游离,失去了焦点。我的声音恍惚,迟疑,微弱。这是来自勃兰登堡那些日子的声音。那时,我29岁,是就读于法律系的犹太学生,我的名字列在盖世太保的通缉名单,我伪装为愚昧无知的21岁护士助理。
当你听见这个微弱的声音,从那个时代传来,黯淡、迟疑,你一定要体谅我。你要叫醒我:“伊迪丝,大声说!说你的故事。”
这段故事搁置了半个多世纪。
我想,是时候讲出来了。
摘选自《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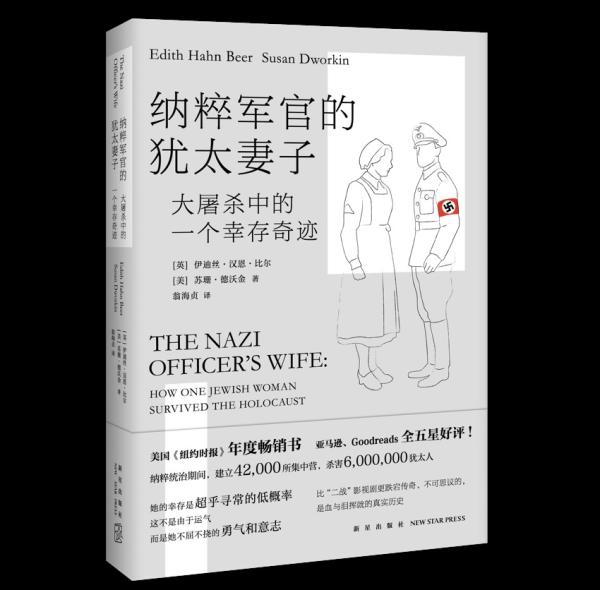
《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大屠杀中的一个幸存奇迹》, [英] 伊迪丝·汉恩·比尔 / [美] 苏珊·德沃金 著,翁海贞 译,新星出版社2020年5月版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