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像《长安十二时辰》这样的小说,还有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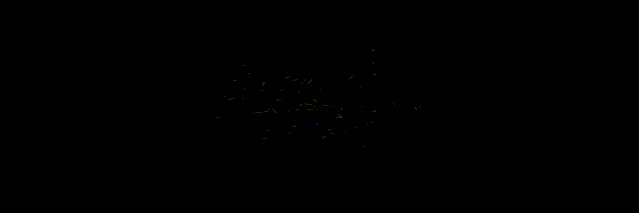

这些新历史小说,比传统历史小说更好玩。/《长安十二时辰》
在今天的这四本与历史有关的小说里,作者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在文字和过去的时光之间,建立起某种崭新的联系。
中国人对历史的执念,本质上是对时间的感怀,以至于在“怀古”这个绵延千年的巨大命题下,激越之声总掺杂着丝丝缕缕的伤感。
凭吊古迹,栏杆拍遍,滚滚长江东逝水,这是中国式的浪漫,也是中国式的悲情。当历史的沉郁和小说家的幽思结合在一起,便造就了历史小说的蔚然大观。
宏大叙事是这一类文本的传统,比如《虬髯客传》里风尘三侠的故事再传奇,红拂女还是要拉着李靖顺应大唐兴起的历史大势,从江湖奔向庙堂。至于传播度更广的《三国演义》《说岳全传》之类小说,更是如此。

红拂女于乱世之中识得李靖和虬髯客两位豪杰,三人结为莫逆之交,一同在风尘乱世中施展才华,被人们敬传为“风尘三侠”。图/《风尘三侠之红拂女》
近代以来,历史小说的手法和主题一再变化,但鲁迅所说的“七分写实,三分写虚”依然是主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潮流仍作为小说的主体存在。
李敖没去过法源寺,但《北京法源寺》借寄住寺内的谭嗣同,回顾了维新变法的一段历史;
高阳精通清史,一生流落民间,人称野翰林,他所写的《胡雪岩》也是沿着这位巨商的轨迹,展开一幅清末社会的图景;
姚雪垠写完一本厚厚的《李自成》,自己已经成了明史专家;
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在中国崛起的年代恰逢其时,掀起了之后绵延二十年的“帝王热”。
时至今日,网络架空小说在前,大热的《长安十二时辰》在后,历史小说似乎已经悄悄发生改变。视角下沉,史实逐渐从叙事中抽离,成为药引子、背景板,历史成为舞台而非主角。
在不必沉重的时代,历史小说身上的道德重担已经被卸去了很多,它可以尝试更多文体,也可以很类型化,可以很轻盈,也可以很硬核。

“如果你活着,早晚都会死;如果你死了,你就永远活着。” 图/《让子弹飞》
比如在电影《让子弹飞》里,姜文饰演的张牧之自我介绍,曾追随松坡将军(蔡锷)。
熟悉历史的人听到蔡锷,梁启超、护国战争、小凤仙等名字自然会闪过脑海,对眼前这个张麻子的理解也就更深一层,而对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而言,观影体验也并不会受影响。历史在这里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彩蛋”。
在今天的这四本与历史有关的小说里,作者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在文字和过去的时光之间,建立起某种崭新的联系。

刀背藏身
徐皓峰武侠短篇集

作者:徐皓峰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的边界,一向很模糊。
在传统的历史演义、话本小说里,江湖草莽是常见的角色,直到九十年代二月河的笔下,仍有武林高手出没。
另一方面,武侠小说也特别乐于化用历史,最广为人知的当属金庸,喜欢将虚构的人物置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中,浑然天成,虚虚实实之间,小说的魅力翻倍,尤其成为历史爱好者的盛宴。
徐皓峰以一己之力,为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开辟出一个新的境界,而历史,则是他手中一件格外趁手的兵刃。
在这篇不长的《刀背藏身》里,历史只是一个引子、一个配角,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道滋味。
故事说来很简单:孔老爷子武艺精纯,擅长刀法,退隐乡下之后,一个练刀的青年上门挑战,孔老爷子不得已露了一招,吓退青年。
青年后来奔赴抗日战场,再没回来,他留下的女人,孔老爷子的孙子和收养的孙女,以及一个冒名顶替青年身份和刀法的男人,四人之间产生了一段纠葛。
但这些纠葛没有超出乡野杂谈的范畴,与历史和武术的关系也都很遥远了。

传奇刀术生死较量的背后,是武林人士的侠义风骨,以及大时代里的爱恨纠缠。图/《刀背藏身》
徐皓峰的文字和叙事向来比较寡淡,但在平静的水面下,这篇小说还有一条影影绰绰的主线,就是真实发生在1933年的喜峰口抗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进犯华北的野心昭然若揭,在喜峰口与中国的二十九军爆发过一场战役。二十九军来自西北,装备不佳,但性格勇猛刚烈,很多士兵身背一口大刀,练习民间武术家专门为这支军队编写的“破锋八刀”。
在喜峰口,抗日将领赵登禹率领士兵冲锋,挥刀肉搏,这柄大刀成为抗战初期民族精神的象征。1937年,作曲家麦新根据其事迹,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大刀进行曲》。

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而徐皓峰表示,《刀背藏身》是一部可以“见众生”的作品。图/《刀背藏身》
小说中,这一事件成为贯穿全篇的背景,推动情节的关键。孔老爷子刀法精湛,曾在军中传艺,人们都说二十九军的刀法是他所传,青年上门挑战的理由恰恰也是“二十九军你教过,我也教过,许多人都教过,怎么砍日本的刀法成了你的”。
后来,青年战死沙场,战友顶替了他的刀法,才赢得了武术家的名声,而为了在之后起起伏伏的时代浪潮中求一个安稳的生活,他又需要抗日英雄的名声,不得不真的从孔老爷子孙子那里学来破锋八刀,苦苦练习。
历史上的大刀队究竟有没有那么神,难有定论。当时,桂系将领黄绍竑曾问《申报》老板史量才:“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么!”史量才回答:“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

电影《刀背藏身》首次以女性视角切入, 许晴饰演的阚智慧串联起整个人物故事脉络。图/《刀背藏身》
但小说不全以史实为根基,自然也不必像传统的历史小说一样为史实负责。
徐皓峰笔下的破锋八刀,有了历史真实之外更多重的象征意味。这种真实与虚构相交融,以真实驱动虚构的手法,在他其他的作品如《道士下山》《民国刺客柳白猿》中也多有运用。
“世上本无破锋八刀,老百姓传说的。去过二十九军的武师多,都传过刀法,何止八刀?”大历史沉入民间,成为家族掌故和人物传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书写历史,历史亦是小说。

六里庄遗事

作者:东东枪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六里庄,唐代长安以东六里许一个普通的村子。遗事的遗,是遗忘的遗,说明书里没多大点事,注定被遗忘。
严格来说《六里庄遗事》算不上一段完整的历史,《太平广记》《聊斋志异》式的笔记小说体裁,让它读起来更像是人断断续续的记忆。
甚至六里庄里的人也不像历史书中会出现的人物。他们各自带着奇怪的名字出现在纸张上,沈三变、冯有道、杨温柔、周如麻、李有鬼……他们整天算命、耍猴、做鬼、逃难、写诗、做梦……做的尽是些鸡毛蒜皮、插科打诨的事儿。
书的开场白中,作者东东枪自己也写道:“这是一本芜杂的书,说的是一些芜杂的人。他们活在一个芜杂的时代,过着芜杂的生活,于是活出了一些芜杂的故事。”

除了长安、洛阳、扬州等大城市,唐代的其他城市、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鲜为人知,进入不了历史。图/《明皇幸蜀图》
六里庄没有江湖,也远离庙堂,生活在这里的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平凡,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混入哪本列传,名垂青史。
这便是作者的历史观,“被记住是个奢望,被忘记才是必然。这不是少数人的不幸,而是大多数人的标准待遇。”
他通过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近600段零散记忆,拼凑起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六里庄宇宙。
而生活在这个宇宙中的小人物,倒也落得了一个自由。
他们认定了自己作为宏观历史局外人的身份,便不用像主人公一样为家国情怀、江湖义气而苦恼。
于是,六里庄的人便都能使出全身的精力来,对真正在意的小事执着,对真正在意的人好。在不大的一片天地中,人与鬼与妖和谐共生,大家都不甘寂寞着,都认真地活着。

在任何一个时代,家国之外的生活小事才是我们的日常。图/《我的唐朝兄弟》
他们活得无聊又有趣。
像高老太太。她死后仍坚持砍树,光是因为自己乐意,别人管不着。
像那棵被她砍的树。树也有灵,因为闲着也是闲着,就装出一副要被砍倒的样子,逗老太太高兴。
像高老太爷老在自己家门外的路上撒几枚铜钱,没别的,就是为了高老太太捡着钱高兴。
像有妖仙在河里整出好几十根大冰柱子,不为仇也不为冤,纯粹就是好玩儿。
他们偶尔也会遇到自己无论如何都要耍帅的场合。
有一小伙子命苦,妻子病故,家中财产为了治病安葬就剩下几十文钱。开算命摊儿的袁大师,收下这些钱,说能为他指条明路,随后就拿着钱买酒去了。
可他喝完酒,又和开酒馆的罗老二死皮赖脸地借了十贯钱,在约好“指明路”的时间地点,悄悄赠与小伙子。

在这座唐代的小村庄里,藏着多少现代人的心事。图/《我的唐朝兄弟》
但更多时候,他们都在自己的命运中挣扎着。
像冯有道呈现的就是一副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形象。他会在家中对着墙角叹气,叹自古圣贤不数出,伏羲、神农、周公、孔子,算上自己才5个。
他写七言绝句:生活对我没有爱,我跟生活耍无赖。比如他还给自己拟了一个碑文,“我与世界不欢而散”,后来又反悔了。
杨温柔可能是六里庄最不凡的人。传说他活了特久,经历过许多朝代,但也没干出什么改变历史的大事。
他不过是收藏了点竹林七贤的酒壶,孔子和颜回躺过的凉席,孙膑坐过的轮椅……如此轻盈地介入历史,恰到好处地“意淫”的,让人不禁想起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
在六里庄发生的事,也可以是门头沟、苏州河、东山口、春熙路发生的事。或许当我们每个人来到生命尽头,脑海中回闪过的不过是一块美味的糕点,是谁欠你的钱没还,是突然想起来怎么回怼隔壁床老张头的话,是你曾经“撞鬼”的经历……
是啊,六里庄就是这样光怪陆离,不讲逻辑,但这些可能已经是你人生中最值得提及的事了。
只是还有一个问题,六里庄的人多半太贫太逗,让人疑惑长安以东六里地,怎么大家都长着一缕天津人的灵魂。

长安十二时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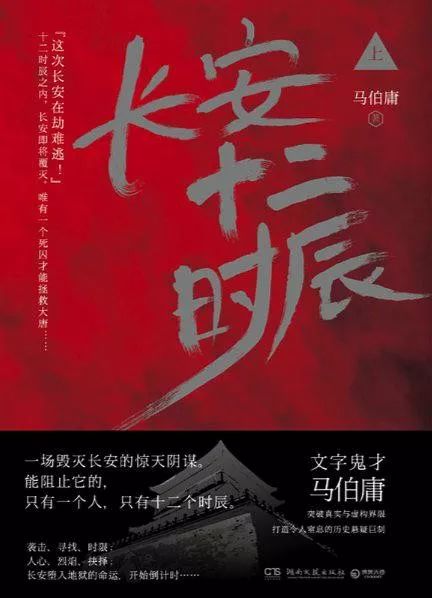
作者:马伯庸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翻开中国古代厚厚的正史,常常被历史的诡谲吓退,要么粉饰过度,要么三缄其口,要么指鹿为马,要么春秋笔法。
于是乎,走出庙堂,往街边的说书摊子凑一凑,稗官野史、戏说杂谈总有市场。
利用历史的蛛丝马迹,构建出一个古色古香的空间,再把现代的精神内核填充进去,这是马伯庸所期待的“历史可能性小说”该有的面目——它既有别于传统的历史演义,也和网络文学中的架空门类不太一样。
比如那本著名的《风起陇西》,把谍战的故事装进三国,我们很难将其简单归入现有的某种文学类型。

读者将《风起陇西》《风雨<洛神赋>》《三国机密》等马伯庸的代表作列为“考据型悬疑文学”,也有人认为这是“历史可能性小说”。图/《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
四大名著中最爱《三国演义》的马伯庸,捡拾起其中无人问津的碎片,将原本的隐线重新编织修缮,用雄厚的知识储备、沉稳冷静的笔触、苍凉肃杀的氛围,开创了“考据型历史悬疑文学”的风格路线——我们姑且先将它划入这样一种类型。
相似的手法,同样可以在《长安十二时辰》中看到:历史上张小敬确有其人,《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记载,马嵬坡之变中,太子李亨、陈玄礼密谋发动兵变,正是张小敬开弓将奸相杨国忠射下了马。
马伯庸把这个不起眼的人物翻拣出来,抖去尘土,重新上色,为己所用。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作者用历史细节搭建了一方精致的舞台,天马行空的故事在其中上演。

张小敬的原型出自《安禄山事迹》,是大唐第一批募兵,曾经当过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图/《长安十二时辰》
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同,马伯庸的还原体现在背景上。看塔的小沙弥、专做毕罗饼的回鹘老头、驯骆驼的阿罗约、崇仁坊的舞娘李十二、卖纸船的瞎眼阿婆……种种配角、器物以工笔画般的细致,展现盛唐风情。
正史中的佐料,也被马伯庸拿来大做文章。剧中引发极大讨论的“平康坊一霸”黑人葛老,正是当时被贩至长安的昆仑奴缩影,只是其实际体征应更接近东南亚尼格利陀人,而非极为少见的非洲人。
当时随处可见的胡商,似葛老一般痴迷于珠宝,亦善于经营香料、马匹、酒店、高利贷生意。有胡商搅活市场,“国际大都市”长安自然更具魅力。
胡人贵族来此开展外交,享受家乡难得一见的繁华盛境,乃至乐不思蜀。胡人平民在此谋生,有为奴为婢,有致仕从政,亦有奔走经商。

这部美版“反恐24小时”,细节精致得就像一个华丽而庞大的梦境。图/《长安十二时辰》
到了故事主角和主线身上,作者就不囿于历史了,80后的身份,或许是给马伯庸带来了更现代的视角,在这个故事背后,读者能隐隐约约嗅出美剧的味道。
这种现代思维与史料的糅合,才是《长安十二时辰》攻下图书市场、影视改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始终在“跑酷”、一人之力拯救世界的男主角,先相杀后相爱、关键时刻打得一手好辅助的女主角,将主人公从囹圄中解救出来的伯乐,越挖越渗人的幕后黑手……和高度还原的长安风情相比,似乎就不那么历史了。
一只古朴的瓶子,盛满来自当下的味道,马伯庸的新历史小说尝试,目前来看算是成功了。

城邦暴力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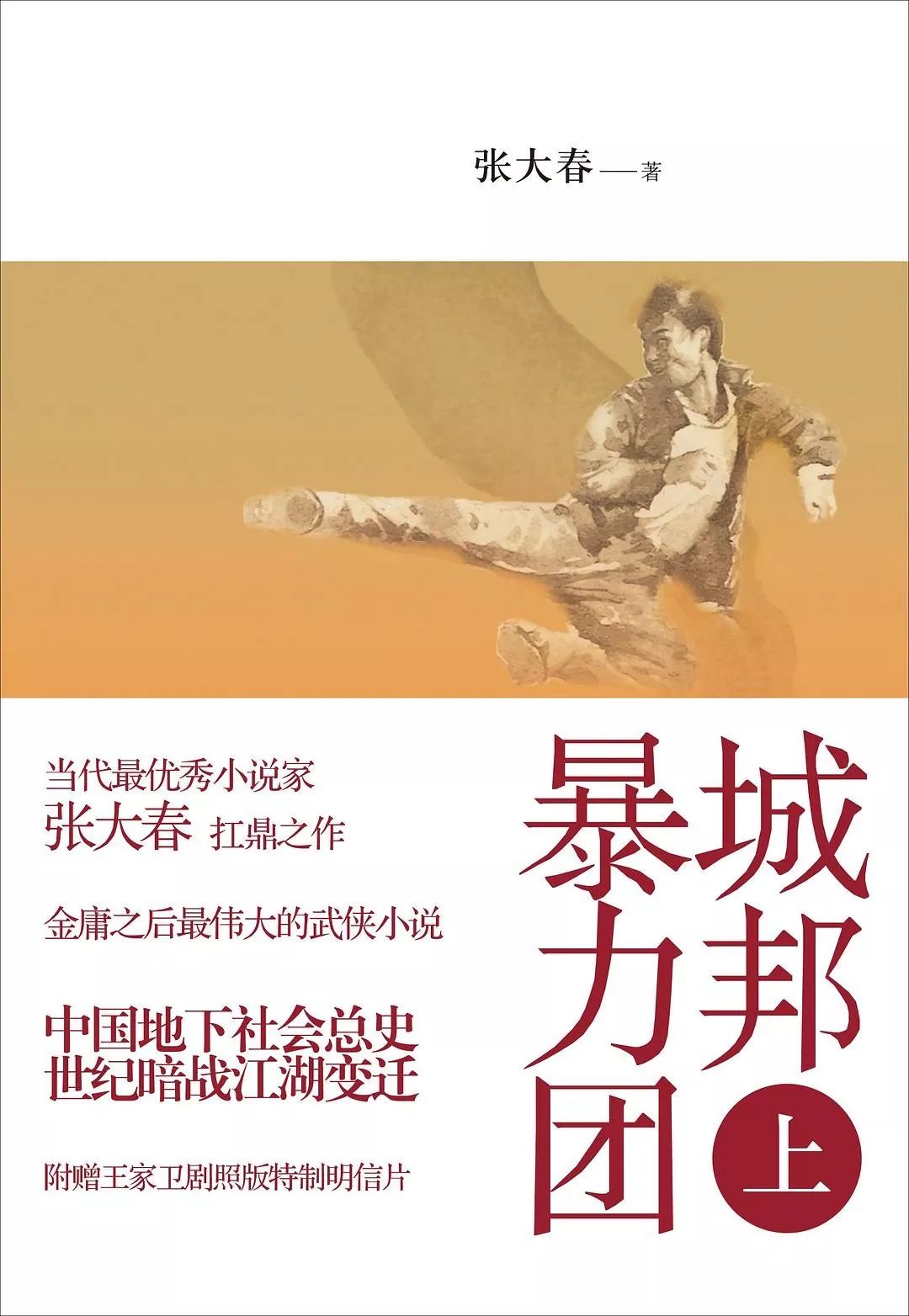
作者:张大春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唯浅妄之人方能以此书为武侠之作。”
在《城邦暴力团》的序言里,张大春假借历史小说家高阳之口,如此评论一本叫做《七海惊雷》的书。这句话用来形容《城邦暴力团》,似乎也成立。
首先,这本书究竟是武侠小说还是历史小说?作者说,这是“一个关于隐遁、逃亡、藏匿、流离的故事”。
要说是武侠小说,它跟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或者任何一本书名类似《七海惊雷》的武侠著作都不一样,里面的武打场面读起来更像一个摇头晃脑的说书人绘声绘色地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要说是历史小说,它和那些硬桥硬马地写帝王将相、历史事件演义的小说又绝不一样,它并非不涉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但它里面隐藏了许多掌故、野史,钩沉往事,草灰蛇线,一般读者可能读不出来。

除了作家,张大春还有个职业就是说书人,他曾在电台开设说书节目,讲《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历史小说。
就连这本书的缘起,张大春也说得亦真亦假,高阳在现实世界确实是他的老师,但《七海惊雷》这本书究竟有没有呢?
其他六本启发了《城邦暴力团》创作的书——《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奇门遁甲术概要》《食德与画品》《神医妙画方凤梧》——是真的吗?
张大春的回复也跟他的小说一样狡猾:
一老太金婚之夜被丈夫闲言问起:“这一辈子有没有过别的人哪?”老太迟疑了半天,羞道:“在你之前有人写过一封信给我,我没理他的茬儿。”丈夫听了,一巴掌就招呼上来:“你居然还记得!”老太夺门而出,放声大哭,儿孙来问缘故,老太说:“不能说呀!不能说的就是不能说呀。”
可以肯定的是,张大春让主角“孙小六”和叙述人“张大春”揭露了清末庙堂与江湖会党的纷争、民国武林人士被卷入历史风云的挣扎,野心恐怕不仅仅是写一本 “金庸之后最令人期待的新世代武侠作品”(倪匡语)。

《一代宗师》里的宫保森。
概而言之,《城邦暴力团》讲的是江湖如何消失、为何消失的故事,在其中主导江湖秩序的并不是帮会,更不是哪一路大侠。
作为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顾问,张大春曾经撰文解读赵本山饰演的丁连山在厨房说的那番话。
当时宫保森率领八卦门南下广东推动“中华武术会”,倡导南北武林放下门户之间,共同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在佛山金楼宴请武林同道时,宫保森发现退隐江湖的大师兄丁连山就躲在后厨当厨师。
丁连山送给宫保森一句话:“你我有如衣服,尔为一表;我为一里,尽管彼此相依,却也两不相侔。然南北议和之事,切记不宜横柴入灶、操之过急,你也要学会‘反穿皮袄’!”宫保森若有所悟,遂不再强行推动此事。

丁连山。图/《一代宗师》
张大春写道:“这话说了没几个月,刚从欧洲考察返国的胡汉民神秘地暴死在一枰棋局之上,地点就在广州。蒋介石随即要收编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军政大权,以反戈消灭桂系的李宗仁,两广事变接着就发生了。”
《城邦暴力团》的故事发生在“竹林市”,张大春解释说,这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它可能是佛山这样的武林重镇,或者街头金碧辉煌的大酒楼,也可能只是偏僻山里的一座小神庙、一家小餐馆或者一间马桶堵塞的公共厕所。
但是,在张大春构建的历史世界里,你是没有办法“主动”前往竹林市的,因为它可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出现,就像“没有任何人能够在凶杀案发生前准确指出哪个地方即将发生凶杀案”,你只能在无意间误闯,或被某种力量卷进那个世界。
这不就是“命运”或“命数”吗?更准确地讲,竹林市是“历史”的一个隐喻,唯有这样才符合张大春对它的定义——竹林市之所以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是因为它“过于真实”。
✎新周刊硬核读书会出品
本期坐馆:苏炜,孙名梓,詹智彦,朱人奉
欢迎分享到朋友圈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