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虽然“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概念
原创 刚刚Plus 双相躁郁世界

今天在公交上听着贝多芬的《热情第二乐章》,想起来上次因想要自杀而住院已经是八个月以前的事情了。这几个月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待着,内心比以往几年都感到平静。
如果不是每天都要按时吃几颗药片,我都不会记起自己是个双相病人。即使我很想表现得情绪很平静,对生活很坦然,但是内心依然在痛苦挣扎。
作者|刚刚Plus
编辑、排版|Emile
我将影响双相的因素分为三类。生理方面,我有家族遗传史,不必多言,这是我硬件的问题。心理方面,从记事起,我的想法和行为就和周围的同辈们显得不一样,自卑、焦虑、狂躁、抑郁……种种情绪我都一遍一遍经历过。
也幸亏我运气不差,环境不算太坏,遇到很多很好的长辈和朋友,同时自己一直在做心理建设,慢慢改变自己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到最后发现,最难解决和影响最深的,还是纠缠不清、撕扯不断的社会关系。

现实情况是,我的社交往往是很失败的。有时候过于热情,被对方误解;有时候过于情绪化,让双方煎熬;有时候过于迟钝,因而失去最好的机会。还好,总体上还是有几个朋友愿意被我打扰,不会让我觉得做他们的朋友是在拖累他们。
但是,有些失败的社交经历让我十分痛苦。我依旧记得高中的一个女生,她笑起来两颗不对齐的虎牙会很明显,遮虎牙的手很长,常年泛着粉红色,走路老是踮着脚尖。我看着她从短发变成长发,后来又经常梦见她。这成为我的执念,让我很难再去建立亲密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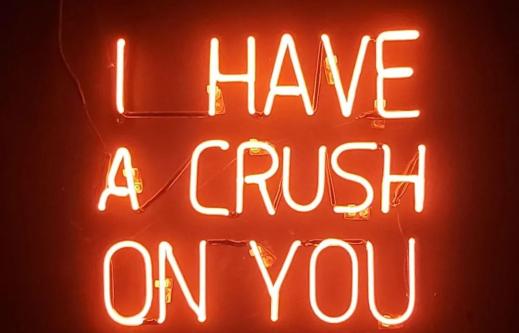
原来我从出生到长大,没有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没有和父母一起建立有效稳定的互动模式,一直生长在危险的、不稳定的环境当中。我没有被爱过,怎么可能学会去爱别人、去感受爱?我的童年记忆老是笼罩着阴影,父亲常年在外,母亲整日愁容满面,不是埋怨自己命运不幸,就是埋怨自己为我付出不易。
我家第二个孩子刚出生就在医院待着,四年之后才不用去医院。这段时间,我在很多地方都生活过,大夏天掉进过河里,吃着发霉的饼(一种北方的干粮),喝着生水,听着异地方言的玩笑。我的内向、自卑、敏感,大概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并深深影响了我,直到现在。

尽管如此,我对我身处的社会关系还是有很矛盾的情感。一方面,我理解并同情我父母的遭遇,他们早年陷入贫穷,连续失去两个女儿,才有了我这个儿子,青壮年都在还债务;另一方面,我又很仇恨父母给我的遭遇,从小到大他们对我的忽视、错误的教育、还有严重的家庭暴力。
因此,我对父母和整个家庭的态度也是不稳定的。有时候我很好,尽可能去做一个负责任的家庭成员;有时候我很坏,尽量拉开和家庭的距离,无论是空间上还是心理上。我至今不愿意长时间在家里待着,这次疫情发展一趋缓,我就去外面租了房子自己住。

我开始关注自己内心的需要,从外界获取我想要的,搭建丰富充盈的心理世界。虽然这并不代表我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心理上的危机,但是我接纳这种危机重现的可能性,并且把它当作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这样子,我反而不再会过分焦虑和难受了。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