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夫马进:“民告官”案件的背后——民国乡镇中的近代风波
2019年8月27日,杭州召开了一次龙泉司法档案研读会。此次研读会由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组织。与大多数研读会不同的是,此次会上几乎只选择了记录有一件诉讼案件的档案,由20人左右的研究者花费一整天时间进行讨论。本文作者夫马进,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也是此次研读会的受邀人和发言人。会后,夫马教授撰文介绍了《龙泉司法档案》的相关情况,并围绕这一具体案例展开讨论。文章原题《〈龙泉司法档案〉与龙泉司法档案研读会——围绕民国初年教育界与商业界弹劾警察案件的讨论》,发表于日本《东方学》第139辑,2020年1月。经授权,中译文首发于澎湃新闻,限于篇幅,对原文略有改动,并分作两篇,此为下篇。

在这次研读会的阅读文本中,我选择的第一个案件是“民国二年 李兴唐等控卓识等纵警仇学案”,第二个案件是“民国三年 曾林裕控程作祺等诈欺取财案”。这两个案件的共通点在于,处理的都是刚刚建立的近代警察的腐败问题,而且在两案中,八都派出所所长薛瑞聪都被人告发。一方面,如果一大问题是关心地方(特别是镇层面)的近代化是如何进行的话,那么第一个案件中原告的父亲,即八都镇的商人、养正学校的创设人、其后的浙江省参议员李镜蓉便很重要。即使在《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二辑》所收录的有限案件中,李镜蓉相关的诉讼便至少还有“民国三年 李承纶控王朝信等欠债不偿案”(1914年,第六册,235页-395页)与“民国九年 李镜蓉与刘开成基地纠纷案”(1920年,第二十四册,367页-456页)两案。前者的原告李承纶便是李镜蓉本人。而且至少在前者中,诉讼的草稿也通常被记作“自叙”,这意味着诉状的草稿是由本人写成,即大概可以认为是李镜蓉自己写作了草稿。而且,诉状的样式也不是讼师秘本中所载的“古风”,而是新式式样,推测是受到了日本诉状样式的强烈影响。此处所浮现出来的李镜蓉形象,正应该称为“近代的健讼绅士”。不过考虑到如果再加上这两个案件的话,数量会变得过于庞大,因此在研读会上选择的只有前两个案件。
新旧时代转型下的弹劾警察案
第一个案件是“民国二年 李兴唐等控卓识等纵警仇学案”。此案可谓意味深长,因为在其中可以体会到在浙江省的偏远地区,新时代的氛围是怎样一种感觉。在原告方面提出的诉状中,大量使用“秩序”、“治安”、“野蛮手段”、“文明办法”、“人民无幸福之增进”、“平等”、“法律之公平”等词汇。而文章结构本身也是新的,与过去的诉状不同。
事件的起因,是在于刚刚创设的近代学校和近代警察之间的对立。原告方的主笔人李兴唐,是龙泉县八都镇新设立的养正学校(高等小学校)的校长。根据原告栏内的信息,李兴唐当时25岁,职业是“儒”。据记载,养正学校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李兴唐的父亲李镜蓉在八都李氏宗祠内设置的学校,学生近百人,包括8-10人的寄宿生。所有的学生都免学费。(李盛唐、李振民、李爱鸾“先父李镜蓉生平”,《龙泉文史资料》第七辑,1988年,147页)。李镜蓉生于咸丰九年(1859),清朝时为贡生,民国二年任西远区自治会议员、商会董事,民国十二年任浙江省参议员。而另一边的被告卓识,则是龙泉县警务所(警察署)管辖下西远区八都派出所(民国元年创设)的巡士。
事件发生在民国二年的六月五日。卓识在经过校门前时,正遇上学生休息,便对学生出言讽刺,还殴打了当时在场的学生李起唐(李唐,是李镜蓉的第三子,李兴唐之弟)。随后,李镜蓉带着李起唐前往县城警察署验伤,知事也认定其确有负伤。第一份诉状是在6月8日,由校长李兴唐与三名教员联名提出。我们在研读会结束之后也探访了龙泉市八都的李氏宗祠,其位置是沿街边小路进去后一处较深的处所。根据当地人的介绍,事件发生的养正学校,应该是位于面向八都的街路,即面向现在的“长安街”的位置。这一点应当无误。之后,学生与警察、巡士之间,不断有相互间的仇视和殴打,在此都省略不叙。新式学校的学生蔑视警察、巡士,而警察、巡士也反过来仇视学生,这一事态不仅在八都这种乡村,而且在县城里也同样存在。
这一案件的重要性在于,这一诉讼乃是所谓的“行政诉讼”。更进一步说,从“民告官”的历史来看,本案也是意味深长。确实,在第一份诉状中,李兴唐等起诉的被告是“巡士”卓识,但在诉状中一直被质疑的则是警察机构本身,以及八都派出所的“所员”薛瑞聪。虽然如后所述,“所员”也是“官”,但学校校长李兴唐的批评却越过了他而直接指向龙泉县警务所所长即警察署长,甚至指向了受理诉状并写作批示的龙泉县审检所长即龙泉县司法长官。所谓审检所,即是审判厅(裁判所、法院)与检察厅一体的机构,其长官由龙泉县知事兼任。因此李兴唐批判的便是龙泉县知事。在李兴唐的第四份诉状中批评到,警察腐败,而应该监督警察的知事反而做出拥护警察的批示。对于这一批评,知县再写下的批示则是努力为自己辩护。若将这一点与清代进行对比,就显得非常奇妙。而且在该批示中,知县将李兴唐称为“贵堂”(您们学堂),此点也很奇妙。
在第一份诉状中,批评巡士卓识的问题是“知法犯法”,而第二份诉状的题目就清楚地写成“警政腐败”。在原告的诉状中,“法律”一词不断重复到令人生厌的程度,而在后续档案的各处,巡士都被替代为“政警(行政警察)”、“警察”的称呼。卓识是在八都当地雇佣的,据李兴唐所言:“该所(八都派出所)巡士,大半出自本地无业游民”,因此大概可以认为,与司法警察同清代的差役相差不大这一点类似,巡士即行政警察也与过去的差役大同小异。在清代及以前,将人民在上级官厅对官员进行起诉、告发的行为,称为“民告官”。由于差役不是官,起诉差役不会产生问题,所以在《巴县档案》中也可以见到很多起诉差役不正行为的案件。但是,李兴唐等所弹劾的乃是警察机构本身的腐败。警察本来是“维秩序,保治安”,但问题却在于“巡警为保护人民生命身体而设,今反出而凶殴”,“警察似狼似虎”的实态。
在诉状中,作为被告遭到起诉的“官”,具体是指八都派出所所员,正式说来是警务分所所员(西远区第三派出所所员)薛瑞聪。但是,甚至连一县警察机构的长官(龙泉县警务所所长)夏涛,以及龙泉县知事朱光奎,都是诉状中批判的对象。在李兴唐的起诉巡士的第一份和第二份诉状之中,已经潜在地将薛瑞聪称作“所员”进行了弹劾。因为他本来有监督巡士的职责,却容许了巡士们的不法行为,没有对巡士进行谴责。在诉状中可以见到“巡士恃警官为头目,而警官则恃巡士为手足”这种语句。即是说,巡士与警官是不同的,薛瑞聪说到底还是“官”。第二个案件是“民国三年 曾林裕控程作祺等诈欺取财案”,但我认为案件题目叫做“薛瑞聪朋比营私案”似乎更加合适,因为此案处理的是卷入逮捕赌博犯事件的薛瑞聪收取贿赂的问题。据此案记载,他是温州府瑞安县人,并非当地雇佣,而是经浙江省民政长官委任来担任西乡的警官。所以,他与曾经的差役完全不同。薛瑞聪被李兴唐作为“刑事诉状”的被告起诉,同时在龙泉县“商民”等人向浙江省内务司递交的呈文,以及龙泉商务分所送往内务司的电文中,对他也有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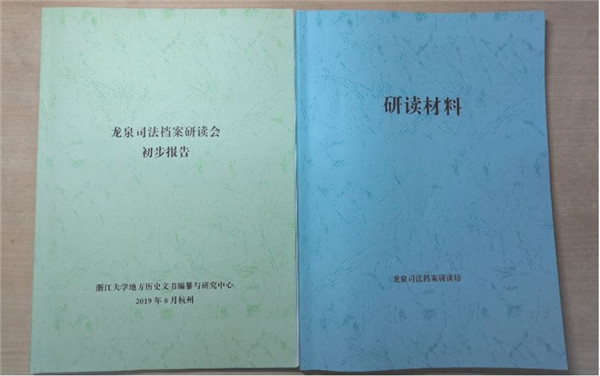
而在由龙泉县教育会送往浙江省内务司的电文,以及李兴唐送往内务司的电文中,则对龙泉警务所所长夏涛进行了批判。薛瑞聪的答辩,没有采取提出诉状的形式。由于上级官厅下发了指令,命令汇报实情究竟如何,所以他采取的是答复指令的形式。7月14日进行了审讯。在点名单中,虽然可见原告方有据称被殴打的李起唐,被告方则有卓识等相关者的名字,但是都没有见到“原告”李兴唐与“被告”薛瑞聪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这正体现了民国二年这一时期的行政诉讼、即民告官的实态。
从档案中可以看到,李兴唐对于起诉官员、弹劾警察行政之事,似乎是乐在其中。而且,为了嘲讽官员和警察,诉状中也到处点缀着中国历史故事,此点与清代的诉状相同。不过可能是由于写作者的学力低下,常常看到误引与本事案不相符合的故事。
这个案件中的另一个重点在于,镇层面上的有权势者李镜蓉,一方面是捐资修建新式学校和义仓、热心公益事业的“慈善家”,是受到乡人信赖的人物(前揭《先父李镜蓉生平》),但另一方面,其是否也有可能是“土豪劣绅”呢?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档案之中有一份浙江省行政公署训令,其中记载了警官薛瑞聪向龙泉县警务所所长夏涛提出的答辩书,以及夏涛基于此而做的判断。其中的记载与原告方面展示的李镜蓉形象完全相反。根据薛瑞聪的记载,“查李镜蓉由市侩起家,虽为西乡殷富,实素行卑污,好与地痞赌棍辈结交。现在八都开有吉春字号南货店,宰卖猪肉。警察成立后,禁烟禁赌,商业减色,并屡次催纳警捐,抗延不缴。”龙泉县警务所所长夏涛的看法也与此大致相同,称“今李镜蓉挟警察禁烟禁赌,多方不利于己之嫌,抗捐不已。犹复蠱动学生潜谋殴警察,破坏警政。所长恐文明之世界,出此凶殴警察之学生,则下流社会,群起效尤,其害不知伊于胡底。”,主张“迅将教唆犯李镜蓉、凶犯黄云、李起唐一并提案讯办,以保警政而整学务。”而在同一份文书中,还可见到李兴唐指责薛瑞聪与警察行政,主张“伏思共和政体,人民一律平等,职官犯罪,理应停职归案审判”。在此,大概可以看到两股势力之间的对立,即将李镜蓉看做是“土豪劣绅”,并努力依靠强权来推进近代化的警察势力,与同样主张近代化,赞成“守法律,人民平等”的教育界和商业界势力的对立。
第二个案件是《民国三年曾林裕控程作祺等诈欺取财案》。如前所述,在第一个案件中被起诉的薛瑞聪,在此案中则被指控有收受贿赂的嫌疑。不过在研读会上,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说明问题所在,我只是提出如下几点,如近代警察与几乎没有工资的清代差役相比有何不同,警察的工资从何处来等,以及从该案中可以看到,警察在后来如何变得健全,以及中国在该点上似乎极为困难等。此外,我还指出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也有类似于差役的“目明”存在,以及民国初年的警察似乎是依靠征收“警捐”这种地方捐(税)来支付其工资。不过根据档案,这种警捐似乎是由警察自己来征收,例如在第一案中可见,如果警察与地方有力者或者商人之间互相仇视的话,警捐就无法顺利征收,那么警察工资大概也就无法顺利支付。由此可见,中国警察的近代化过程在支付工资这一点上似乎就极为困难。原因成为结果,结果又生出原因,导致警察的腐败似乎长期地维持了下去。
最后,我将巴县档案中残留的清代同治年间的诉讼案件数与民国初年的诉讼受理案件数进行了比较,发现后者大概是前者的2.5倍之多。对其原因,我介绍了我的假说,即由于同治年间的巴县档案没有保存“不准”和“未准”的案件,所以案件数较少。我提出的问题则是,从民国龙泉档案来看,这一假说能否成立呢?
言人人殊:研读会之所得
以上是我对于从这两个案件中能够读到什么,以及提出什么问题的论述。在此之后,八位参加者也简单地叙述了自己从中读到了什么,以及提出了什么问题。实际上,他们的发言稿事先已经通过电子邮件寄来,我也已经阅读过。在阅读这些报告时,我感到有趣的恰恰是如下的现象,即他们的报告与我的兴趣和问题几乎没有重合的部分。即是说,关于在诉状中见到的新用语,差役与司法-行政警察、民告官、行政诉讼问题、李镜蓉是否可能是“土豪劣绅”等问题,报告中都没有提及。由于八名参与者提出的问题太过多样,在此予以省略。不过章军(浙江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对于龙泉诉讼档案进行的数量分析,是在其他地方难以听到的内容。根据他所做的统计,在1930年到1933年之间,龙泉县的诉讼激增至顶峰,随后又迅速减少。我询问原因为何,他的回答是认为在政府控制力增强的时期诉讼增加,而在控制力减弱的时候则诉讼减少。即是说,诉讼数量与国民政府的变迁有关系。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即在《龙泉司法档案》之中,“准”、“不准”、“未准”实际上如何表现出来的问题,参加者们也有数个发言。对于该问题,我在前往杭州之前,也预先向吴铮强先生询问过。吴铮强先生指出,由于不清楚现在保存的是龙泉县审判厅的全部档案呢,还是已经丢弃了一部分的残存部分,所以无法回答我的上述疑问。而且他指出,根据《龙泉司法档案》,1916年之后“不准”便大量减少乃至几乎消失,而直至1929年龙泉县法院成立以后,“准理制度”才被取消。简单而言,“不准”这一处理方法从1929年才开始取消,而1930年以后龙泉县的案件数激增,可能正与“准理”制度的消失有关。
对于将第一个案件看做是与民告官和行政诉讼有关的事件,参与者也有很多的发言。某位参与者指出巡士并不是官,我也同意这一点。研读会中参与者还提出意见,认为有必要区分民告官与行政诉讼两个概念,必须要注意当代概念与当时现实之间的不同。
对于将李镜蓉与李兴唐看做“土豪劣绅”的问题,张小也先生认为即便可以将其称作“土豪”,也不能称其为“劣绅”。某位参与者的发言指出,在共产党政权下可能将李镜蓉看做“土豪劣绅”,但在国民党政权下却可能并不将其看做“土豪劣绅”。对于这一意见,我则认为只要他们抱有“巡警为保护人民生命身体而设”的看法,对于不维护治安反而加害人民收取贿赂的警官采取不积极缴纳“警捐”(地方税,充当警察的生活费)的行动,那么对于国民党政权而言,就会被看做“抗捐”,也很可能被看做是“土豪劣绅”。也有参与者指出,虽然民国时期的警察是将“警捐”作为生活费,但是也存在国家支付上级警察工资的情况。不论如何,我认为研读会上达成了一个共通认识,即必须以实态为基础对“土豪劣绅”的概念进行重新思考。
对于李镜蓉这一人物,参与者们也很非常关注。吴铮强先生很清楚李镜蓉经常参与诉讼的事实。在刘陈皓(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的报告中,也引用了前引《龙泉文史资料》中登载的《先父李镜蓉先生》一文。在研读会的参与者中,有十人参加了28日-30日的龙泉县实地调查,共同前往八都的李氏宗祠与李氏的后人直接交流,还得到许可拍摄了他所持有的《李氏宗谱》(民国时期编纂)。而在龙泉市档案馆中,不仅收藏有《龙泉县司法档案》,而且还制作了电子数据库。由于我对李镜蓉到底有多么好讼这一问题感兴趣,所以委托同样参加研读会的章亚鹏(龙泉市档案馆馆员)进行检索,结果发现李镜蓉作为原告的案件有10件,作为被告的案件有6件,可谓相当好讼。

虽然在研读会上没有触及到,但是前记《民国三年 李承纶控王朝信等欠债不偿案》,是龙泉县初次对于债务者的资产进行拍卖和强制执行时的案件。债权者李镜蓉对于当时新颁布的法令非常熟悉,在对龙泉县第一审结果不服之后直接上诉到浙江高等分庭(温州高等分庭)。这一案件中最有趣的是,原告李镜蓉与写作批示的龙泉县知事(龙泉县审检所长)之间的对话。很明显,李镜蓉要比知事更加熟悉新法律,所以是由他指导知事进行了龙泉县历史上首次强制执行的程序。换言之,在龙泉县这样偏远的县里,对于应该如何来进行近代化,是由民领导着官来推进的。从这一点上,确实能够感受到时代的光明,以及当时人对于未来所持有的光明印象。但另一方面,李镜蓉这样的知识人、绅士要比知事更加了解近代知识,而且指导知事这一点,是否也导致在其后的近代化过程中,由于官方丧失了充分的统治力,反而极大地增加了近代化的困难呢?从李镜蓉斥责知事不知道所谓近代,以及“请县执行,至今无批,更不执行”一句来看,至少他自身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此后民国将会经历的多难之途。
以上便是龙泉司法档案研读会的概略。我从研读会的参与者那里学到了很多,也与中国的年轻研究者们共享了自己关心的一部分问题。遗憾的是,虽然这样仅仅讨论一、二个档案的研读会花费了一整天,但时间依旧不够充分。
对于我这位日本研究者而言,轮读会(会读会)或者以史料阅读为中心的研究会,是相互切磋琢磨相互启发的有效手段。我也向吴铮强先生提及了此点。据吴先生说,他此前对这样一种研读方式并不熟悉。在这次研读会体验的基础上,我热切希望,今后在各地举办的此种国际研读会能够给予更多的讨论时间,展开更加充分的交流探讨。
附记:写作本稿时得到了吴铮强先生和凌鹏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