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将无同》阅读系列︱六朝民族史研究省思——以山越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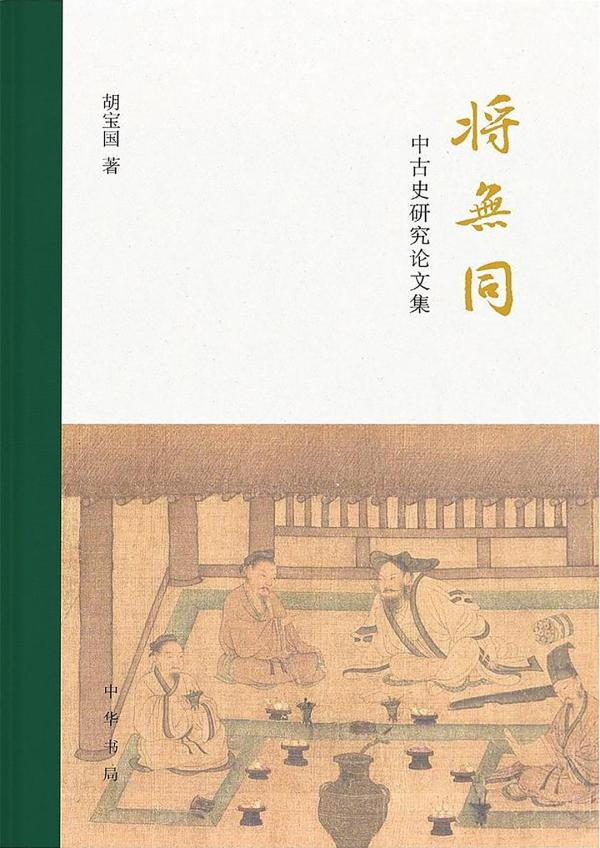
胡宝国先生的新著《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一书收录了作者具有代表性的三十篇文章,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许多论题都有自己独到而精深的见解,而为笔者所关注的是其中关于区域人群的研究视角。如《两晋时期的“南人”、“北人”》一文对南北地域界限以及“南人”“北人”的辨析,注重从时代变迁与个人语境还原人群称谓的意涵,这种思路对解释中古时期的族群现象也同样适用。借此机会,谈谈笔者对六朝民族史研究的某些思考。
“民族”概念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引入中国后,古代的“华夏”与周边的“四夷”便被赋予了“民族实体”的含义,对现代民族进行溯源式的研究,实现与古代各种区域人群的对接,复原各民族在历史上分布、迁徙、交流、融合的演变特征,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二十世纪末,兴起了“历史记忆”“主观认同”“政治实体”等研究新潮,对各时期民族史的研究取向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六朝民族史的研究,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陈寅恪、周一良等,至本世纪初的鲁西奇、罗新等,呈现出从“民族实体”的传统范式向“政治实体”论转变的趋势。民族史学者从族属源流、分布迁徙、经济结构、社会形态、文化习俗、民族政策、阶级斗争、民族融合、地区开发等线索建立起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因种种内在矛盾而难于自圆其说,逐渐受到质疑,出现了对“民族”本质的重新思考。基于政治史的视角阐释“民族”,无论是象征王朝国家的“华夏”,还是未纳入统治的蛮、越、俚、獠等“非华夏”,都被视为以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来的各种“政治体”,“政治体”属性越来越多地被提倡运用于六朝民族史的研究。
其实,即使是提出以“文化”分别“民族”这一重大命题的陈寅恪,在考证东晋南朝各种人的族称与族属时就有言,“古史民族名称,其界说颇涉混淆,不易确定”(《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则已经感到族称与特定文化人群难以一一对应,且族称彼此之间无明确界限。这一困惑在关于“山越”族属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学界对此的认识始终存在较大分歧:刘芝祥、井上晃、吕思勉、唐长孺、川本芳昭等主张山越的主体是逃入山中的汉族,即使有古越人后裔,也已相当程度的汉化;叶国庆、陈可畏、川胜义雄、胡守为、施光明等则坚持认为山越就是居于山地的古越人后裔,其民族性尚存,属于非汉民族。这场论争备受关注且旷日持久,导致六朝民族史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出“山越”一枝独秀的现象。虽然至今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思勉、唐长孺等淡化“山越”民族性的主张,强调了其脱离政府控制的政治性,与后来的“政治实体”论者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这一思路被鲁西奇、胡鸿等应用于“蛮”的研究中,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蛮”与“山越”一样不具备民族性,本质上都是非华夏统治的政治体,从根本上瓦解了分类溯源的民族史研究范式。
在“政治实体”这一新的话语体系中,纠缠不清的族源问题看似不复存在了,然而过分强调“蛮”“山越”等非华夏人群的同质性,似乎又掩盖了这些族群称谓本身所具有的不同内涵及范畴。即以“山越”而论,按《三国志》所载,其分布范围不出孙吴扬州界域,而与“山越”互称的“山贼”“山寇”“贼”,却遍布孙吴全境,荆、扬、交、广所在皆有。换言之,二者的边界是不同的。如果像鲁西奇认为的那样,“山越”之名是官府士人对居住于山区、不服“王化”的土著人群赋予的“非我族类”之歧视性称谓(《“越”与“百越”:历史叙述中的中国南方“古族”》),何以使用范围仅限于扬州?显然在时人的认知中,扬州的“山贼”区别于他处的“山贼”。《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称丹阳郡的“幽邃民人”与“逋亡宿恶”:“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东晋以前,江东社会普遍继承了先秦以来越人轻悍好勇的风气,即使被陈寅恪称为“文化士族”的吴郡四姓,在孙吴一代不仅拥有大量私人武装,并且出掌军权,对武力的重视远胜过对文化的兴趣。可想而知,居于山林中的丹阳“民人”势必保留了更多越俗,《后汉书》卷三十八《度尚传》称丹阳宣城县“盗贼”所谓“椎髻鸟语”之词恐非虚言,连质疑“鸟语”记载真实性的吕思勉,也承认“华人之入越地者”,“大率椎髻,不足为异”(《吕思勉读史札记》乙帙“山越”条),这恰恰印证了越地旧俗的存在。于是,扬州九郡的“山贼”被冠以“山越”之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秦汉时代越人自江东至岭南遍布东南沿海区域,覆盖了孙吴扬、交、广三州之地,但岭南的交广二州却绝无山越踪迹。谭其骧指出:“秦、汉时南越国人即俚人,而俚之所以不见于《史》、《汉》者,以其时中原人与俚相处犹暂,未尝熟知其种族名,故率以泛指南人之‘蛮’、‘越’称之也。”(《粤东初民考》)“俚”,始见于孙吴万震《南州异物志》:“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长。恃在山险,不用王法。”“俚”的出现,是孙吴经营岭南的结果,自此在王朝史家的认知中,岭南土著人群脱离了“越”的族类范畴。然则成书晚于《南州异物志》的《三国志》中却未见到“俚”称,岭南地区惟有“高凉渠帅”“郁林夷贼”“苍梧建陵贼”“揭阳县贼”“交阯九真夷贼”等,可见“俚”作为岭南非华夏人群的族类专称,在孙吴西晋时代尚不明确。尽管如此,岭南诸郡县“贼”“夷贼”之别于“山越”,则确凿无疑,惟其族类特征有待辨明。
与岭南情形相似的是《三国志》对荆州非华夏人群的表述:“武陵蛮夷”“五谿蛮夷”“五谿夷”“桂阳湞阳贼”“长沙贼”及长沙郡的“山寇”“山贼”、零陵郡的“山贼”。对照《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传》,这些人群大抵可以划属“蛮”这一族类:“武陵蛮”“五溪蛮”“长沙蛮”“零陵蛮”“桂阳蛮”。盖“蛮”作为长江中游非华夏族类的专称,至迟形成于《后汉书》成书的刘宋时代,而晚于《三国志》成书的西晋时代。《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有“夷民”“夷新兵”的记载,魏晋官印中也有许多册封长江中游“蛮夷”的印文,结合《三国志》关于孙吴多次用兵“武陵蛮夷”等荆州土著人群的记载,可知随着双方接触与联系日增,这些山民不再被视为普通的“贼”,而带上了具有族群内涵的称呼,但其族类特征尚未被识别之前,暂时赋予了“蛮夷”“夷”这类非华夏族群的一般性称谓,而非冠以“越”这种特定的族类名称。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孙吴西晋时人的眼中,荆州诸郡县“蛮夷”“贼”同样有别于“山越”。
放眼孙吴全境内的非华夏人群,呈现出这样的特点:记载最详细的是扬州,其次是荆州,再其次是交广,但就其数量而言应是反向的,政府与非华夏人群交涉的程度和当地与首都的距离是成反比的,而族类的认知与书写也表现为类似的圈层结构。首先是核心区域扬州的三吴地区,作为政权支柱的吴姓大族,这些华夏化程度最高的人群早已自认华夏族类,甚至成为族类书写规则的制定者。其次是扬州山区没有完成华夏化的土著,相对于体制内的吴人而言,他们身上保留着更多的“越”特征,很容易被前者识别,当然也不排除前者刻意夸大两者间的差异,建构“合法”与“不合法”的需要,但不论如何“山越”作为扬州山区族类专称的特殊意义是为孙吴西晋时人所认可的。再次是荆州武陵山区的“蛮夷”与广州南部滨海区域的“俚”,前者是除了山越以外,孙吴最大规模讨伐的南方土著人群,其族群性异于华夏自易被感知;后者由于孙权屡屡耀兵海外、乐于海外征伐,《南州异物志》所述多海南诸国方物风俗,广州俚人的发现亦非偶然,不过因为距离遥远,孙吴与广州土著人群产生的联系尚少,时“俚”称之不见用于正史官书也属正常。最后,在以上这些已知的不同程度上具备族类性质的人群以外,南方广大地区非华夏统治的那些未知族群性的人群,则被目之为“贼”这样简单化的方式处理。
总之,站在孙吴政权的立场上,无论“山越”还是“武陵蛮夷”抑或“广州俚人”,都是抗拒统治、不服王化的“贼”。因为越人的华夏化进程相对南方其他地区而言较早,孙吴一代“山越”问题基本解决,所以“山越”未入后来的正史“四夷”传,没有经过像长江中游的“蛮”那般复杂的谱系建构。正是这样的原因,从而在现代引发了多年悬而未决的族属争议,当然也为传统的六朝民族史研究打开了一个缺口。然则一旦从“民族实体”论走向另一个极端“政治实体”论,造成泛化的“共性”“本质”研究,无异于堵上了“具体”“个别”研究之路。
通过对“山越”等孙吴时代族类概念的初步解析,不难发现其内涵并非近年来流行的“政治实体”论所能完全解释得通的。东晋南朝继“山越”之后,“蛮”“俚”“獠”成为南方非华夏族类的主角。随着建康政权不断向西部、南部山区拓展统治空间,王朝史家的族类识别不断深入,族群分类更加细化,“蛮”“俚”“獠”彼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关于“蛮”,吕春盛认为这一概念从秦汉时四方异族的通称到魏晋南北朝时逐渐缩小范围,狭义地专指长江中上游流域的异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蛮”及其概念之演变》)。然而六朝“蛮”称的使用范围仍遍及南方各地,只是相对集中于长江中游一带,那么“蛮”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需要从不同区域、不同语境、不同称谓组合等多视角的解释。相对于“山越”“蛮”而言,“俚”“獠”的研究更是始终停留在族属源流、社会文化、民族关系等传统视域徘徊不前,特别是作为“民族实体”的“俚”与“獠”,二者边界及相互关系是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陈寅恪曾推论:“凡史籍之止言獠或夷獠联文,而属于梁益地域者,盖獠之专名初义。伯起书之所谓獠,当即指此。至属于广越诸州范围,有所谓獠,或以夷獠俚獠等连缀为词者,当即伯起书之俚也。”(《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此说虽产生一定反响,但无论赞同者还是反对者,囿于“民族实体”的范畴,均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从“政治实体”论着眼,“俚”“獠”两者并没有本质区别,同样无法解释。
一味强调“政治实体”的共性,不仅会抹去不同族群的个性,而且族群概念本身的内涵也被无限放大了。众所周知,六朝时代由于战乱逃亡、大族荫庇等原因引发的户籍人口流失现象非常严重,这些脱籍的人是否都被时人归入“蛮”“越”等族类范畴,还有待商榷。如果说,“政治实体”论揭示了中古时期“民族”现象共同的本质,那么,“族类观念”说则为各“民族”内涵的差异性提供了一条思考的路径。若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庶几可更接近中古“民族”的真相。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