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记者殷盛琳:错过疫情的现场报道,我想一年后和他们当面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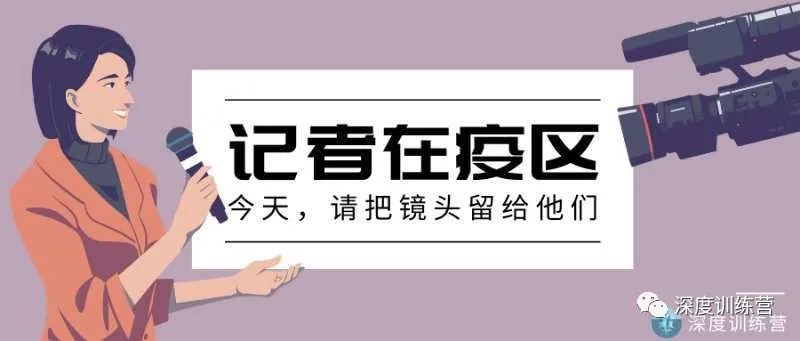
深度训练营作为新闻学子的大本营,将对话八位疫情一线的记者们,还原他们文字背后的努力和思考,传递他们为新闻坚守的专业技能与热情。
今天对话第四位记者——极昼工作室的殷盛琳记者,也是深度营的一期学员。

供职媒体:极昼工作室
毕业院校:河海大学
从业时间:一年
*以下均为殷盛琳自述
1月23日,武汉正式封城,编辑部也进入疫情报道,这项工作仍在继续。我们建了专门的疫情报道小组,参与的记者会一直跟进武汉的最新动态。
目前发表出来的报道大概有四十多篇,但我参与的只有七篇。作为一个刚刚进入新闻行业的菜鸟记者,没有亲历现场,只能把一些非常浅薄但真实的感受分享出来。
在我参与的报道中,主要分为两类主题。一是武汉封城/流浪的武汉人/TR188航班这类动态的,即时类选题;另一种则是普通人的疫情瞬间这类时效性偏弱,呈现人的状态与感受的选题。
在写武汉封城稿时,这个题非常紧急,我们几个记者是分头去找采访对象,然后采访完在群里简单说一下自己拿到的素材,再把自己的素材写成一段叙述体的小章节,由编辑承担最后的合稿工作。
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其他合作稿都是两个记者商量着分工,然后各自写自己的那部分,把一篇完整的初稿发给编辑。
如果你愿意聊一聊,我是很好的倾听者
寻找采访对象的过程,还是与以往常规报道一样。
通过各个社交平台以及做过相关报道的同行介绍,唯有两次比较特殊。
一个之前一起实习的朋友,我们一直维持着普通网友关系。有一天,她突然发来一篇自己写的文章让我帮忙提意见,主题是疫情下自己的感受,正好和我的选题相关。她在武汉度过大学四年,而留在当地的朋友和老师都不可避免地卷进这场灾难里,她自己也思考了很多之前毫不在意的问题。
另一个则是豆瓣有名的博主,在给他发采访邀请时,我也顺带发过去一些之前发表的报道。当天发过去之后并没有收到回复,我以为这条线黄掉了,结果第二天再打开私信页面的时候,看到他回复说,觉得自己不太适合,但他看了那些文章,很愿意帮忙介绍合适的朋友来跟我聊。后面我有两个采访对象都是这个遥远的陌生人介绍的。记者很多时候就是仰仗这些善意,才得以完成报道。
在寻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遇到拒绝采访的情况实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之前非常想采访一位逝者家属,他在微博上写了很多封信给离开的妻子。我给他写了很长的约访信,但最后还是被拒绝了。
如果是其他选题,我可能会再试几次,但在疫情报道里,如果对方明确拒绝,我就不会再去打扰。以前约访时,我会想办法告诉对方我们是互相给予的关系,你也能从中获得些什么,如果真诚面对别人,自然会有回响。但对着这些患者,家属,医生,我说不出这样的理由。我只是告诉他们,我对你的处境和经历好奇,如果你愿意聊一聊,我是很好的倾听者。
和常规的长报道相比,疫情报道并没有很复杂,它对记者最大的挑战是,隔着电话,如何通过采访去尽可能还原场景。
你没法看到现场,只能通过细致的采访获得场景细节,然后在打电话的时候根据对方的回答进行追问,至于什么时候需要更细致地提问,什么时候只要对方呈现框架就可以,需要记者的经验和判断。
写人物稿件就更难操作,隔着电话你能把他的行为逻辑搞清楚都不容易,想深入他的心理层面太需要能力了。我做不到,但我可以把前段时间,我可爱编辑的前主编张捷老师分享给我的一段话也分享给你。记者的叙事是自己理解力的呈现,理解越深,越接近事实的真正意义。发现表象,需要好奇。想到要写表象背后的原因,需要多一点的好奇,至于透过人家给你的烟雾探到最深层的心理原因需要的是敏感。

张捷老师说,“记者不能只问个大而化之的问题等着对方给东西,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小刀小剑扔出去看对方的反应,没准哪一个问题戳中对方的内心,对方的话就像潮水一样涌出来。总而言之,要有基于阅历的想象力,洞察人心的各种可能性”。

我很想在一年后去和这些人见面聊聊
因为我不在现场,只是隔着电话和人交流,也没有操作更加硬核的问责报道,所以现在留在印象里的都是很微小的瞬间。
印象深刻的瞬间一个是,我采访一位回家乡合肥做中学语文老师的华东师大女生。在疫情发生前,她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对很多事情都是惯性而不加审视。疫情给她提供了一个缝隙,看到这个社会更复杂的边角。
一开始,她在微博上看到那些批评官员的网民,会替对方觉得委屈,因为她觉得疫情发生太过偶然,一个官员可能在整个政治生涯里都不会面临这样的大事件,慌乱很正常。
但后来,她得知一位曾教过自己的老师也得了肺炎,看到空无一人的楚河汉界和非常绝望的个体求助,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想法:如果自己身在其中,患病后找不到床位,只能在家隔离,还可能传染给家人,那愤怒的确是应该的。她会去思考更多——看起来双方都有自己的困境,那么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到底谁该为个体的悲剧负责?她说这次疫情可能和我们之前遭遇的很多事件一样,逐渐平息,然后被忘记,但她会记住李文亮,记住艾医生,如果下次有必须发声的事情,她会和这两个人一样,勇敢地站出来。
还有一位去武汉做心理援助的医生,他被分配到金银潭医院工作。刚开始,每天有一二十人去世。尸体被拉出来,装进裹尸袋,拉走,火化,没有葬礼。他说“肺炎患者在生命尾声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有患者告诉他,自己不想再治疗,不是因为他不想活着,而是太疼了”。
之前他总觉得一个人为了家庭,为了未来,疼痛是可以忍受的,但现在才知道,当生理性疼痛到达一个边界时,人只想解脱。还有一个老奶奶,吵着出院后要去杀了给儿子治病的医生——她的儿子是第一批确诊患者,已经去世了,之前离过婚,留下一个十几岁的孙子。这个医生说,“对于武汉而言,疫情会留下无数漫长的心理伤痕”。
还有被迫流浪在外遭受歧视的武汉人,因为疫情没有举办婚礼的医护夫妇…太多了,我很想在一年后去和这些人见面聊聊。
我想自费去武汉,结果还是不行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去武汉,这可能是我大学以来最遗憾的事。像这样巨大的灾难发生在身边,作为记者居然只能在房间里打电话,我可能真的没办法原谅自己。我问过编辑,能不能请年假然后自费去,结果还是不行。
只能安慰自己,不同的媒体平台都各有限制,我们输出的这些报道或许没有那么硬核,但也真实地记录了这场灾难,拼凑了整个版图的一角,有属于它的价值。
作为菜鸟记者,还没有资格谈经验,我只是不断告诉自己,要成长起来,在这样重大的灾难中,有能力去做一篇真正专业的报道。
项目统筹
谢婵 韩凤兰
采写成员
阮协协 郭嘉仪 谢婵 李叙瑾 刘田
余晓璐 吴敏霞 陈嘉玲 罗方清
END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