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马国川:我为什么如此关注日本?
原创 文度记 文度记

之前《国家的启蒙》,主要是通过描写1853年“黑船”叩响日本国门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的历史,探索“日本帝国崛起之谜”。作为一名财经记者,近年来致力于对日本史的挖掘与写作,为什么对日本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访谈者 高明勇(评论人)
对话人 马国川(财经杂志主笔)
缘起:福泽谕吉是我的“引路人”

作者: 马国川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文度记:你之前长期关注财经领域的报道,和改革主题的访谈,什么样的机缘,促使你对日本历史如此感兴趣?
马国川:这完全是一个“意外事件”。2016年我获得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的资助,到庆应大学做了4个月的访问学者。这所大学的创办者,就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此前我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了解极少。2016年8月1日我抵达东京,才注意到最大面额的万元日钞上的人物就是福泽谕吉。当天晚上,我走进庆应大学校园,看到福泽谕吉的雕像,就特别想了解这个人的故事。
通过阅读,我发现,福泽谕吉一生没有涉足官场,却以自己的思想引领日本走向近代文明。作为远东之东的岛国,日本从被迫打开国门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书写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多少风云人物活跃在这段历史中,壮怀激烈,成败兴亡,难道不值得追寻吗?因此,我决定利用这宝贵的4个月时间,好好地寻找这个国家近代发展的轨迹。我阅读历史书,外出游览也有意去探寻斑斑史迹。每有兴会,就把那些可感之人、可述之事记录下来。我在“界面”网站开了一个专栏“扶桑读史”,大致每周发表一篇。这些文章获得了读者的共鸣,既然吾道不孤,我也就更加努力。2016年11月底回国后,我继续写“扶桑读史”专栏,直到2017年11月中旬完成最后一篇,才结束了一段奇特的阅读和写作体验。
对我来说,集中这么长时间阅读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这是第一次。我一共写了60篇文章,汇集在一起,就在2018年出版了《国家的启蒙》。
文度记:从1853年的“黑船事件”,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整整是60年时间。而你这本书也正好是60篇文章。两个“60”,是巧合还是?
马国川:不是巧合,而是我有意为之。不过,这些文章绝不是按年度选择的,所写的人物或事件都是我认为重要的。我想通过这些人物和事件,反映日本告别旧体制、走向近代国家的过程。
文度记:《国家的启蒙》第一篇写的是“黑船来航”事件,也就是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领舰队叩响日本大大门。为什么选择这个故事作为开始?
马国川:因为“黑船来航”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就像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一样。其实,在1853年之前,日本和中国一样,与世界隔绝,酣睡在太平梦中。正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所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问题是,坚船利炮驶进东亚,打破了停滞宁静的迷梦,中日两国由此开启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我看来,在19世纪中期,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面临同样的“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的人们对此懵懂无知,我们作为后人看得很清楚,对中日两国来说,从被推入现代化的巨流的那一刻起,它们的命运是共同的,就是走向世界、走向文明。
文度记:但从两个国家的近代史来看,面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却有很大差别。
马国川:是的。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没有打一次“鸦片战争”,而是审时度势,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因为它清楚自己的实力远远不如对手,知道清王朝早就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所以就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然后日本就打开了锁闭的大门。作为日本近代史的起点,这种识时务的做法对于日本后来的走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主动打开国门,所以日本能够告别旧思想、旧体制,接受外来的思想,学习先进的思想学说和国家制度,而不是别别扭扭地半推半就,更不是蛮不讲理地一概拒绝。中国的路径完全不同。因为是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才被迫打开国门,清王朝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这些邪恶的外国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假如他们不跑进来,我们照样是太平盛世。清王朝一直没有清醒地认识自己,拒绝改革,丧失了发展机遇。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曾提出“路径依赖”理论,指出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物理学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轻易走不出去。如果说,近代日本的路径是好的,那么清王朝选择的路径显然是不好的,导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走得分外艰难。
触动:异国的改革者似曾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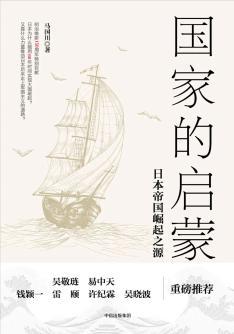
作者: 马国川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文度记:尽管两个国家选择的路径不同,不少人在读《国家的启蒙》的时候,却有似曾相识之感。
马国川:尽管中日两国在具体路径选择上迥乎不同,一个被动而顽固,一个主动而决绝,但是历史大脉络惊人地相似,因为它们要完成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活跃在历史中的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对“国家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作出回答,并据此决定个人的选择。因此,不同国度出现许多相似人物、相似事件,并非不可理喻。
比如那位森有礼,当年是日本思想启蒙运动的健将,后来却成为极力维护专制体制的国家主义者。中国近代以来也这样的思想转向者还少吗?再如,日本开国之后的“爱国贼”们,以爱国者自居,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卖国的本国人士横刀相向,肆意砍杀,中国这样的“爱国贼”不也是很多吗?
文度记: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国家的启蒙》的主要内容是明治维新,出版时恰逢明治维新150周年,记得当时引起不小的反响。但奇怪的是,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日本关注明治维新的人似乎并不多,反而是在中国有不少人在回顾、讨论明治维新。你怎么看?
马国川: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走出了明治维新的历史阴影。因此日本人回顾明治维新,是把它作为单纯的历史来审视,很难激起情感上的波澜。中国不同,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1840年以来的历史延长线上,我们还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明治维新是中国的镜子,当我们回顾明治维新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审视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让我们知道百年中国的进与退、得与失。只要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我们就走不出历史的延长线,追问“日本做对了什么”就有价值。
文度记:往往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崛起的转折点,在研究过程中,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或认知的改变?
马国川:确实,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实现了近代化,成为一个“与万国并峙”的强国。与之相比,清王朝是一个失败国家。可是,追赶西方国家初见成效之后,日本社会就开始出现了宣扬日本“特色”、维护“国体”的保守主义舆论。在20世纪初,日本出现了“和平崛起”与“武力崛起”的争论。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导致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思潮兴起,为日本后来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因此,我认为明治维新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建设现代国家的成功故事,而是一个成败参半的改革故事。如果历史在1912年戛然而止,这个国家从封闭落后一跃成了世界列强,很是值得学习。但是如果我们站在1945年来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日本的现代化故事毋宁是一个失败的故事。
反思:戒慎戒惧,才有可能避免歧途
文度记:写完明治维新,又为什么想到要写《国家的歧路》?
马国川:我所尊敬的吴敬琏先生在看过《国家的启蒙》书稿后说,这本书好像没有写完,应该写到日本战败。确实,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自1853年黑船来航至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完整阶段:开国-追赶-崛起-歧路-毁灭。这是一个以成功始、以失败终的故事。《国家的启蒙》虽然多处指出明治晚期已经出现了歧途,毕竟没有将故事讲完。在先生的启发和鼓励下,我从2017年底开始写作《国家的歧路》,历时近两年才完成。
文度记:围绕一个国家,两本不同的书,两段截然不同的历史,写作过程中应该是五味杂陈吧?
马国川:如果说,明治维新是一首由低沉到高亢的英雄交响曲,那么从1912年开始的日本历史则是从充满希望的欢快节奏开始的,后来越来越混乱低迷,至1945年曲终之际,已经绝望哀痛,不忍听闻。
文度记:在《国家的歧路》里,你有一个说法,就是把日本与美国开战称为“民族切腹”,认为这是“20世纪世界史的最大谜团”,你认为谜底是什么?
马国川:“民族切腹”是1930年代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说法,我认为非常准确而形象。1941年日本和美国GDP总量比例为1:26,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力比例为77.9:1。国力如此悬殊,与美国开战显然是愚蠢至极。其结果不但让世界遭受涂炭,也让自明治维新以来几代日本人奋斗得来的现代化成果毁于一旦。
造成“民族切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狂热的民族主义控制了日本。在大正时代,日本政治多元化、社会多元化,但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气质发生了变化。彼时的日本人对国家驯服,认为满足国家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将国家利益置于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才是爱国的表现。强调忠诚于国家和毫不犹豫地为国捐躯,酿成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民族主义可以蒙蔽国民的心灵,也可以蒙蔽国家的双眼。特别是在遭受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日本没有审视自己的问题,而是把西方视为自己的敌人。它自暴自弃地退出“国联”,不断地宣扬自己文化独特、制度优越,号称要“近代之超可”(克服现代性)、“超越西方”,仿佛全世界都应该学习日本。于是,政党政治、议会制度等现代文明被践踏,天皇制度被吹捧为世界最好政治体制,胆敢怀疑者就会被斥责为“非国民”(日奸),遭受打压。
盲目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爱国主义的合流,必然导致军国主义。于是,日本帝国就像一个失去理智的狂兽一样,走向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
文度记:通过明治维新,日本成为跻身世界强国,给其他后发国家以巨大的鼓励。可是最终它却自取灭亡,有观点认为这是后发国家追赶现代化的宿命,无可避免,你有什么看法?
马国川:当然不是。深入历史现场观察就会发现,即使是在历史转折点上,也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可走,而是有多种选择。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也完全有避免战争的余地。纵观日本现代化的过程,这个国家似乎每向前迈进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甚至两步才行,结果以失败国家告终。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荆棘的道路,只有戒慎戒惧,才有可能避免歧途。作为后发国家,尤其要保持理性,不要被盲目的民族主义所左右。这就是近代日本的最大启示吧。
计划:写作延长线上关注日本“重生”
文度记:目前由于新冠病毒蔓延肆虐,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也在一些国家高涨。你怎么评价这样的现象?
马国川:其实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就已经进入多事之秋。这次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加剧了民族主义思潮,导致全球化受挫,民粹主义上升,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要警惕和抑制民族主义,绝不能放任、更不能纵容民族主义。
战前的日本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惨痛教训。当时日本所有的举措看起来好像都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日本人正是在赞同、甚至欢呼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举措中走向了战争深渊。虽然有个别清醒者没有被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潮流冲昏头脑,但是大部分、包括知识精英都成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吹鼓手,推波助澜,将国家推进灾难的泥潭。殷鉴不远,能不慎乎?
文度记:在《国家的歧路》里你写了不少知识分子,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马国川:因为我认为,知识分子对于追赶型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从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现代化道路上竞走。追赶型国家里的知识分子,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衡量本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不断地提醒国家要走在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因为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而错误的道路却有无数。一个国家一旦踏上错误的道路,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就像日本,在1930年代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思想启蒙的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只要一天不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知识分子就一天也不能松懈。
文度记:我看你在《国家的歧路》的前言里说,“比起欧美国家来,中国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是日本”。这是为什么?
马国川:对于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国家而言,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深入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避免歧路。我特别喜欢周有光先生的名言,“要站在世界看中国,不要站在中国看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失去世界视野和历史眼光,囿于本国,难免重蹈失败国家的覆辙。纵观世界近代史,失败国家不是少数,而且有些国家还会在相同的地方栽跟头。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都面临同样的历史任务,就是国家转型。日本一度走在中国的前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因此,日本是中国的镜子,也是中国的鞭子。
如果说,《国家的启蒙》所写的日本是中国的镜子,可以在对照中发现中国现代化道路曲折艰难的内在原因;那么,《国家的启蒙》所写的日本则是中国的鞭子,让我们时时保持警醒,一定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千万不能误入歧路。中国至今仍然处在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历史延长线上,因为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国运可长亦可消,端看是否能够学习和反思。
文度记:《国家的歧路》之后,你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马国川: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日本三部曲”的写作计划,通过三本书描写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国家的启蒙》和《国家的歧路》作为前两部已经完成,正在写作第三部《国家的重生》,计划从1945年战败写到1973年日本成功起飞。
穿越日本近代历史长廊,深感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道阻且长。为了实现现代化转型,后发国家是否注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没有外力推动,东亚国家只靠自身努力是否能够完成现代化转型?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来看,似乎都很难。这个结论,令人沮丧。但是我相信,历史不是等来的,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近代以来,好几代中国人都在为建设现代中国而奋斗,“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