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走进袁哲生的小说世界:人一旦开始躲藏,就很难停下来了
文 | 宗城
袁哲生在处女作中写了一只“静止在树上的羊”。“那天冷清的园区令人难忘,四处是灰灰的石头和天空,找不到特别想看的目标,除了一只白色的山羊。我从远远的地方发现它站在一根横斜的树干上,像是刚刚才在陈列馆里看见的标本被人放到树上去的。我走近去看它。它的眼睛眨动了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记忆是否真实,随着回想距离的拉长,记忆中的景物不是渐渐变淡,而是慢慢静止,不再移动,直到景幕中的我也变成了一个标本。树上的羊依然文风不动,像是静止在半空中的一个白色问号。”
在小说中,袁哲生常会书写这样梦一般的意象,比如“时计鬼”,比如“秀才的手表”,最后通往的都是人内心的隐秘角落,现代人无从解决的失落和孤独。这是袁哲生小说的一个主题。
他与黄国峻、骆以军、邱妙津、赖香吟等人齐名,被文坛称作“五年级作家”。他们崭露头角于上世纪末,通过两大报的文学奖、联合文学新人奖走上台面,比起戒严时期的文学作品,他们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注重技巧和审美。在打破现实主义束缚的同时,关注人的内在世界,袁哲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5年过去了,两岸三地的文学浪潮层层叠叠,可袁哲生的名字依然如同静默的迷,被悬置在岛屿台湾的孤独角落。

袁哲生(1966—2004),台湾高雄县冈山镇(今高雄市冈山区)人,毕业于文化大学英文系、淡江大学西洋语文研究所。曾获台湾第17、22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第20届“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第33届“吴浊流文学奖”小说正奖、“五四文艺奖章”小说类等等。
1. “人天生就喜欢躲藏,渴望消失。”《寂寞的游戏》是袁哲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作品有七个短篇,描述了人世间诸多关系。小说人物各异,他们共同的情绪是“寂寞”,袁哲生写道:“人生就是一场寂寞的游戏。”他在小说中提到许多与寂寞有关的片段,譬如“有的人记起了在一个遥远的台风过境后的傍晚,自己一人莫名地走在淹水的巷弄里,一直走向布满紫色云朵的天际那头;也有人回想起在某个无聊的冬日午后,自个儿孤零零地坐在池塘边等待鱼儿跃出水面......”那些人物年龄不一,但都像倚靠窗边的少年,云朵是他说话的对象。
《寂寞的游戏》有“少年感”,这份感觉恰似内地版的封面图案——深蓝的背景中,一个黑色的孩子弯下腰,在铁轨边寻找着什么。铁轨下方有一句话:“天一旦开始躲藏就很难停下来了,这点我始终深信不疑。”
整部作品可谓少年的内心剧场,表演着五颜六色的童年幻想。譬如:小说谈到“我”小时候挨打,想做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浸泡在水里,“每拨动一下流水,成群的金色小鱼便游梭起来,把水面织成一匹泛着银光的白布,四周宁静无比。一会儿,少年又再度潜入水里去了”。通过描写,袁哲生将读者引入岁月深处的宁静角落,或许在他心中,童年始终是一个合理的避风港。
但《寂寞的游戏》并不总是光亮。怅然在小说里时时浮现。比如回忆起年少好友时,叙述者说:“幸好,朋友是越来越少了。”比如看到下雨,诚觉“雨天更适合死亡”。《父亲的轮廓》里,袁哲生再度提起死亡。当“母亲仿佛一个做错事的小孩那样,将门重新掩上、离去”,小说中的“我”的眼前恢复成一片黑暗,“坐在床沿,紧握双拳,心中又重新燃起了一股想死的念头”。
袁哲生以“我”的口吻叙述了父亲的去世,他遭遇车祸,“我”和母亲毫无防备地收到他死亡的讯息。小说中,亲戚们传说他是因为千金散尽之后,沦落到贫病交迫、众叛亲离的境地,所以才选择撞车自杀。父亲死后,“我”悄悄去过几次事发现场,小说写道:
“父亲在我心中的无名英雄形象,变成了一个用白色漆线勾勒在柏油路面上的空白轮廓,肢体虽然扭曲,但是依然完整。南来北往的的车辆不断地从父亲的轮廓上压辗而过,每压一回,关于父亲的生前种种便更加清晰起来。父亲依旧活在我的心中,依然继续为我增添新的记忆,只是不再与我分担新的悲伤。.....父亲的轮廓日益模糊、褪色,终至消失不见。”
死亡的音乐在小说里阵阵作响,让童年多出令人不安的气息。除了死亡,袁哲生关注的主题还有人与人在现世的隔绝,这在小说《密封罐子》里体现的最为形象。密封罐子既是小说中的重要器物,也是关于隔绝的隐喻。
小说中,丈夫与妻子在山间生活,每日面对的只有彼此,可即便如此,丈夫和妻子在剥除表面的恩爱后,内心仍然对对方封闭,她们彼此想知道对方的想法,可这种企图仍然落空。妻子想玩一个二十年约定的游戏,用密封罐子,关住两个人对彼此最想说的一句话,二十年后再揭晓。可原来丈夫没有写下话语,放进了空纸片。而丈夫在妻子过世后,没有遵守二十年后再打开的约定,提前打开密封罐子,却发现里面只有他的那张空纸片。他才知道早在五年前,妻子已经知道了罐子里的真相,充满失望的离开。可是,她却故作无事的仍然与他生活,直到死去。只要想到这五年来,妻子是如何隐藏自己的失落,维持看似安稳的婚姻,那无法与外人道的孤独,就足以把一个人压得喘不过气。
《寂寞的游戏》不以故事为重,通篇注重感觉的营造,有的篇目读起来甚至像散文,比如获得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的短篇《送行》,评委张大春在决审意见中说道:“几乎没有所谓‘故事’的《送行》是如此地轻描淡写,以至于很容易启人疑窦:这是一篇小说吗?还是一篇散文?”
袁哲生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文体,他打破了一般读者对小说的认知,使得文本犹如他的私人日记,又好像散文诗一样,但叙述和故事仍保留了小说的风味。他对文体的融合并不生硬,相反十分柔顺,可以说,故事性不再是他的小说的根本,语言才是。他能通过语言营造出精确的氛围,不依靠情节就让读者沉浸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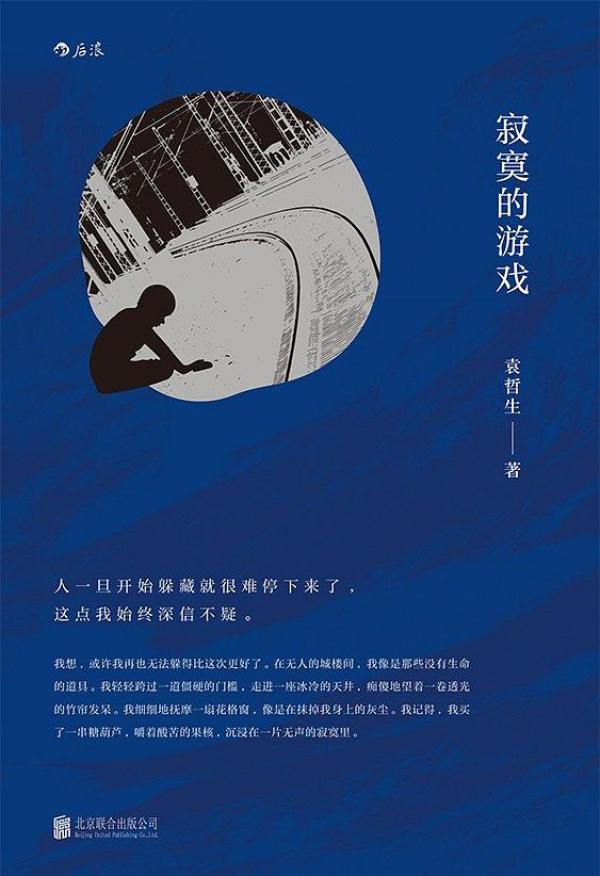
《寂寞的游戏》,袁哲生 著,后浪出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9月版
2. 袁哲生的小说里不只有回忆,也有超现实的虚构,由《秀才的手表》《天顶的父》《时计鬼》三篇小说组成的“烧水沟系列”就是后者的代表,它们被收入小说集《秀才的手表》。
这三篇小说都以台湾少年的视角展开故事。“我”、秀才、空茂央仔、吴西郎、算命仙仔、外公黄水木、外婆阿妈、火炎夫妇、武雄、武男以及老师、牧师等人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埋藏在闹剧氛围里的失落穷乡图景。借这三篇小说,袁哲生希望给予读者异质性的感受,还原那些无法被“整体化”概述的边缘生活。
在“烧水沟系列”中,袁哲生并未采用都市中产阶级的视角,也没有选取知识分子作者的惯常姿态,而是模拟乡村内留存的少年的口吻,不加道德渲染的刻画那个走向黄昏的少水沟,这让烧水沟系列避开了廉价的道德说教。荒腔走板的文字惹人发笑,也令人心中郁结。
纵观袁哲生的小说,以小孩子的视角代入的作品总是格外灵动,他笔下的小孩/少年,就像电影《一一》里那个拍别人看不到的部分的小孩子,具备一种天真的清醒。大概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大人们笑小孩子不懂事,小孩子因为这不懂事,才能看到和说出更多真实。也因此,袁哲生的小说很少世故气。
烧水沟就像“秀才的手表”这个书名一样,是一个混合了前现代与后现代、陈旧与崭新、迅速与凝滞的场域。 许多格格不入的事物集中在一个地方,违和却又充满现实感。仿佛我们脚下的中国,人工智能和求神拜佛共处一室,女权主义与生女不如男的观念同时存在。这种混合体,对局外人来说是奇观,对我们这些中国的子民,却是生活。于是,我们在阅读《秀才的手表》等小说时既感到陌生,也感到熟悉,恰如评论者李黎在《生不能生,死不能死》一文中所说:“所以《秀才的手表》一书,是作者关于何为真实世界的一种辩论写作,他要证明的是,‘烧水沟’这个地方以及相关的人物,是真实的,尤其是当他们被置放在一个巨大的版图之下时,他们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不能被一笔抹去。”
“烧水沟”是有真实感的,因为袁哲生用大量细节和诚挚的语言让我们愿意相信存在这么一个世界。“烧水沟”也是超现实的,所以秀才才会寄没有邮票的信,烧水沟才会有躲藏在钟表里的鬼,这只时计鬼可以让时钟变快变慢。也因此,当算命仙仔说这里要死一个人时,阿公和火炎仔突然抢着去死,结果,死的却是算命仙仔自己。
在虚构与非虚构、现实与超现实的结合中,袁哲生模仿一种稚气的口吻,娓娓道来烧水沟里人命的无常,那高于人的意志的存在,摆布着人间的一切,那些看似坚固的东西,在天数面前脆弱不堪。叙述上反差的感觉,内容中存在比人的意志更高的存在,使得袁哲生的小说不局限在传统的乡土书写中。
“烧水沟系列”充满了台湾方言点缀的活泼与戏谑,但即便在轻松自在的语言下,死亡仍然在故事里突然发生。比如《秀才的手表》里的秀才之死,突然之间,“我和阿公一起看见了秀才的大铁马歪歪扭扭地倒在铁道边的钭坡上,而秀才则在另一头,他的身上盖了一张大草蓆,只露出半截手臂在外面。 ”
这冷清、突兀的死,让我想起《寂寞的游戏》里孔兆年对死亡的想象。“我学孔兆年那样想象自己死了,变得轻飘飘了。我像电视上的航天员那样浮在半空中,轻轻地翻转僵硬、笨拙的身体,慢慢向前滑行,向无垠的黑暗慢慢游去……”在袁哲生笔下,死亡是是生活里的一点小荒诞。毕竟,“死亡就跟对发票一样,早晚会中奖的……”(袁哲生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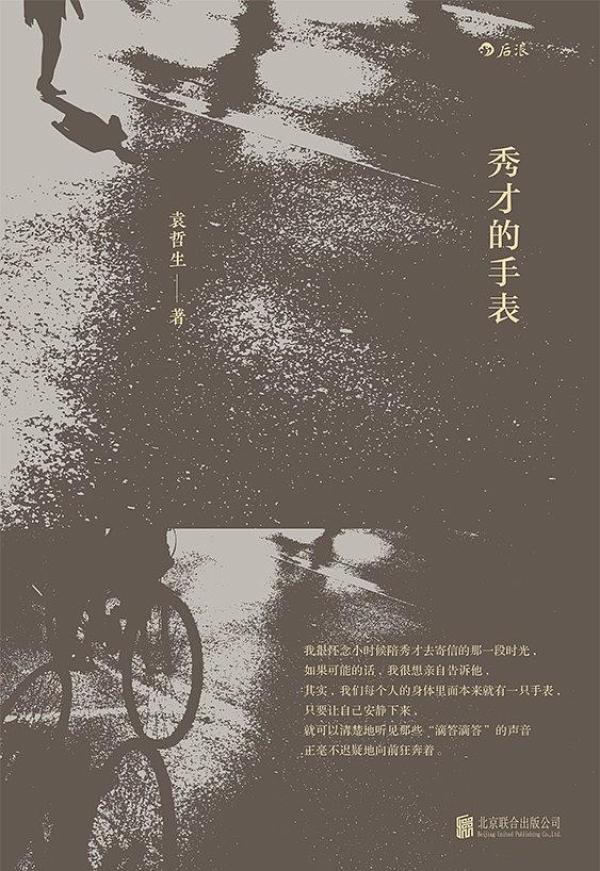
《秀才的手表》,袁哲生 著,后浪出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9月版
3. 袁哲生把孤独写到极致,那不是一种无病呻吟,而是相当一部分人无法回避的存在状态。归根究底,小说里的主人公与世界总是隔了一道墙,他们曾经尝试融入世界,但以无果告终。在袁哲生的小说中,自我和社会、人的自由意志和规范之间的撕扯,得到的多是一个沮丧的结局。于是,失意的人只能退回自己的梦。
中篇小说《雨》就是一篇关于孤独的暗语。在这个故事里,袁哲生唤起我们关于青春期的回忆,“我”在下雨天待在家里静静凝视窗外成为故事里最典型的意象,“我”在看什么?原来是邻家小女生梁羽玲的母亲吕秋美——一个嫁给退伍军人的年轻少妇。在她的身上,我们能看到英国作家伍尔夫代表作《达洛维夫人》的影子,还有基耶斯洛夫斯基导演动人的《爱情短片》,故事里的女性,都步入成熟,站在性与爱的激流中,却被干枯的生活所困住。她们面临着感性与理性、欲望与现实的冲突,在“遵循自我”还是“顾全他人”间徘徊。“过怎样的生活”,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雨、雾、玻璃窗、忽明忽暗的灯,都是人物内心的投射。在《雨》中,“我”之所以时时凝视窗外,留心吕秋美的生活,是因为“隐隐意识到吕秋美和自己一样留守在内心对爱情的深深渴望里”(袁哲生:《关于<猴子>),尽管“我”和吕秋美实际上缺少交往,但在共同的孤独中,“我”心中把她作为同类,一个亲切的对象。这种感觉,青春期的男孩感同身受。而小说最精彩的一笔就在结尾:吕秋美不再犹豫,为爱出走,“我”成为唯一的目击者,却心生怅然,梁羽玲回来后,“我”不知该如何告诉她妈妈出走的事实,最后脱口而出三个字:“下雨了”,尽管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午后。
《雨》是袁哲生小说美学臻于成熟的体现,也流露出他对生活的进一步思考。《雨》常有猝不及防的失落。像生活,陡然到转角。这篇小说不能快读,一字一句,都要留意,才能觉察字里行间节奏感的变化。譬如:上一段,“我”担心“像一滴水珠那样从天上摔下来”。下一段,“外边一个人都没有,我早就知道了”;上一句,“我回过头,母亲将手伸进我的胳肢窝,把我举起在半空中”。下一句,“这是母亲最后一次抱我”。这些句子让小说持续处于不安的边缘,也让读者替叙述者担心,油然而生怅惘和心疼。
《雨》里面一切欲求都是得不到解决的,人物的困境到结尾也没有释怀,只不过是走到下一个十字路口,或者以克制收束,这是袁哲生对乌托邦式希望的弃绝,也是他对人生的一种明白与宽忍。尽管知道生活中有无法解决的困境,依然去热爱值得热爱的部分。
《雨》的故事没有终结,“我”的青春暗流继续在另一个中篇《猴子》里涌动。《猴子》表面上是欢快轻松的青春恋语,然而,袁哲生要写的实是无法回避的“残酷”。“我”暗恋梁羽玲,却成为童党好友荣小强与梁羽玲间的传书者。梁羽玲以为能从荣小强那得到理想的爱情,却只是荣小强眼中一个证明自己能力的战利品。而这位在“我”心中美好的梁羽玲,在现实中,甘愿为了赚取五十元,在体育场的厕所以“烧完一支火柴的时间让男学生看下体”。残酷的是,“我”无法改变这一现实,为了获取瞬间的亲密感,反而加入了观看的行列。在黑暗中,伴随着燃起的火光,“我”和梁羽玲的一线之隔,恰似成年人对青春的回望,美好,却遥不可及。
梁羽玲的行为看似荒唐,但结合她的经历,并非不可理解。母亲出走,父亲一度想把她送给友人,家庭的失位与伤害,让她过早体会人间的残酷,也过早对罗曼蒂克失去信心。在朴野潮湿的岛屿边地,梁羽玲如一只春日空中的风筝,放逐,又渴望被什么牵引。所以,她误信了排球队的小太妹,错误理解了荣小强对她的态度,她的自轻自贱,令人差异,细思后却是体认的苍凉,而这些被敏感的“我”所理解,因之,知道真相后,“我”没有厌恶梁羽玲,仍试图接近(哪怕是卑微的方式)她。
生活的残酷在袁哲生的小说中时有出现,对于这些残酷,袁哲生没有选择正面强攻,而是用极为平静留白的手法叙述。情感本该激烈的段落,他用字简省,一般人煽情处理的戏码,他一笔带过。若读者不加留意,就会忽略雨中暗藏的难堪,唯有把留白的片段补全,仔细品味叙述者的口吻,小说的暗面才会徐徐展开。

《猴子·罗汉池》,袁哲生 著,后浪出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9月版
4. 如果说“猴子系列”系列代表了袁哲生的小说美学成就,“罗汉池系列”则体现出他对宗教与世俗的思索。袁哲生试图借助“罗汉池系列”表达的是:一个人在特定条件的激励下,会展现出他近乎神性的品质,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神性时刻,而那才是世间万物最美好的时刻。恰如童伟格所说:“在他(袁哲生)的笔下,众生皆低眉垂首而活,重压他们,使他们扼杀个人热望,放弃追求更可喜之生活的,毋宁是人世里的情感绊结。袁哲生表述了一种深情的退让:因为不忍离弃异亲者,人选择认命;而总在退让一刻,人对彼此,展现了近于神的质地。”
因为对生活的体悟,袁哲生不是一位单纯的感伤派作家,他的故事不是纯粹的青春梦话、恋人絮语。和爱丽丝·门罗一样,他精确地捕捉到日常生活中凝重的瞬间,勾勒出那些缠绕在我们心中的无法愈合的伤痕。他的小说没有波澜壮阔的大国盛景,没有血肉横飞的军队战争,也没有试图揭示一个时代的千钧气魄,但正因为解构了冠冕堂皇的启蒙、怀旧或抒情叙事,他的小说才更接近平凡生活的本来质感。
正因如此,无论是《猴子》、《罗汉池》还是《寂寞的游戏》,其实都是“反恋旧小说”。通常的恋旧小说,都会粉饰过去,作为对放下堕落的对照,譬如工业革命后出现的一系列乡土小说、童话小说,揭露象征当下的都市、机器的丑陋面,渲染象征过去的乡村生活的淳朴和美好。但在袁哲生的小说里,无论是童年还是村庄、庙宇,它们看似美好,实则都充满难堪,它们都不是痛苦的绝缘体,都有远大于甜蜜比重的残酷,所谓孤独,所谓艰难,并不是成年以后才有的东西,只不过是在我们一轮又一轮的成长中,记忆被不断筛选过滤,我们对过去的回望也平添了滤镜罢了。
袁哲生用文字建起一座童年乌托邦,那里没有主义,没有争斗,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处处提防,那里有童年往事,父亲垂下的背影,清风拂过的水塘,潮湿的雨季,捉迷藏的孩子,和一场场寂寞的游戏。童年的气息干净纯真,暗里却是少年对眼前万物即将变质的无力。他唯有用书写保留,遁入文学来对抗世俗的侵扰,文学是他回归岁月深处的方式,最终实现一种永恒的生活。
哲学家列维纳斯认为:当代文学在根本上从未摆脱对自身性和主体性的追问。在袁哲生的小说中,对自我与“我与他者”的关系的追问也从未停止。《密封罐子》里对人与人无法感同身受的处境;《雨》之中我对那位陌生少妇的隔空思慕;《猴子》里“我”和梁羽玲的一线之隔,还有《寂寞的游戏》中那些孤独的篇章,都显现出袁哲生对人活于世的困境的认知。在袁哲生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个体无法消弭的孤独,也看到人生如同一条半圆的线条,上升又下滑。但是,袁哲生的小说并不仅仅诉诸个体经验,在他小说中那些孤独的灵魂,也绝非闭锁自身,放弃与外界对话。某种程度上,小说中的这些人物,恰是在意识到自身的困境以及这种困境在人群中的普遍性后,才会他者产生真正地共情与理解,因之,这些原本沉默的个体,才有相互对话的可能。他们不求感同身受,求的只是一份理解与温暖。
小说家张大春吝啬赞美,却说袁哲生“撑起 21 世纪小说江山”,足见后者在他心中的分量。袁哲生是一位难得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有独特的生命美学,是真正稀有的文学力量。在“文学之外”因素日益介入文学的今天,这样真正的“纯文学”不多见。只可惜,他最终没有熬过现实的难关,同我们匆匆告别,朝岁月深处疾步离去。
在文学失落的时代,这样的结局令人遗憾。设想,凭借袁哲生在世时的造诣,他若是坚持写下去,假以时日,成就文学中的大师气候并非难事,可是,随着多年以前的那一场不辞而别,这一切假设都得不到验证。行文最后,笔者想起了袁哲生在悼念好友、小说家黄国峻时写下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就像一场壕沟激战之后的人员清点,不可避免地,我们即将在一面摧折的军旗后方,或是三、五公尺外的下一个散兵坑里,发现我们年轻、善良,然而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弟兄们。这一次,终于轮到我们这一连,这一班,这一伍来品尝这杯饯别的苦酒了。敬完这一杯酒,我们的队伍更加孤单了,更糟的是,未来,我们不知要使用多少次的沉默来面对失去弟兄的那格空白。沉默是战后的通行证。他们说你是自己选择离开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曾经长期埋伏壕沟之中的兵士来说,那样的解释仿佛也没有太多意义了,因为,激烈的肉搏战后,已经没有人说得清楚,到底我们的弟兄是因为别人或自己的子弹而倒下的。现在,我们只知道刚刚失去了一位弟兄,我们选择麻木,因为,在硝烟弥漫的浓雾里,悲伤,恐惧,怀疑,甚至思念都会令人软弱。国峻,相信你也体会过的,悼念战士的哭泣声,往往是在下一个偏远而宁静的壕沟里,才突然发出它哀哀的悲鸣的......暂时再见了,我敏感而善良的朋友。或许真如你说,我们应该发笑,好让上帝开始思考......”
(本文原题为《残酷之梦:袁哲生小说论》,首发于豆瓣网,略有删节)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