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乔治·斯坦纳:把批评作为文学去创造,并且敢于冒犯权威
乔治·斯坦纳去世的那一天,我并没有转发悼念新闻,而是重读他的《语言与沉默》。他是一位批评家,更是一位文体大师和人文主义者,他这辈子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批评作为一项文学艺术,而不只是小说等门类的附庸。他的批评就像雷蒙德·钱德勒写的侦探小说一样,抽丝剥茧,雄心勃勃,在不乏幽默睿智语言的同时,又流露出苍凉的叹息。
《语言与沉默》是一本容易写垮的书,因为斯坦纳面对的不是文学新人,而是荷马、莎士比亚、卡尔·马克思、君特·格拉斯、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经典作家。他们不只有诗人、小说家,也有剧作家、社会学家、媒介分析者这样传统文学批评不会照射的领域,斯坦纳玩心大发,要用一张网把他们容纳进自己的文学世界,可这也是棘手的麻烦,若不做到势均力敌,读者只会记住荷马、莎士比亚,而不会理会他乔治·斯坦纳,评论经典作家的书已经烂大街,鼓吹圣贤的陈词滥调连厕纸都嫌贵,斯坦纳有什么办法,能在旧瓶子里玩出新意?这是一本理论批评著作最大的挑战,而现在人们知道,斯坦纳不但完成了任务,而且极其出色,如今人们翻开这本书,首先想到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不走寻常路的批评家。

把一本批评著作写成文学作品,直到今天仍被阅读而不至于速朽,斯坦纳是怎么做到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对文学批评的定位。
关于文学批评,斯坦纳引用了一段诗人庞德的话:
“谈到《尤利西斯》的时候,庞德宣布,‘我们受制于语词,法律刻写于语词,文学是保持语词活力和精确的惟一方式。’利维斯补充说,只有批评才能担保文学完成任务。利维斯认为,批评是‘人文核心’(the central humanityiy),是技术、道德、社会价值的展览者和守卫者。”
斯坦纳把批评作为一种高贵的艺术,他没有低着头哈着腰佝偻着背去做批评,而是敢于冒犯权威,在写作中保持批评和被批评对象之间的平等。诸多文学批评的问题,是批评家害怕得罪权威,所以不敢痛下狠嘴,而是扭捏着身子,佯装圆滑,说一些看似有理实则不痛不痒的片汤话。这些批评很精巧,犹如学术论文一样规范,但在里面没有“人”,只有“术语”,没有“作者”,只有“主义”,读者不买账,因为它们不过是陈词滥调的拼贴,而非创新的艺术。
《语言与沉默》打破速朽的原因在于它重视腔调。读者阅读它,无论是辛辣点评还是笔锋婉转,都能感受到作者的诚恳、用心和他所经营的“腔调”。乔治·斯坦纳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古板的圈子内读物,而是像小说家一样练习自己的风格,把这种风格应用到批评实践中,这种乔治·斯坦纳风格,是一针见血和华丽掉书袋之间的结合,也是作者致力于以语言为基础来展开的文学议论。斯坦纳之所以重视语言,是因为语言乃是人类展开自己的交流乃至生活方式的源泉,语言不但决定着文学的质量,也深刻影响着一个社会主流的思考方式和意识形态。
在书中,斯坦纳敏锐地指出:“在我们时代,政治语言已经感染了晦涩和疯癫。再大的谎言都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再卑劣的残忍都能在历史主义的元词中找到借口。”他致力于辨析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指出文学与历史和政治的紧密联系,他破除了那类文学可以独善其身的想法,而是冷峻地告诉世人:沉默的引诱——认为艺术在某些现实情况下微不足道、无济于事―—也近在眼前,集中营的世界,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外,也是在语言的范围之外,如果要说出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会危害到语言的存在,因为语言本是人道和理性之真理的创造者和存载者。一种充溢着谎言和暴力的语言,不可能再有生命。”
斯坦纳格外关心奥斯维辛的历史,对纳粹的批评成为书中的一条隐线。他注意到纳粹等热衷于扩张的统治组织如何征用语言,通过对语言的改造,来加强民众对他们的信任。在回顾纳粹德国的统治时,斯坦纳说出了一个令人悲观的事实: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与此同时,一个人可以在高等学院接受启蒙主义教育,享受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启迪,但这不影响他面不改色地操控对“他者”的屠杀。
二十世纪的大屠杀,往往是理性进入到一个极端产物,看似是乌合之众和刽子手,背后却不乏哲学家、知识领袖的身影。理性训练可以让一个人更成熟,也可能让他变得更冷漠,对他者的生存困境更加无动于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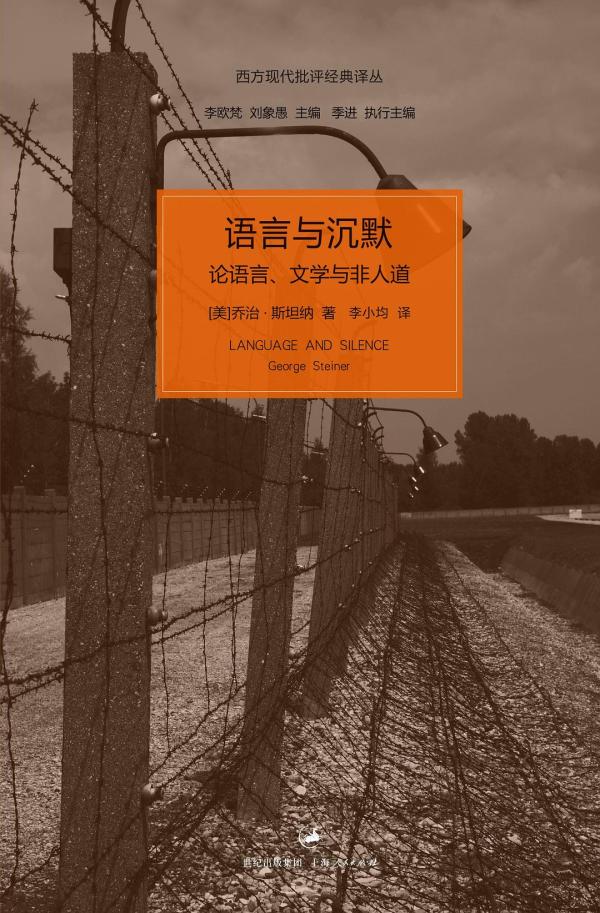
《语言与沉默》适合与另一本书对照来读,这本书是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从工具理性和官僚机构运作的角度分析了大屠杀“如何成为可能”。他首先梳理了犹太人流亡的历史和西方反犹主义的由来,指出由于宗教信仰和习俗的特殊性,犹太人长期处于“无民族的民族”状态,被污名、被驱逐,在欧洲的土地上只能作为“永恒的边际人”而存在。但是,鲍曼并不认为犹太人的特性是造成大屠杀的根源,他质疑两种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陈词滥调。一种是犹太人特殊论,即仅仅将此事作为针对犹太人的特殊事件;另一种是将其视为广泛社会现象的一个极端,并最终把责任归咎于几个政治强人身上。针对这两种观点,鲍曼提出质疑:“大屠杀究竟是现代性语境下一种极端性的失败现象,还是其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扉页上,鲍曼引用了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41年出版的《英格兰,你的英格兰》里的一段话:“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施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利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鲍曼全书论述的就是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的关系。大屠杀并不外在于现代文明,纳粹式的大屠杀就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现代文明缔造的科层制、发达官僚主义和先进技术,为大屠杀中大部分人的道德豁免提供了条件。鲍曼的论述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解释。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当时,阿伦特以《 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平庸之恶”的关键在于作恶者的无意识——他们不认为自己在作恶,而只是在完成任务或随波逐流。有时候,他们甚至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而参与到集体的恶行,阿伦特希望人们意识到,“平庸之恶”是一种更普遍的恶行,沉默和附庸并非道德的豁免权,当集体之恶发生时,沉默或者趋炎附势也在加剧恶行。
如今,奥斯维辛已成历史,但“平庸之恶”并未远去,在大量人群成为雇佣劳动力的社会背景下,“平庸之恶”的一种普遍反应是“打工者心态”带来的道德豁免。人们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常会以“我也没办法,这是我的工作”、“我也是被逼的”、“我只是打工的”为借口,来谋求道德中立的位置,使自己不受到良心的谴责。然而,斯坦纳和鲍曼在回顾二战历史时都发现,这种明哲保身的心理、自我安慰的语言恰恰是大屠杀里的雇佣人员的说辞。纳粹德国把迫害这一整体恶行,切割成一道道工序,每个工序由专人负责,他们没有全程参与到迫害中,但他们成为迫害流程的一分子,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不是最后的刽子手,手上没有沾染鲜血,但实际上,正是他们的举报、捉捕、虐待、拷打,乃至准备关于清洗的物品,一步步把受害者推向深渊。而在接受审讯时,他们的借口就是:“我也是被逼的……这是我的任务……”这就是现代性的屠杀,集体暴行被工具理性和程序化,那个所谓的恶,被推脱到虚无缥缈的集体,或者几个代表者身上,而大多数参与其中的人,因为逃避了追责,没有惩罚,也就无所谓深刻的忏悔。
针对这种明哲保身的心理,斯坦纳提出一个词叫“意识的孤岛化”。当一个人在一项活动中只把自己当做零部件,他只想完成任务、保全自己,而不再去思考基本的是非善恶,不关心他人遭受的残酷,他的意识将逐渐变得孤岛化,在孤岛化意识的指引下,人们倾向于思考“安全”,而不是思考“创造”,人们选择更保守的策略,而不是开放地去接纳不同的语言。
斯坦纳同时在《语言与沉默》中指出:“科学可能中立。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局限;正是这种局限学归根结底还是‘微不足道’。科学不可能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暴行根源何在。”有趣的是,这一说法同样与鲍曼不谋而合。他们在重审大屠杀时通往了同一条路,那就是对现代科学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当20世纪的科技革命带来人们对科学的崇拜时,他们却多次提醒科学和理性存在的局限。如果人们放弃是非善恶的判断,不加反思地拥抱技术和工具理性的神话,那么人们就只会是一个机械的人,而不是一个健全的、体察他人处境的善良人。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曾引用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暗示科学与理性并不能抓住人类的本质。《没有个性的人》是一本堪比卡夫卡《城堡》的巨作,书中的主人公乌尔里希是奥匈帝国筹备皇帝在位30周年庆典委员会的一个小小秘书,他努力进取,渴望出人头地,故事开始时的1913年8月,他32岁,正处于人生的迷茫期。他先后尝试过当军官、工程师和数学家,但都以失败告终。后来,主人公反省道:在一个整体的秩序中,自己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零部件,一个缺乏自由和自主的人,也即小说的标题所揭示的——他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而这正是现代文明科层制对很多人的塑造,阉割个性,量化量产,人们把听从指令、完成任务作为生活的第一要务。
穆齐尔写道:“今天……已经产生了一个无人的个性的世界,一个无经历者的经历的世界。”最终,主人公乌尔里希意识到:“对他来说,可能性比平庸的、死板的现实性更重要。”
鲍曼援引《没有个性的人》,是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勇于反抗平庸,重拾自我的个性,在技术理性之外,重新思考实践精神和人文主义。不要相信权威和技术告诉你的神话,而是从实践中解放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文学,都可以通过“细腻”、“共情”来给予读者生活的启示,而这也是对时下“文学无用论”的回应——文学并非无用,而是对工具理性的反抗。写作者很多时候像一个种下种子的人。文学不是最终实现理想的那一个,但文学往往是种下可能性的东西。因此,现如今热心于文学事业的人,不必气馁。身为作者,我们可能不是最后看到春天到来的人,但如果我们都自暴自弃,春天是永远不会到来的。一代人的理想在上一代人的交付之中生根发芽,如今,作者很大程度上完成的是交接棒的工作。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