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外祖母与“魔幻现实”
加西亚·马尔克斯出身于加勒比海地区。“香蕉大屠杀”事件后,当盖坦去进行调查,他遇到的一位重要调查对象,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外祖父的关系,远比我们一般能想象的亲密得多。
在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头就讲了,他第一次见到妈妈,是三岁时,三岁才认识自己的妈妈。那他又在什么时候认识他爸爸呢?那是七岁零九个月,他生命中第一次见到爸爸。

那么生命中没有了战争,会变成怎样?就变成了时间的停滞、无穷无尽的等待。当年他们在为政府打仗时,得到过来自政府的许诺——等他们退役后,会提供他们丰厚的退休金。那就是他们等待的对象。外祖父的老房子加上庄园,脱手卖了七千哥币,后来他们拿这笔钱搬到附近的大城,盖了一栋房子。加西亚·马尔克斯被哥伦比亚第二大报《观察家报》派去巴黎时,他一个月的薪水是五百块钱。而政府承诺要给他外祖父的退休金,是一万九千块钱。这样我们可以具体理解这是笔大钱。政府以这笔大钱为承诺,笼络他们卖命,但也正因为承诺的数额庞大,所以政府根本付不出来,甚至根本没打算付。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作之一,是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小说里的退役上校每个星期都去问:有没有信来?他所等的,就是通知他去领退休金的信。我们可以这样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他的生命明确分为两种时间,前一种是以各式各样的战争与死亡为标记的,后一种则是近乎停滞,被关锁在对退休金的漫长等待中。
有意思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母,有着和外祖父完全不一样的时间感。小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住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大房子里,同所有的小男孩一样,他很好动,爱乱跑,外祖母管他,叫他乖乖待在一个地方,他怎么可能听话?于是外祖母就会说:“你现在坐在这里不要动,千万不可以去那边,你如果去那边的话,会吵到你姨婆。”要不然就说:“你不能去那边,去那边会吵到你的大表哥。”这些人是谁?他们都是已经死了的人。外祖母不让他乱跑,理由是:活人不可以扰动死人。对外祖母来说,屋子里不只有活人,还有更多幽灵。
如果小加西亚·马尔克斯跌了一跤,外祖母就会说:“你看,不乖又被姨婆推了一把了吧?刚刚有没有看到姨婆啊?啊?我好像看到了。”走在街上,外祖母会指着空荡荡的街道对他说:“这条街你不能够乱跑,因为街上太拥挤了,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碰到哪个死掉的人,跟人家走到什么奇怪的地方去。”因为这样,原本顽皮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变乖了,哪里都不敢乱去。
我们无法追究,这到底是外祖母带小孩的一种策略,还是她真的相信、真的感觉到那些幽灵?大概两种成分都有吧。不论原因是什么,这样的环境在一个小孩,尤其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小孩心中,留下深刻、无法磨灭的印象。他活在一个充满幽灵的空间里,而且那些幽灵可不是恐怖片里的贞子,他们是有身份的,都是和他有关系的人,都是死掉了的亲人。那是空间中曾经活过的人的延续,不是莫名其妙外来的鬼。这是阿公的阿公,那是舅婆或阿公,都是和他有具体明确关系的。
这样的环境,背后必定有连带的信念——人不会真正死掉,或者说,人不会真正消失。人死了,不过是换成另外一种存在,而且随时可能会被唤醒,会被吵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小时候,就因而产生困惑。被某个姨婆推了一把跌倒了,他忍不住想:这个已经死了的姨婆,她变成了幽灵,那这个幽灵还会不会再死掉?如果幽灵死了,死掉的幽灵又会变成什么?死掉的幽灵会变成二度幽灵吗?那二度幽灵还会不会再死掉?
《百年孤独》就是建立在两种异质交错的时间意识上。一种是外祖父的时间,以死亡与永远等不到的东西标记出来的线性时间;另一种则是外祖母的时间,一种奇特幽灵存在的轮回。死掉的人变成了幽灵,幽灵再死掉,变成另外一度的幽灵,再死掉的幽灵变成……当你不相信人真的会死掉,你也就不可能相信幽灵会消失,对不对?人死了都还在,那幽灵为什么要消失,凭什么幽灵会消失?所以它就变成一种永恒存在,但是既然永恒存在而死亡又必然卡在那里,于是就只能是循环的存在形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小说里,不断试探着这两种时间彼此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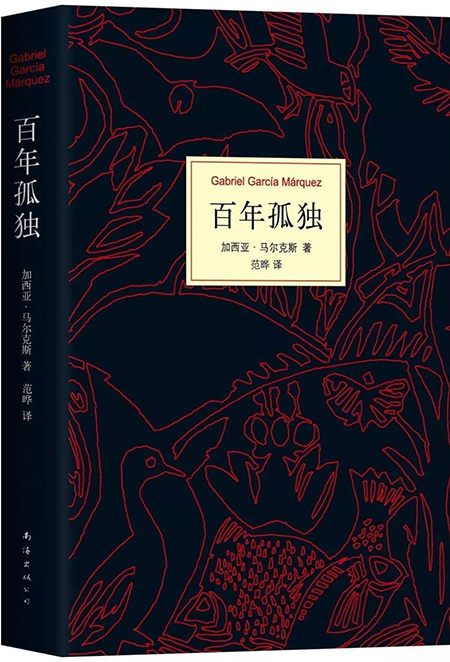
这本经典小说书名叫作《百年孤独》,一百年的长时间跨度,当然牵涉到历史。小说也真的碰触处理了哥伦比亚一个世纪间发生的事,不过这绝对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小说。除“百年”之外,小说还要写且更要写“孤独”。小说中表达“孤独”主题时最常用的手法,就是铺陈一种循环的时间感。事情一再地重现,换一个面貌再来一次,又来一次,不断循环,不断绕回原点。
每一件事情的叙述,几乎都是以布恩迪亚上校回想面对行刑队的情景为开端的。小说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面对行刑队,面对死亡的临界,到后来好像连那个临界划分,都在反复中变得模糊了,他活着,但同时他也死过很多很多次。
原本现实存在中绝对不可能重复的事——死亡,一个人只能死一次,死过一次就是完全、绝对地死了——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里面,却会一再重现,重新经验。而且不只是布恩迪亚上校,《百年孤独》里面有好多死了不止一次的角色。
如果加上《百年孤独》以外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其他小说,那么反复死亡的现象就更多了。例如他最早的短篇小说就写过没有办法死透的人。肉体已经死了,精神却不肯死,所以他很清楚感觉到自己被活埋,活埋也不会让他死掉,因为他原本就死了啊。接着他又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腐败,被身体腐败的气味弄得受不了,想要逃走,但逃不掉,都已经下葬的人能逃到哪里去。
后来在《枯枝败叶》里又有死了但是不能下葬的人,没办法将这个死人下葬,给周遭的活人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困扰。读过这部小说的一位朋友,就劝加西亚·马尔克斯去读古希腊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名作《安提戈涅》。那部戏的主轴就是安提戈涅决定违背禁令去为亲生兄弟收尸安葬。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接触古希腊悲剧的重要契机。
我们一般认为死亡就是生命的结束,也就是生命故事的结束。然而对于受到外祖母强烈影响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死亡往往是另一个生命故事的开始。这样一个由外祖母带大的小孩,他生命里面还有另一种特殊的东西——那就是外祖母众多迷信组构成的世界观。
外祖母相信,在空间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阴魂。小孩子躺着的时候,如果门前有出殡的队伍经过,要赶快叫小孩坐起来,以免小孩跟着门口的死人一起去了。要特别注意,不能让黑色的蝴蝶飞进家里,那样的话家里将会死人。如果飞来了金龟子,表示有客人来。不要让盐撒在地上,那样会带来厄运。如果听到“kingkingkongkong”的怪声,一种从来没有听过的声响,那就是巫婆进到家里了。如果闻到像温泉般的硫磺味,就是附近有妖怪。

这些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小时候生活教育的重要内容。他受的是加勒比海沿岸区而不是波哥大都会的教育,而且是那个地区一个没有经过西化理性冲击的老太太所给予的教育。她教的,是典型、传统的拉丁美洲世界观。这套世界观中,众多事物尚未经过理性处理分类,尤其是还没有分别出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那里残留着世界还没有被分化开来的一种概念、一种气氛,活人与死人没有绝对的界划,活人随时会变死人,死人会变成幽灵,而幽灵一直处在活人之中。这中间没有绝对的界线,那是一个连续而非断裂区隔的世界,那个世界没有必然不会存在的东西。
理性带来最大的影响是:训练我们相信什么东西一定不会发生。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的理性为什么逐步席卷了全世界?可能有人会回答:因为理性是对的,由理性产生的科学,比其他传统社会原本所相信的——例如巫术、宗教、神启等——都要来得灵验。
我们当然可以接受这样的解释。不过人类学家斯坦利·坦比亚(Stanley Tambiah)在他的名著《魔术、科学、宗教与理性的范围》中,提过另一种不同的解释。简单说,理性最大的诱惑,在于它能够提供其他知识形式、其他宗教信仰都无法提供的、最稳固的安全感——理性将许多事情清楚地排除出去,清楚主张那些事是不合理的,一定不会发生,所以人们连想都不必去想。
理性是什么?理性有着强烈的、近乎绝对的排除法则。有一天你按照理性了解了为什么二加二等于四,那么从那一天起,你就不必担心在什么状况下,二加二会突然等于五。那是不可能的。有一天你按照理性规则懂得了地心引力,从那一天起你就不必担心身边的东西,会突然飞到天空中消失,没有东西会往上飞,所有的东西都只能往下掉。
理性及其衍生的科学知识,帮我们排除了很多再也不需要去考虑的事。理性愈发达,我们的世界也就愈来愈小,面对这个世界需要做的准备也就愈来愈简单。我们活得愈来愈方便,愈来愈安全。不过当然相对地,这世界也变得愈来愈无聊。很多事情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已经排除了它们发生的可能性。这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现代社会“除魅化”的意义。没有什么现象、什么观念可以再魅惑我们了。
拉丁美洲的小说如此好看,恐怕很大程度上必须感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母。她给童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提供了如此广大的、未曾经历现代“除魅化”的、丰富且混乱的世界图像。
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外祖母那里承袭下来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规则,但这些规则都不是铁律,不是颠扑不破的。非理性或者该说前理性的世界中,最有趣的现象正是——所有的预言都是对的。怎么可能所有的预言都是对的?因为当现实没有依照预言发生时,人们总能够找到或发明另外一套规则来解释为什么该发生的没有发生。
例如说走在路上,我看到一片叶子以奇特的方式旋转落下。啊,这意味着明天有钱会进来,刚好有一个家伙欠我钱,于是我有充分理由预知明天他会还钱。到了第二天,他没有还。所以预言失灵、预兆错误了吧?不见得,因为我会想起来,还有一条规则,是关于日出时间的。如果那天日出时间早于五点半,那么原来会有的财运都要打折扣。查查日出时间,唉,果然早于五点半。
那个世界有各式各样的规则,管辖应该要发生的事。这些规则是平行并列的,东一条西一条,没有整合,也无法整合。因而全部规则加在一起,仍然无法告诉你什么事一定发生,什么事绝对不会。童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所有被拿来解释因果的规则,彼此都是平等的。
理性发达之后,科学就取得了高度的权威先行性,科学有比其他信念更高的地位,帮我们解释各种现象。科学以外的解释,就只能运用于科学无法充分解释的范围。然而在一个还未形成科学权威的世界,有着五花八门的道理,竞相提供着对事物现象的解释。每种解释听起来都蛮有道理的,都和现实经验有一定的对应,但也都有点怪怪的,无法和现实经验完全密合。因而在那个世界里,一旦有新鲜的现象冒出来,就会刺激高度的骚动。那样的新鲜事物是真正的新鲜,那样的兴奋是真正的兴奋,不只是这项事物我们没看过,而且它背后的道理我们也没想过。更重要的是,任何新鲜事物加进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都要因此改变其解释架构。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忆和小说中,都出现过这样的情景——一场巨大的蝗灾过去了,村民们为了让自己从巨大的灾难中苏醒过来,就办了一场狂欢节。附近村镇的人都来参加,狂欢节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吉卜赛人。不晓得从哪里得知消息的吉卜赛人带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出现了。
吉卜赛人卖一种“马古阿鸟粉”,那是专门对付不顺从的女人的,如果家里的女人不听话,很凶很坏,就把这个“马古阿鸟粉”带回家去。吉卜赛人卖一种看上去像果子般的东西,卖的人说那是“野鹿眼”,抓到野生的鹿,把它的眼睛摘下来可以用来止血。吉卜赛人卖四瓣干切柠檬,说是可以用来逃避妖术。吉卜赛人卖“圣波洛尼亚大牙”,那是一种看起来像牙齿的东西,其特殊的、明确的用途,是帮助人掷骰子时掷出较好的点数。吉卜赛人卖风干的狐狸骸骨,记得种田时要带着,可以帮助农作物成长。如果你要去跟人家打架,或者是去参加摔角,吉卜赛人会卖你另外一种东西——贴在十字架上的死婴。晚上走路时,想要避免碰到不认识的幽灵,那你就应该跟吉卜赛人买蝙蝠血。
吉卜赛人带来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总体来说,他们在狂欢节上真正卖的是藏在所有这些平常看不到碰不到的物件背后的、一种对世界的解释。解释世界当中的特殊因果,什么样的东西会制造什么,什么样的因会产生什么样的果。真正吸引人的,是那些不寻常的因果环节。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事,很容易以“迷信”一笔带过,或者对这些江湖郎中、江湖术士嗤之以鼻。然而江湖郎中、江湖术士在那样的社会里绝对是重要的,他们在不断提供、发明关于世界的种种解释。
当然有些人在解释世界方面,拥有比郎中、术士高一点的权威。例如神父,神父说这个世界是由天主造的,是天主管辖的。然而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成长的环境里,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传统中,甚至连神父、传教士用来说服人们相信其解释时的手法,都沾染了浓厚的江湖郎中、江湖术士的色彩。他们用来说服一般人相信天主的手段,不是读《圣经》,不是做弥撒,更不可能是教义问答。要让所有人相信天主,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展示奇迹。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会极度强调奇迹的重要性,教会中的神父因而也就具备了许多创造奇迹的本事。
拉丁美洲的狂欢节中,走在最前面的通常是十字架。跟在十字架后面的,是可以当场表演奇迹的神父。他们可以在众人面前让自己腾空飞起。“来,告诉我有谁敢不相信天主吗?不相信天主的,请看这里,眼睛不要转啊,小朋友,你敢不相信天主?那就看着啊,我飞给你看!”这简直就和路边的魔术师没有两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小时候就曾被这样表演奇迹的神父吓到过。
外祖母认为小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够笃信天主,就带他去找一个神父。那个神父对小男孩说:“眼睛瞪着我,看着我,不要动,看着我的脚。”然后他的脚就离地,人飞起来。目睹这一幕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此害怕天主,怕得不得了。每一个神父都有自己的把戏,有各种不同的玩法。例如要人先盯着十字架看,然后呢,闭上眼睛,再马上将眼睛张开,就看到原本干干净净的十字架上,突然有一道血流淌下来。
在某种程度上,神父和吉卜赛人是同一种人。他们都是用“壮观的表演”(spectacular performance)说服大家接受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接受他们解释世界的权力。这样的做法,过去曾经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然而奇异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当理性已经如此巨大,已经战胜、征服了那么多地方,竟然还有如此素朴的现象存留着,管辖着众多人口的生活样态。
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能充分理解,为什么《百年孤独》会如此开头: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里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接下来,最重要的这段话说:
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每年三月前后,一家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都会来到村边扎下帐篷,击鼓鸣笛,在喧闹欢腾中介绍新近的发明。
吉卜赛人带来的两大块磁铁好玩得不得了,老布恩迪亚看到那大磁铁,冒出了念头,想要用它们把地里的黄金吸上来。结果没能吸出黄金,他又拿磁铁去换了别的东西。
《百年孤独》要写的,是回归到理性横扫全球之前的一种状态,一种还没有完全被理性整理解释的状态。加西亚·马尔克斯要去逼视并描述那样的状态。这是一项英勇的尝试,因为难度极高。比较容易的当然是接受已有的解释,别人给我们且已经有很多人相信、接受的解释。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走这样容易的路,他要用文字带读者回到没有明确答案,依然充满不安全感,感觉上几乎所有事情都还有可能发生的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气氛,告诉读者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气氛中,发生了什么。
这是《百年孤独》的起点,也是“魔幻写实”的起点,更是使得“魔幻写实”与《百年孤独》能够横扫西方文坛的起点。什么是“魔幻写实”?“看起来真实的魔幻景象”。没错,但这样说只是把四个字拆开来讲而已。应该要强调的重点是:“魔幻写实”必须建立在感受或信念的基础上,也就是人要愿意或被诱惑回到那个状态中,接受《百年孤独》的这个开端——“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这是最关键的。
“魔幻写实”由拉丁美洲开始,借着像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小说家的优秀作品,流传到拉美以外的地区,引来了众多的模仿者与模仿作品。当全世界都在写“魔幻写实”小说时,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拉丁美洲的“原汁原味”毕竟是不一样的。其他地方的模仿者,始终没有办法让自己进入那个魔幻世界里,真正感觉到“经过屋内转角,很有可能就会碰到死去了的姨婆”。其他地方的作者没办法让自己“返祖”到接受那些非理性、违背理性的事真的会发生且真的发生了,而不只是存在于人的自主或不自主的幻想幻觉里。其他地方的作者写不出那样一个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缺乏理性保护的、极度不安全的世界。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成长背景当然很重要。那个背景环境有许多和我们很不一样的条件,把他拉进那不安全的存在中,又帮助他度过不安,不至于发疯。例如理性化的社会中,文学不太会和妓院扯上关系,但是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写作里,妓院作为一个社会机构,也作为一个生命主题,却不断反复出现。年轻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真的曾经长期住在妓院里。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他写过一个令人难忘的老鸨,她引诱了一群年轻人到她的妓院去。她看待这些年轻人,一方面是顾客,一方面又是孩子。让年轻人在妓院里胡搞了一阵子后,她会关心地问他们:“功课做了没?饭吃了没?这两颗维他命给我吃下去。”这是很奇怪的关系,难以理解,却又那么具有说服力。
本文摘自《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杨照/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19年12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