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吗?
Nick Chater 利维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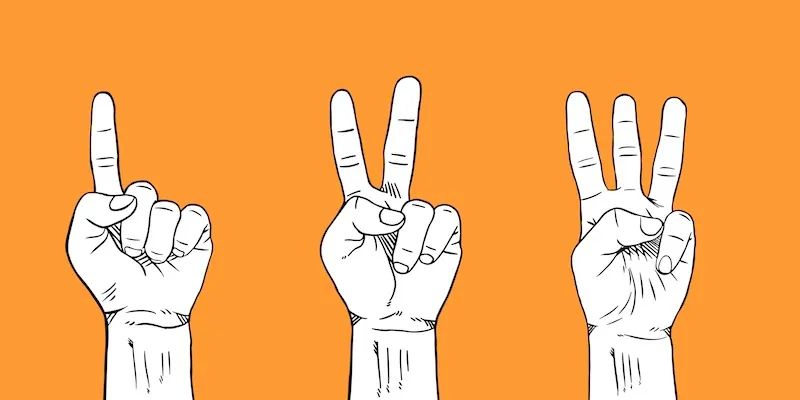
利维坦按:
谁都无法否认规则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到如今水平的重要因素——就像拔河,只有劲往一个方向使,才能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但与之相矛盾的是,每个时代每个地区的几乎每个个体,都在渴求自由。
卢梭曾写道: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种矛盾感在弗里特约夫·博格曼的《自由论》中被进一步展开并加以阐述)。如果你也认为规则是团体中的大多数人所达成的契约,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生下来就被要求遵守这样一个由前人和他人所制定的契约——每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教育不能穿着裤子拉屎。规则的强制性在逻辑上可能会令人反感,因为规则是横阻于你与更大程度自由之间的那道水沟,因为规则的存在,你的自由具备了边界。但另一方面,萨特认为我们都在试图“逃离自由”,因为我们发觉自由太过痛苦。因此,你真的需要更大程度的自由吗?换言之,你究竟需要多大程度的自由?
也许更关键的并不是所掌握的自由的多少,而是保有追求自由的权利。
“我现在快30岁,感觉自己正越来越被规则所束缚。从扶手电梯上无穷无尽的标志告诉我‘站在右边’,公共场合里‘禁止滑板’,到一切不成文的社会规则,比如人们期待我具有定所,买房,拥有家庭。我们真的需要这些规则吗?为什么我要遵守规则,如果人们全都无视规则又会发生什么?”28岁来自伦敦的威尔说。
我们都能感受到规则压迫性的存在,无论是成文或不成文的——这几乎就是一条生活规则。公共空间、组织机构、晚宴,甚至人和人的关系以及随意的谈话,都被似乎能规定我们每个行动的规则和繁文缛节充斥着。我们抱怨规则冒犯了个人自由,并声称规则就是“生来被打破的”。
但是作为一名行为科学家,我相信一般的规则、规范和习惯并不是问题——没有正当理由的规则才是。其中棘手但重要的一点正在于如何建立二者之间的区别。
让我们先想象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除了我们的身体遵循的那些非常严格而复杂的生物学法则——没有这些规律我们都活不了——我书写的每个单词也遵循英语的规则。在拜伦式的艺术个人主义时代,我可能会做梦一样去想象把自己从语言规则中解放出来。但是这种新的语言学自由真的存在什么好处,或者真能解放我的思想吗?
一些作品——比如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诗《Jabberwocky》——成功在文学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译者注:Jabberwocky全篇都由无意义的英文单词构成)。但是总体而言,打破语言的规则并不会让人感到无拘无束,反而更像是语无伦次。
拜伦在他的一生中因破坏规则而声名狼藉,但他同时也对韵脚和格律极为坚持。比如在他的诗歌《当初我们俩分别》(When We Two Parted)中,拜伦描述了一场禁忌之爱,一场打破规则的爱,但他仍然严格遵守了一些成熟的诗歌定律。许多人会说,这让他的诗更富有力量了。
In secret we met
In silence I grieve,
That thy heart could forget,
Thy spirit deceive.
If I should meet thee
After long years,
How should I greet thee?--
With silence and tears.
你我秘密地相会,
我又默默地悲伤,
你竟然把我欺骗,
你的心终于遗忘。
如果很多年以后,
我们又偶然会面,
我将要怎样招呼你?
只有含着泪,默默无言。
(注:穆旦译,来源网络)
再想想作为运动、游戏和猜谜之根本的规则——即使这些活动本应该只是为了娱乐。打个比方,国际象棋的规则在以下情形中会触发小情绪:如果我想用王车易位避免被将军,但规则说我不可以;或者当我发现你的兵走到了我这边,吃掉了后、车、马或象。与之相似,让我们试着找出一个从没有因为越位规则而狂怒的足球迷吧。
没有规则的国际象棋或足球就不再是国际象棋和足球——二者变成了完全不具备形式和意义的活动。实际上,没有规则的游戏就不再是游戏。

许多日常生活中的规范恰恰扮演着与游戏规则相同的功能——它告诉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说“请”和“谢谢”的传统在年幼的孩子看来让人厌烦,这些规范也确实没什么道理——但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传统,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大家就传统的内容达成了共识——人们的社交沟通才更顺畅。
靠左或右行驶,红灯禁行,排队,不乱扔垃圾,捡起宠物的排泄物,这些规则都属于同一类别。它们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石。
当然,有些人一直想追求一个不那么形式化的社会,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一个个人自由优先的世界:这即是无政府状态。
规则往往不受人控制地诞生于双方自愿的社会和经济交往中产生的需求。
但是,无政府问题的状态在于它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人类会持续、自发地产生新的规则,用以来规范行为、沟通和经济交流,而旧规则的分崩离析就和新规则诞生得一样快。
几十年前,书面语中的代词一般都是阳性的:he/him/his。这一规则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推翻了,这么做也是正确的。但是取而代之的不是规则的完全消失,而是一套不同的、更广泛的规则,用以规定人们如何使用代名词。
或者让我们重新回到运动上来。一场比赛可能开始于踢着猪屁股,让它从村子一端跑到另一端,没有成型的队伍,还可能伴随着暴力。但是几个世纪之后,这场比赛最终会产生一大本复杂的规则手册,指导游戏的每一个细节。我们甚至会创造国际理事机构来监督规则的执行。

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于2009年和他人共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现,当人们集体管理土地、鱼塘、灌溉用水等共享资源时,也会出现自发建立规则的现象。
比如,她发现人们会就以下问题共同建立规则:一个人可以在何时何地,同时放牧多少只牛;一个人可以获得多少水,当资源紧缺时应该怎么做;谁来管理谁,有什么规则解决争端。这些规则并不只是由规则制定者发明并由上至下的实施——相反,规则往往不受人控制地诞生于双方自愿的社会和经济交往中产生的需求。
想要推翻僵化、不公平或毫无意义的规则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或者没有想要坚持某些规则的倾向,社会将很快陷入混乱之中。确实,许多社会科学家正是把人类创造、坚持和实施规则的倾向视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础。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5014575_The_Logic_of_Appropriateness)
尽管我们抗议不要规则,但规则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于人类的DNA之中。
我们和规则的关系确实看上去是人类独有的。当然,许多动物的行为都是高度仪式化的。比如不同种类的极乐鸟都会有奇异而复杂的求偶舞蹈行为。但这些行为模式是它们的基因所固有的,并不是几代前的鸟儿发明的。此外,虽然人类通过惩罚违反规则的行为来建立和维护规则,但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并非如此。黑猩猩可能会在它们的食物被偷时进行回击,但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们一般不会就偷食物的行为施行惩罚,即使受害者是它们的近亲。
(www.pnas.org/content/109/37/14824)
在人类身上,规则也很早就站稳了脚跟。实验表明,孩子们到三岁时完全可以学会任意的游戏规则。不仅如此,当由实验者操控的“木偶”出现并开始触犯规则时,孩子们会批评这个木偶,抗议说“你这样做错了!”。他们甚至会尝试教木偶如何做得更好。
(www.eva.mpg.de/psycho/staff/tomas/pdf/rakoczyNorms.pdf)
诚然,尽管我们抗议不要规则,但规则似乎已经根深蒂固于人类的DNA中。事实上,人类遵守和执行任意规则的能力对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功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从头开始为每条规则辩护(为什么我们在一些国家靠左行驶,在另一些国家靠右行驶;为什么我们说请和谢谢),大脑就会陷入停顿。相反,人们能够不用问太多问题就能学习极其复杂的语言和社会规范体系——我们只是要掌握“我们在这里做事的方式”。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65079/)

但是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这其中隐含着暴政。人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想要强制实施一些有时令人感到压抑的行为模式,包括拼写正确,没有滞留介词,没有分裂的不定式,在教堂里脱帽,唱国歌时起立——无论这些规则的理由是什么。虽然从“我们都这样做”到“我们都应该这样做”的转化是众所周知的伦理谬误,但这种谬误深深地植根于人类心理之中。
(psycnet.apa.org/record/2016-38724-006)
这样做的危险之一在于规则可能会形成自己的势头:人们可能会对随意的着装规则、饮食限制或对待圣物的正确方式变得如此狂热,以至于他们可能会采取最极端的惩罚来维护这些规则。
政治思想家和宗教狂热分子经常进行这样的报复,但专制国家、欺凌人的老板和胁迫性的合作伙伴也会这么做:规则必须遵守,因为它们就是规则。
规则,就如同良好的治安,它依赖于我们的同意。
不仅如此,批评规则或执行规则不力(例如,不让人们关注穿着不合适的人)本身就成了一种需要惩罚的违规行为。
这就是“规则蔓延”:规则只需不断地增加和扩展,我们的个人自由就会日益受到限制。计划限制、安全法规和风险评估似乎可以无休止地积累,其范围可能远远超出任何最初的目的。
对翻修古建筑的限制可能过于严格,使得任何翻新都不可行,最后导致建筑倒塌;对新林地的环境评估可能太严苛,导致几乎不可能再植树;对发明新药物的监管可能过分严厉,导致一种可能有价值的药物被放弃。通往地狱的道路不仅仅是用善意铺设的,还伴随着执行这些善意的规则,无论其后果如何。

个人和社会都面临着持续不断的规则之争,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其目的。因此,在自动扶梯上“站在右边”可能会加快每个人的通勤速度,但要小心那些对所有人都没有明显好处的惯例,特别是那些带有歧视、惩罚和谴责的惯例。
规则,就如同良好的治安,它依赖于我们的同意。而那些没有得到我们同意的规则可能会成为暴政的工具(编者注:卡尔·波普尔认为“……多数人永远是对的——不能被视为民主的原则,‘大多数表决’还是可能会犯下最为严重的错误,投票的结果甚至还会引进专制统治……希特勒在奥地利就席卷了90%以上的选票。”)。因此,也许最好的建议是遵守大多数规则,但永远要问为什么。
文/Nick Chater
译/火龙果
校对/Carlyle
原文/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00220-could-we-live-in-a-world-without-rule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火龙果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原标题:《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吗?》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