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除了“她”,谁都不能说生育是件理所当然的事 | 成为母亲
原创 苏惟楚 偶尔治愈


躲在卫生间里的女人,灯光从头顶照下来,头凑在那根试纸上看了又看,「两道杠」。
仿佛一场考试的信号,有人会因此欢呼,有人措手不及,但不管怎样,铃敲响了。
你要去医院建档,定期做检查,数值「是否漂亮」,医生的眉毛抬高了几度,都成为你了解成绩的风向标。你要开始研究合理膳食、进行运动管理、学习一切与孕期相关的知识。
这些是你要成为一个「好妈妈」的「必备之事」。
直到诞下一个孩子,你交卷了。
周围的人赞美你,恭喜你成功到达河流彼岸。但身体数据,医生还有你自己都清楚,一路上,你跌跌撞撞穿过多少「暗礁」 —— 每一次产检伴生的焦虑、身材变形带来的失控与自卑、激素对情绪的冲撞、可能出现的妊娠期并发症、产床上疼痛加剧与尊严丧失。
很快,你发现,生产并不是终点,它是下一场考试的开始。
穿过生育的河流,转身回看,「母亲」,也许并不是一种本能,或者一种自然现象。
今天是母亲节,这是偶尔治愈「成为母亲」系列策划的终篇。
两道杠
一萌的生育焦虑是从 28 岁开始的。逼近的 30 岁好像成为一个门槛,离门槛越近,周围人「催生」的音量就越大。
「女性的黄金生育期就那么几年,你错过去,之后身体和精力都没有办法再负担一个孩子,就太可惜了」。
于是,一萌的身体像被放在聚光灯下,遭到无尽的审视和打量。
「你穿一件宽松的衣服,别人会来问是不是怀孕了,别人看这么久你肚子还没有起来,就来问你怎么还没有怀孕」。
她心里不舒服,但又觉得对方是「为自己好」,只能笑着回应,「现在还不想生」。
其实,一萌已经开始备孕。
2018 年,她去做了孕前检查,开始吃叶酸,以及各类复合维生素,拔了两颗智齿。她还想生一个「猪宝宝」,如果是 9 月前就最好了,这样不耽误孩子以后入学。
备孕了半年,妈妈偷偷问不见动静的一萌,「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去检查一下吧」。她气愤地甩开妈妈的手,「检查了,好着呢!」
一萌的丈夫也开始着急,「我原来没那么想要孩子,结婚才一年,好像大家都在提,那就要吧,但没有怀上。检查不是她的问题,那是不是有可能是我的问题?我又觉得不应该啊。不敢想,太伤自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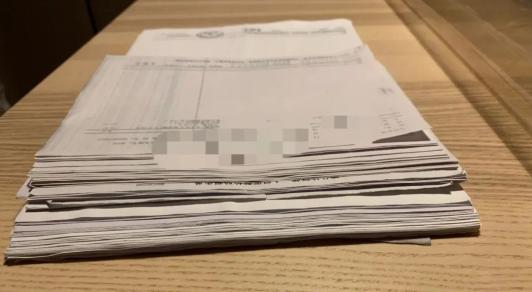
图源:受访者供图
「我真的想要一个小孩吗?」一萌问自己,答案好像并不是百分百,更多是觉得「年龄到了」。而且「等我到了 35 岁,两人想要孩子,我生不出来了,到时候怎么办?会不会有矛盾?」
在中国,很多时候,生育和婚姻被紧紧捆绑。
房玉英是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心理科的负责人,走进她诊室的,大多是遭遇生育障碍的女性们,很多人开口的第一句是,「医生,我这次(试管婴儿)要再不成功,老公就要和我离婚了」。
最严重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女人上午检查出了试管婴儿再次失败,下午丈夫就拉着她,去民政局办离婚。给房玉英打电话时,女人一只脚已经伸出了窗户。
对于希望怀孕的女性来说,月经、早孕试纸的「两道杠」、医院给出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 )浓度数值,被赋予了诸多意义。
每月月经前,是一萌和丈夫最紧张的时刻,月经来了,考试就算「失败」,下个月再来,直到「通关」。
在一萌差不多同一时间,36 岁的沈甜也在等待她的第一次试管婴儿成绩。
移植两颗胚胎之后的第 10 天,她发现自己下身出血,医生告诉她,可能是受精卵着床,也可能是失败了。沈甜买了一根早孕试纸,一道很深的杠,另一道杠「若有若无」。

图源:受访者供图
「五分钟看一下,十分钟看一下,试纸还是没有变化」,她发图片给护士和朋友。
「你看,这不是有吗?」护士小姐在图上标了一个圈发回给她。
三天后,沈甜去医院抽血检查,报告上的数据告诉她,「通关了」。
如果孩子不健康,我会恨死自己
怀孕到生产,一萌换了两个医院,三个医生。
她在西部的一个三四线城市,能供她自由选择的余地并不太多。
孕早期时,一萌第一个产科医生告诉她,「孩子着床晚,可能发育不好」,给她开了保健品,「不能刷社保卡,只能现金买,后来还接到许多推销产品的电话」。
一萌开始不信任这个医生,她在线上寻找医生问诊,一个北京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她,「可以先观察,不需要吃药」。
她又换了个男大夫,上海来的。「大夫经验很足,我俩坐在诊室里,谁都没把谁当成异性,我就是他的病人,他是我的大夫,我信任他,他在帮助我。」
但每一个数值变化,都会让一萌紧张,从孕 6 周开始,她就在一个 App 上建档管理,提醒自己孕期必做的事情,包括记录每一次体重数值。
沈甜的情况比一萌还要复杂。
她在怀孕期间患有妊娠并发症,甲亢和妊娠期糖尿病。
有报告显示,未经治疗的重度甲状腺功能可能导致母亲出现心脏问题或者「子痫前期」疾病;存在早产临产或自然流产的风险。而妊娠期糖尿病则令巨大儿发生率明显增高。

图源:受访者供图
医院按照「妊娠风险五色」进行建档,妊娠高危因素划分为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和紫色。因为甲状腺功能亢进,她从「黄花一下跳到了橙花」。
每天早起测血糖,如果餐后血糖数值超过标准数值 0.1 ,沈甜就开始紧张,告诉自己,「那口包子你不能吃了,下一顿多吃点青菜,那口牛肉也不能吃了」。一次检查数据里,沈甜发现自己的促甲状腺素下降了 0.02 ,她放弃 12 元一次的普通挂号,转向 100 元一次的特需。
「我是觉得我要尽一些努力让孩子保住,我要把他平安健康地生下来。」

图源:受访者供图
沈甜怀孕第 25 周时,做了一个胎儿心超。
「我不太会读片子,但医生说可能是『室缺』,建议我做羊水穿刺排除。但做羊水穿刺是有流产风险的,我又觉得不能冒这个险。而且『室缺』后天是可以做手术的」。
但她为可能给孩子带来潜在的风险感到愧疚,「我是不是接触了不好的物质?吃了不好的东西?但我翻遍了,发现我没有,当然,后来的结果也证明,孩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我那时候就是紧张」。
39 周到 41 周的时候,一萌被医生要求定期去医院测胎心,「可能孩子有点大,怕缺氧」。那时候是夏天,天很热,医生只有上午才坐诊,一萌必须早一些起床,坐丈夫的车去医院。
「有过特别不想去的时候,太辛苦了,那时候肚子太大了,我连睡觉都没睡过整觉,腰也很难受,但又想,这是你的孩子,你得保证 TA 的健康,如果因为有一点点没做到导致了什么后果,那就是不称职吧」。
在互联网上,「要不要陪妻子去产检」「要不要让丈夫陪同去产检」,诸如此类的问题充满争议。不少怀孕的女性们提出,「这是丈夫应该做的」。
一萌的丈夫对这样的说法有些抵触,「我愿意去,是我自己的态度,但如果很强硬地说,这是『你的义务』,感觉自己有点被道德绑架」。
他试想自己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如何跟丈夫沟通这件事,「一起去,我们可以一起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的事情,多好」。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永远无法感同身受「怀孕」这件事。
分娩:不只是疼痛
临产前,一萌问丈夫,「保大还是保小,你保我行吗?」
「肯定保你啊。」丈夫说。
为了「无痛分娩」,一萌又换了一个医院,但不幸,她先「见红」了,在医院经历了一天一夜,发现羊水已经被污染。
她躺在床上,医生把手探进去,「把羊水抠出来,看一下污染」,她疼得叫出声,医生说,「就这程度你还想顺产呢」。

图源:受访者供图
一萌形容,这种痛跟阵痛不一样,「阵痛是敲打肚子,但屏住呼吸,就能缓解,一会就停了」,但是这种内检是「医生把整个手伸进去,在肚子里面掏,像掏内脏一样」。
「疼痛覆盖了你的所有感官,而且特别没有尊严」。
来往的医生和护士,时不时重复「抠羊水」的动作,一萌「模模糊糊记得快十次」。之后再有医生进来,还没动作,一萌的腿就开始发抖,「条件反射」。
她觉得自己像一块没有灵魂的肉,又像一个没有痛感的机器,躺在那里,「谁都可以来操作一下」。
因为羊水被污染,孩子生不下来,一萌只能剖腹产。生产后,护士按压她的肚子,说是「排恶露」,她「嗷」得叫出声,像被一把大锤压扁了。母亲想把孩子第一时间抱过来,给一萌看,但她眼睛都睁不开,摆摆手,有点抗拒。
「太疼了,身体每一个部位都疼,我已经没有精力处理其他的事情,而且之前查资料,说哺乳也很疼,我不想再疼了」。生产后的两天,一萌都没有抱孩子。
和一萌一样,沈甜也是剖腹产。
沈甜在孩子出生那一刻,开始掉眼泪。她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使然,似乎是期待已久,爱意翻涌上来。
孩子在她肚子里太久了,拖到第 40 周 +3 天,她住进医院的 VIP 病房,和丈夫听着外面其他产妇撕心裂肺地叫,夫妻俩「睡得呼呼的」,「孩子一直不发动」。
羊水破了一天之后,孩子还是生不出来,医生建议沈甜剖腹产。
孩子被取出的过程并不煎熬,因为打了麻药,但沈甜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她在产前得了蜂窝组织炎,一种常见的皮肤感染,和剖腹产的刀口重合,导致刀口愈合很慢。

图源:受访者供图
生产后七天,医生帮她清创,发现刀口确实没有长好,医生「把周围的一些腐肉扒掉」,沈甜眼泪一直没停。别人的刀口长好要7天,沈甜花了70天,没办法抱小孩,去厕所,都是艰难挪动蹭着去。
和沈甜和一萌不同,对于其他选择顺产的女性来说,分娩过程中会阴会遭遇被拉伸或撕裂的风险,而会阴切开术更会加剧这种不适 —— 产妇们可能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被剪刀剪开会阴。
生产的风险更不必多说。数据统计,大约 2% 的分娩会发生大出血,这大多数发生在过长时间的分娩、多次分娩或子宫感染后。产后出血是产妇死亡的第三大常见原因。在国家卫健委 2019 发布的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18.3/10 万。
这意味着,大约每 5400 个女性怀孕,就有一个因为孕产而死亡。
分娩过程出现的产后子宫感染、剖宫产切口感染和肾脏感染,以及逐渐被更多人知道的产后抑郁,则是更广泛地存在。
生育不是终点,是起点
「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人区分开,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于是女性对于存在的意义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蕾切尔·卡斯克在《成为母亲》一书中这样写道。
一萌觉得自己好像不再是一个「女人」,她失去了自己的性别属性,「只是一个妈」。
乳房对于她而言,本来是带着一些隐晦色彩的,但给孩子哺乳之后,好像就只是一个「功能器官」,她失去了自己的隐私,妈妈和婆婆时不时伸过头看一看,「喂得好不好」。
与此同时,她回到岗位之后,发现自己走进了职业的窄巷。
她在公职单位上班,怀孕期间仍然要加班,那时,她的考核永远是单位前列。但生产之后,她变得「很闲」。领导跟人事部门反应,说部门缺人手,人事说,你们年轻人很多啊,点到了一萌的名字。领导回应说,「她孩子太小,好多工作没办法安排,等孩子两岁以后吧」。
单位年底评优,一萌和另一个同事同样的票数,但只能推选一个,按照流程应该重新投票,但领导告诉她,你休产假了,就不要参加了,让给他吧。
「我从来不觉得,我和男同事会因为性别不一样就会做不同的工作,但都一样有了小孩,只有我这样。我们犯了一样的错误,别人就会说我『一孕傻三年』,这是一种侮辱」。

沈甜也陷入了育儿的困境中。
她很爱这个孩子,但也会因为无法平衡工作和孩子的事情陷入暴躁。尤其在半夜喂奶的时候,「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她会委屈。
她清楚,这是一个人无法解决的事情,但很多时候,又好像只有她一个人在面对这些。
「我只能跟自己打气,这是你的选择,这是你的孩子,你要对他负责」。
育儿从来都不只是女性单方面的事情。
章珏是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的父亲,他的困惑比妻子还多,没有一本指南教导他具体在妻子的孕期和分娩时做什么,妻子看的书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章珏很难体会到那种身体经验。唯一能做的,是照顾妻子的情绪,安抚她。
比起妻子在肚子里就跟孩子有了交流,章珏还正在找「做爸爸」的感觉。
有一次,因为想抱孩子遭到抵触,他偷偷掉了眼泪。过年的时候,他和妻子把孩子从姥姥家接回来,独自照顾,再送回去时,「有点失落」。
「现在能想到的可能是孩子再大一点,怎么教养他,他现在太小了,除了吃就只是睡。可能有的爸爸觉得,孩子不需要我,他们就放弃了。我是觉得,能做一些事情就做一些吧。」
「毕竟,孩子是两个人的。」
尽管身体和生活遭受巨大改变,受访的妈妈们在谈到孩子时,语气温柔或者兴奋,旁人眼中的那些惊心动魄,甚至「牺牲」,在她们这里,都化作了「也还好」「习惯了」「孩子平安健康就好」。
她们的心甘情愿,并不意味着旁的人可以轻易得到这样的结论,「生育不过是一种自然过程」。
章珏的妻子永远记得第一次在三维彩超里看见孩子嗦大拇指的震撼;沈甜半夜爬起喂奶时,孩子小脸贴在她的胸脯上,她想永远留在这一刻,「这样亲密的,只属于我们俩的时间,过去了就再也体会不到了」。
如果现在问一萌「保大还是保小」,她会毫不犹豫,「当然保孩子,放弃我」。
(一萌、沈甜、章珏系化名)
撰文:苏惟楚
编辑:于陆
海报设计:韩菲菲、高闻笛
封面图来源:站酷海洛
「成为母亲」系列策划前两篇(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阅读):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