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赵燕菁观察| 新《土地管理法》的制度含义

经济学圈子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就是把现实中原本行得通的东西,放到模型里看看是否行得通。”
中国的土地制度就是如此。尽管实践已经验证了这一制度的巨大成功,但由于在西方主流意义上的“经济学模型”那里无法通过,从其诞生那天起,要“从根本改变土地制度”的呼声就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2020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土地管理法》中提出的两个概念:“成片开发”和“公众利益”。
“成片开发”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内涵只有放到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下才能被充分理解。那么什么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如果说西方主流的土地制度是“从广泛私权中界定出公权”,中国的土地制度则是从“广泛的公权中分割出私权”。两种土地制度的差异,源于不同的城市化增长阶段和路径。
厦门大学双聘教授 赵燕菁
01 不同的城市化路径
所谓城市,简单讲就是“一组公共服务的空间集合”。任何商业模式的完成,最大障碍都是资本不足。如果让企业自我提供道路、电力、给排水、通讯、治安等这些基础设施服务,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也是极其昂贵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由政府统一提供这些“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被这些公共产品覆盖的地区,就是“城市”。是否具有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构成了城市和乡村的主要差别。
显然,如果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必定是极为昂贵的。改革开放之前,企业不得不自己“办社会”,就是城市化严重滞后的结果。可以说,拥有发达基础设施的城市,是各种现代商业模式的平台:城市将各个商业模式中的重资产部分剥离出来统一提供,为企业的轻资产运营提供了可能。由于城市集成了所有部门的重资产部分,就决定城市化必定是一个需要巨大资本的进程。
其中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土地。由于城市公共产品(道路、管线、机场、火车、港口……)不可能从私有产权的土地中自发产生,城市化必定是一个“私有-公有-再私有”的过程。其中最困难的环节,也就是卡住大多数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环节,就是从“私有-公有”这一环。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能否启动,很大程度取决于其启动时的制度,能否跨越土地公有化这第一道门槛。
从世界范围看,实现城市化的国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有殖民地的原住民国家”(欧洲旧大陆国家、日本),它们通过掠夺、战争、贸易、殖民攫取外部资本,然后通过赎买完成宗主国土地公有化;第二类是“没有原住民的新大陆国家”(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这些国家的宗主国通过无偿攫取的土地,完成殖民地的土地公有化。没有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直接获得无主土地(本地人被视为无任何权益的动物)。跨过公有化这一步后,城市才能配套基础设施,通过市场再出让给需要公共服务的企业和家庭部门。这两种城市化路径,也体现在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明显的城市规划差异上。
和大多数发展国家一样,中国属于没有殖民地的原住民国家,城市化的土地从私有到公有的这一步因为缺少资本而无法完成。因此,原住民国家极少能获得完成城市化的第一步,更不要提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上的工业化。所有建立在已经完成再私有化基础上的经济学模型,都无法指导原住民国家启动城市化。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发达国家的普遍私有化,是公有化以后再私有化的第二步,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吃“第二个包子”。
02 什么是“成片开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之所以取得巨大突破,在于中国创造了一个原住民国家低成本获得土地,并靠自身资本完成公共产品重资产投资的土地模式(新加坡、以色列或许是少数更小的样本)。这个模式可以抽象为以下几个步骤:
1)城市土地公有化。1950年代以来的计划经济,特别是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为中国跨越农地公有化这一门槛提供了宪法基础。
2)垄断一级市场。200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条,使中国成为原住民国家中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能够由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国家。这一制度意味着只有政府才能将农业土地(无公共服务)转变为城市土地(有公共服务)。
3)资本市场。一级市场的垄断使地方政府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本,投资公共服务(如“七通一平”)这些重资产。这里,投资的主体可以是政府、企业(开发商),甚至农民。无论是谁,没有垄断的一级市场,就不可能筹集基础设施的投资。
这三步构成了支持中国过去40年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核心动力机制——土地金融。在这个框架里,我们就可以看清中国“成片开发”的本质。所谓“成片开发”,就是“包含公共服务投入-产出全过程的综合性开发”。
“成片开发”土地的用途大体可分为两类:
1)公共设施用地。这类用地也就是所谓“公共利益”用途的土地,包括道路、学校、供水、电力这些公共重资产。这些土地及其设施大多是净投入(政府收益小于成本)。
2)商业性开发用地。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收益,覆盖第一类土地的投入。在中国,这部分土地又被分为资本性收益土地和运营性收益土地。前者主要是商品房市场,政府通过土地拍卖获得资本,用来实施“七通一平”,建设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后者主要是产业用地,包括工业、商业、办公、酒店等能带来税收的土地,用来覆盖基础设施日常维护需要的一般性支出。
03 “公共利益”的涵义
显然,这两部分土地的比例取决于其具体区位:靠近城市现有基础设施近一点的(比如学校、水厂),第一部分土地占比会小一些;远离城市现有基础设施,需要更多自我服务的,第一部分土地占比就会大一些。“成片”的大小、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出让价格的比值,都会影响“成片开发”中不同用地的比例。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不存在一个“公共利益”用地的“合理”比例。
在征地时给定具体“公共利益”土地用途比例,只会逼使地方政府各种造假。如果还要利用这一规定对开发后的“公众利益”用途占地比例事后追究,就会引来一系列针对地方政府的诉讼。土地用途及其改变都是市场的函数,市场用途不可知,用途管理就只能是事后的。城市规划事前给定用途的做法,都是在没有市场使用者之前公共服务提供者的经验推定。各种用途的比例,都是基于过去经验的模拟,而非基于“科学”的计算。一旦土地进入真实市场,规划用途管制就必须从“事前”转向“事后”。
明白中外土地制度的根本差异,也就可以理解“公共利益”这一词汇本身在中西方的不同的语境里,也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按照中国特有的土地金融模式,“成片”开发里的两类土地互为前提:哪怕是政府出让的商业用地,也是在为提供公共服务创造前提。这就意味着“成片开发”的每一类土地,都是广义的“公众利益”!在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下,新《土地管理法》在用途上区分“公众利益”和“非公众利益”从一开始就是误导。
在西方的增长模式里,中国从1982年版宪法开始实施的城市土地国有化本身就是“旁门左道”,因为在它们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下,城市土地不同用途间不存在中国那种成片开发土地间互相支撑的财务关系。除非我们在中国城市道路的语境下重新定义自己的“公众利益”,否则中国土地管理与中国增长模式之间的制度冲突就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在西方语境下,“公众利益”对应的是“私人利益”,是从广泛私人利益中区隔出来的公共部分,其投入和运营都来自私人的税收。地方政府在西方是“服务型”政府,就像是中国的“物业公司”,业主通过“业主委员会”(议会),来约束“物业公司”通过侵犯业主的物业权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在中国的增长模式下,私人利益是从普遍的公共利益中区隔出来的。
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发展型”政府,它更像是酒店,要通过不断改进自己的公共服务(比如酒店大堂)和其他酒店(城市)竞争。企业和居民更像是房客,通过购买长期居住权使用酒店的公共服务。对物业公司来讲,你把小区绿化改为停车位,就是侵犯公共利益;对于酒店来讲,它改造每一部分,都可以视作公共利益。
在中国的土地制度下,政府建学校征地和搞房地产征地都是“公共利益”。没有垄断的土地一级市场,不能“成片开发”是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无法升级为“发展型”政府的主要原因。那么在中国,怎样辨别“公共利益”还是“非公共利益”?答案不是在前端——看土地用途是什么;而是在后端——看土地收益用在什么地方。
1) 作为公共利益的土地收益,不能进入财政,不能用来弥补预算缺口,不能用来支付一般性支出,而是要限定用途:只要土地的收益是用于“公共利益”,征地无论做什么用途,都应被认定是“公共利益”。
2) 通过设置土地支出的科目,甄别征地是用于“公共利益”还是“非公共利益”。在土地收益使用环节区分“公”与“非公”,要比在土地用途上区分“公”与“非公”来的更有价值。因此,“成片开发”的标准,应当是管住土地收益而不是限定土地用途。
04 概念背后的深层问题
长期以来,很多中国学者对中国土地制度的特色认识不清,盲目将西方土地制度中的“词汇”纳入中国土地制度的“语法”。“成片开发”中的“公共利益”还是“非公共利益”之争,就是典型的语言错乱。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错乱,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城市经济学中,土地被认为是一个孤立的生产要素,否定政府“成片开发”,把征地限制在“公共利益”范畴,就是要让土地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但现实中,城市土地是由为其配套的各种公共服务所定义的。由于原始农地并不自带这些服务,因此,原始农地不可能“自由”进入城市土地市场。
生搬硬套错误理论,往轻了讲,会导致政策与法律间的内在冲突和混乱;往重了讲,会逐渐侵蚀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根基。很多似是而非的政策,比如“农地自由入市”、“同地同权”在被写进中央文件甚至国家法律时,起草人为什么不肯看一下现实中已经发生的“自由入市”,如小产权房、违章建筑,以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贫民窟现象?这些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各国城市化的实践表明,农地入市越“自由”的国家,城市化质量就越差。缺少有效的用途管制,几乎是所有城市化失败国家的制度标配;相反,越是用途管制严格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反而越高,经济越发达。难道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今天,建立在土地制度基础上的土地金融,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巨大资本来源。土地制度是中国经济制度中,少有的几个相对制高点。在城市化没有完成之前,如果轻易放弃这一付出巨大革命代价才换来的制度遗产,中国可能一夜之间被打回原住民国家的原形,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就会功亏一篑,我们也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注:文章2020年5月5日首发于爱思想网,道亦有道传媒平台经作者授权,全网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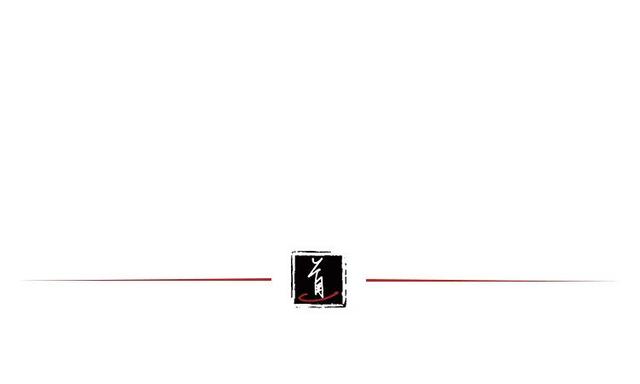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