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塞拉·本哈比谈国际治理与新冠疫情

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当代著名土耳其裔哲学家、批判理论家、思想史家,现任耶鲁大学尤金·麦耶政治与哲学教授。本哈比是七十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批判理论、交流伦理学、女性主义思想家之一。她结合海德格尔、阿伦特和阿贝马斯的思想传统,从移民、迁徙、边境、族群、性别等国际政治维度创新理论,对当今全球思潮走向影响甚巨。目前,本哈比转移至马萨诸塞州伯克夏县隔离。在接受《上海书评》的采访时,她分析了当前新冠疫情对国家政治、国际治理、社会文化、移民和难民的影响。
阿伦特对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析,究竟与极权主义有何结构性关系?如果不是单纯的导因与结果的关系,又作何解?
塞拉·本哈比:《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结构和构成一直是个谜团。早时,大多数历史学家并不理解阿伦特究竟意欲何为。因此,此书拥有若干不同的题目。1951年英国初版,书名定为《我们时代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s)。之后在美国出版时,改为《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5年德译本发行时,书名是《极权主义的元素与起源》(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对我而言,这部书最为珍贵的一点,也是我重点分析过的一点,是她与瓦尔特·本雅明的交汇点。这很重要,因为阿伦特接受了本雅明对历史哲学的批判。在本雅明的力作《论历史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中,他批判了关于历史是“按阶段不断前进,直到克服全部的苦难与压迫”这一过度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他认为值得怀疑的是,资本主义是否注定因为自身矛盾,自动步入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本雅明此文成于1940年,最直接的写作语境是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本雅明的观点是:如果我们认为历史沿着一条势不可挡的目的论的轨迹前进,结果必定是一场灾难。事实上,他认为这种目的论式的历史观导致了德国工人阶级对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和清醒度。阿伦特吸收了本雅明对历史目的论的批判。她拒绝承认历史本身具有因果性,能导致自身的发展。但她也不认为历史只是“一件又一件烂事”(one damned thing after another)串联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反犹主义与帝国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元素,而非导因。

这一立论十分不易理解。她想要说明的是:社会文化一旦形成一些特征,譬如种族化歧视,那么它会作为一种元素继而渗透到其他社会现象中去,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在西欧、东欧,种族偏见最早是针对犹太人一些特定和特殊的境况。但帝国主义承袭了这种“种族排他”,远渡重洋,带到了非洲大陆。你一定记得阿伦特最重大的理论之一便是欧洲各国帝国主义势力如何“发现了深色大陆”。但这与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有何关联?如你所说,这不是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帝国主义发明并传播了某些技能,譬如行政化大屠杀(最早是屠杀各地原住民)、设立集中营地(最早用来制服非洲原住民)等等。所以这些“种族化排他”的元素会在欧洲经历极权主义时复苏,浮出水面。《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的构成便是一种“片段性史学”(fragmentary historiography)。她寻觅的是一些单独的元素,它们在文化和历史现实中连亘成群,汇成“星河”(Konstellation)——这是本雅明喜爱使用的另一个词。
阿伦特的“星河分析法”在后极权主义时代,最适宜应用在哪些谜题上?是某种极权主义的延续,还是性质完全不同,但意义相等的平行政治现象?
塞拉·本哈比:可以从若干维度来思考。首先,我们仍然处在“种族排他”时代。全球世界并非全球主义世界。近日流行批判世界主义,时兴“回归民族国家主义”,对此我深感沮丧。有些人声称,世界主义等于新自由主义资本市场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这是何其的浅见。世界主义还反对种族主义,反对部落式的民族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尚不足以成为世界主义全球,因为我们尚未实现对人格和人权的保障、对道德和法律平等的尊重。这个世界也尚未战胜种族主义。现实正相反。特朗普总统与蓬佩奥坚持在称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时与“中国”甚至“武汉”挂钩,而七大工业国组织(G7)甚至无力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如今,“种族排他”针对各个群体,时刻存在,蔓延全球。
阿伦特思想的另一维度也与时局相关:国家解除公民身份、导致大量公民丧失国家、形成大量难民的权力。阿伦特曾说过:国家最绝对的权力,莫过于赋予和移除公民身份的权力。试看缅甸罗兴亚群体(Rohingya)的境遇吧!一夜之间,百万民众流离失所,进入“无国家”状态,缅甸、孟加拉国都不愿收容。谁又知道他们究竟是何状态。他们像静坐的鸭子——最易遇险。这种情况下,种族屠杀最易发生。没有公共权威做后盾,这是少数族裔群体最终的脆弱之处。目前联合国难民署(UNHCR)已经介入,到了现场,但我们很清楚,这还远远不够。
除“种族排他”和“无国状态”外,我们生活的世界还具有一个特征也与阿伦特的政治关怀契合:“集中营地”的存在。写成《汉娜·阿伦特:不情愿的现代主义》(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不久后,我在剑桥做了题为“他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Others)的“西利演讲”(Seeley Lectures)。它直接脱胎于我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研究,源自阿伦特对难民、移民者、寻求庇护者地位的反思。过去五十年内,跨境人口流动持续增加。虽然目前移民仍只占全球七亿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五,但跨境移动的增长率超越了世界人口的增长率。当然,这引发了各国对于丧失边境控制的恐慌。面对跨境人口流动的加强和加速,国家条件反射地保护自己的边境。而保护边境的方法之一便是创建集中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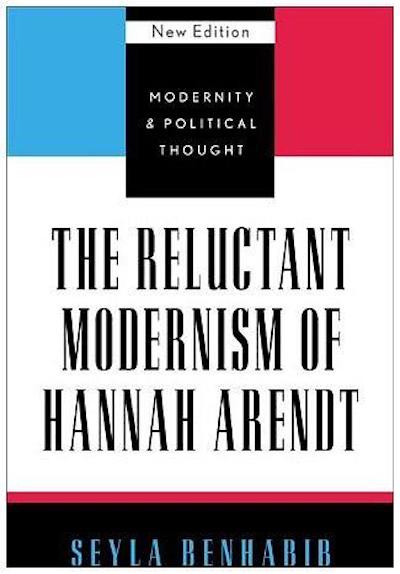
营地是属于我们时代的非正常空间。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当代政权——这里我主要指欧洲和非洲——有义务尊重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Convention relative au statut des réfugiés)。一方面,他们承认难民来到自家门前,同意他们申请庇护,装模作样地遵守《公约》。但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接收这些个体进入自己的司法管辖权,甚至无意真正审理他们的庇护申请。结果,我们剩下了什么?我们建立了集中营地。企图从法国西北部跨越英吉利海峡的难民们一直寄居在“加莱丛林”(Jungle de Calais),直到法国警方摧毁了这座难民营。我们还剩下了什么?在情势紧张的非洲,肯尼亚达达阿布(Dadaab)有一座错综复杂的难民城,容纳着超过四十万难民。与此同时,这些无家可归之人都还保留有自己的权利和要求。他们不能惨受种族屠杀,也不该“被消失”。他们似乎在三界之外的灵薄幽狱中游荡。这同样也是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分析的一种状况:除非我们有充分的国际和政治组织、民事和社会力量去有效地阻止,“种族排他”很可能会导致无国家状态、难民困境、群体脆弱性、甚至是种族灭绝。
阿伦特一度曾对二战后鼓吹的“新国际权利法案”持怀疑态度。她认为此举缺乏植根于城邦政治的法理基础。她甚至还尖刻地讽刺道:“所有企图发起一套‘新国际权利法案’的鼓吹者和赞助人,概属边缘人士——如少数毫无政治经验的国际法学家,以及受到职业理想主义者飘忽不定的情感支持的职业慈善家。”但她终于还是乐观地看待国际公法体系,渐渐向《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始作俑者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靠拢。最终,二者都认可国际制度在维护全球正义方面应起的作用。但她的批评至今回声不绝。那么,从今后着眼,我们应该在国际层面上建构性质上与目前植根民族国家的共和制度、民主主权相等的超级政治组织,还是应该从公约和条约体系入手,以习惯法、国际协定为基础,扩充、衍伸这些双边和多边章程,甚至自我束缚似地加强我们对此的依赖,最后再谋求这些跨境体系与现有的国内制度相互协调?
塞拉·本哈比:你提出了我们时代全球政治理论中最棘手,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首先,二战之后的国际体系有两座规范性基石:一是国境司法管辖权,包括尊重民族国家的疆土边境和国防安全;二是尊重普遍人权。二者之间一直不乏某种臲卼的张力。一些思想家认为:所谓张力,是杞人忧天,因为只有在民族国家的语境内,才谈得上实现人权。对此,我坚持认定人权更具超越性,人权必须在社会语境内得以实现。我承认,这种社会语境最终以何种政治组织形态呈现,是由圈定边境的民族国家司法权?还是小型城邦国家?还是其他某种“后民族时代”的司法管辖形式——譬如欧盟?——这是个可供自由发挥的开放题。组成国邦的模式,以及邦际联结的模式,都多种多样。世界全球化不仅以大国为单位,也在国家内部创造了许多“下单元”集体(sub-unities);在欧洲,是加泰罗尼亚;英国语境中是苏格兰;土耳其内部,则是库尔德人从未实现的自决要求。“下国家”(sub-national)单元的局部自我治理,目前已形成了一种全球需求。国际层面的经济、技术和媒体发展,既在逐渐整合,也同时在分解,因为它们允许更多种多样的联通交流,而不再依赖民族国家的垄断。我可以再以个人经历举例:在我的孩提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耳其只有一家官方收音机频道,直到七十年代,普通百姓家里都没有彩电。今日电台五花八门,有线和无线电视眼花缭乱,也模糊了我们对于“国家”与“官方”声音的界定。
但我绝非民族国家之敌。过去数百年内,现代国家取得了夺目的成就。我反对的是“物化”民族国家概念,从而丧失灵活机动地应对新秩序、新主权形式的能力。关于建立一个“全球国家”的庞然大物,阿伦特,以及许多其他人——她绝非当时唯一持“非共和主权即全球国家”观点的人——是持批判态度的。这种批判源于康德的观点:倘若有一个“世界政府”,它必是“没有灵魂的专制政治”(ein seelenloser Despotism)。当大多数人谈到“全球国家”时,他们心中想到的首先是个霸主,一个“贝希摩斯”(Behemoth)怪兽,凌驾于所有国度之上,作威作福。我不可能不同意,这是一幅惊悚的画面。但这绝非唯一的可能性,也并非真正发生在现实世界的境况。目前,一个全球公共领域正在萌生。我们二人现在进行如此跨国家、跨文化、跨传统的对话,便是最有力的例证。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对彼此了解匪浅。全球公共界域并非“全球国家”,但它是新兴政治意识的预兆。
关于国家公民与狭义上“全球公民”之间的反差,特蕾莎·梅(Teresa May)有句名言,说“全球公民”绝无可能,因为“如果你自认为是世界公民,那么你无处是公民”——这并不正确,因为公民并不仅意味着法律上的“国家公民身份”,还包括沟通交流、选择立场,以及对身居远方的他人油然而生的责任感。这些是跨越距离的团结形式,也是康德在《永久和平论》(Zum ewigen Frieden)中对“公共界域”(Öffentlichkeit)的定义之一。所以,尽管我们不知这种“国际交流民事共同体”具体会以何种政治形式运行,我坚信它的客观存在。因为旅行、交流和教育,我们不仅拥有国际市场,而更是缔造了一个国际公民社会。
您构建的宏大世界主义愿景如何兼容女性主义思想具体的历史和身份诉求?作为七十年代以来最主要的性别平等、性别解放理论家之一,您如何看待主流批判理论对于女性主义的批判?霍耐特(Axel Honneth)在与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的争论中,坚持“承认”概念是普遍的,一定不能陷入文化具象性。而阿伦特是位对女性主义不感冒的女性思想家,起码她的政治论述体系是“无性别化”或“去性别化”的。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一点,又该如何对照她与波伏娃更显性的“性别化”哲学话语体系?总体而言,性别身份的争执与全球正义的诉求有何概念上或策略上的关系?
塞拉·本哈比:我与弗雷泽一样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我们面临着一种全新形式的斗争和社会运动,其中意义尤其重大的一种便是女性运动。但若要理解世界各地为何兴起的女性运动,就必须考虑女性大批涌入劳动力的历史。这是一段普遍意义上的历史,而非局限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与此同时,平等理念蔓延全世界。批判种族排他,无法不同时连带着批判性别排她。所以在此期间,众多维度汇流,一起孕育了1980年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女性运动。这不是单数的一场女性运动,而是复数的诸多女性运动。这不只事关“承认”问题,还是人权和人类平等的诉求。

Nancy Fraser
我曾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发表了一篇研究女性运动的论文,题为“跨境伸张权利”(Claiming Rights Across Borders)。这种国际性的诉求会以许多形式展开,如解决两性之间工资收入的不平等、铲除家庭暴力,再如改善女性的健康和卫生条件。这便阐释了:我的世界主义愿景并非清一色的。也正因如此,我区分全球化与世界主义。所以,针对霍耐特,我的答复是:“承认”是不够的。如果只紧紧握住“承认”这面旗帜,会显得女性运动的目的无过乎“承认差异”而已。必须承认,这一观点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因为正如你所说,在法国八十年代的语境内,有一股女性主义思潮是以“差异理论”“承认差异”为基础“构建性别”的。你也很清楚,我是在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那部名作《以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引起巨大反响后,动笔开写女性主义和伦理问题的。但我一直坚持认为这种“不同的声音”必须纳入普遍的伦理认知之中。“不同声音”的问题不应沦为对于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所谓的“差异权”(le droit à la différence)的辩护。所以,我涉猎性别研究,应用的理论框架,既非“承认”,亦非“再分配”。我不否认,这两个概念在当初开启对话和辩论时,价值巨大。但我认为它们还不够。在我的辞典里,“全球诸女性主义”与“世界主义诸女性主义”相互印证。毕竟,连结人类物种的另一纽带,是我们的两性分别。在一些语境内,这已经开始动摇了。但是,普遍而言,我们生而为男女。这一分歧性,或二价性,是世界各个社会共通的特征。我们必须普遍地思考,同时也去研究那些具象性的实体,而不拘泥于某些物化的“差异”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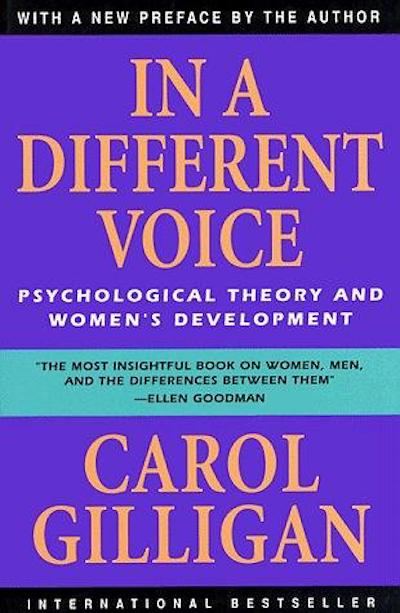
您试图在具象的身份意识和普遍的种族意识中间架起桥梁,打通女性主义与世界主义,这在方法上很具解放意义。您刚才短暂提及了女性权益与普遍人权重合的另一维度:公共健康与卫生。当前纽约成为了新冠病毒在北美的震中,您在麻省伯克夏县隔离。您对周边的疫情与防疫措施,有何直观感受?
塞拉·本哈比:这里地处麻省山脉之下,算是乡间,人口密度比纽约和纽黑文稀少。许多纽约人在此处安家,目前都来避难,包括我和一些同事。但这里防疫情况诡异,效率不佳。许多人无法检测,而那些检测过的人,有些三四日后才得到回音,甚至丢失了结果。这种无能程度,令人惊讶而失望。
您是否已在构思“新冠病毒的政治哲学”?
塞拉·本哈比:国际社会陷入的窘境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社会是何等互相依赖、相互联结,但愈是如此,政治思想家们愈是满口“回归民族主义”。剑桥的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刚在《卫报》(The Guardian)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声称疫情向我们揭示了“霍布斯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发现,政治究竟还是强权,或者说,是谁向谁施加强权。我很尊敬朗西曼,但我实在不敢苟同!严肃地讲,他这套想法简直是谬以千里。我们实际看到是:我们的确需要公共权力部门实行司法管辖。但每当听取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Mark Cuomo)汇报抗疫进展时,我都发现,对于我们这些往来奔走于麻省、康州和纽约的民众而言,他的权力和语言与特朗普总统的相比,对我们切实生活的影响大得多。所以问题不是我们是否需要公共权力,而是何层、何级的公共职能。诚然,抗疫必须行使权力,甚至在一切政治活动中都普遍如此。但我们更需要集体行动。譬如,我完全无法理解:既然没有任何一例难民被证实携带了新冠病毒,为何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对难民关闭?我的老同事,耶鲁教授詹姆斯·斯考特(James Scott)称此为“像国家一样审视”(seeing like a state)——国家有一套结构和心态,而国家官僚机器的要义便是“圈地”与“权力”。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新冠政治哲学”一定不应回归我称之为“逆流民族主义”(retrograde nationalism)的老路。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主义的开放社会:新冠病毒首次现形时,我们不惩戒,而是称颂那些医生们。此时,国际社会开始协同防疫,合作研发疫苗。事实正相反,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2月初还在抱怨新冠病毒是民主党的大骗局,声称道琼斯指数如此之好,市场形势如此之妙,民主党人试图用新冠病毒阻挠他再选。极权主义的本能便是否认问题的存在。极权主义领导人的本能是推卸个人责任。与此相反,世界主义社会在于即时分享知识。在美国,还发生了其他的怪相。奥巴马时代的“全球健康安全议程”(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抗击流行病项目,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大幅缩减。
这些项目确实一度陷入削减经费的困境。再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曾在中国设立了“实地流行病学训练顾问”(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Program,简称FETP)岗位,截至去年年底,由琳达·奎克(Linda Quick)医生担任。去年美方砍掉这一要职,对新冠发现初期中美防疫紧密合作增加了难度。
塞拉·本哈比:一点不错!所以,我认为行政机构削减、弱化保护本国人口的公共卫生机制,这有悖良知与常情。鉴于此,我不理解为何我反而应该赞美民族主义。同样,意大利的英雄是一批又一批的地方行政人员们、市长们、奋战在健康危机一线的医生和医护人员们。而意大利国家政府并未及时醒悟过来,采取有效措施。所以我也不明白,为何要赞美意大利政府?总而言之,何妨想象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论在这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这种想象听上去有多么乌托邦,我邀请各位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我们从2019年12月开始国际合作,我们本可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以民族国家视角审视新冠危机的另一局限性是:它忽略了国境之间的人口。目前,欧洲各国的叙利亚难民营迎来了第一波感染案例。这些场所平日便无法达到基本的卫生标准,现在每人每家只领取到了一块香皂!一旦病毒攻破难民营的帐篷,灾难不言而喻,甚至无法想象。这些无国界的空间,以及国家之间窄小的生存空间,缺乏管制力度和问责机制,每逢天灾人祸,必是最为脆弱的群体。
塞拉·本哈比:完全如此。你所说的这一悲剧揭示了那些认定城墙能阻挡无形之物者是何其的短视和无知。高耸的城墙平地而起,用以阻挡视城墙为无物者,这种行径荒诞得甚至颇具诗意。面对病毒入侵,难民营一定惨遭横祸。脆弱的空间不只有难民营,还有监狱。纽约监狱的新冠感染数量已经触目惊心。今天早晨,一位德国的记者朋友从法兰克福写信问我:“病毒侵入了达喀尔、卡拉奇、墨西哥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超级大都会,又当如何?”当新冠部病毒的震中从纽约转移到世界的其他人口密度高、但缺乏公共职能部门有力介入的大都会,挑战可想而知。所以,恐怕我们与病毒斗争还是长路漫漫。
流行病期间,人类生活形式剧烈震荡,这对人的社会性与公共意识有何影响?
塞拉·本哈比:是的,新冠病毒的影响不局限于狭义的政治,而渗透在广义的社会之中。这正是我们的恐惧所在。有一个违背直觉,也违背人情伦理的现象:当人类遭遇困境和灾难时,譬如战争硝烟和自然灾难,我们本能地将自己与他人纽结在一起,加深了团体意识。但流行病迫使人们四散独居。祖父母无法与儿孙团聚,而孙儿也不该探访老人,因为害怕传染给免疫力更弱的前辈。这种难以想象的与世隔绝很容易令人们屈于极权式的解决方式。毕竟“与世隔绝”可以致命地打击民主,甚至让民主完全消失,使大写的人缩减为被支配的形体。在美国,一个又一个州在延迟民主党初选。如此,我们又回到了汉娜·阿伦特:即使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孤独感也是威权与极权诱惑和滋长的苗床。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