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七位作家笔下的七种梦境
创意写作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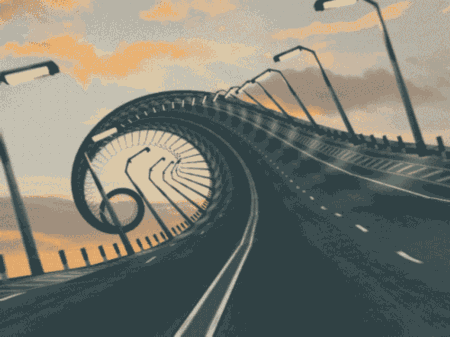
无论是写作还是画画,以及其他具有创作性的行为,都可能会利用到梦境。也许作者的灵感就来源于梦境里的一段情节,画面,或者是精神上的刺激感。让我们看看这些作家们的梦境吧。(另外,欢迎大家留言关于自己的印象深刻的梦境,说不定有人和你做过同样的梦。)
by 米兰·昆德拉
她上了楼,回到房间中。开始,她觉得辗转难眠,但最终还是睡着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梦之后,她在午夜醒来。在这个梦中出现的每个人都只存在于她的过去之中:她的母亲(很久以前就去世了),还有她的前夫(她已经几年没有见到他了。他看起来与以前不一样了,就象这个梦的导演选错了演员),以及他那位专制的,精力充沛的姐姐和他现在的妻子(尚塔尔从没见过她;可尽管如此,在梦境中,她还是没有怀疑自己的身份)。最后,他还含糊其词地向尚塔尔提出了一些性要求。而他的新妻子则在她唇上重重地吻了一下,还把舌头探入到尚塔尔的嘴中。那舔来舔去的舌头只让她感到厌恶。事实上,也正是那个吻让她从梦中醒来了。
这个梦给她带来非常强烈的不安,使她努力想去找出那个令她不安的原因。她想,让她不安的一定是因为那个梦否定了她的现在。而她是那么地依恋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能诱使她把现在与过去或是将来作交换。这就是她不喜欢做梦的原因:它们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强加了一个让人不能接受的等价物,—个与某个人所经历的一切对等的时期。它们否认了“现在”的这种有特殊权利的地位,它们怀疑“现在”。在那晚的梦境中,她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被抹去了:让·马克,他们共同居住的公寓,所有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而它们的位置却被过去给强占了。
而那些早已失去联系的人则企图用陈腐的性诱惑之网来俘虏她。她仍能感觉到覆盖在她嘴上的那两片潮湿的,女性的唇(她不是一个丑陋的女人——这个梦的导演完全按他的意志选定了演员)。这种感觉如此地令人不快,以至于她在那样的午夜冲进洗手间,不停地漱口,直到嘴里那种令人作呕的味道被彻底冲掉为止。
选自《身份》董强 译

我真切记得第一个不成眠之夜的情形。当时我做了个不愉快的梦。一贯黑洞洞滑溜溜的梦。内容记不得了。记得的只是那不吉利的感触。在梦的顶峰我醒了过来。若再沉浸在梦境中势必积重难返——就在那紧急关头像被什么拽回似的猛然睁开眼睛。睁眼好半天那只顾大口大口喘气。手脚麻木活动不自如。而凝然不动,便知横卧在空洞中唯闻自己的喘息如雷贯耳。
是梦,我想。我依然静静仰卧,等喘息平复下来。心脏急剧跳动,为了迅速往里输送血液,肺叶犹如风箱一张一缩。但其张幅随着时间的流动而慢慢减小慢慢收敛。现在到底什么时候呢?我想看一眼枕旁闹钟,却无法顺利扭过脖子。这时,忽然觉得脚下好像有什么冒出,如隐隐约约的黑影。我屏住呼吸。心脏肺叶以及我体内的一切都一瞬间冻僵似的停止不动。我凝目往黑影看去。
凝目一看,黑影急不可耐的性状急速清晰起来。轮廓变得分明,实体注入其中,细部历历在目。原来是个穿着紧身黑衣服的瘦老人。老人头发又灰又短,双颊凹陷,一动不动站在我脚下。他一言不发,只管目光炯炯逼视我。眼睛特大,连上面鼓起的红血管都清晰入目。但脸上却没有表情。他全然不言不语,洞穴般空空如也。
这不是梦,我想。我从梦中醒来。并且不是迷迷糊糊醒来,而如被弹起一般。所以这不是梦,这是现实。我想动一动。或叫起丈夫,或打开灯。然而拼出所有力气也动弹不得,实在是连一根手指都不能动。明白不能动,我立时一阵惶恐。那是一种追根溯源的恐怖,犹如从记忆的无底深井中悄然冒上的冷气,一直冷彻我存在的根。我想喊叫,但喊叫不出,连舌头都不听使唤。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定定注视老人。
老人手里拿着什么,细长而线条圆熟,又闪着白光。我定眼细看。细看之下,那个什么也开始呈现出像模像样的形状。是水瓶,老人在我脚下手持水瓶。陶水瓶,以前的老式样。片刻,他举起水瓶,开始往我脚上倒水。但我感觉不出水。能看到水泻在我脚上,能听到其声响,可是脚一无所感。
老人仍然不停地往我脚上倒水。奇异的是,无论怎样倾倒,水瓶里的水都源源不断。我开始觉得我的脚不一会有可能腐烂溶解。如此长时间淋水,腐烂也无足为奇。想到自己的脚将腐烂溶解,我再也忍耐不住了。
我闭上眼睛,发出大得不能再大的叫声。
然而我的叫声竟出不得口。舌头无法震动空气,叫声只在我体内无声回荡。无声的叫在我身体里往来流窜,止住心脏的跳动。刹那间脑袋一片空白。叫声渗入细胞每一间隙。我身上有什么在消亡,在溶解。那真空的震颤闪电一般将关系到我存在的许许多多毫无道理地焚毁一尽。
睁开眼睛时,老人不见了,水瓶也不见了。我看自己的脚。床上没有淋水痕迹。床罩仍是干的。但我身上却大汗淋漓。汗出得怕人。很难相信一个人竟会出那么多汗。可那是我的汗。
选自《眠》施小伟 译

约瑟夫·k做了一个梦。
那天天气很好,k想去散散步,可当他刚刚迈出两步,就已经到了墓地。
那里有几条蜿蜒曲折的路,看起来若隐若现,扑朔迷离。他就在其中的一条路上急速地滑行,犹如在湍急的水流上稳当地漂浮。远远地,他就已经注意到了一座新的坟丘,并且想在那儿停留片刻。这座坟丘好像对他有种特别的诱惑力,他想以最快的速度靠近它。可是,偶尔他几乎又看不见那座坟丘了,因为有一些旗帜挡住了它。那些旗帜舞动着,相互用力撞击着,虽然看不见旗手,但那里似乎还充满了欢呼声。
当他将目光再次投向远处时,突然看到刚才的那座坟丘就在他身边的路旁,几乎就在他身后。他急忙跳进草丛,但脚下的道路在继续飞奔,他左右摇晃着,几乎把握不定,然后正好跪倒在刚才的那座坟丘前。坟丘的后面站着两个男人,他们正举起墓碑,几乎没等到k出现,就把这块墓碑深深地戳进了泥土里,于是,墓碑便像被紧砌了似的稳稳地立在那里。这时,从灌木丛中立刻走出第三个男人,k一眼就认出他是一个艺术家。那人只穿了一条裤子和一件没有扣好扣子的衬衫,头上戴着一顶金丝绒帽,手里握着一只普通铅笔,在靠近坟丘的时候,他在空中画着图形。
艺术家拿着他的笔开始在墓碑上写字,墓碑很高,他根本不用弯腰,但是得将身子前倾,因为这座他不愿践踏的坟丘,正好将他与墓碑隔开。于是,他踮起脚,左手撑着碑面,右手做了一个特别熟练的动作,这支普通的铅笔便在墓碑上写出这样一行金字:“这里安息着——”。每一个字都是那么清晰、漂亮、入木三分、而且是纯金的。当他写完这几个字之后,回头看了看k,而k这时正焦急地等着看碑文下面的内容,他根本没有注意那男人,只是盯着墓碑。果然那男人又开始继续写,但不知出了什么故障,他无法再写下去。于是他放下笔,又一次转向k。这时,k也正看着艺术家,他发现艺术家的神情中满是窘迫与尴尬,令人莫名其妙。此时,先前所有的活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k也因此陷入了窘境之中。他们互相交换着目光,是那样的无助和无奈。有一种讨厌的误解将他们无情地隔开,谁也无法解除。墓地教堂的小钟也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艺术家挥动了一下举起的手臂,钟声就停了下来,然而片刻之后,它又开始响起来了。这次声音很小,而且没有人制止,自己就立刻中断了,好像只是想检验一下它的声音是否跟从前一样。k对艺术家的这种处境感到难过,他开始哭泣,长时间地用手捂着嘴呜咽着,抽泣着。艺术家等待着,直到k渐渐平静下来,他才决定继续往下写。因为他只能继续写下去,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他写下一小笔,这对k来说是一种解脱,然而,艺术家好像极不情愿地才把这一笔完成,字体已不那么秀丽,而且也失去了金光,变得苍白无力,模糊不清,只是无把握地延伸着,但是字母却很大,这是一个字母“j”。刚刚写完它,艺术家就暴怒地伸出一只脚向坟丘跺去,跺得周围的土不断地向上飞扬。
终于,k明白了他,然而想要求得艺术家的原谅却已经晚了。艺术家用十指挖着泥土,泥土似乎很顺从。一切像是准备好了似的,一层薄薄的泥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挖开表土,立即出现了一个墙壁陡峭的巨大墓穴。这时,k感到有一股轻柔的气流从背后推动着他,随即便坠入墓穴中。当地被无底的深渊吞噬的一瞬,他还直着后脑勺呢。这时,他的名字带着显赫的装饰被刻在了石碑上。
他欣喜若狂,然后,他醒了。
叶廷芳 译

星期六我睡得相当早。然而到了两点左右,风刮得紧了,我不得不起床把一扇没拴住的百叶窗关好,是它把我吵醒的。我稍稍回顾刚才睡着的那一小段时间:驱走了疲劳,没有不适,没有梦,我很欣喜。我刚刚重新躺下,便又马上入睡。过了一段难以估摸的时间,我渐渐地醒来,确切地说是渐渐醒在一个梦的世界里。起初,我无以区分这个梦幻世界与平时睡醒后才感觉到的真实世界,这个梦幻世界是那么的清晰。我躺在特鲁维尔的海滩上休息,这海滩同时又成了一个陌生的花园里的吊床,一个女人脉脉含情地看着我。她便是多罗西B夫人。比起早晨我醒来认出了自己的卧房时,我并未感到更为惊讶。
不过,那时我对梦中的同伴那神奇的魅力已没有更多的感受,她的出现曾激起过我的对其肉体和心灵的强烈渴慕也减弱了。当时,我俩神情狡黠地对视着,正在创造一个幸福和荣誉的奇迹,对此,我们心照不宣,她是这个奇迹的同谋,我对她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可她却对我说:“真傻,谢我干什么,难道你没为我做同样的事吗?”这一感觉(实实在在的),即我也为她做了同样的事,使我如痴如醉,仿佛这象征着最亲密的结合。她用手指做了个神秘的示意,并微笑着。我好像已经和她融为一体,明白她的意思:“你所有的敌人、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遗憾、所有的怯弱不是烟消云散了吗?”我尚未开口,她却听见我在回答:她轻而易举地成了胜利者,摧毁了一切,痛痛快快地吸引住了我痛苦的身心。她挨近我,双手抚摩着我的脖子,慢慢地撩起我的髭须,然后对我说:“现在我们去和其他人接触,让我们走进生活吧。”我心花怒放,精神抖擞地去履行这幸福的约会。她要送我一朵花,于是便从酥胸中央取出一朵黄里透红、羞闭着的玫瑰,将它插在我的衣服扣眼里。刹那间,我为一种新滋长的快感所陶醉。这朵插在我衣服扣眼里玫瑰开始发出爱的芬芳,那香气直扑我的鼻孔。
我发现我这种不为己知的兴奋扰乱了多罗西的神思。正当她的眼皮(我为神奇的意识所支配,竟能感觉到她身上的东西。我肯定)微微痉挛,泪水将夺眶而出之际,我的眼睛里却充满了眼泪。这肯定是她的眼泪,我可以这么说。她靠近了我,仰起的头挨着我的脸颊,我能凝视着她的脸庞,尽情享受那神奇的恩泽和迷人的活力。她从鲜润含笑的嘴中伸出舌头舔去我眼角的泪水。继而,随着她嘴唇发生的轻咂声,她将眼泪咽了下去,我感到仿佛有一个陌生但更亲热、更撩人的吻直接印在我的脸上,我猛然醒来,认出了自己的卧房,就像临近地区暴风雨中紧跟在闪电之后的一声雷鸣,与其说是令人眩晕的幸福回忆接踵而至,不如说它已和确实地让人震惊的虚幻和荒谬化为一体……
唉!爱情就像这梦一般,带着同一种变颜改容的神秘力量在我心中逝去。同样,知我所爱,但没有出现于我梦中的诸君,请不要给我什么劝慰,你们是无法理解我的。
译者不详

现在要讲一个我都觉得是最完美的梦魇,因为梦魇的两大成分它都有:因遭受追赶而肉体难受的故事情节和一种超乎自然的恐惧。华兹华斯告诉我们,他当时在面临大海的一个岩洞里,是中午时分,正读着他特别喜欢的《堂吉诃德》,塞万提斯讲的游侠骑士冒险的故事。他没有直接指明,但我们都知道是讲谁。他说:“我放下书思考起来。我思考的恰恰是科学与艺术问题,一会儿时间到了。”强有力的中午时分,闷热的中午时分,华兹华斯坐在临海的岩洞里(周围是海滩,是黄沙),他回忆说:“睡意把我笼住,我走进了梦乡。”
他在岩洞里睡着了,面对大海,周围是海滩金黄色的细沙。梦中一个撒哈拉的黑色沙漠包围着他。没有水,没有大海。他在沙漠中心——在沙漠中总感到自己是在中心——他在想着能用什么办法逃离这茫茫沙漠时,心中害怕极了,这时他看到身边有一个人。说也奇怪,是阿拉伯贝都因家族的人。这个人骑着骆驼,右手拿着一支长矛,左臂下夹着一块石头,手中拿着一个号角。这个阿拉伯人说他的使命就是拯救艺术与科学。他把号角凑近他的耳朵;那号角非常之漂亮。华兹华斯(“用一种我不认识的语言,但我还是懂了”)说他听到了预言,一种激情横溢的颂歌似的,预言着地球正要被上帝的暴怒所指派的洪水摧毁。这个阿拉伯人对他说,洪水真的要来了,但是他的使命是拯救艺术和科学。他拿出石头给他看。真奇怪,那石头上居然是欧几里的几何学,却仍然是一块石头。接着他又给他看号角,那号角也是一本书:正是告诉他那些可怕事情的那本书。那号角同时也是全世界是诗句,包括(为什么不呢?)华兹华斯的诗。这个贝都因人说:“我必须拯救这两样东西,石头和号角,两者都是书。”他向后转过脸去,一时间华兹华斯看到那个贝都因人的脸变了,充满着恐惧。他也朝后面看去,看到一道强光,这道光已经吞没了半个沙漠。这正是即将摧毁地球的洪水发出那道光。贝都因人走开了,华兹华斯看到那个贝都因人也是堂吉诃德,那头骆驼也是罗西南特(堂吉诃德的坐骑)。就像石头是一本书,号角是一本书一样,贝都因人也是堂吉诃德,而不是两者之一,而是同为两者。这种双重性正好就是梦中可怖之处。这时,华兹华斯一声恐惧急叫,醒了,因为大水已经追上他了。
我觉得这个梦魇是文学上最精彩的梦魇之一。
选自《关于梦魇的演讲》陈泉 译

我在梦中经历了三个回合。先是躺在海滩上,枕着黄沙,双足浸在水中。我咬着一根草茎,眯缝着眼睛,哼着一首歌儿。我试图回忆我哼的是什么歌,但实在想不起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继续哼下去,两脚打着水,直到哼够了才停下来。我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昏昏欲睡,这时突然想起了我的全部处境,我是自由的,是自己的主人,我爱干什么,爱允许什么,就干什么,就允许什么,我是躺在海滩上,一段时间内除了我四周没有第二个人。于是我一跃而起,发出一声短促的印第安人的号叫,一跃扑入水中,击得海水噼啪响,我击水,划船,游出去又游回来,感到饥,跳上陆地,甩一甩发中的水滴,躺倒在打开的背包前。我缓缓从包里掏出一大块面包,这是昨天出炉的非常好的黑面包,还有一根香肠,同我们孩提时代参加节日般的学校郊游时所得到的那种一样,还有一块瑞士奶酪,一个苹果,一块巧克力。我把这些东西排列在面前,长时间地观赏着,直到再也按捺不住,便饿狼般地扑了上去。我满怀喜悦激动不已,从面包和香肠中嚼出一种遥远的、被淹没的、内在的男孩的喜悦,它滚滚涌来,把我全部身心席卷而去,使我沉浸在忘我的幸福之中。
没过多久,场面变了。我衣冠楚楚,一本正经地坐在阴凉的、面向花园的房间中。在窗上嬉弄着的树影透窗而入。我坐着,捧着一本书,完全沉浸在书中。我不知道这是本什么书,只知道是个哲学家写的,但不是康德也不是柏拉图,而是像安格鲁斯·西雷休斯那样一位。我读啊,读啊,深深吸入这难以言喻的享受,自由地,无干扰地,感觉不到昨天或明天地投入这个大海,投入这由聚精会神,提高和忘我构成的美丽的汪洋大海之中,预感到书中的结论将证实我的自身和我的思想。我边读边思索,慢慢地一页页翻过去。窗边有只金褐色的蜜蜂嗡嗡营营地低吟着,仿佛整个沉默的世界都凝聚在它们内,整个世界只想表达它充实的寂静和满足,别无所求。
选自《归途梦》译者不详

我不明所以地做着这样的怪梦。
梦里我的妻子像梦游般的屈折身子坐在一艘漂浮在漆黑太空的宇宙飞船驾驶舱里。舱外的金属船壁因极寒冷而结了一层薄冰。我的妻子穿着一身连身套头的银色太空装,像那种出土古墓里尸身不坏公主身上的银丝缫织的贴身软猬甲。我不确定她是否处于昏沌的睡眠里,似乎只能从后方看见她的背面,以及环绕着她的,一整面像一只巨兽的复眼般的上千个冷光仪表。
我则在距离妻的宇宙飞船数十万英里的地球表面,在一个,类似下放知青插队的偏僻乡村的劳动公社,或是游击队藏匿的山城聚落里,和一群对世界的想像只有女人(而且是像乳牛一样的胖妓女)、酒、自己卷的劣质烟草,从敌人那里掠夺来的弹药和粮草,以及彼此胯下的顽癣及跳蚤……这样的男子汉堆中,像一个被他们亲昵嘲弄的窝囊废同伴:自己餐风露宿喝那种淡出鸟味来的麦酒,每天卖力气挣那其他人刚够溜下山脚小镇喝两杯外国烈酒或找个女人睡一宿的铜子儿;而我却攒下钱来,供我那(我想到一串他们描述我妻子的形容词:瓷娃娃、不食烟火的豪华女人、鹤妻、花钱妹、刷卡娘子、夫妻宫坐禄存财帛坐地空……)像城里女人一般赶时髦每年一定要出国一趟旅行并shopping的妻子(“才像给快枯萎的盆栽换水那样地活过来”),一年参加一次孤寂又遥远的外层空间飞行。
光棍们围着我攒掇我说说那外层空间的景象,“有啥好看的?”即使我搔破了头皮,虚荣且夸饰地描述我心中的想像,也不总是一无止境的黑暗夜空,以及妻孤独一人蜷缩在里头的小小的一枚太空舱么?
“其实是很危险的呐!”这样说着,自己的内心亦空空洞洞地不着边际。
在距离那么远的地方,旅途中的时间计量又不是我们地球上的方式。譬如交代她到了机场或饭店(不要怕贵)打个长途电话报平安的可能也没有(即使因为时差在大半夜接到她那头正是白日异国街头打来电话的怅惘等待也没有);连到入境大厅跟人们干拐子卡位只为盯着那个通关电动门的电视屏幕几个小时的接机这件事都无从安排——因为她的回程一进了大气层就是自个儿挑个太平洋随便哪一处海面自个儿摔下来,然后才有海军直升机去把她从太空舱里吊出来……
是那么孤寂的一种旅行方式哪。
选自《遣悲怀》
转自楚尘文化
摄影@Martin Vlach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