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过劳时代:人越来越像机器里的原件,停不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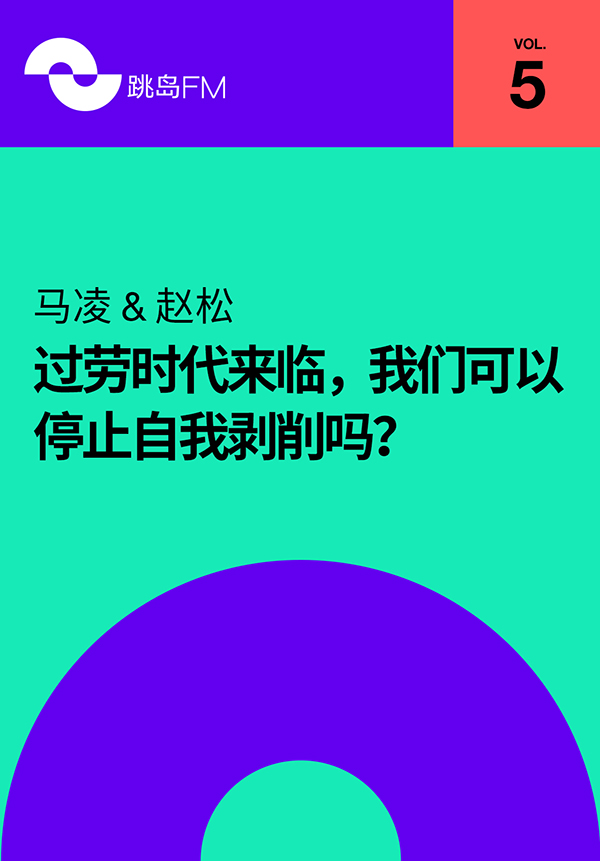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4月29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和作家赵松来到“跳岛FM”第五期,从他们最近的办公经历和感受出发,聊聊当代社会中人的“自我剥削”与疲劳。
疫情期间,赵松曾一个人在办公室上了近一个月的班,而马凌即便不在疫情期也基本都在家办公。马凌说:“我想这次疫情使大家有了一个体验,过去很多人羡慕每天宅在家的工作,但真让你在家办公的话,你发现根本就不是996的问题了,是16×7,每天16个小时、一周7天,这样的工作方式既不健康,也不快乐。”
赵松则感慨:“回顾从现代社会开始到现在的近100年的历程,你会发现我们眼前的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传统的西方基督教社会和中国儒家社会基本上都已经瓦解了。一方面人制造了一种 ‘人无所不能’的幻觉;另一方面人的信仰逐渐消失了。人越来越像一个机器里的原件,根本停不下来。这导致了整个当代社会的危机感和碎片化,甚至家庭的解体。应对它唯一的可能性大概就是恢复个人对世界的感知能力和思考能力,以及个人精神生活的能力。”
倦怠感也成为暴力,撕毁一切亲密关系
疫情发生后,不少人都感慨远程办公、在家办公混淆了生活与工作的界限,已造成越来越多人“自愿”加班。
赵松提及,学者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提到过这是现代人的一个特点。早期现代人还是处在一种被剥削状态。但到了当代社会,高频率、快节奏、高密度的生活工作已经催生了人的自我剥削。
“韩炳哲的《倦怠社会》是他一系列著作当中的一本。跟现代社会相连接的,除了倦怠社会,还有其他关键词,比如透明社会、功绩社会、爱欲社会等。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我们跟19世纪、20世纪前半期的人有了很大不同。”马凌称,过去社会给了人们百般限制,但现代人的行为失去了限制,在大量过激的行为中产生了一种疲倦,这种疲倦是所谓“我行我能”才带来的疲倦,而不是过去那种 “你不行你不可以”所导致的压抑。
“你会希望你的各个方面都能够更出众一些,包括减肥、塑身、整容,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达成一种更完美的、超乎常人的心理诉求,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剥削的心理状态。如果他达不到更强的状态,他不仅产生自我厌恶,甚至和亲近的人都会产生强烈的分裂感、断裂感。我就发现有一些经常加班形成习惯的人,慢慢地会和家庭产生距离感,然后他有时候为了回避这种矛盾会自主加班……最后会变成很扭曲的关系状况。”赵松说。
两人都认为,工作时间太长所导致的疲劳是一种对人的异化。赵松表示,韩炳哲的《疲劳社会》里头有一段特别提到了汉德克,说功绩社会的倦怠感是一种孤独的疲惫,造成了彼此孤立和疏离。这种倦怠感是彼得汉德克在《试论疲倦》中所说的分裂的倦怠感——两个人不可避免地彼此分离,陷入高度个人的倦怠感之中。
“这种导致分裂的倦怠感使人变得失去观看的能力,陷入沉默,只有自我占据了全部视野。它们是一种暴力,由于它们撕毁了一切共同体、集体和亲密关系,甚至摧毁了语言本身。”
欲望像病毒传播,我们生活在他者目光之下
文学中也有很多有关疲惫、倦怠的意向。

赵松举例,古希腊神话中喀戎的马人被赫拉克勒斯射伤脚踝,他是不死的,但疼痛永远都在,为此他就祈求宙斯免除他的永生,摆脱这种疼痛。在承受这种疼痛的过程中,喀戎的马人身心俱疲,这时死亡反倒是变成了一种解脱,永生就变成了永远的折磨。又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其实也是通过对人的不断投胎转世来展现人无法摆脱的永劫轮回。
“人类都渴望永生,以为永生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人还会有厌倦,没有身体疲倦,也有心理的疲倦,并不是说生命长度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普罗米修斯被宙斯钉在了高加索山上,白天老鹰过来啄他的内脏,晚上伤口再慢慢愈合。普罗米修斯是不死的,只有痛苦无休止地延续。也正因如此,最后被解救的普罗米修斯成为了一个从罪与罚的循环困境中被解放的希腊神话故事。”他说。
马凌想起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他早在19世纪就意识到一件事情,正在到来的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是平等产生的欲望与平等所能提供的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对立,使人们感到痛苦和疲惫。换句话说,在普遍的竞争、攀比、羡慕、嫉妒、仇恨当中,无论是爱情、地位、财富还是其他的个人成就都被毒化了。人们只对其他人的欲望垂涎。这种欲望就像病毒一样在传播,我们每个人都是沾染上这样一种病毒了,都是生活在他者的目光之下。”
在赵松看来,这就像科学家在探索外星时发现有个太阳系以外的地方,但实现远征外太空的理想是会把地球的能量耗尽的。“根本就实现不了。我觉得这非常像一个隐喻,现代人为了追求一种更强烈的更完美的快感享受,其实最后是在还没有抵达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耗干了。”
能够体验到与众不同的生活,比其他的都重要
马凌提到,韩炳哲引用了本雅明的一句话——如果说睡眠是身体放松的最高形式,那么深度无聊则是精神放松的终极状态。“一味的忙碌不会产生新事物,它只会重复加速业已存在的事物。本雅明哀叹说,由休息和时间构筑梦之鸟的巢穴,在现代社会日渐消失了。没有了放松和休息,我们便失去了倾听的能力。”

至于大家经常谈论的996,赵松认为,这仍然是一个“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的问题。“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跑到高压的一线城市去寻求所谓的发展的机会。996是个社会问题吗?说是也是。但是反过来讲,也是个人选择。另外一点我是觉得工作本身肯定有它的价值,不仅仅是谋生的价值。关键这个社会最致命的一点是整个社会和资本系统对个人的压榨剥削已经是常态了。大家都在呻吟。现代人的选择余地非常小,这是导致现代人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前所未有的强烈的一个原因。”
他感慨,现在的小孩从小就竞争激烈,长大以后又要面对996。“我认为, ‘90后’会比 ‘80后’厌倦得早, ‘00后’比 ‘90后’厌倦得还要早。”
那么,面对这样的精神困境,我们还能怎么办?
马凌说:“思来想去只能是自我解压。如果你自己不解放自己的话,没有人能够解放你。尼采曾经提过,我们可以做一种否定性的选择。这是一种说 ‘不’的能力。可能退步会使生活变得好。”
赵松则认为,要想办法就是切断这种不断增长的欲求。“我有时候就想,小孩看个蚂蚁就能看半天,还看得有滋有味的。反而是成年人失去了这种能力和乐趣。所以归根到底,人还是要努力把自己从那过于强烈的群体欲望链条中解脱出来,回到一种在寻常事物里就能找到乐趣的状态,过自己的生活。而在并不漫长的一生中,能够体验到与众不同的个人生活,其实比其他的都重要。 ”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