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武汉肖像:口罩下只露出眼睛,也藏不住热爱生活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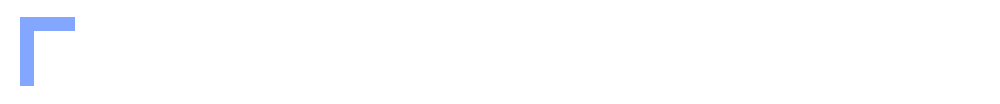
广东医疗队离汉后,摄影师钟锐钧把镜头从ICU里移开,开始在街角观察这座陌生的城市。
几年之前,这里留给他的印象是街边的尘土和拥堵的交通,以及叮叮哐哐永不止歇的施工噪音。但现在,他为这里渐渐喧嚣起来的烟火气息由衷开心。他用“摄影天堂”来形容武汉的街头,汉口的老街里偶尔走过西装革履领结整齐的大叔,也有红裙摇摆的阿姨,他们面对镜头,在自己的审美里毫无怯懦。钟锐钧拍过很多时尚人士,也有明星演员,他珍惜未经镜头训练的鲜明个性。
“口罩下的脸孔只露出眼睛,也藏不住热爱生活的光芒。这些面孔,就是现在武汉的写照。”钟锐钧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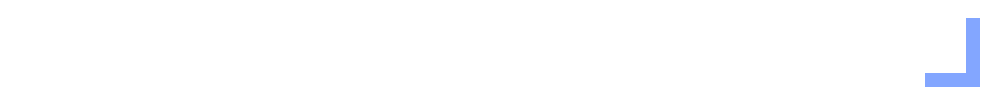
武昌得胜桥社区 | 4.11


理发师杨师傅 · 自制面罩
因为理发的时候要和顾客近距离接触,杨师傅用洗衣机导管和矿泉水瓶自制了一个面罩,借此可以呼吸到背后的新鲜空气。

汉口天声街 | 4.5

市民许大叔 · 笔挺洋装
60岁的许叔叔近三个月来首次出街,为此特意搭配一番,除了一身笔挺西装,他还有一张讲究的手帕。

汉口民主一街 | 4.11

市民李阿姨 · 墨镜红裙
65岁的李阿姨烫了头,穿着一身红色出门采购食品,袋子里还有消毒水。一身红装走在黄色水马围绕的街道上,格外亮眼。

汉口江滩 | 4.13

视频博主周思辰 · 河马姑娘
24岁的周思辰是一名视频博主,随身携带的河马公仔是她的“必备单品”。从封城第五天开始,她用视频记录疫情下的武汉。周思辰说,河马是她的朋友,可以交流,也会孤独。

汉口江滩 | 4.15

摄影师阮阮 · 摄影师
摄影师阮阮和朋友来到江边拍照,有过良好的镜头训练,她娴熟地摆出pose。

汉江码头 | 4.8

保洁员应女士 · 小波浪头
应女士第一天回到码头上班,为了搭配工作用的马甲,特意换上红色卫衣,在社区理发店烫了新发型。

汉口中山大道 | 4.9

黄先生和女友 · “善恶”腰包和小熊贴纸
黄先生和女朋友在武汉读大专。1月23日封城后一直待在家中,这是他们春节后第一次出门,也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汉江一路 | 4.9

HR李小姐 · 黄色雨衣
在时尚公司任职hr的李小姐把雨衣用作防护服,身后是垒砌成墙的黄色水马。

武昌民主路天桥 | 4.11

市民刘叔叔 · 勾花皮衣
65岁的刘叔叔手提女儿送的酒水和烟返回黄鹤楼附近的家里。这是封城以来他第一次去汉口看望女儿和外孙。为此,他特意穿上了8年前妻子给他的生日礼物,这件皮大衣单价3800元。

武商广场 | 4.16

营业员李女士 · 白色防护套装
住在武昌的李女士今天第一次自己坐公交回家,之前一直是家人接送。家人叮嘱她穿好全套防护服。但李女士觉得,明天应该不需要穿那么夸张了。

武汉大学凌波门外 | 3.25

年轻摄影师 · 蓝色贝雷
两名年轻摄影师出门拍摄,轻车熟路地摘下口罩,躺在栈桥上。小猪佩奇在湖面静静观赏。

汉口民主一街 | 4.18

清洁工胡阿姨 · 防水裤腿
54岁的胡阿姨穿着自制的红色防水裤腿。家在湖北其他市县,整个疫情期间她都在外工作,春节也没能回家。每个月工资收入两千块。

汉口站 | 4.21

吉林汪大爷夫妇 · 碎花背带
72岁的汪大爷和68岁的老伴张大娘带着孙子回吉林老家。两位老人去年12月20日来武汉看望儿子一家,因为疫情滞留至今。

武昌得胜桥社区 | 4.11

市民应师傅 · 皮绳遛狗
应师傅终于有机会遛遛自家的大狗。他花了5000块训练它,大黑狗很听话。

武昌汉街 | 4.3

某Cyber市民 · 渐变色遮阳帽
太阳帽能遮挡飞沫,也是超现实时尚单品。

武汉长江大桥边 | 4.11

护士王玉新 · 医疗志愿队服
以个体身份驰援武汉的护士王玉新,即将回到沈阳,回归普通市民的生活。既没有出发时的壮行,回程也没有高规格的礼遇。回家最想做什么?“春节前刚买了车,还没开过。三个月过去了,我得回去保养它。”

武昌汉街 | 3.29

消毒志愿者 · 破洞防护服
汉街即将恢复营业,负责消毒的志愿者在进⼊下一个现场之前整理防护服。他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工作,防护服上已经出现破洞。

武昌汉街 | 3.29

园丁 · 铲花园丁
手持菜⼑作为铲子的园丁,口罩已经带了一整天。同行的摄影师给了她一个N95口罩,但她并没有换。

“
关于WUHAN FACES
眼光工作室(以下简称YG):怎么想到拍摄这组人像的?你的最初立意是什么?让你产生拍摄冲动的又是什么?
钟锐钧(以下简称Z):天胜街头的那个西装革履的大叔,也是我拍摄过程中印象很深的一个人。能感觉到是一个很在意自己外貌,并且平时有服装搭配习惯的人。我当时震惊了,在广州几乎不可能看到一个穿得如此正式的男士。更何况在疫情进行时。遇到他的时候我和同事在扫街,他从我面前走过,正好打了一个喷嚏,取下口罩用手帕擦鼻子,我当时就叫住他,给他拍了一张肖像。也是这个契机,让我想用人像来表现这个城市。
我最初是想拍一组Wuhan fashion的,疫情中的时尚,但觉得现在时机还不合适。最后变成了Wuhan faces。但其实没啥立意,最初只是想拍有趣的东西而已。让我产生拍摄冲动一个是好看,另一个是超现实,一个城市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穿着防护服在江边散步的。
YG:你的镜头曾经也对准过很多公众人物,再次回到普通人身上,感觉有什么不同?
Z:普通人戴着口罩,他们的脸就更没有辨识度了,这也是很特别的一点。明星都是会摆的,他们知道自己哪个角度好看,但普通人未必。这个时代,普通人更多是面对自己手机的前置镜头,他们在我们面前摆姿势,会有有趣的一面。比如上了年纪的阿姨,会很喜欢交叉脚站着,这就是很鲜明的特色,她们可能都有广场舞的经验。你就会知道那个年龄段的人拍摄的套路。男士可能就更放得开,就那么一站。年轻人爱耍酷。但我们会觉得中老年人更icon一点。
我看了太多专业的人怎么被拍。我会觉得这些人不专业,但他们有自己的审美。我觉得武汉人在他们自己的审美里也很努力。
YG:武汉这次给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这次疫情拍摄给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Z:之前来过两次武汉,一次是武广高铁通车的时候,第二次应该是18年,来武汉拍一次演唱会。但我对武汉一点印象都没有,基本是第二天就离开了。留下的唯一印象是很堵车,永远在搞建设。
这次对武汉的认识其实有点超现实,千万级的城市,早期的时候几乎人都见不到。现在看着它慢慢恢复,感觉还不错。
我觉得武汉是一个很有鲜明性格的城市,体现在武汉人身上。相比其他地方,武汉是个采访天堂,武汉人特别愿意被拍,特别愿意表达。友善,烟火气息很重,尤其汉口。
还没有梳理过这种感觉,但其实挺累的,尤其是早期,但后来(解封之后)心态上就往有趣的方向发展了。会觉得,诶,这个城市很有意思,并且能够观察到一个城市的变化。
YG:之前你有跟我聊过和张志韬老师用周黑鸭成功突围社区的故事,能描述下吗?
Z:那个是我第一次去得胜桥,当时我挂着记者证就去了,结果被轰出来了。后来打电话,但社区和街道也相互踢皮球,当时有点生气。第二天我就想了个办法,把器材装在周黑鸭的袋子里,上面盖了一件衣服,佯装本地人,就成功进去了。周黑鸭还挺管用的。
YG:拍摄器材是什么?想买徕卡Q2,为什么呢,这个相机是28的镜头,并不算好的人像焦段。
Z:Canon EOS RP,35mm或者40mm的镜头。但我和同事一直陷入没有带中画幅来的后悔之中,但后来觉得没所谓了,器材不太必要,重要的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
徕卡太贵了,也想把自己限定在28mm这个焦段里,逼着自己去拍一些街头的东西。
YG:这组照片里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吗?
Z:喜欢穿西装的大叔,桥上穿着皮衣的大爷,和拿着菜刀的园丁。和江边的摄影师阮阮后来闹翻了,她要求我用她p过之后的照片,但纪实摄影不能这么做,我的拍摄流程没有问题,不想让步。汉街的那对小情侣挺有意思,小姑娘后来把我的照片做了一些加工,拉长了自己的腿。
关于疫情拍摄
YG:在武汉拍摄了多久?拍过哪些题材呢?我看到目前的照片你有去过方舱医院,有拍过医护人员,开城的时候也有拍摄。
Z:2月5日到的武汉。刚到的时候就很想扎到汉口医院去,一是因为广东医疗队在汉口医院,二是汉口医院本身是一个“重灾区”。后来有机会进去了,也和广东医疗队的人住在了一起,和他们一起上下班。
2月11日的时候,已经有了拍“疫痕”的想法,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最美逆行者”。3月20日广东医疗队离汉之后,我开始扫街了,也渐渐开始关注武汉这个城市。
YG:疫情开始后官方话语把这次疫情称作一种抗战,你也曾经去过真正的战场,觉得战役这种说法准确吗?
Z:我觉得不太能做一个比较。我只能说我去过那些地方(战场)都没有这次那么紧张。这个东西(病毒)看不见。但比如我之前在泰国,在利比亚,我知道哪些地方可以躲,是安全的。在武汉就没有办法,危险看不到。两者的性质不太一样,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YG:怎么消解这种紧张呢?
Z:接触到广东医疗队之后我就不那么紧张和害怕了。我们一起接受了院感培训,也是在他们的带领下进入病区的,会有比较规范的防疫措施,我们防护不到位的地方他们也会指出来。我们最初自己住宾馆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回来怎么消毒。
他们对我们也特别好,会问我们防疫物资够不够用,会把富余的消毒酒精给我们,其中有一个队员直接把他的小型臭氧机送给我。这种踏实感让我不那么害怕了。
YG:封城之后来的武汉,现在解封也有一段时间了,解封前后的城市有什么不同吗?人们的情况呢?
Z:我们比较能观察到的地点:一个是集市和街巷,一个是江滩,还有一个是大街。解封前后,街上的人并没有爆发式的增长,那时候社区管控还是挺严的,人是慢慢多起来的,最近这五天,路上的车突然变得很多。不过人多了,街道上一些不文明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了。
2月5日刚来的时候,街上碰到的人是没有什么生气的。我那段时间和医疗队一起在路上走,因为会带着防护帽,所有人看到我们都会很明显地绕开走,甚至躲到马路对面,因为知道是从医院出来的。但后来医疗队准备回家的时候,我们在医院门口合影,会有人从楼里喊“谢谢你们,一路平安”。
还遇到挺好笑的事情,我们当时和广东医疗队住在一个酒店里,当时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广东医疗队每天就只能往返于医院和酒店,大家没地方去,整天待在房间又压抑。有天天气特别好,就一起到天台上吃盒饭,第二天就被隔壁楼的人举报了,说我们聚众聚餐。那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是医疗队,后来知道之后,还是那栋楼的人打开窗对我们喊“谢谢”。
现在的话,走在路上的人大多性格都挺开朗的感觉,说说笑笑,街上的气氛也很生活。
YG:武汉醒得最明显的地方是哪?
Z:我觉得是吃。几个朋友的描述也是这样,大家可能开始讨论,哪家外卖又开了,哪个小吃街开始排队了。大家会用吃来mark这个时间点。
YG:你是一个易感的人,这次有没有什么让你难以忘记的瞬间或者故事?
Z:那个是曾经的我。我拍照的时候是冷静的,反而不拍照的时候和其他人聊天时会能感受多一些。
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有经验的记者,情绪也相对稳定。但你见到的东西还是能影响到自己,这次也亲眼见到一些生死,记得当时在ICU拍摄的时候,有一个病患当时已经被告知脱离了危险,但一个半小时后病情突然恶化,就在我面前死亡了。我现在还能记得护士当时做了什么,怎么拔掉仪器,护士穿得是什么衣服,都记得。那种影响更像是在潜意识里进行的,我是一个睡眠质量及其好的人,但在武汉有几次都睡不踏实。
我记得解封之后我做过一个梦,有一天我终于要离开武汉了,我是坐大巴走的,上车地点是一个城门楼,我拖着行李箱往城门外面走的时候,发现外面是地震过后的意大利,我当时举起相机就开始拍,一边拍一边希望车开慢一点,想多拍点东西。那个画面挺模糊的,到处是尘土。画面的远处是一个游乐园的旋转木马,被震塌了,有一群孩子哭着朝我们走过来。我跟朋友蹲下来抱着孩子,和他们说着“OK,OK”,然后就哭醒了。人做梦是很难被记下来的,但那个梦在我脑海里非常清晰。我是一个很少哭的人,在武汉可能只哭过这一次。
关于摄影师身份
YG:几年前说过不想再做报道摄影师了,这次事件之后这种心态有变化吗?
Z:依然不想,我是一个娱乐摄影师。之前有段时间突发和娱乐一起跑,娱乐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缓冲。但我当时接到来武汉拍摄的电话时,是一点没犹豫的。我后来也有想过,原来我在碰到事情的时候我还是会去现场。这种心情挺复杂的。但我希望这些事情(突发灾难)不要再发生了。
但有一天我在汉口医院等医护人员下班的时候,我很直接地对自己说,回家以后想过一种很平静的生活。以后有这种事情,我可能会不冲在一线,但一回头,又觉得不能为以后的自己做决定。
在武汉第一次吃堂食的时候,我拼命想抓住那种感受。我太想过回正常的生活了,这应该是我回广州之后的方向,继续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
YG:最初约稿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钟锐钧是肖像很棒的摄影师,怎么定义自己的摄影身份?想要有一个定义吗?
Z:并不是吧。对我来说拍照片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在工作角色中并没有很享受它,但在生活中,拍摄生活场景,或者对大家没有用的东西会让我开心。
对我来说,摄影是让我自己记住事情的方式,我在看照片的时候我会回想起当场的气味,当时的气候,这种感受是被照片勾出来的,我会很享受。
要定义的话,娱乐摄影师吧。定义更像是别人说的,我自己高兴就好了。
YG:看到之前的采访,说你在每个活动都会发飙爆粗,这几年脾气有好些吗?这次有没有发飙?
Z:脾气好了很多。我想通了,很多时候发飙并不能解决问题,挺耗自己的,先解决问题再说吧。现在会稍微理性一点。
YG:在武汉拍摄之余会做些什么?会听什么歌呢?会不会看一些剧或者电影吗?
Z:还好,都听平时听的歌。Techno(科技舞曲),HVOB,朴树,张悬,或者谍影重重第二部的原声带。最近不太会看剧,生活挺简单的,除了拍摄就回宾馆睡觉了。我是一个超级咖啡爱好者,现在武汉开了的比较有名的咖啡店我都去过。
YG:疫情期间有你喜欢的摄影报道或者摄影师吗?
Z:喜欢一组New York Tough,是老老实实的一组报道摄影。
YG:离开武汉后最想做什么?
Z:回家,撸我的猫,我有四只。马上就回去了,已经网购了一些咖啡豆,准备回家好好给自己煮一杯咖啡。
”

摄影师钟锐钧,广州人,2007年进入南方都市报至今

摄影 / 南方都市报 钟锐钧
编辑、设计、采访 / 宗辰
文字 / 宗辰、钟锐钧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