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重建纽带 ——伽达默尔论友谊与团结
编者按:在现代“原子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日益加剧,共同生活的纽带也逐渐消失;面对这种情况,伽达默尔呼吁人们发现真正的团结。在伽达默尔看来,共同生活的纽带是一种非对象性的知识,它因共同体经历的共同历史而实现,因此重建纽带意味着去倾听历史的声音,感受历史的温度。为了保证这种对团结的领会,伽达默尔强调了友谊的重要性。在建立友谊的过程中,人们意识到了自我与他人的边界。个体因面对他人而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并且意识到与他人的共同之处。伽达默尔用Oikeion来形容这种共同性,这种Oikeion中也包含了陌生人,从而它也指向了团结的场域。因此,借助友谊,人们能更好地领会那种将人们团结起来的共同纽带。
引言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审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二十世纪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伽达默尔试图回应历史主义的危机(注1):如特洛尔奇所指出的那样,“严格应用历史方法将导致一切有关人的确切知识的消亡,导致所有稳定的价值的相对化”(注2)。伽达默尔将这种历史主义称为“第一等级的历史主义”,而他应对危机的方法则是提出一种“第二等级的历史主义”,强调“并不存在任何永恒的真理。真理就是与此在的历史性一起被给出的存在的展开”(注3)。另一方面,伽达默尔积极地发挥解释学的伦理学与实践哲学维度,意在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诸如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个体原子化等进行回应。随着1978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的出版,伽达默尔的这一角色越发凸显了出来。

事实上,伽达默尔所扮演的这两种角色的语境是共通的:现代社会所涌现的种种伦理政治问题,其根源之一正是历史的断裂与传统的缺失: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仿佛仅仅成为了单纯的”过去之事”,从中我们无法听到事关当代的任何回响。如历史学家诺拉所言,我们正在“越来越快地跌入一个不可逆转地死去了的过去”,“我们的经历中根植于传统的温暖、习俗的心照不宣和传承的往复回环之中的东西”正被连根拔起(注4)。因此,通过抢救式地发掘、援引经典来为现代社会的困境找到出路,成为了二战后知识分子,尤其是流落美国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决心。在阿伦特那里,这一点表现为对经典之“权威”的呼唤;而在伽达默尔这里,解释学似乎具备这种可能性。在伽达默尔看来,“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 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注5),因此历史便成为了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共同之处,从而有可能以此为基石重建现代社会中已然支离破碎的人类共同生活的纽带。这种因共同性而联结在一起的人类生活,伽达默尔称之为“团结”(Solidarity)。
然而这绝非易事,首先这一方案面临理论上各种挑战。在舒尔茨看来,这种“第二等级的历史主义”无非是传统历史主义“反思的、深思熟虑的”另一种形态;而施特劳斯则更加直接地指出,这种发端于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因其彻底性而将走向彻底的相对主义:“我们发现所有客观的、理性的知识之根基乃是一个深渊。最终,支持着一切真理、一切意义的别无他物,只是人的自由。客观地看,最终只有无意义性、虚无。”(注6)根据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循环,我们只能理解我们已经具备了“前理解”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能够确保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滑入主观性与随意性的泥淖?而倘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理解,共同的纽带又何以可能?
伽达默尔自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真理与方法》中他指出,尽管我们对文本的理解总是以“前理解”为条件,但前理解在“完满性”上也有程度的不同,一种“完满性的先把握”要求尽可能地放低解释者的姿态,倾听“事物本身”的声音(注7)。但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对此伽达默尔真正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倾听“事物本身”的声音,而在于倾听他人的声音。“他人也许是正确的,这种可能性乃是解释学的灵魂。”(注8)这一点体现在伽达默尔对“友谊”的分析之中。
团结:共同生活的历史纽带
在1967年题为“专家的局限性”的讲座中,伽达默尔指出了现代社会的高度官僚化、组织化以及官僚化,传统的力量疲敝,宗教与教会难以提供将人们统一起来的力量。然而伽达默尔依旧相信人们可以团结在一起,在人类生活的各种准则背后,依旧有一种深深的团结——但这种团结并不明晰,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公共生活是有缺陷的,因为它过于强调不同的、有争议的,强调那些被辩驳和被质疑的。因此,我们所真正共有的东西,以及那些把我们联结起来的东西,可以说是喑哑无声的。”因此,尽管还存在这样一种团结,但它并没有展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在这里,伽达默尔所使用的祈使句仿佛是在表明,连他自己也并不知道这种团结是什么,但他要求我们“去觉察那将我们联结起来的东西”(注9)。1986年,伽达默尔在演讲中再次提到团结,此时他的口吻变得更加急切:“去发现现存的真正的团结,仅仅是这一点都已经变得难以置信得困难,在我看来这对于我们的处境来说是最危险的。”(注10)但他依旧没有直接指明这种团结是什么,或者说到底什么才是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1993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又将“更普遍地意识到我们深深的团结”当做现在最紧急的政治任务(注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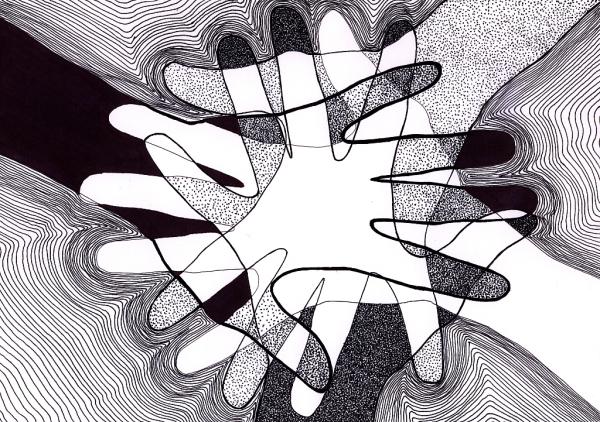
对于团结的“歧义性”,伽达默尔意味深长地说,“我可不是随意说说而已”。亚里士多德谈到,“当城邦的公民对他们的共同利益有共同认识,并选择同样的行为以实现其共同的意见时,我们便称之为团结。”(注13)而在这里伽达默尔并不仅仅是在批评那些因个人利益而放弃共同利益的人,而是通过这种歧义性思考是什么让人们真正地团结在一起。“Soldium”一词的歧义暗示了,哪怕人们追逐的是私利,他们也必须考虑可靠性的问题。而“Sold”只有在共同体中流通才能成为真正的钱而不是伪币。“Sold”的可靠性来源于共同体之“Soldium”的保障。换言之,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即便在背离的情况中,我们依旧能找到某种团结。如此,让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东西必定比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更为基本,它提供着团结的纽带,但却默默无闻。
这种团结因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无区分的统一而得以可能:在两者被单独拿出来作比较之前,它们就处在这样一种统一之中。此时,个体将无法区分什么是个人利益,什么是共同利益;他们好像自说自话,但又像达成了一致。为了共同利益放弃个人利益,这一点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团结。因为意识到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分离这一点已然成为了个体与共同体的隔阂。在谈论团结的时候,伽达默尔的措辞是:我们并非是发明团结,而是去发现那种现存的团结并加强它。从而,人们总已经达成了某种共同性,尽管人们对此还未能觉察。
因此,借助“歧义性”,伽达默尔所暗示的是一种“前反思”的团结:他们难以说出是什么将它们联结在一起,因此人们事实上团结着,但他们甚至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唯有这种团结才能超越功利主义式的利益换算,并使得真正的共同生活得以可能。而即使人们事实上已经不再团结了,这种团结依旧作为一种潜能暗藏于人类生活之中,因为那使得人们得以团结起来的共同之处并不会因此而丧失。由此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伽达默尔始终在谈对团结的觉察而非发明,因为它无法被形塑,只能形成于潜移默化之中;我们也得以理解,为什么伽达默尔并没有指明这种使得人们得以团结的共同之处是什么,而只是让我们去发现;因为它并非某种可以被指出的对象,它需要人们去切身领会,而对这种共同之处的领会本身就可以将人们引向团结。
Walhof同样认为,伽达默尔所说的团结并非一种对象性的知识:“将团结视为对公共善的关心或对共同利益的追求,这使得团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自觉意愿……伽达默尔不希望将团结还原为被意识到的共同利益,因为这种还原错失了政治共同体之下共同生活的丰富性的复杂性。”在他看来,这一点使伽达默尔的团结有别于罗蒂所说的基于身份认同的团结。在后者看来,我们只有依据某些“相似性”,将他人看做“我们的一员”时,团结才有可能;这也允许人们去扩大团结的对象。而在伽达默尔看来,由于团结并非意识的对象,我们无法仅仅依据相似性而互相团结。我们对于这种团结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将其回忆起来(注14)。
无疑,这种团结是有限度的,它无法像罗蒂的团结那样无限扩张。如Walhof所言,它与特定的历史阶段与文化背景有关,因此它所能团结的只能是某个特定组群中的人。更准确地说,它是历史给予某一共同体的珍贵礼物,经过漫长的、乃至以代际计算的岁月,它逐渐沉淀成为这一共同体的遥远记忆,并具身于风俗、习惯、仪式、器物乃至最日常的语言交流中。伽达默尔所说的这种前反思的、使得团结得以可能的东西,接近历史学家杨·阿斯曼所说的文化的“凝聚性结构”:在其社会层面上,这一结构构造了一个“象征意义体系”,“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这个空间起到了连接和约束的作用,从而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并且为他们指明了方向。”(注15)这种结构根植于历史并因历史的积淀得以可能;就在这同一过程中,历史也逐渐成为了这一共同体的历史,它所具有的丰富性远远超出了事件与事件单纯的接连相续。因此,共同体的团结是有深度的团结,而共同体的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
友谊:自我、他人与Oikeion
人们事实上已经团结着,但人们总是一再地将其遗忘,在伽达默尔看来,我们要做的仅仅是觉察它的存在,也即将其回忆起来。这种回忆不会回想起某种具体的东西,它呈现为一种朝向共同体之共同历史的姿态,从这一姿态中那种将人们联结起来的共同之处将得到呈现并且被领会,尽管它们不能被对象性地指出。
但这一计划存在着一个缺口:团结是一种扭结性的力量,它联结的是个体与共同体,因此仅通过团结,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纽带是无法被保证的。这样就始终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有他们不同的对团结的领会。换言之,他们确实听到了历史的声音,但他们听到的是不一样的声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共同体的团结最终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伽达默尔对团结的论述揭示出为人类共同生活进行奠基的本体论可能性:人们确实可以说,共同体因历史所提供的纽带而得以可能重新团结;但在实践上,需要追问的问题则是,是否每个人都能无所偏离地发现这种团结?对此我们需要“友谊”。
相比于团结,伽达默尔在友谊问题上花的笔墨要更多一些。1928年,伽达默尔在马堡大学任教的就职讲座即以“友谊在哲学伦理学中的角色”为题。80年代,伽达默尔在多篇文章中谈到了友谊,并且对其重要性予以高度肯定,其中较为专题性的考察见于《价值伦理学与实践哲学》以及《友谊与自我知识》。在此之后,友谊主题在1999年的演讲《友谊与团结》中得到了更多的论述。除此之外,在2000年发表的文章《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主体与人》之中,伽达默尔讨论了海德格尔对他人与有限性的看法,并提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关切,在思想进路上这也与友谊的主题一脉相承。
通过对古希腊伦理经验的考察,伽达默尔指出友谊的主体间性特征:它是一种善好,但并不是一种德性,因为它不是个人的品质;友谊要求一个人具有各种结友的能力与禀赋,但却不能就此保证一定能结成友谊。伽达默尔珍视友谊所体现出来的他异性,在他看来“:像友谊这样的现象,它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不能通过自我意识来正确地理解”,这一点使他对海德格尔的“共在”有所不满。“对海德格尔而言,共在乃是他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退让,‘操心’总是对其本己的存在的一种操劳……实际上,它是有关他人的一种弱观点,更多地是让他人存在,而不是真正的‘对他人有兴趣’。”(注16)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有限性与被抛的论述深刻地启发了伽达默尔,但伽达默尔认为他错失了真正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每个人原则上都是有限的。我所关心的是,为什么我要通过与他人的照面才能经验到自己的局限”(注17)。在他看来,我们不仅需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还需要认识到这种局限是可以借助“对话性的、交互性的解释学过程”而得到超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与他人的友谊,“他者,或者说朋友,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不是因为他的需要或匮乏,而是为了他自己的自我实现(self-fulfillment)。”(注18)
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伽达默尔也认为友谊同样含有“自爱”的面向,早在1928年他就已经强调,友谊中的这种自身关联性(self-relatedness)不能被还原为主体性的结构(注19),而自爱也不能自私或自足(self-sufficieny)意义上被理解,它是迎接他人的必备条件。与此同时,伽达默尔赋予自爱的另一种重要含义是,真正的自爱要求“持续地与自己取得一致”(注20),而这恰恰需要他人的参与才得以可能。这也即“自我实现”意义上的自爱。自我将他人当做自己的镜子,他从他人身上认出了自己,而在理想的友谊中双方都将因此而达成一种“互惠的共感知”(注21)。这种“互惠的共感知”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自我实现与自我提升,原因在于我从他人身上获得的自我认识,比我原本具有的更为完整:“一个人从镜子中辨认出的,是由于他自己的弱点而无法清楚地看到的东西。”(注22)之所以“持续地与自己取得一致”只有在于他人的友谊中才能首先,正是因为我无法仅凭借自身之力去认识真正的自己。只有借助友爱而完成的自爱才能被提升至如此高的地位:“所有与他人的可能联系以及对自己的责任, 在此自爱中, 都得到了真正的基础与条件。”(注23)
看上去,这里存在着一个自爱与友爱的循环。一方面伽达默尔宣称“友谊首先就是人们与自己的一致。人们需要这样的前提, 才能与他人联系在一起”(注24),另一方面只有借助他者之镜才能获得对自身更为完整的认识,从而才可能与真正的自己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友谊的推进与自我认识的提升是互相交织的、永无休止的进程。在这里,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何者在先,而是这样一个问题:我出于自己的弱点无法看到的“真正的自己”究竟是什么,以至于它出现在他人那里?
我们需要将“互惠的共感知”看做一种真正的主体间性:不是我,也不是他,而是我和他所共同构成的“我们”才是这种共感知的所属者。自我单凭一人之所以无法对其“真正的自己”有足够的明察,正是因为这种“真正的自己”并不属于他。它能在他人身上被看到,但它也并不属于他人。更准确地说,它在他人那里的显现是因为他人与自我形成的共同生活。这种共同生活提供了自我理解他人与理解自己的土壤,自我与他人“互惠的共感知”只有“通过参照相互间的共同之处而互相理解”(注25)才得以可能。所谓的自我知识“并不意味着对自己比对别人更有兴趣;它恰恰与自己和他人的共同之处相适。一个人带着赞许或责难地从这样一面镜子中看到的,并不是他自己的特殊性,而是那种对他自己和别人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注26)。
在1999年的演讲中,伽达默尔谈到“Oikeion”一词便与这种“共同之处”有关。这个有家园和故乡的含义。但我们却很难具体地讲明它到底是什么,因为“故乡是某个无法清楚地追忆的地方;是某个无法解释的地方——为什么它总是萦绕着我们的灵魂, 又将人们联系在一起。故乡与出身就表现出某种联系,某种共同体,某种真正的团结。”家园或者故乡是共同生活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成员必定具有相似性,如同在“团结”的主题中那样,伽达默尔否认了可以从相似性推出友谊。在分别谈论了几种不同类别的友谊之后,伽达默尔貌似离题地谈到希腊人对存在的理解:并非将其理解为种属,而是看做“那种闪耀动人,却又在遥远、持久与永恒中散发出迷蒙之光的东西。”伽达默尔暗示了Oikeion与存在之间的可能联系:如同存在一样,Oikeion也无法被归纳为种种相似性,由于其含义的丰富,它无法被对象化的概念所描述,“人们只能经历友谊,却不能定义它。”(注27)如此,这种Oikeion同样具有前反思的特征。在自我与友爱他人之间所充盈的就是这样一种Oikeion的光晕,从中折射出自我与他人的共同之处。这种共同性并不仅仅是自我与他人两个人的共同,通过对Oikeion一词的援引,伽达默尔进一步打开了这种共同性:Oikeion呈现为一种能够同时包容自我和他人的家园,在其中我们还能发现陌生人,尽管他们并不因同在家园之中而成为友谊的对象,但他们也具备结友的可能性。因此,Oikeion指向了团结的场域。
在团结与友谊之间
我们很容易发现友谊与团结之间的亲缘性。亚里士多德指出“团结似乎就是政治的友谊”(注28)。但在伽达默尔这里,他从未详细地谈及友谊与团结的关系。在1982年的文章中,他谈到友爱在实践哲学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时,也提到了“它包含了一种支配一切意识、一切欲望的团结”(注29)。另一处他谈到“(友爱是)一种持续性的团结,它让人类之共同生存的有序组织得以可能”(注30)。在1999年的文章中,两者间的关系似乎被突出地强调了,但他仅仅指出“在友谊与团结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状态”,“人们从‘友谊与团结’ 这个题目立即可察觉到其中所蕴含的某种充满张力的真理”(注31)。
如我们上述分析所见,伽达默尔提出团结与友谊的时间与语境是相近的,即都在试图重新建立人类共同生活的纽带。但两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Walhof认为,“团结是一种局部的、暂时的纽带,它反映了一种互惠的共感知的公民的共同生活——这种纽带可能包括友谊的纽带,但也可以延伸到我们的朋友以外的公民……随着友谊不断揭示朋友之间的交织生活,友谊现象凸显并使我们习惯于去揭示公民同胞之间的交织生活的新方式。”(注32)他所沿循的是亚里士多德对友谊与团结的解释,也即团结的对象里面包括了那些不是朋友的人。在他看来,团结包含了友谊,而友谊作为一种更为敏感的形式,有利于加强人们对新的团结的可能性的感受。这一看法的要点在于,他将人们在友谊中所达成的自我知识的提升看作某种对新的共同体知识的领会,也即对一种新的共同体纽带的可能性的领会,从友谊中的个体出发,这种领会或将推至整个共同体,从而共同体的团结便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含义。
然而,如果将伽达默尔的思想放在历史的断裂与传统的丧失的语境下,这一解读或许将形势看的太乐观了些。想一想伽达默尔在几次演讲中流露出来的悲伤口吻:仅仅是回想起现存的团结,这一点对于我们而言就已经极为困难了。伽达默尔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与“非我们”的人团结,而是“我们”自身如何团结。当务之急不是探索新的团结的可能性,而是抢救性地去回想起那些原本就在的、正在被遗忘的团结的可能性。
一方面,伽达默尔所说的友谊通过引入他人的维度,超出了个体-历史的解释学循环。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与法国哲学家诸如列维纳斯等关于他人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面对他人,自我意识到自身的限度以及理解的缺陷,从而使一种更为完满的先把握成为可能。只有借助他人,而非海德格尔所谓的“常人”的声音(注33),人们才能修正自身偏颇的前见,并且不至于落入主观性与随意性之中。
另一方面,伽达默尔又认可了自我与他人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的价值,以及作为自我与他人之中介的“共同之处”的重要性。而友谊中闪现的Oikeion不仅是两个人的世界,它指向的正是一个有关陌生人的团结的场所。在友谊的最深处,我们发现了它与团结的连续性,尽管Oikeion如同存在一样迷蒙。因此,友谊不仅使人不断超克自身的有限性从而有机会审视并改进对自我、历史以及共同体的理解,它还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种约束着并连接着自我与他人的东西,即Oikeion,对共同体的联结也具有提示的作用。
总而言之,通过对友谊的阐述,伽达默尔提供了共同生活之共同性,也即团结的纽带的明见性保证。个体对共同体之共同性的领会,在面对他人时体现出有限性,但这也正是克服偏狭的契机。与此同时,在个体一次又一次的、不断进展的友谊中,我们能感受到来自Oikeion的律动,这种律动有望去矫正已经失序的现代共同生活的节奏。在历史断裂、传统丧失的情境下,友谊中所闪现的“共同存在”的迷蒙之光,或许比理论和冥思更有可能唤起共同性。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纽带位于历史之中,伽达默尔呼吁人们将其回想起来,但并未指出如何具体的方法;友谊或许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对那种团结的回想因此不是封闭的思考,而是投身于共同的伦理生活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团结与友爱之间的“张力”,实际上就是共同历史与共同存在的张力,而这也是我们生活的真理。
引用文献:
1.G. 舒尔茨指出,面对历史主义的崩溃,德国哲学做出了两种克服的尝试,第一种是以新康德主义与胡塞尔为代表的路径,即寻找“超历史的、普遍有效的价值上之支撑点”;第二种即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尝试:“朝向生命及现在、朝向发生着的历史”,“当它在历史的无可回避之河中共潜共泳而尝试去安排自身时,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的历史主义。”见G. 舒尔茨,《诠释学中的历史主义之争》,林维杰、潘德荣译,安徽电力职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7期;相关的讨论见宋友文,《历史主义与历史性》,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5期。
2.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彭刚、顾航译,译林出版社,2014,第25页。
3.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Ⅱ: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19页。
4.皮埃尔·诺拉,《在历史和记忆之间》,转引自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
5.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Ⅱ: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92页。
6.列奥·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潘戈编,郭振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76-77页。
7.关于伽达默尔提出“完满性的先把握”从而试图超出解释学循环的封闭性问题,可参见何卫平,《略论伽达默尔对解释学循环的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8.转引自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197 页。
9.Hans-Georg Gadamer,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pert”, in On Education, Poetry and History, ed. Dieter Misgeld and Graeme Nichols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192.
10.Hans-Georg Gadamer,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Yesterday, Today, Tomorrow”, in On Education, Poetry and History, ed. Dieter Misgeld and Graeme Nichols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59.
11.Hans-Georg Gadamer, Gadamer in Conversation, ed. and trans. Richard E. Palm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80. quoted in Darren R. Walhof, “Friendship, Otherness, and Gadamer’s Politics of Solidarity”, Political Theory, 2006, 34(5).
12.Hans-Georg Gadamer, “Friendship and Solidarity”,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2009,39(1). 中译参见伽达默尔,《友谊与团结》,林维杰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1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1页,1167a25-26.
14.Darren R. Walhof, “Friendship, Otherness, and Gadamer’s Politics of Solidarity”, Political Theory, 2006, 34(5).
15.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页。
16.Hans-Georg Gadamer, A Century in Philosophy: Hans-Georg Gadamer in Conversation with Riccardo Dottori, trans. Rod Coltman and Sigrid Koepke, Continuum, 2004, p23.
17.Hans-Georg Gadamer,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subject and perso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2000.33(3).
18.Hans-Georg Gadamer, “Friendship and Self-knowledge”, in Hermeneutics, Religion, and Ethics, trans. Joel Weinsheim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8.
19.Ibid, p131.
20.Hans-Georg Gadamer, “Friendship and Solidarity”,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2009,39(1).
21.Hans-Georg Gadamer, “Friendship and Self-knowledge”, in Hermeneutics, Religion, and Ethics, trans. Joel Weinsheim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8.
22.Ibid, p139.
23.Hans-Georg Gadamer, “Friendship and Solidarity”,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2009,39(1).
24.Ibid.
25.Hans-Georg Gadamer, “Friendship and Self-knowledge”, in Hermeneutics, Religion, and Ethics, trans. Joel Weinsheim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8.
26.Ibid, p139.
27.Hans-Georg Gadamer, “Friendship and Solidarity”,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2009,39(1).
2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71页,1167b4.
29.Hans-Georg Gadamer, “The Ethics of Value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in Hermeneutics, Religion, and Ethics, trans. Joel Weinsheim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18.
30.Hans-Georg Gadamer, “Citizens of Two Worlds”, in On Education, Poetry and History, ed. Dieter Misgeld and Graeme Nichols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219.
31.Hans-Georg Gadamer, “Friendship and Solidarity”,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2009,39(1).
32.Darren R. Walhof, “Friendship, Otherness, and Gadamer’s Politics of Solidarity”, Political Theory, 2006, 34(5).
33.也有论者认为,海德格尔的“良知”的来源可能是与共此在,并因此指出在“常人”那里也存在哲学性的友谊的维度。参见陈治国,《哲学的友爱: 亚里士多德、 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