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澎湃思想周报|提高性同意年龄之争;大流行下的世卫危机
提高性同意年龄的争议
N号房事件背景下启动的对国内儿童色情网站的调查结果尚未公布,上周,上市公司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鲍毓明被指长期性侵“养女”一案再次引爆舆论场。其中,鲍毓明的专业法律人士身份、与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媒体报道中的立场选择等因素,都使得这一事件极具复杂性。
针对上述观点代表的自由主义与家长主义的争论,罗翔教授也在其个人公众号“罗翔说刑法”上作出了回应,他表示自己赞同缓和的家长主义与禁止剥削的混合理论,但也承认这种立场有一定的弊端,“比如它可能导致权力的扩张,国家会以保护为名过度干涉个人自由。而法律的平衡点需要不断去探究。
此次事件中,多家国内媒体的报道方式引起争议,《全球深度报道网》发布的访谈“法国调查媒体Mediapart如何报道性侵案件”或能带来启发。Mediapart 是几位曾在法国《世界报》(Le Monde)工作过的记者于2008年创立的独立调查报道网站,近十年来刊发了多篇影响深远的性暴力报道,包括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丹尼斯·鲍平(Denis Baupin)性骚扰同事的案件、法国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在青少年时期被导演克里斯托夫·鲁吉亚(Christophe Ruggia)多次性骚扰的案件等等,调查过程往往长达数月甚至一年,成功让性暴力成为新闻业关注的议题之一。
在这篇《全球深度报道网》法语编辑 Marthe Rubió对Mediapart 资深记者 Lénaïg Bredoux 和 Marine Turchi的专访中,关于性暴力议题,Bredoux指出调查报道行业仍然是男性主导的,性暴力在很长时间内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Turchi则表示,直到今天,性暴力、杀害妇女和恋童癖犯罪都只是出现在报纸“其他新闻”的栏目中,没有人深入调查其背景和沉默背后的共谋。谈到性暴力调查的方法,两位受访者指出,对性暴力的调查应该像调查政治和金融案件一样,要有一套核查系统,要对自己写的东西负责,确保即使上交法庭也无可指摘。Turchi还提到,在揭发反腐的案件中,证人们会将自己视为吹哨人,而在性侵案中,证人往往是最难被说服开口说话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明白在案件中他们证词的巨大作用,而记者在使用这些证词时必须负责人,要明白报道对于他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而在被问及与性暴力受害者的关系时,Bredoux表示,记者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关心他们,她经常把非政府组织的电话给受害者,但从来没有鼓励他们去求助,因为记者的职责是报道事实,而不是劝人们应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疫情下重温托尼·朱特社会民主主义演讲
近日,微信公众号“东方历史评论”推送了“托尼·朱特最后的演讲: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一文,该文改编自这位历史学家生前于2009年10月在纽约大学所做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后收入文集《事实改变之后》(陶小路 译),虽已过去十年,但对于理解正在被新冠疫情的大流行重塑的全球政治经济仍有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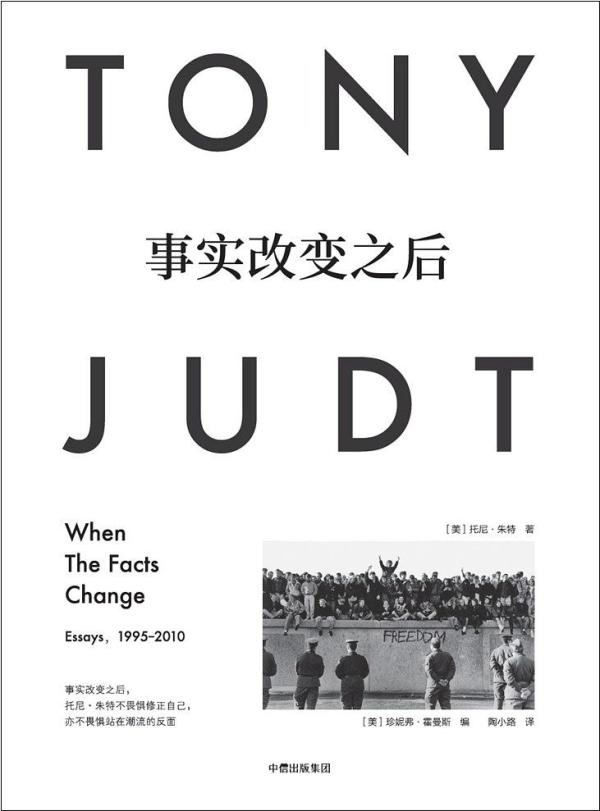
托尼·朱特从美国人既渴望更好生活又反对福利制度的认知失调出发,指出“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当下提出质疑的能力,更不用说提供替代方案。”他由此开始追溯今天人们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普遍诉诸“经济主义”这一偏见的历史脉络,指出“只考虑利润和亏损(最狭义的经济问题),避免做道德上的考虑并不是人类天然的状态”,而是后天习得的。18世纪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孔多塞侯爵对于资本主义侵占“自由”的预言,都说明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中从来不乏对政治的思考。此后一场漫长的辩论导致了今天这个时代狭隘的经济学视角。
文章中说,这场辩论中影响最大的是五位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他们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纳粹入侵并占领其共同的母国奥地利的历史所震撼,此后的流亡生涯中,在试图回答自由社会为何会崩溃并被法西斯主义所控制时,他们的答案是左派在1918年后的奥地利引入国际计划经济体制的尝试失败,直接导致了极右的反动,他们由此认为,捍卫自由主义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政府远离经济生活。
然而,在同样的历史挑战面前,英国思想家凯恩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认为,“上升到不安全和集体恐慌水平的不确定性会形成一种腐蚀力量,这种腐蚀力量曾经威胁并可能会再次威胁自由世界”,因而寻求让国家的社会保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凯恩斯主义取得的普遍成就是在战后信奉它的国家中成功地遏制了不平等,更大的平等使得对极端主义政治的恐惧减弱了,然而福利国家的悖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成功会削弱其吸引力,对那段恐怖历史没有记忆的后代人不再对社会民主制抱有共识。1970年代后期撒切尔-里根主义下的一系列改革使得不平等再次成为西方社会的问题。
在朱特看来,美国1996年颁布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是倒退到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做法,它与近两个世纪前英国的《新济贫法》如出一辙,都是迫使穷人和失业者在低吸引力的工作和低水准的救助之间做出有辱人格的选择,而二十世纪中叶的福利国家认为“只有参与经济活动才能具备公民身份是极不妥当的”,接受公共援助成为了公民享有的一项正当权利,而不再与耻辱挂钩。尽管后者意味着更高的经济成本,但朱特认为,在前一种方案中穷人所受到的羞辱也应当被量化并计入社会成本。同样的,过去30年间被很多政府推崇的私有化不仅低效,而且存在道德风险,而被私有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若运行不善仍然是政府的责任。私有化取消了国家的责任,损害了它的能力,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间机构不复存在,互惠服务与义务组成的网络随之消失,这些损失难以从经济角度作出衡量。
朱特认为,要回答何为“好社会”,应该对不受限制的市场的缺陷和不负责任的国家进行道德批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安全时代,经济上没有安全感,文化上也面临不确定,比二战以来任何时候都缺乏对集体目标、环境福祉或人身安全的自信,因此必须重新审视二战后的一代人如何应对类似的挑战和威胁。在此情形下,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更自信地讲述自己过去取得的不凡成就:社会服务国家的兴起、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作为权利的福利的确立以及提供福利成为一项社会责任。“带着畏惧之心的社会民主主义”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退群”的美国和世卫的困局——一个全球问题
在美国世界4月14日的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宣布美国将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他指责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及时分享疫情信息,没有及时提供防疫政策建议,没有及时宣布“全球大流行”等。特朗普称“在这么长时间后,是时候让他们为此负责了”。

对此,世界卫生组织(WHO)在4月14日发表声明, 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危险的挑战之一。首先,这是将对人类造成严重健康和社会经济后果的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拥有数千名工作人员,他们身处前线,在会员国抗击病毒的过程中提供指导、培训、设备和具体的救生服务,以支持会员国及其社会,特别是其中最脆弱的国家与新冠进行抗争。我认为必须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因为这对世界赢得与新冠病毒的战争的努力至关重要。这种病毒在我们的一生中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做出前所未有的反应。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相同的事实可能被不同的实体作出不同的解读。一旦我们最终翻过新冠病毒的这一页,我们必须花上大量时间来充分回顾这次危机,以便了解这种疾病是如何出现并如此迅速地在全球传播并且造成破坏,以及有关方面如何对危机作出反应。我们所吸取的教训将对有效地处理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挑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不是那个时候。现在也不是减少世界卫生组织或任何其他人道主义组织用于抗击病毒工作的资源的时候。”
WHO的作用与困境
CNN4月15日的一则报道指出,作为成立于1948年的联合国机构,WHO的成立是为了协调国际卫生政策,特别是关于传染病的政策。该组织由194个成员国组成,并由其运营。每个成员国都选择一个由卫生专家和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代表该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该组织的决策和决策机构)。成员国直接控制组织的领导和方向——大会任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确定其议程和重点,审查和批准预算。自成立以来的70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取得了许多成功的成就:它帮助根除了天花,减少了99%的小儿麻痹症病例,并且一直在应对埃博拉等疫情的斗争中处于前线。 同日,《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提到,在像应对新冠病毒这样的紧急情况下,WHO旨在作为一个中央协调机构 ,指导遏制病毒,宣布紧急情况并提出建议,与各国共享信息以帮助科学家应对疫情。 但是,WHO在其运营过程中也遭遇了相应的问题。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它缺乏有意义的执行权,并且受到预算和政治压力的影响,尤其是来自美国等强国和盖茨基金会等私人出资者的压力。
世界卫生组织的收入来自分摊会费和自愿捐款。分摊会费基本上是强制性的会费,联合国会员国必须按份额和财富确定的比例缴纳份额。WTO的数据显示,自愿捐款约占其总预算的80%,这些自愿资金可以来自成员国、国际组织和非营利组织,通常专门用于特定项目。 其资金来自参与国和私人基金会,而美国是其中最大的捐助国,占其预算的14.67%。美国的捐款几乎是第二大捐款国英国的两倍,英国贡献了世界卫生组织预算的7.79%。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支付了预算的9.76%。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的大部分资金用于消灭小儿麻痹症,开发疫苗以及增加获得基本保健和营养服务的机会。在美国,只有2.97%的捐款用于紧急行动,而2.33%的资金被指定用于疫情的预防和控制。乔治敦大学奥尼尔国家和全球卫生法研究所所长劳伦斯·戈斯汀(Lawrence O. Gostin)说,美国约有70%的资金已经用于它指定的计划,例如针对艾滋病、心理健康计划、癌症和心脏病预防。
另一方面,许多WHO的会员国也拒绝完全遵循WHO的建议和规则行事。根据《纽约时报》3月12的报道,在WHO公开表示共同抗击新冠病毒的重要性后,数十个国家无视国际规则,无视自己的义务。根据规定,各国有义务在48小时内向卫生机构报告其采取的超出集体指导原则的任何措施,并报告其采取行动的依据。在冠状病毒爆发期间,许多国家未能做到这一点,世卫组织对此无能为力。还有一些人无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制定了国际旅行限制,而且没有通知全球卫生官员。世卫组织一再警告说,国际禁令可能会阻碍所需的资源,或延误援助和技术支持。世卫组织说,这种限制只有在疫情开始时才合理,以便为各国争取时间做准备。除此之外,它们更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危害。此外,一些国家不愿解除防护装备出口禁令,这让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更加复杂化。法国和德国已经限制了这类设备的出口。 “我们可以理解,政府对本国的卫生工作者负有首要责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表示,他敦促各国停止囤积物资,并呼吁全球团结一致。而由于缺少对于会员国的惩罚和约束措施,WHO在本次新冠危机中疲于协调会员国的行为,并显示出了其被动的一面。
来自美国的指责和被转移的责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批评中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对病毒威胁的反应太慢,并且未对中国作出批评。然而《纽约时报》4月11日的一则报道指出,早在一月份, 特朗普政府就被告知新冠病毒有暴发的可能性,特朗普本人也曾在推特上称赞了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抗疫措施。 根据《卫报》的报道,关于世卫组织获取病毒样品的延误影响了各国防疫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中国科学家于1月11日公开发布了新冠的基因序列。到2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分发新冠测试,但美国政府选择不让它快速通过审批。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进行了自己的检测,但它存在缺陷,必须召回。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美国的测试将推迟6周以上。 特朗普表示,世卫组织非常以中国为中心;但是,他并未对这样的说法作出解释,也未能阐明这与美国国内的大规模感染有着何种联系。

事实上,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由其部署的针对移民的政策和一系列“孤立主义”措施都影响了世卫组织的运作。乔治敦大学奥尼尔国家和全球卫生法研究所所长劳伦斯·戈斯汀(Lawrence O. Gostin)说,“多年来,美国也一直是世卫组织的‘眼中钉’,世卫组织在获取药品方面的一些努力受到了阻碍,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的全球行动计划也受到了削弱。”
另一方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与特朗普不同,更多的美国人不同意特朗普对病毒的处理。在过去几个月里,特朗普多次指责新闻媒体、州长、国会民主党议员和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并表示他们应对美国医院里泛滥的病例数量负责。在3月中旬,当被直接问及他是否应为美国缺乏测试能力而负责时,特朗普说,“我根本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讽刺的是,美国总统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猛烈抨击也与他自己在六周前对该组织的评价背道而驰。2月底,在人们对特朗普的无所作为进行最严厉的批评之前,他对世界卫生组织大加赞扬,并表示该组织一直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有着密切合作。他在推特上写道:“在美国,新冠病毒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我们与每个人以及所有相关国家保持联系。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努力工作,他们的工作非常杰出。对我而言,股票市场也开始转好!” 对比特朗普在二月的言论与近日针对世卫组织的批评,特朗普似乎将世卫组织作为新的替罪羊,以此转移国内对其失败治理的抨击。
美国退出带来的全球影响
面对具有极强破坏性和传染力的新冠病毒,各国政府纷纷表示本次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而此时美国的孤立主义行为也将会影响其他国家的抗疫进程。考虑到本次瘟疫的传播速度之快,一旦瘟疫在任意国家大规模暴发,就可能形成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巨大威胁。根据《卫报》的报道,“我们仍处于危机的第一阶段,各国主要集中于控制国内暴发的最初浪潮。如果我们不想这些努力白费,那么就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把专门知识和资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特别是在这种疾病目前在全球南部贫困国家扎根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有效执行此任务的网络和专业知识的组织。即使在世界领先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和紧张局势下,该组织也有取得成功的先例……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决定利用其实力、财富和影响力来积极破坏、而不是慷慨地支持这些努力,这是一种道德盲目的行为(an act of moral blindness)。”
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决策也引起了本国及全世界的批评。美国医学会(AMA)总统帕特里斯·哈里斯(Patrice Harris)称其为“朝错误方向迈出的危险一步,将不会打败新冠病毒”,并敦促特朗普重新考虑。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洛尔表示,这个由27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对资金被暂停表示“深切的遗憾”,并补充说,联合国卫生机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抗击这一大流行病。他说:“只有通力合作,我们才能克服这场无国界的危机。”非洲联盟负责人法基·马哈马特(Faki Mahamat)称该决定“令人深感遗憾”,并说在大流行期间,世界有“集体责任”帮助世卫组织。而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新西兰总理雅辛达·阿登在内的各国领导人纷纷对世卫组织表示支持,强调了在疫情期间各国合作的重要性。
美国暂停资金援助的行为,可能将会带来更为长远的负面影响。除了眼前棘手的新冠威胁之外,对于医疗体系尚未成熟和低收入国家而言,世卫组织的资金削减将使他们暴露在其他疾病的威胁之下。悉尼大学世卫组织体育活动、营养与肥胖症合作中心联合主任阿德里安·鲍曼教授向ABC新闻网表示,美国削减资金将影响他们所做的工作,包括在太平洋等极度脆弱的地区。该行为将影响到每个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和每个国家,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和我们的邻国,将受到影响,不会有全面的基础设施来帮助控制疫情,或者帮助免疫项目。最近太平洋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麻疹疫情。这类事情将会复苏,那将是一场全球健康灾难:美国也不会从中受益,因为疫情将会延长,经济低迷也将对美国不利,美国将失去信任和领导力。”考虑到世卫组织在中东以及非洲为消除小儿麻痹症、提供针对脊髓灰质炎,麻疹和霍乱疫苗作出的贡献,美国退出世卫组织的行为可能为该地区的医疗援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