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荣新江︱困学苦读记
“困学苦读”引子
聪明的读者一看,就知道我这个题目袭用自马克垚先生的大著《困学苦思集》,的确如此。马先生一向是乐天派,但从这个书名可以看出,马先生对待学问,是处于逆境而后生的那种,这是他那个年代做世界历史研究的真实写照。这部《苦思集》小十六开,525页,都四十余万言,收入马先生有关西欧封建社会、古代社会比较研究、世界史体系探索三个方面的代表作,列为“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可谓名实相副。该书2016年9月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0月即蒙先生惠赐一部,其中有些文章,如曾收入所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的篇章,曾经拜读。但大多数有关世界历史的文章,还得慢慢领会。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孽之际,我也响应钟南山医生的呼吁,不出门,窝在房间里读书。可是,这时节,读什么书呢?
按照做学问的理路,本来应当读的一些书在研究室里,像有关丝绸之路、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都不在手边,也不敢到学校去拿。1月23日就曾上演惊险一刻:中午从蓝旗营骑车进北大东门,保安刚刚接到命令,给每个入校的人测量体温。据说我是第一个被检查者,我下自行车积极配合,支持学校工作。结果一测头部,38.8°!立刻被五个保安围住,到一边用体温计检查,五分钟之后,结果出来:36.2°,不知是因为骑车头上发热,还是温度计的问题,差点被移送发热门诊。虚惊一场,吸取教训,还是找找手边可以拿得到的书来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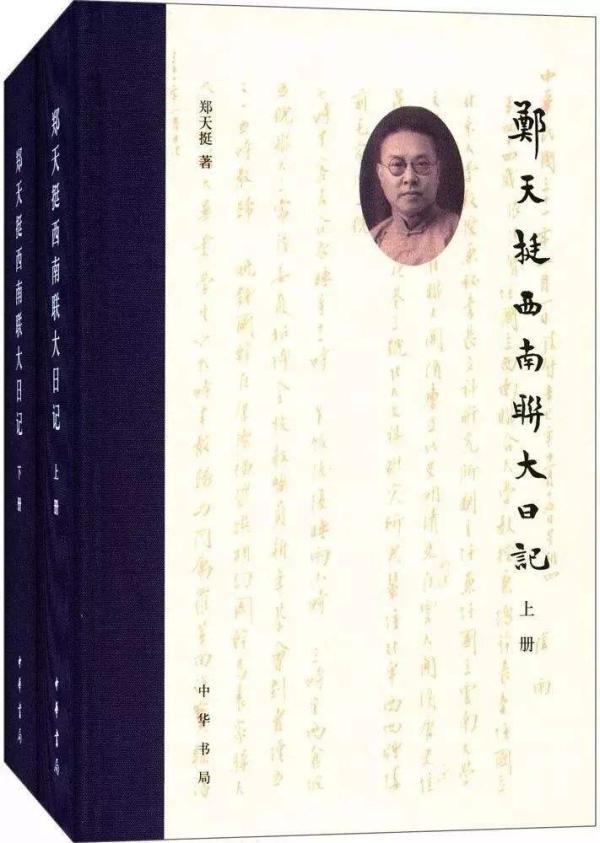
西南联大的教授是在博戏,还是读书
在这个阴沉苦难的冬日里读书,还是要找点轻松的读物,我想日记、书信之类的,多学人掌故,看起来不累,又于学术史或有收获,所以是首选的读物。最先想到的是北大前辈郑毅生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看看日本侵华的灾难日子里,流离到西南地区的北大学人,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读到1938年2月9日的《日记》:“自国难日急,学者好读遗民诗文,余则主读中兴名臣集,以为遗民诗文固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所作,于激励正气外,兼可以振发信心。当千钧一发之际,不有匡济之术,乌可以复兴哉?”能感受到毅生先生的正气所在。现在的疫情期间也是同样,网络上充斥着许多悲哀的声音,而我更希望读的是那些“振发信心”的文字。
《日记》内容颇杂,有事必记,读者阅读,兴趣点也不一样,有人留意到其中有关打扑克,搓麻将,猜诗谜,玩博戏的记录,似乎表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流离失所中,仍能泰然自若。然而事实上,作为一个学人,郑天挺先生的学行,主要还是读书和教书,而当时学者们集中居住,便于相互切磋学问,这些在《日记》中比比皆是。《日记》1938年6月8日记:“上午读《唐书》。下午授课一小时,述唐代对外族用兵之先后及唐代外族势力之消长。”此时正是同在昆明的陈寅恪思考《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时,其下篇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两者之相互切磋及影响,可见一斑。此时郑天挺关注西南民族史地,写成《发羌释》一文,后更名“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送陈寅恪求正,“寅恪又为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多处”,又记“陈寅恪送还文稿,为正对音一二事,并云敦煌写本字书以特番对Bod”(《日记》1938年6月30日,7月6日),可见学术交流之深入。寅恪先生此处提到的敦煌写本,实即P.2762(P.t.1263)背藏汉对照词表,“特番”原作“特蕃”。郑天挺文最后发表在1939年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1分,后收入作者《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1939年以后,郑天挺先生又开始讲授明清史,《日记》中有大量阅读明清史料的记录,实即读书札记。如7月25日记其读江标《咸同以来中俄交涉记》,有三页之多,还特别提到腾固从江小鹣处携来之本的佳处,是书眉所引《西域释地》《新疆识略》《北江集》及沈子培之考证。其读书之广,非我能力可以俱述,只略提一二。如1940年7月8日始,“读《崇正集》,觉明(向达)自法国移录者也”;13日,“读《熙朝崇正集》向觉明抄本”;8月31日,“读觉明自巴黎所抄《熙朝定案》”,前后亦有考证文字。1941年1月11日,“读觉明抄本天主教文件,大都录自巴黎图书馆及罗马教廷图书馆者,迄夜半读竟,并摘要录之。”《崇正集》是明万历、崇祯年间有关天主教、钦天监的奏疏和碑文,《定案》则是清康熙朝的同类文献,原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是国内难得见到的书籍,今有韩琦先生整理本:《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16年版),可以参看。可见,虽然困难时期书籍有缺,但郑天挺先生仍然不停地阅读,想办法找书来读。
为学术前途苦思冥想
不过,郑天挺不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也不是一位普通的教师。1933年他就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并在中文系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下,经长沙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历史系讲授隋唐五代史。1939年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任副主任。1940年2月开始,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直到1945年8月复员回到北平,仍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翻看《日记》,越到后面,事务性的记录越多,学术性的内容越少。此书虽然有助于了解北大学人如何艰难度过抗战的苦难日子,但学术本身越来越淡,往后阅读,也不免有点失望。
我平日关注敦煌学史事文字,本来觉得毅生先生与向达先生同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一段时间里朝夕相处,有关记录或许较多,但《日记》上下两册翻检一过,没有太多有关向达的学术性材料,多为事务性的记录。其中有关敦煌学的最重要文字,还是郑天挺先生自己在《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序》中引过的那段文字,即1943年1月17日《日记》:“锡予(汤用彤)来,示以觉明(向达)敦煌来书,随与之长谈〔北大〕文科研究所发展事。余意,语言调查可在云南,若历史考证,此后唯敦煌一路。其中未广布、未研究之文献甚多。且其地为国际学术界所注意,关涉甚多,影响甚大。此后北大文研(文科研究所)之发展,舍此莫由。今觉明开拓于前,吾辈正宜追踪迈进。”(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与中华本差一字)此后1943年10月11日《日记》有:“作书致觉明,劝其仍赴西北考察,并表示所得古物北大不争取,但保留研究权。”这是关于向达第二次参加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作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前的信,这话背后蕴藏着一些北大与合作方的关系问题,可惜止此一条,没有更多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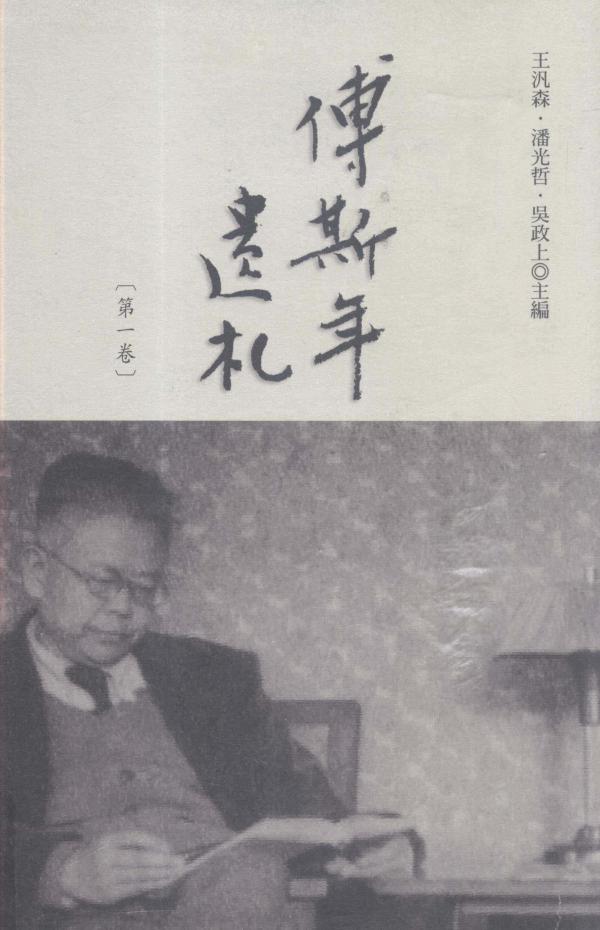
《傅斯年遗札》的遗憾
与郑天挺同样在大后方忙碌的人,还有傅斯年。傅斯年出身北大,后留学英、德,回国后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出任所长。翌年史语所迁往北平,傅斯年又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后(1934年10月)史语所迁往南京,1936年春也随之移居南京。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随史语所迁往长沙,1938年转到昆明,继续主持史语所所务。1939年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兼任所长,与郑天挺等朝夕相处。1940年冬随史语所迁至四川南溪李庄,一度兼任中研院总干事。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史语所返回南京,傅斯年一度代理北大校长,直到1946年9月胡适从美国回来接任。这位脚踩中研院和北大两只船的人,无疑是民国学术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那么,傅斯年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情形如何,就是我在看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之后非常想知道的。傅斯年没有日记出版,王汎森写过他的传记——《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三联书店2012年版),但对于这段时间的记录比较简略。2002年9月,我受邀在台湾史语所讲学,为了调查向达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和“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事迹,花了足有十天的时间,抄录下来史语所所藏向达致傅斯年的所有信件,当时也曾找寻傅斯年致向达的信件,但从电脑给的索引上看,傅斯年的信件数量巨大,无从下手,只好作罢。2010年3月,我编辑出版了《向达先生敦煌遗墨》(中华书局),收录了所有能够见到的向达在敦煌考察期间所写的书信,但向达与傅斯年之间的联系,有去无回,许多事情还不是很清楚。
到了2011年10月,中研院史语所出版了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三位先生合编的《傅斯年遗札》,上中下三卷,总计1908页,作为民国学术史料,可谓宏富。如果加上吾友欧阳哲生教授所编《傅斯年文集》第7卷《书信》(中华书局2017年10月版),目前能够看到的傅氏信札,大概就是这些了。翻检抗战八年期间傅斯年的书信,有关论学的相对较少,主要都是处理各种事务,收信人上至蒋委员长,下至找工作的年轻人,各色各样,但主要还是在学术的圈子里,其中与史语所和北大相关的信函最多。
《遗札》和《文集》几乎囊括了现藏中研院史语所、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以及零散发表的傅斯年信札,但让人有些失望的是,傅斯年没有给西北考察中的向达写很多信,只有《遗札》所收1944年7月11日的一封电报,12日的一封书信的抄件而已,难道是所有寄出去的信都没有留底,这不符合傅斯年处理公文的习惯。
傅斯年虽然没有给向达写多少信,但有关三方合作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和“西北科学考察团”,《遗札》中保留了一些珍贵的材料,如1942年4月15日傅斯年、李济致叶企孙、辛树帜信,有“西北史地考察团谈话会纪录”; 1943年1月15日致朱家骅信,附有“根据向觉明先西北初步调查报告草拟本院西北工作站计划”;9月1日致蒋委员长信,汇报史语所包括西北史地考察团等项事务进展;等等,不一一列举,将来有空,当专门讨论。
傅斯年炮轰的,都是些什么人
不过通过《遗札》,我们还是可以对某些事情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如关于张大千毁坏敦煌壁画一事,早在向达告状之前,1941年12月傅斯年、李济就给刚刚从西北考察回来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写信,据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与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两位的来信所指出的:“张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傅、李二位提议:“甚望其立即停止进行,俟研究妥善保存上层办法,有剥下后不致毁伤之把握时,方可以逐层为之”,“敬祈卓裁,能即电张大千先生,停止逐层剥取之计”(第二卷1190-1192页)。此信石沉大海,在此后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傅斯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直到1942年12月5日,在接到向达有关张大千破坏壁画的来信及所附《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后,傅斯年再次联合李济,给于右任院长写信,举出张大千命人“破三日之功,剥去外层”的实据,建议于院长“电张先生,于其剥离壁画,任意勾勒……加以劝止”,写的十分客气,并附上冯汉骥、郑德坤的来函和向达的文章。据《遗札》,冯、郑二位来函的油印本存史语所,档号III:808,我第一次见到,十分珍贵。而向达文章,“傅斯年档案”中未见,实则当年的油印本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欧阳哲生录入《傅斯年全集》第6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其实在当时的学人眼中,于右任和张大千是一伙的。1943年1月19日汤用彤致在美国的胡适信中就说:“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以于髯(于右任)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恐为一疑问。”(《胡适往来书信集》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其背后的潜台词,也是西北古迹遭到人为破坏。所以这次傅斯年果断行动,在给于右任写信的同一日(1942年12月5日),又写了一封致新闻界及艺术界的公函,把油印的向达上引文分寄出去,希望“贵报分日节出篇幅,为揭载全文”。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重庆《大公报》1942年12月27、28、30日连载的文章。傅斯年将作者化名方回,并加了按语。有关张大千与向达的学案,详见拙文《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收入拙著《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油印本与《大公报》刊本合校而成的向达文,也收入拙编《向达先生敦煌遗墨》,《遗札》即据此过录,此不赘述。

期盼观展
《傅斯年遗札》中,还有一批有关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居延汉简出版的信札,如其1940年8月25日致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信所附致袁复礼函,火气很旺,但属于一家之言。傅斯年有超强的史语所本位意识,这必然有得有失。有关居延汉简出版问题,牵扯更广,颇值得玩味。致袁复礼信中有言:“兄能将兄之材料一百三十五箱早日出版,岂不大妙?”(1111页)其讥讽之意,毫无掩饰。这里所说的一百三十五箱材料,斗转星移,现在大部分由袁复礼家属捐献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其中一些精彩图片,由朱玉麒教授选编,正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袁复礼旧藏西北科考团摄影·新疆”专题展中亮相,我期待着疫情早点过去,到静园的二院去看那些珍贵的图片。
(2020年3月12日完稿)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