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个神童,在37岁时决定重新出发
去年一整年,郎朗都很忙,
他完成了好几项大事——
结婚、发了三年以来第一张录音室专辑,
与四大顶级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还抽空和妻子吉娜上了次综艺,
贡献了若干次热搜。
“2019是我丰收的一年。”


13岁摘得国际大赛冠军,
成名经历激励了中国一代钢琴琴童,
也是中国最早“破圈”的古典音乐家。
他以勤奋、精力充沛著称,
别的钢琴家一年的演奏会最多几十场,
他长期保持的频率是一年120-150场。


直到两周前,开启了新一年欧洲巡演,
演奏曲目是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
这首曲目被誉为“音乐史上最难、
最伟大的变奏曲”,
是所有钢琴家的终极挑战,
也是郎朗2020年的头等目标。


如果你从小就是神童、巨星,
到了37岁的时候,还能开拓的空间有多少?
郎朗绝对不甘心就此止步,
“37岁的他正处于从神童到成熟、
再到元老级艺术家的下一个升华阶段。”
2020年初,一条摄制组跟随郎朗、吉娜,
辗转上海、包头,
记录了这位神童站在人生门槛上的模样。
自述 郎朗 编辑 谭伊白、石鸣


身边的人都叫他“大师”,并对他抱有一种骨子里的尊敬。这让通过综艺或者春晚第一次认知到郎朗的人很难想象。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眼中,他萌萌的,像熊猫一样可可爱爱,在台下,一口东北话,自带“老铁”的接地气喜感。
他自己录钢琴教学视频,语言表情都非常地放飞自我。别人邀请他到知乎上答题,“一整个交响乐团打群架谁会赢?”他真的去了,很认真地思考后,答案写了好几百字。最近他还回答了“把ACG文化和音乐结合起来会怎样”,61个回答中他的答案被置顶,并且标注了“专业”。

而且不光是知道名字,还能把名字和人对上号。去年郎朗和吉娜在法国拍摄婚纱照,化妆师说“不敢去室外拍的”,不然会围上来一大帮人,“都认得他”。
高晓松认为,论中国人在国外的刷脸知名度,成龙排第一,郎朗排第二。但其实这个第二比第一要更不容易,因为“成龙是干流行文化的,郎朗是一弹钢琴的。”

他并没有出身于音乐世家,完全可以说是天赋异禀。两岁的时候,就能仅凭听力,在钢琴上复奏出动画片《猫与老鼠》的主题曲旋律。“一个人有没有天分,通常听10到30秒就能够知道,郎朗显然是有的。”

早年在北京求学的时候,郎家因为和体制内意见不一而受到排挤。直到后来郎朗被柯蒂斯音乐学院的格拉夫曼教授看中,给他发了全额奖学金。
这所音乐学院是全美招生条件最苛刻、水平也最顶尖的音乐学院之一。现在大家熟知的几位中国钢琴家——王羽佳、张昊辰,都是这所音乐学院毕业的。欧阳娜娜当初进入的也是这所音乐学院。
在和他同代的中国钢琴家中,郎朗是走得最远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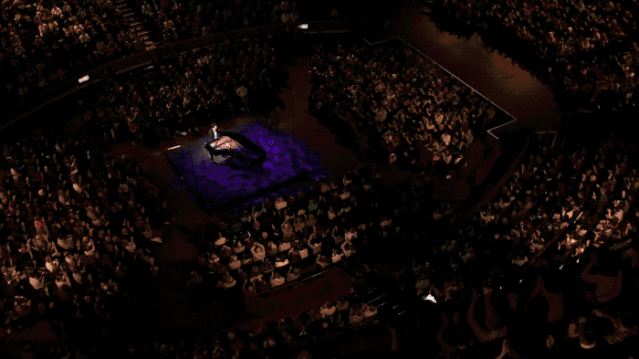
2003年,他已经成名4年,在伦敦演出,穿的是蓝色唐装、白色裤子,弹奏风格也非常“野”,结果被所有评论家狂嘘。英国媒体说他是一个对自己“伟大天才”夸夸其谈的21岁青年,是中国独生子女中的“小皇帝”典型。
那个时候国内的乐评界,以欧洲为导向,一开始有些人对他也是不接受。偏激一点的人甚至认为,他对待音乐的方式太过夸张而表面,充满了炫耀的土豪感,他是在自我陶醉,而不是服务于音乐,因此不配被称为一个古典音乐家。

如果一开始是在英国和法国打开市场就好了,“古典音乐家可以打开欧洲市场之后再去拿美国,但我是在美国上学的,起步在美国。”
他没有别的办法对抗偏见,唯有不断的努力,把一切留给时间。别的钢琴家一年最多也就开几十场音乐会,他一年要开150场,少一点也要120场。别人一场音乐会弹两首协奏曲,他弹三首。

他反应也很快,排练时可以迅速地合上乐团,基本上每次都能在规定时间内结束排练。这非常受乐团的欢迎,毕竟谁也不想加班。
有一次音乐会,乐团准备的是莫扎特24号协奏曲,郎朗准备的却是莫扎特17号协奏曲。24号协奏曲第二乐章有一段华彩,是没有固定乐谱的,需要钢琴家和指挥商量确定。当时离音乐会开始已经不到两个小时了,郎朗临时回忆出24号协奏曲的所有谱子并且自己编好了第二乐章的华彩段落,演出最后非常成功。
最关键的是,他不是一场两场音乐会表现好,而是十几、二十年水平一直发挥稳定。世界各地的顶尖乐团都愿意不断地请他回来。

那一年的10月15日,钢琴大师内田光子在《金融时报》上说:“十年之后,我们再谈(郎朗现象)吧。也许那时已经消失了。如果没有,我会说,‘郎朗,干得漂亮!’”
这个时候的郎朗,已经是世界著名钢琴家,定期出唱片,有自己的基金会,开始做音乐教育和公益慈善。然后呢?这就是他事业追求的尽头吗?
大家公认的是,郎朗很聪明,很擅于模仿和吸收他所看到的一切,身边的音乐家,都是他艺术养分的来源。但是,什么时候热情广阔能够生长出独一无二?什么时候郎朗能够超越自我,形成一个足以成为历史标点的内核:不是从任何人那里来,也无法被任何人学去?
2017年4月,郎朗取消了一系列音乐会。一开始是取消半年内的,后来一年后的音乐会也取消了。人们听说,郎朗生病了。
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大危机。因为感冒加上练习过度,他在弹奏拉威尔的《左手钢琴协奏曲》过程中,不小心导致了左臂发炎。他决定休整一年半,直到2019年7月才正式复出。

了解郎朗成长经历的人会知道,这场比赛、这个名次对他有多么重要,在他备受身边人的否定的时候,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国际比赛奖项。

我们可以把这张专辑当做他休整一年半的句点,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2019年录制的综艺节目,也同样如此。一年半来,郎朗说,“我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思考了一切。”
接下来,他要重新出发了。他要向一个少有人到达过的山顶攀登。
以下是郎朗的自述:

播出来还真的很多人关注,这个我没想到。可能我总觉得所谓的正事是弹音乐会、做大师课,但是现在这个社会还真不只是这样,像真人秀这种事儿好像关注的比我跟维也纳、柏林弹多少次还要多。
所以关注古典圈的人还是少。有时候我就在想怎么样能让不是这圈的人也感受高雅艺术,比如说和不同的歌手合作,或者跟不同的品牌尝试跨界,不是说自己关在一个小屋里就干自己的事,所以为什么一直有人说你一个弹钢琴的整天搞这搞那的,说到底,都是为了能让古典乐给更多人听到。

我也在学着怎么活用社交网络,比如B站上我开了个频道,用视频给大家上钢琴课。之前facebook还有《周一学中文》(教外国人讲普通话)、《郎朗音乐时间》(分享音乐)、《郎朗的窗外》(分享美景)。我不觉得社交媒体该成为人们无聊就上去想说啥说啥的地方,社交网络它得改进,它该把人们的灵魂凝聚在一起,也该变成学新鲜事物的平台。
休整一年半,发现我得补东西
2017年下半年开始我休息了一年半,这一年多时间,我有了更多时间去感受原本没时间经历的人生。复出后,我弹莫扎特感受不一样了,不光莫扎特,所有曲子都有些不一样了,感觉世界重新给我开了一扇窗。
弹钢琴也是全身运动,脚也在踩踏板,手、腕子、脖子、肩膀、胳膊,这就是用得特别多。所以如果不慎不注意的话,肯定会出现些问题。
通过我这段休整我就感觉到,我得补东西。

读书一直都在不断地读,因为脑子里一旦空了的时候,我就感觉很不自在了。平常的时候可能读新闻类或者是读短篇比较多,这段时间我就读了很多经典文学。
比如读莎士比亚,你就发现这个跟弹琴是一样的,像弹巴赫、贝多芬的慢板、缓板,你都会感觉东西都凝固起来了,越来越缓慢,有时候感觉像雕塑似的,那种感觉特别好。一个小时冥想以后,你再出来,你就感觉看这个世界又不一样了,你的心态会很舒服,不会很急。


一出来就做了挺多事,把《钢琴书》这个专辑给录了。这些曲子我早就想录了,就是因为我担心有人会说,这些曲子太简单了,什么《小星星变奏曲》、《致爱丽斯》,这个小孩都能弹,大家会认为怎么郎朗弹这么简单的曲子。很多职业钢琴家都不爱录的,觉得录这玩意儿给小孩没意思。
到我这年龄了,我想把我从小最美好的回忆或者不是特别好的回忆给留着,比如练车尔尼练习曲,练得我邻居都想揍我的那种。
但后来我发现,这些曲子真想弹好很难的,就像我小时候看霍洛维兹在1986年的莫斯科的音乐会上,阔别他的家乡50年,他演奏的这个舒曼的《童年情景》,他真的把这首曲子弹得,这是我知道的那个舒曼《童年情景》吗?

所以我这次就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我怎么能把这首曲子弹到我梦想中的声音,而不是我小时候弹的那个水平,也给很多小朋友们制定了一个新的目标。
还有比如说动画片《麦兜故事》的主题曲、坂本龙一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茉莉花》、《阿里郎》等等,因为我小时候弹琴的时候,亚洲乐曲还少,我就希望在我这个时代,就是中国的作品包括亚洲的作品,它能和这些欧洲的古典的精品能相提并论。
那天我见披头士的主唱保罗麦卡尼,他跟我说,你看现在我都成了“古典”摇滚了,我说对。
但是他在他那个时代却不是,包括很多周杰伦的歌现在也变成了经典,还有张学友、刘德华。所以在这个近20年里面,有很多优秀的新的钢琴作品,一点点也融入到经典这里面来,所以我一定要把它们也放进来。

看网上大家都很喜欢看我那些教学视频对吧,挺逗的,做的那些效果啊啥的。我对自己要求挺严的,但是我可能对小朋友我会稍微把话收回来,因为老师太严格不好,对小孩会有阴影。
我小时候就有阴影,怕,特别怕,一怕就不敢弹了,一不敢弹了什么都没了。所以我就先稍微严一下,完事我就开点玩笑,把这个劲拉回来。


小时候我爸严,他有的严格是对的,但是有的严厉完全是自我陶醉。你不能光苦,光苦谁愿意当钢琴家,苦尽甜来那太晚了,那已经是荒废了很多人的希望。
弹钢琴的人是最需要交流的,弹钢琴的人太孤独了,是所有乐器里最孤独的人。你看我从小,我堂弟吹黑管的,人家每次都是拿着黑管就能出去,随便就吹了,我要出去玩吧,我上哪儿弄琴呢?没琴我哪儿也去不了。
我经常碰到太多有天赋的孩子,都问我:“我以后该怎么走?我下一步该去哪儿学呢?您能给我些建议吗?”但我个人的圈子是有限的,所以我想要有更大的关系网,成立个基金会,就能跟孩子们说,你可以去这个夏令营,我的基金会能给你联系这个机构,来帮助他们练琴甚至经济上的问题。

我开始建立目标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音乐能改变人生,而不是我去一个地方访问一下就再见了,这一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去第二次、第三次,就是一阵旋风吹过去没了,怎么能扎根?种棵树在那儿,留下一个真正的体系。
就开始研究课程,而且智能钢琴出来了,当地的老师给孩子上课就容易很多。

都37(岁)了,在第一阶段必须走完了,再不走完怎么走第二阶段?那肯定是往成熟、往对音乐理解的能力和对自身调整、这个方面去努力。
作为钢琴家你不进步就退步,你可以搞教育,但是问题是你越弹越烂的话,你先教一教你自己吧,所以还是要活好,活儿得越来越好。
今年我就是从3月份以后,全都弹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它是最传统的,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最后还是作品说话,我觉得这个作品就是能代表第二阶段的开始。
今年我还想录制《哥德堡变奏曲》的专辑。我打算30多岁时录一次,50多岁录一次,70多岁争取还能录一次。年轻的时候弹,可能缺少些理解,但总得有个录音先试一下,总比不录强。
有的时候这神童没长大以后,他就永远变成一个儿童,你看很多特别有才能的小孩,到了一定年龄就上不去了。我不敢说弹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快乐的,但我至少有80%都是,所以为什么我还能一直弹下去。
对我来说,弹钢琴的时候,我需要传达超越演奏本身的一切,而不仅仅是演奏。因为我不觉得世界上还需要多一个钢琴家。我不是在演奏曲目,我得演绎出整个宇宙。在艺术里,你怎么能不冒点险?

原标题:《一个神童,在37岁时决定重新出发》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