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黄小峰丨观看的力量——读石守谦近作《山鸣谷应》
石守谦作为一位在中国和北美接受过严格的艺术史训练、在大学与博物馆来回穿梭的学者,他的每一篇论文及由论文汇编而成的每一本著作,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本文将分两部分来讨论他的新书《山鸣谷应: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简体中文版2019年出版)。第一部分介绍书中的主要观点,第二部分尝试把这本书放在石守谦的学术脉络及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整体脉络中来略做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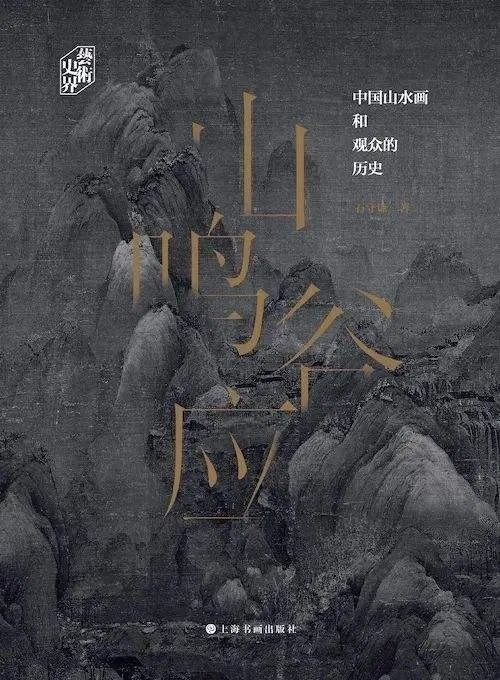
山鸣谷应: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
石守谦 / 著
京不特 / 译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11
《山鸣谷应》是一部由问题串联起来的中国山水画通史。这么一说,脑中浮现出的是在大学时代对笔者影响很大的陈传席的《中国山水画史》(1988年初版)。简单来说,想一句话归纳陈著是不可能的,勉强可概括为:它全面梳理了山水画(家)的基本文献与图像。但石著却可很容易地归纳为:作者追问了“中国山水画为什么能够形成‘历史’(风格史和观念史)”这个问题,并从画家与观者互动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因为有这个核心问题的支撑,尽管全书体量不小(简体中文版近500页),却能让人一气读完。
此书的问题意识鲜明地体现在副标题“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中。主标题“山鸣谷应”也很妙,用山川中人的回声凸显山水画与观者互动的主题。在总主题之下,全书12章的分主题也十分鲜明。每一章都交织着隐显两条线索:“显”的是不同时代的山水画变迁,“隐”的则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社会身份的观者的思想变化。
第一章“序论 :山水画前史”说明了全书为什么要从“画家与观众互动”的角度讲述山水画的历史。作者的思考过程是这样的:山水画为什么在中国绘画中具有崇高地位?因为山水画具有特殊的意义。山水画的意义不断发生变迁,形成了山水画的历史。为什么山水画的意义会不断变迁?是因为始终有观众的参与。山水画的意义(作者用“意涵”一词)主要是观念层面的,但也包括风格层面的。为了更好地统一观念与风格这两个层面,作者提出“画意”的概念。并以有无“画意”为标准,判定山水画的历史应该从10世纪开始。
第二章“山水画意与士大夫观众”讲述的是山水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大致在10世纪中期到11世纪中期之间。作者讨论了几个问题,分别对应这一章中的三个小节:为什么从五代开始,山水画突然得到迅速发展,并出现了隐士主题?为什么北宋初年的山水画中出现了大量对行旅人物活动的描绘?为什么士大夫文官大量歌咏山水画?这一章认为,五代到北宋中期的约100年间,士大夫文官阶层是山水画的欣赏主体,山水画也因此形成了以隐居、官员迁徙的行旅、表现公务生涯中的精神寄托为主题的画意。
第三章“帝国和江湖意象:1100年前后山水画的双峰”讨论的是北宋后期山水画发生的一次重要转变,即政治性的山水(作者称之为“帝国山水”)与反映私人情感的文人山水(作者称之为“江湖山水”)的兴起。这两种蕴含不同画意的山水画分别代表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具有政治身份的观者和有意消除政治身份的以文官群体为主的观者。和上一章的士大夫文官观者有所不同,这一阶段的文官士大夫生活在北宋后期巨大的政治压力中,他们是失意文官,是努力解除政治牵挂的已经离职或做好离职准备的文官。在这种政治语境中,“帝国山水”的代表是宫廷画家的绘画、帝王的绘画,如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宋徽宗的《雪江归棹图》等。“江湖山水”的代表是郭熙为离职文官所画的《树色平远图》等以朦胧烟云为重要特征、体现潇湘主题的绘画,尤其是“米氏云山”和苏轼交游圈中的绘画,如王诜的《烟江叠嶂图》。作者也因此讨论了典型的失意文官苏轼和以他的经历与诗文为主题的绘画,如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图》。

《早春图》郭熙(北宋),绢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树色平远图》郭熙(北宋),绢本,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第四章“宫苑山水与南渡皇室观众”讨论的是为什么南宋的宫廷山水画会得到如此繁荣的发展,并形成淡化政治色彩的诗意化特征。在第三章,作者要努力阐述与“江湖山水”对应的失意文官观众与北宋初年的士大夫文官观众的区别;在第四章,作者也要极力说明南宋和北宋后期的宫廷和皇家观众有什么不同。作者不同意以往简单地认为南宋宫廷山水画形成诗意化特征是因为受到文人文化的影响的观点,批评其为“文人中心主义”。他认为应该放在南宋的政治大环境中去看,即南宋宫廷抱有一种“过渡”的心态,因此对山水画的要求从表现北宋帝国山水的雄心,转向体现宫廷燕游之安乐闲适。
第五章“赵孟頫乙未自燕回的前后:元初文人山水画与金代士人文化”讨论的是美术史中的一个大命题——元代变革。在山水画中,这种变革集中体现在两点:一是“复古”,二是书法入画。为此,尽管和大多数学者一样,作者也聚焦于赵孟頫,但却独出新意,没有讨论他的个人画艺,而是以他为线索,讨论元代初年文人山水画的形成与特殊的文人文化圈的关系。作者认为,赵孟頫和他身边的江南文人圈之所以发生转变,与他们接触到的金代文人文化有直接关系。在这个思路下,作者先是重新讨论了金代山水绘画和图像,如武元直的《赤壁图》和李山的《风雪杉松图》中的怀古主题、金代磁州窑生产的磁枕上的山水图像和墓葬中山水壁画反映的民间宗教趣味;然后讨论元代初年北方地区直接传承自金代传统的山水画;最后再落脚到赵孟頫,讨论了他在北方为官后回到江南,其绘画开始强调古意,书法用笔出现新的画意。

《赤壁图》武元直(金),纸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磁州窑白釉黑褐彩芦苇仙鹤纹枕(金),来源:河北博物院官网
第六章“赵孟頫的继承者:元末隐居山水图及观众的分化”讨论的是以“元四家”为代表的元末山水画,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书斋山水”(何惠鉴语)及“地产式山水”(Landscapeof Property,文以诚语)。作者基于画意的概念,将之定义为“隐居山水图”。在这一章,作者要回答的是元末的文人隐居山水与宋代的不同。同样,突破口也在于观众的不同。作者对“元四家”一一进行了讨论:先是讨论吴镇绘画中典型的“渔隐图”模式及这种画意与隐居不仕的文人观者的关系;然后讨论倪瓒及其绘画中看似平淡的水边空亭的隐居生活所折射出的戏剧性的个人生活变迁;接着讨论黄公望绘画中的道教因素。这三个人的绘画都有关隐居,但却是不同原因的隐居。在这一章最后两节,作者把隐居图的观者放大到了群体,先从马琬和张渥为杨竹西所作的隐居图来讨论元末隐居山水中的富裕士绅观众,最后借“元四家”的第四人王蒙颇具动感的隐居图讨论元末苏州地区虽处于隐居状态但却跃跃欲试想在剧烈的社会政治变动中建功立业的文人群体。正是这些在不同的隐居图里表现出不同状态与心态的观众,赋予了元末山水画特殊的面貌。
第七章“明朝宫廷中的山水画”重新处理了明代宫廷绘画与“浙派”的问题。宫廷绘画当然是为宫廷观者所作,但作者的新意在于,他认为从明代初年到后期宫廷山水画脉络的变化,基本都与帝王观众的转变有关。比如,明初宫廷与西藏僧侣的密切关系,使受到佛教绘画影响的青绿山水成为宫廷山水画的主流。皇帝变了,趣味随之转变——正如简朴的宣德皇帝喜欢简朴的水墨山水,追求个性的成化皇帝喜欢吴伟狂肆的画风。除皇帝外,宫廷观众还包括明代的宦官和藩王,作者也讨论了他们对山水画的影响。这一章最后还讨论了“浙派”晚期绘画与道教社团的观众之间的关系。
第八章“明代江南文人社群与山水画”其实是第七章的姊妹篇,讨论的是明代以苏州为中心的文人画艺术的出现和发展。在作者看来,正是由于明代发达的宫廷艺术,才会出现相对应的文人艺术。如果说宫廷山水画是“专业”的,文人山水画强调的就是“非专业性”,并刻意与宫廷绘画划清界限。作者认为,到了明代,文人山水画变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所以要从更普遍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文人社群的角度来讨论其画意和观众之间的关系。这一章处理的问题很多。作者先是在明代的文人山水画中区分出“雅集山水图”“纪游图”“茶事图”“别号图”等不同画意的类型,来进行社会史式的讨论;同时也处理了从“吴门画派”过渡到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的传统主题。作者意识到,明代的文人文化中也包括一些试图进入精英文化圈的文化新贵,他们与职业画师的绘画有着密切的互动。此外,作者还关注女性观者,讨论了仇英的“闺情山水”。这一章最后还讨论了晚明文人中大量出现的佛教“居士”与山水画中具有宗教意义的画意之间的关系。
第九章“17 世纪的奇观山水:从《海内奇观》到石涛的奇观造境”讨论的是明末清初山水画中的尚“奇”风尚,以及由此形成的“奇观山水”。与明代中期以来纪游图式“实景山水”不同,“奇观山水”刻意凸显奇特视觉经验,与旅游文化和大众文化有密切关系。在这个背景下,清初以石涛为代表的一批画家有意识地要超越流行的大众图像,创造出了新的“奇观山水”。石涛的新绘画对应了新观众,其中,作者着重分析了旗籍地方官员和徽州商人这两类。作者还把眼光放宽到东亚的范畴,讨论了“奇观山水”通过使节传播到朝鲜的情况。通过跨文化的比较,作者注意到了“奇观山水”背后隐藏的国际文化竞争。
第十章“以笔墨合天地:对18世纪中国山水画的一个新理解”和第十一章“变观众为作者:18 世纪以后宫廷外的山水画”也堪称姊妹篇。前者讨论了清代中期宫廷山水画和宫廷观众的互动关系,后者讨论了清代中期和后期社会中山水画的新趋势和观众群体的新变化。清代宫廷山水画和宫廷观众与宋代、明代有什么不同呢?简言之,清代宫廷在部分接受西洋艺术风格的基础上,重拾对明代以来实景山水的特殊兴趣。因此,宫廷画家和与清代文化有关联的旗籍画家创造性地发展出一种将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派画风与新的自然观察方法相结合的“巨观山水”。而在宫廷文化之外,以《芥子园画谱》为代表的版画画谱使山水画成为简便易学的技艺。于是,画家与观众的关系出现了新变化——观众同时也是画家。这便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专业画家为了与通过画谱自学的人相区别,会刻意描绘画谱以外的题材,比如庭院山水,其作品也因此流行起来,袁江、袁耀的园林界画就是其中的代表。以黄易为代表的低级幕僚所作的山水画和“访碑图”则是另一种成果。此外,19世纪一些心怀经世致用抱负的文人自己也能作画,就可以相对自由地发展出一种对地理新景观的探索。
第十二章“迎向现代观众:名山奇胜与20世纪前期中国山水画的转化”作为这本书的终章,讨论了20世纪前期新的观众群体的形成与山水画在功能、形式与画意上的巨大转变。出于对真实感的追求,画家会借助摄影照片进行绘画,同时把传统的写生、临摹加以新变。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种“名山奇胜”山水。在作者看来,这是中国山水画史中最具有观众意识的时代,也是艺术迈向“现代”的标志。
《山鸣谷应》与作者的前几部著作相比,有明显的传承与发展关系,给人以“集大成”之感。石守谦在其最早的论文集《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1996年)中提出中国绘画研究的基本理念,即关注文化史范畴内的风格史变迁。从这本文集的几篇论文中,尤其是讨论“浙派”绘画的兴衰与贵族品位的关系及讨论“吴门绘画”中的“避居山水”与苏州失意文人之间关系的论文,已经可以明显看到作者对观众的讨论。文集中的第一篇《文化史范畴中的画史之变》,简直就是《山鸣谷应》的萌芽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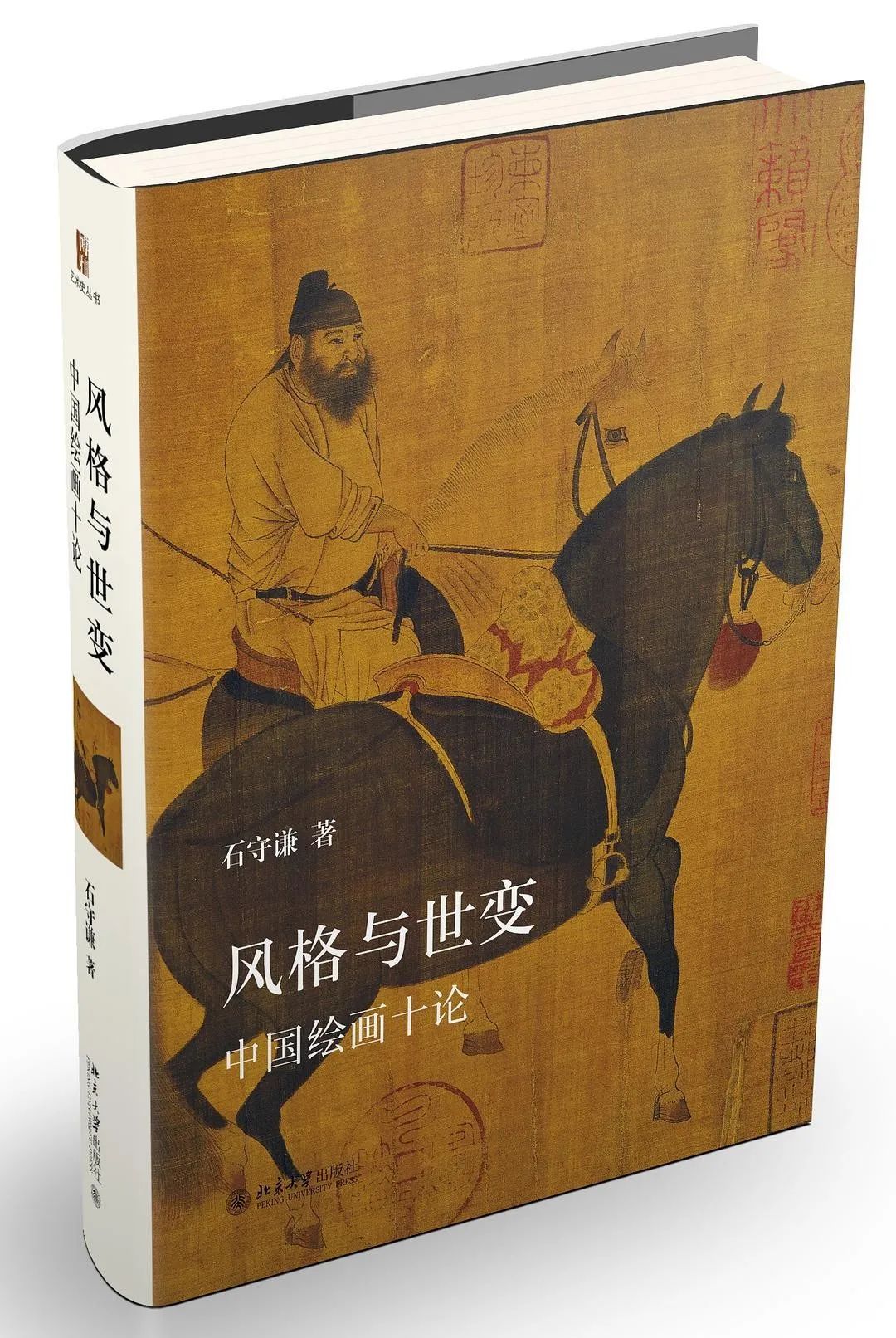
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
石守谦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08

从风格到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
石守谦 /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08
在之后的第二本文集《从风格到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2010年)中,石守谦完成了其研究理念的升华,即把对绘画史的讨论重点从风格史转向了“画意”。其中最主要的论文是《风格、画意与画史重建——以传董源〈溪岸图〉为例的思考》,第一次完整提出了“画意”的研究思路。这篇发表于2001年的论文,写作背景是1999年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行的围绕《溪岸图》真伪的大讨论。这次众所周知的、充满戏剧性的讨论带来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散——无论是对于直接辩论的双方(高居翰和方闻),还是对参与讨论的其他学者。方闻认为《溪岸图》很可能是董源之作,高居翰(James Cahill)则认为是张大千伪作。问题就在于对山水画,特别是对早期山水画的研究方法存在巨大分歧,看似科学的形式分析在不同人的理解和使用中有很大的不同。与《溪岸图》真伪讨论伴生的,是方闻和高居翰的另一次隔空讨论。高居翰在发表对《溪岸图》质疑的同时,还发表了《关于中国画“历史”与“后历史”的一些思考》一文(Some Thoughts on the History and Post-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1999年11月讲座文稿,2005年正式出版),提出了“中国绘画史的终结”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对风格史的有效性提出了怀疑。而方闻很快撰写了《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2003年)一文作为间接的回应,试图阐述为什么中国绘画具有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风格史。
以己意猜想,我认为作为方闻高足的石守谦在深刻思索并试图调和老师与高居翰的争论中,反映出了为中国绘画建立一部“历史”的困境。方闻与高居翰之所以是海外中国绘画研究的“双峰”,在于他们很早就开始各自探索如何建立中国绘画的“历史”。方闻的努力最早体现在《心印》一书中,由山水画的断代分析切入。高居翰更不必说,他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撰写中国绘画的系列断代史,并在1988年推出《中国绘画史三题》(Three Alternative Histories of Chinese Painting)。放在这个大背景之中,我们会发现,在对《溪岸图》的研究之后,石守谦开始较多地讨论元代以前的山水画,并且逐渐深化了“画意”的研究思路。最终的成果,便是《山鸣谷应》这部为中国山水画撰写的特别的历史著作。而方闻的《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一文中的最后一节,便是“走向中国山水画史”。石守谦通过画意与观众的角度对山水画史的讨论,似乎让我看到了一种传承和致敬。
与《山鸣谷应》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艺术史家柯律格(Craig Clunas)2017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绘画及其观众》(Chinese Painting and Its Audiences)。两本书都不约而同地关注中国绘画中的观众问题,似乎反映出一种新的趋势,虽然两者取向十分不同,也反映了不同的学术脉络。简单地讲,石守谦意在“建构”一部历史,而柯律格意在“消解”一部历史。这恰恰是因为观众。我们每一个研究者,都只不过是历史的观众,但又何尝只想成为观众?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0期,标题有改动)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