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艺术与社群|在污名化机制之下,我们都会成为“声名狼藉者”
“声名狼藉者,他们是主流价值的缺口,是盘踞于遮蔽处的异端,是承纳伦理的容器所溢出的泡沫,是留下糟糕记忆的整体印象。他们以奇怪的身姿走向舞台并让人印象深刻,其中的一些人已然因无可逆转的行为被历史定性,但仍有一些人尚未做出任何出格和可憎之事,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自身特殊的存在就已经在‘破坏’社会固有的规则和契约——传染病患者、流浪者、疯子、畸形人、犯罪分子与城市怪胎……所谓声名狼藉者都在不同程度与处境上让人敬而远之。”2019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青年策展人计划的入选项目《末路斜阳——“声名狼藉者”及其不可解的存在方式》,开篇介绍如是说道。

《末路斜阳——“声名狼藉者”及其不可解的存在方式》展览现场。本文图片均由展览方提供
这段文字明确地向我们提示了这个展览所要探讨的对象——“声名狼藉者”,他们的基本性质,并揭示了这个群体与普通人之间的某种微妙的权力关系。表面上看,这个群体好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遥远。不过,一旦我们进入这个展览空间,诚恳地将我们的感知交托给展览营造出来的情境,就会发现,自己原本固若金汤的刻板印象、安全意识似乎开始一点一点地松动、崩溃,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隐藏在生活中的塑造这些“声名狼藉者”的权力关系。
“声名狼藉者”的产生
声名狼藉者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不难想象,这些看上去承受了坏名声的人未必愿意承认这样一种身份,相反,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认为自己是符合主流价值的“正常人”。然而,在权力关系中,占上风的群体总会以犯罪、怪异、病痛等理由将他们认定为“声名狼藉者”的人清除出群体。中国古代对犯人施以黥刑,在他们脸上刺字,作为犯罪的标志;古希腊时将一些污名的记号刺入或烙进体内,向人通告携带记号者是奴隶、罪犯或叛徒。
日常生活中的观看行为本身就是权力与意识形态塑形他者的手段。在展览的第二部分,艺术家通过对观看行为的分析,从而对这样一种权力机制进行分析和解构,让平时隐蔽在各种生活和意识角落里的权力关系具体地显现出来。

(背景)胡伟,为公共集会(邂逅)的提案,2018–2019,单频黑白有声录像,16'01''
(前景)胡伟,公共喷泉, 2019,玻璃钢树脂、光敏树脂、钢、水泵,180cm x 180cm x 100cm
胡伟在作品《为公共集会(邂逅)的提案》与《公共喷泉》中,通过影像、叙事、装置等手段呈现了某种非常复杂的观看体系,探讨了权力机制如何通过控制社会图像实现对社会的监控管理。这件作品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代表了集体记忆的图像或文本,经由权力机关筛选,再传输到社会中去,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蜕变,而我们的行为与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扭曲和改造;我们是否应该时刻对自己接受的信息与指令、对自己的行为与思想都保持警惕。倘若将张巍的作品《机械博览会》、《控制机》也纳入到这个视野之中,我们也同样要质疑科技对个体生活的控制与影响,进而警惕在权力的掌控之下,科技可能会对人类造成的严重危害。

张巍,机械博览会,2019,艺术微喷,140 x 178cm

张巍作品《机械博览会》、《控制机》在展览现场
在上述管控机制下,个体只不过是一些如同数字、标签一样的认知符号,是架空的存在,凌驾于个体之上的权力可以有无数的理由让自己变得冷漠无情。个体面对权力,就如同何采柔的作品《摇篮II》一般,不断地在安全与戒备的心理之间摇摆,身为个体的人根本无从判断最终落在自己头上的究竟是什么。“声名狼藉者”便在这种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下,被这样称呼自己的群体将人性的低劣性强加在自己身上,被粗暴、无情地划分为异类,遭到日益严重的贬抑和排斥。他们已经不再是具体的、拥有复杂性的个体,而只剩一个符号性的“社会身份”。

何采柔《摇篮II》现场
“声名狼藉者”究竟是谁
然而,倘若我们回过头来观看展览第一部分的作品,就会切实感受到,这些被污名化了的个体也与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人。不论是阳莯的镜头下那群声称看得见外星人的“脑控受害者”,王拓作品《烟火》中的那位“在法律尺度下罪不可赦,却在人性尺度上变得无解的为母复仇者”,还是华伟成的作品《洋人街——像孙治国一样吃火锅》里的那位在洋人街流浪的“疯子”,或是刘玗长期关注的台北车站里那群“自愿亦非自愿被社会制度流放的流浪者”,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符号性的身份,而是处在具体的生活困境里的,有着合理的处事方式,具体鲜活的,和我们一样的人。
艺术家也用自己的方式融入到了这些人的生活情境中,切实地体会他们的境况,并通过自己的作品促使人们抛掉了那些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刻板印象,将他们还原为本来拥有的真实属性。
在阅读和观看这些影像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逐渐放下自己内心的固执与防备,深入到他们的世界中,甚至从他们身上获得相应的认同。正确认识这些“声名狼藉者”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关乎我们所有人想要过的生活。对这样的群体,社会应该尽最大努力改变他们所面临的处境,而非以污名化的方式抛弃他们。

王拓,烟火,2018,单频 4K 影像(彩色,有声),31’17”

华伟成,洋人街—像孙治国一样吃火锅,2018,单频高清录像(彩色,有声),14’00”

刘玗,停泊于车站的愚人船,2016,双频录像装置(彩色,有声),25’16”
这一切都让我不得不去重新反思,按照单一标准运行的权力机制的局限性。而这个展览也在第三部分中进一步打破了权力机制的有限尺度,去探索在权力机制以外,度量个体生命状态的可能性。在这些作品中,艺术家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或许显得有点离奇、不合常理,甚至让人感到不适,但这样的反应或许都源自于我们盲目地服从于长期以来被塑造的、缺乏弹性或想象力的惯性思维。一旦跨出这样的惯性思维,便能明白这些违背我们惯常思维的尝试也的确为个体与权力之间的二元关系填充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回到自身
看完展览再躬身自省,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所说的权力机制绝不仅仅是外在于我们的那些行政机关、商业组织或社会团体,而是同样深刻地镌刻在我们自身的意识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于权力机制之外,倘若对此不加以警惕,那么我们都会成为促使权力机制更加牢固、更加封闭的共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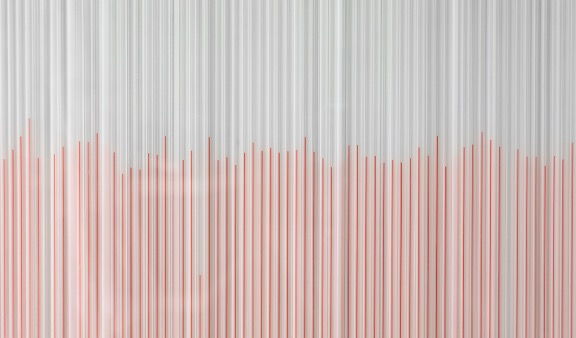
陈萧伊,无法度量(2.0),2019,无刻度温度计,300x80cm,局部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权力机制中的位置与作用之后,估计也就会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污名化现象感到恐惧。现在,我们正深陷于一个全球规模的“污名化运动”之中,那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已经让数万人感染,夺走了上千人的生命。这个目前仍然没有特效药的疾病,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恐慌。尽管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以最大力度来控制疫情,然而,在全国各地防范疫情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现象。这一个多月来,全国各地不断出现一些武断粗暴、一刀切式的防疫方式,对来自疫情重点地区的人进行堵截、驱赶。这种冷酷无情、简单粗暴的做法,导致了一些群众事件和暴力冲突的发生。

胡葳,悲惨世界—同人,2018,漫画,装置,尺寸可变
在这些事件中,一个凶猛可怕的污名化机制也在推波助澜,影响人的感觉,破坏人的心理防线,将人推到一个危险的、失控的悬崖边上。人们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两个群体,武汉或者湖北以外的人群自然地构成了埃利亚斯所说的“内群体”,他们占据了某种道德高地,处于优势地位,对成为了“疫情”、“病毒携带者”的代名词的武汉、湖北人,或疫情爆发期间去过武汉的人,表示恐惧、抵触。他们掌握了话语权,把控着“防疫规范”与“社会规范”,对相关人士加以批评或控制,来彰显自己的规范意识和群体认同。而处于疫情重灾区的武汉、湖北等地的人,以及近期去过该地区的人,则被迫成为了“外群体”,他们一方面对自己的这种临时社会身份感到屈辱,而在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获得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希望得到合理、合情、合法的对待。于是,一种难以调和的权力关系便形成了。

《末路斜阳——“声名狼藉者”及其不可解的存在方式》展览现场
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均衡的权力关系,出于“内群体”成员对病毒的极度恐惧,很容易让自己对外群体的看法走向扭曲认识和刻板印象。在这个时候,他们眼中的外群体成员已经失去了作为个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而仅仅被看作潜在的病毒携带者。在这个时候,不管这些人是否真的带有病毒,全都已经被污名化为“潜在的病毒携带者”。
然而,这样的污名化机制并非一成不变。对他人进行污名之人在不同的条件下也会转变成被污名者。倘若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次疫情的话,我们就会明白,成为“潜在的病毒携带者”的绝不仅仅是武汉人或者湖北人,而是所有中国人。蒙古、朝鲜、俄罗斯等邻国都先后关闭了边境,对这些国家而言,所有从中国来的人都成了“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这也就有必要让我们对自己内部产生的权力关系进行反思,对笼罩在社会之中的污名化机制进行反思。

《末路斜阳——“声名狼藉者”及其不可解的存在方式》展览现场
显然,这样的污名化机制所导致的扭曲粗暴的防范手段,不仅让疫情防范变得冷漠僵化,也会让整个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这样的手段并非对人进行有效的甄别和救助,而是无情的抛弃。例如,温州封城之后,一位温州商人因无法回城而被迫在高速公路上流浪,尽管经过多番检查,他都被证实没有感染疫情,但是多家高速公路服务区等都拒绝接收或放行,这样反而更不利于疫情防范。这样的暴力隔离比疫情更让人感到恐惧。这样的手段很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员为了避免被标签化或遭到非人道的待遇,刻意隐瞒、躲避、抗拒相关的疫情检查,从而让疫情进一步扩散。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应该要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事实恰恰相反,越是非常时期,越要警惕以“非常之名”行“非常之事”,越是需要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充分考虑每个个体具有的差异性与丰富性,充分考虑问题的复杂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具体问题做出相应的理性处理。在非常时期,污名化意识往往会乘虚而入,在社会上搅动起巨大的漩涡,让人不断加固已有的刻板印象,从而导致行为上的扭曲变形,甚至失去了人本该有的基本人性。只有将人作为人看待,而非先入为主地将人视为“声名狼藉者”,才有可能有效地避免自己为污名化的机制所左右,正确判断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权力关系,做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有效行为。
(作者林叶系自由撰稿人、译者。)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