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海外史料:西方人眼里的“京师大学堂”
原创 东评君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沈弘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曾几何时,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是一件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的大事。大学堂成立的消息刚一传出,便不胫而走,招来上千名已获功名的秀才、举人和进士的竞相报名投考,其热闹场面丝毫不亚于如今的高考。
1898年8月9日,光绪皇帝根据李鸿章和孙家鼐的推荐,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为西学总教习之后,当即引起了意大利和德国公使馆的极端不满和“严正交涉”,几乎酿成外交事件。而美国1898年9月23日的《纽约时报》则以《京师大学堂》为标题,发表了美国公使康格(E. H. Conger)从中国京城发回的报道,宣称丁韪良已被任命为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的校长。就连清廷的官方喉舌《京报》也连篇累牍地刊登京师大学堂的相关消息。1898年10月3日,上海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在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京报》几乎每天都登载孙家鼐有关京师大学堂的奏折。这所大学似乎成了文人圈子中最经常和最热门的话题。翰林院有多名学者被聘为大学堂教授汉学经典的教习,而作为校长的传教士和神学博士丁韪良正在仔细挑选西教习。语言系可望在十月中旬开课,医学系约在一个月之后也可以上课。一座由政府管辖的医院将成为医学系的附属医院,以便供学生实习。大学堂各系的所有学生一旦毕业,都将都将被政府授予文凭、官衔,以及政府部门中的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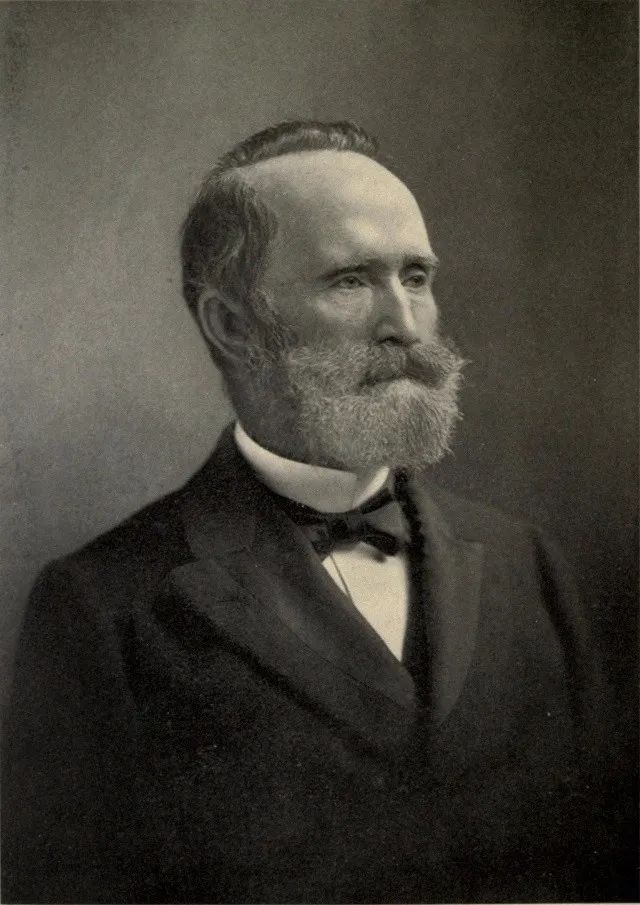
可奇怪的是,时隔不久,所有这些议论和报道便神秘地得以蒸发,并很快被世人所遗忘。时至今日,有关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的中文史料可谓是凤毛麟角,翻遍所有的中文史书和报纸,也很难找到相关资料,即便有,也是语焉不详,王顾左右而言他。更常见的则是拙劣的篡改和刻意的误导。其结果就是如今人们对于京师大学堂何时成立、是什么性质的学校、哪天开学和头一年半办学效果如何,等等最基本的问题都不甚了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北大馆藏的西文图书和报刊中,仍能够找到些许相关资料。那些书和文章的作者均为当时住在京城的外国人,其中包括京师大学堂的西教习、外交官及其家属、记者、海关雇员和传教士等。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们的叙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尤其可贵的是,当时的外国人已经较为普遍地掌握了现代摄影技术,他们所留下的一些珍贵老照片则更是中文史料所无法比拟的。
例如京师大学堂何时成立这个现在似乎仍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西文书中却早就有了定论。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在《1860-1902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第3卷,1902年,405页)和《中国通史》(第4卷,1920年,212页)这两部论著中提到京师大学堂成立时都是列举了两个关键的日期:1898年7月3日,孙家鼐被任命为大学堂管学大臣;同年8月9日,丁韪良出任西学总教习。而英国汉学家马士(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更进一步在其颇有影响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1918,138页)一书中把京师大学堂成立的日期锁定在1898年8月9日,即光绪皇帝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著赏给他二品顶戴的那一天。此后的西文资料中均持此说。高第是巴黎现代东方语言高等学院的教授,法国地理学会会长和法兰西学院院士,同时还是著名汉学杂志《通报》的创办者和编辑;马士是前京师同文馆英语教习和清朝海关的税务司官员,也是著述等身的学者。两人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很长的时间,尤其后者跟丁韪良等人关系密切,并直到1909年才从中国海关退休,因而可以说是京师大学堂筹建经过的目击证人。然而无论是渴望确定建校日期的前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还是北大百年校庆前后曾经炒得火热的那场有关京师大学堂成立确切日期的大讨论,似乎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去向外国汉学家和曾作为目击证人的那些京师洋人们讨教这些问题。
在讨论上述问题时,国内学者往往是把开学的那一天视为成立日期,这样做也是不合逻辑的。一个大学如不先成立,怎么能有人来报考?再说京师大学堂是百日维新运动的产物,它的第一部章程和主要行政和教学人员的聘用和任命都是在维新运动之中完成的。它之所以能够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继续存在,正是因为它的建立木已成舟,“查禁大学堂,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 (荣禄语),并非慈禧太后和守旧派的任何功劳。况且,京师大学堂同时还是清廷掌管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孙家鼐于1898年7至12月期间的一系列有关各地高等学堂和中小学教育的奏折都是以京师大学堂管理大臣的名义签发的,倘若京师大学堂当时并不存在,那他岂不是犯下欺君大罪了吗?

大学堂究竟哪天开学也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陈平原教授曾经在《读书》杂志(1998年第1期)上撰文专门考证过京师大学堂的开学日期。经过令人头晕目眩的繁复考证,他终于得出结论,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12月30日,从而勉强维系了北大创始于1898年的说法。但他始终未能合理地解释《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三二中关于“(戊戌十月)孙家鼐奏开办京师大学堂”的记载和《申报》中关于戊戌年大学堂“定期腊月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四等日,分作四次”给学生期末考试的报道。问题的关键大概是京师大学堂属下的医学堂是在仕学馆之前先行开办的。
实际上,有关大学堂医学堂和仕学馆的开学日期,在西文资料中也有确切的报道。1898年12月4日的《北华捷报》发布了一条写于11月份的报道:“大学堂的医学系已经开办,设在位于琉璃厂的一家医院里,一名西教习正在那儿进行日常授课。据我们所知,他是医学系所设七个教席中目前唯一集主任、教员、教授于一身的人。据说语言系将在农历十月十五日开学。然而鉴于以前几次定下日期均未兑现,最近定下的这个日期是否能够实现仍很难说。(K.,11月18日)。”根据《孙家鼐奏拟医学堂章程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提供的信息,医学堂计划单独招考二十名学生,因此它在11月中已经开办这一事实跟于12月中举行的仕学馆入学考试并不矛盾。上文中虽然没有指明那位医学堂西教习的姓名,但他显然是指原同文馆解剖学教授和后来的大学堂外科学教授满乐道(Robert Coltman)。这位跟丁韪良同属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也和大学堂的其他西教习一样,曾被围困于枪林弹雨的英国公使馆之中。后来他兼任《芝加哥记录报》的驻京记者,并写下了一本《北京被围记》(1901)。作为在率先开办的医学堂独当一面的西教习,他在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初期显然是个功臣。就连1902年张百熙集体辞退大学堂外国教习时,他也是唯一漏网,得以在壬寅年重办的大学堂中继续留任的西教习。

《北华捷报》的上述报道跟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Sarah P. Conger)的说法相符,因此是可信的。由于跟公使很熟,丁韪良在被困于英国公使馆期间甚至曾经跟康格一家住在一起。萨拉在日记中提到京师大学堂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开学一再延期,并且补充道:“丁韪良博士说大学堂到【1898年】11月份肯定会开学,至少是部分开学”。(萨拉·康格《北京信札》,1909,23页。)
自从分部开办以后,大学堂本部也加快了开学的准备。1898年12月19日的《北华捷报》报道:“我们欣慰地从北京获悉,新的京师大学堂正在开办。有通告说,自11月29日起的十天之后,将不再接受入学申请。校长丁韪良博士已经搬入了位于大学校园内的临时寓所之中,旁边的空地上正在建造他的正式寓所。由于房屋的修缮工作延误甚久,是否能在农历除夕之前开学仍很难说。然而入学考试将在本月中举行。”五天之后,即12月24日,又有一个新的报道:“京师大学堂:可以说这所大学仍未正式开学,但我们获知课桌椅现在已经基本上准备就绪,而入学考试即将举行——但愿它能顺利举行。”直到三个多星期后的1899年1月16日,我们才终于在《北华捷报》上看到了等待已久的消息:“新的京师大学堂已于上月31日正式开学。”
关于大学堂本部的这个开学仪式,1899年2月6日的《北华捷报》也作了较为翔实的独家专题报道。因为史料珍贵,特将其全文翻译并转载如下:
京师大学堂
于两星期前举行了隆重的开学仪式。除了该校的西教习之外,没有其他外国人参加这个开学仪式。
对临门的恐惧
京城的传教士们,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对此表示相当愤慨,因为西教习们在开学典礼上对着孔子的灵位脱帽和鞠躬敬礼。他们认为此举表示西教习们跟他们的中国同事们一样崇拜孔子。有人说,尽管西教习们的本意并非崇拜,但本地的中国人却肯定会这样理解。
然而在中国居住时间更长的人就不会这样想。虽然中国人可能会真的报道说西教习们对孔子的灵位顶礼膜拜,但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这样的话,更别提其他人了。西教习们曾被告知,在这件事上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但在开学典礼前举行的教员会议上,他们一致表达了在经过孔子灵位时要脱帽致敬的意愿。中教习中的基督徒也被管学大臣孙家鼐免除了下跪磕头的礼仪,因为后者说他不想强迫他们在这件事上违背自己的良心。孙大人虽然是个保守派,但却通情达理,具有十足的绅士风度。
西教习们
目前有以下成员:校长丁韪良神学博士;英语系的秀耀春先生和裴义理先生;德语系的伯罗恩先生;法语系的吉得尔先生;俄语系的施密特先生;日语系的西郡宗先生和医学系的满乐道先生。以上只是些核心人物,一旦新的大学建筑落成后,还将创建更大和更强的教员队伍。目前已经有三百多名学生正式注册入学,另有一千多人正在等待入学。
K. 1月18日

在马神庙的大学堂本部共分仕学、中学和小学三个部分,但这儿的中小学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小学概念有所不同。因为报考京师大学堂的基本资格就是至少要通过乡试,取得秀才的头衔,即相当于西方的学士学位。上面提到的区别主要是根据官衔和年龄来划分的,如官至七品的举人和进士即为仕学院学生;无官职,但在20岁以上的即为中学生;无官职,20岁以下的通称为小学生。根据丁韪良《中国知识》(The Lore of Cathay, 1901)一书中的说法,大学堂的师资队伍以10名外国教习为主体,另有12名中教习作为助教。后者中除了少数几个原翰林院的编修或侍读之外,多数是教会大学和同文馆的毕业生(20页)。1899年3月6日《北华捷报》的“中国通讯员”报道也支持这一说法:“京师大学堂现有160多名青年学生,大多数为举人和秀才,他们被分班学习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和俄语。自从大约两个多月前,光绪皇帝这个重要的维新改革项目得以实现以来,至少有慈禧太后身边的两名高官用严厉的口吻对大学堂进行了诋毁。他们分别是礼部尚书啟秀(满人)和兵部尚书徐郙。虽然慈禧想以这些诋毁为借口来关闭大学堂,但她身边一些更为明智的顾问,如荣禄和庆亲王等,力劝她不要以此进一步触犯臣民和外国公使。”
正是京师大学堂注重西学这一特点才引来守旧派的诋毁和攻击,以及后来义和团威胁要消灭二毛子的揭帖:“【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佐原笃介、沤隐辑《拳乱纪事》,第二卷,光绪二十七年铅印本,第二页。)但是当我们回到中文史料时,看到的却是一副截然不同的情景。例如喻长霖在《京师大学堂沿革略》(1909)中这样描述大学堂的课程:“学生不及百人,分《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课士,每堂不过十余人。《春秋》堂多或二十人。兢兢以圣经理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学校十三>,8648页。)

喻长霖在这里不仅闭口不提西教习的作用,而且还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第一座新式大学的性质。鉴于中西教习间薪水的悬殊差别(西教习月薪高达五百两,中教习仅为二十五两)和1899年6月慈禧太后下令削减大学堂中国提调和教习的薪水,并引起几位提调和教习辞职的事实(《北华捷报》1899年6月19日),西文资料中的说法显然更为可信。而喻长霖的描述则似乎别有隐情,假如相信他的说法,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同意守旧派的诋毁:即大学堂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兴师动众,“岁靡巨款”,招徕这么些个已获功名的秀才、举人和进士再来背那些他们早已滚瓜烂熟的“圣经理学”,实在是个罪过。
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中国学者至今都站在守旧派一边,对于戊戌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倒是有些跟自己切身利益毫不相干的外国人偶尔会站出来,对大学堂抒发几句由衷的赞美。例如有个叫萨维奇-兰多(A.-H. Savage-Landor)的英国人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充当了战地记者。他在详细描述战争的惨烈和暴行之余,也将目光投向了京师大学堂:
除了那些触目惊心,令人作呕的场面之外,皇城之内还有许多有趣的景色。例如那个建立不久,由外国教习传授西学的京师大学堂。一位富有才华,在中国已经居住了四十多年的美国人丁韪良博士出任大学堂的校长,在他手下还有一个由各国教习组成,声名远扬的教授班子。这个新建的大学堂与翰林院之间有天壤之别,这儿每个房间的墙上都挂满了地图,而在架子上则堆满了用于物理、几何和化学实验的各种仪器。倘若遮住建筑物上那些翘角的屋檐,它看起来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同类正规大学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中国与八国联军》,1901年,第2卷,275-6页。)
如此热情的评价在一百年之后让我们听起来都觉得有点脸红。究竟是这位洋人捕风捉影,看花了眼;还是我们自己色盲近视,妄自菲薄,对西教习们在京师大学堂创建初期的贡献视而不见?
原标题:《海外史料:西方人眼里的“京师大学堂”》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