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罗莎·卢森堡的爱情与革命
原创 东评君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尼尔·阿彻森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我的理想是能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去爱每个人。为了去追求它,捍卫它,我也许要学会憎恨。”写下这些话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还是华沙的一名女学生。她最终没有实现这个理想,但是她也没有学会出于个人原因去憎恨什么。当然,她是一位激烈、出色的战士。她从来没有对错误视而不见,不会放过同道者在学说上的谬误,即使这个人是她的老友——她与自己的仰慕者和赞助人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决裂足以说明这点。当事情变得急切时, 她会拼力反抗,用语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在德国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同道者都放弃了自己的原则,转而支持战争,她写下这样一段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面目是
卑鄙的,可耻的,沾满鲜血的,肮脏的……那个精心矫饰,用美德、文化、哲学和道德、秩序、和平与宪法拼出来的面具总会滑落,人们会看到它真实、赤裸的样子。那个贪婪的野兽将挣脱牢笼,彻底的混乱无序轰然开启,资产阶级受瘟疫感染的气息将给人类和文化带来灭顶之灾……
她的许多温和的同情者一定希望她不要表达得那么“咄咄逼人”!无论是在与德国的社会主义党派自满的宿命论(“修正主义”)作斗争时,在她由于误判对波兰民族自决提出的反对中,还是她对战争和德国军国主义的抵抗,决定参加她知道注定失败的德国革命——她为此最终付出生命,她都拒绝压低声音。“为了捍卫它,我可能要学会憎恨。”她憎恨的是⼀个阶级。她捍卫的是去寻求真正的文明的权利。对她而言,文明不仅意味着礼貌,不仅意味着早晨在干净的杯子里喝咖啡和特快列车,还意味着文化权利,甚至还有“问心无愧地爱”的权利。她的那段“精心矫饰的面具”会滑落的激烈言辞不只是咒骂,它是预言,还是一种对自己信念的宣告。这个预言(没有什么超自然的性质:她对社会力量和历史的认知比其他人的更好)所提到的怪物后来以“国家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了。罗莎·卢森堡在谈到“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的选择时,她是在说,资本主义的崩溃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建立;而在这样的灾难中,“贪婪的野兽将挣脱牢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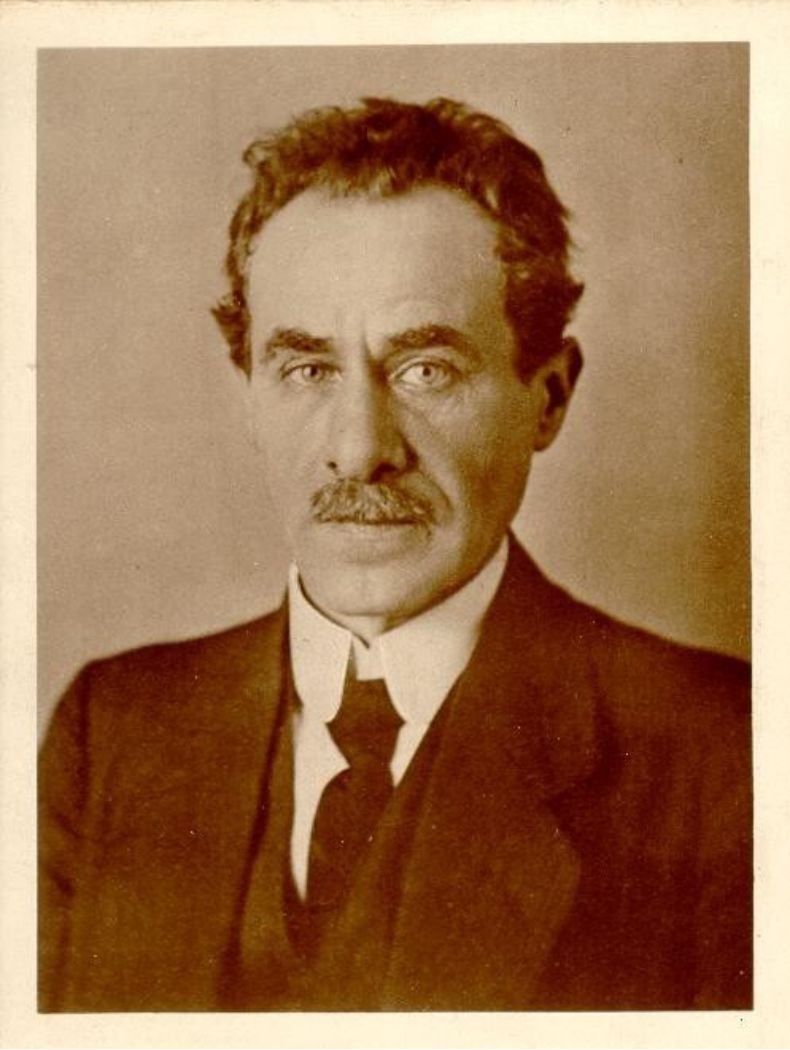
这种宣告信念的方式是她所特有的,那是这位第二国际伟大人物发出的呐喊。埃尔贝塔·埃廷格(Elzbieta Ettinger)在《战友与恋人:罗莎·卢森堡给列奥·约基希斯的信》(Comrade and Lover: Rosa Luxemburg's Letters to Leo Jogiches)的前言中这样写那一代人:“他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们是“开明的欧洲人,其中许多是犹太人”,1914年之前建立起了辉煌、充满希望的革命社会主义。这些人热诚地相信观念的力量,不为那些投入行动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所惧,乘着欧洲理性和人类尊严意识的洪流冲进政治舞台,他们既不会屈尊俯就自己领导的群众, 也不会操控群众。他们是读书人,他们相信社会主义、正派和文明是同义词。到今天,这些人已无处可寻。有些人死在街垒或帝国政权的射击队之前,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死得其所。许多人被斯大林杀害,在惊疑中走向死亡。更多的人则死在纳粹的毒气室。

他们之后的领导人则完全是另一种人。这些人是专制者,他们没有兴趣从事文学活动或提升创造力,只是将文化视为一种感化院的存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会是德皇威廉二世时期的资产阶级熟悉的,而那些社会主义的理念——主观和道德上的解放以及客观上给阶级关系带来改变——在他们金碧辉煌的客厅里则会显得格格不入。但有意识地进行个人的抗争和实验(甚至费边社最开始的名称也叫“新生活协会”)对于第二国际的革命者,尤其对其中的女性革命者来说至关重要,比如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在她早年),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j)和罗莎·卢森堡。我们能从卢森堡的这本书信集里读到她的个人抗争和实验。

这本书信集不会让我们了解卢森堡关于政党的性质或者对辩证法的论述,也不会对论者围绕着卢森堡的思想发生的关键争论产生什么影响——已经过世的《罗莎·卢森堡传》(Rosa Luxemburg, Oxford U.P, 1966)的作者J.P.内特尔(J.P. Nettl)认为她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后来写出《罗莎· 卢森堡的遗产》(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New Left Books, London, 1976)的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则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而非工人阶级的自动胜利,才是她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要素。这本书信集向我们展示罗莎·卢森堡的内心和个人政治,她毕生都在尝试将爱情和工作结合为一体。她并不是女权主义者,总的来说,她更多相信女性受到的压迫和种族主义一样,都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这些不平等现象也会消亡。但是,她与社会主义领导人列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艰难且常常令人恼怒的关系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而现代女性运动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
她必须克服这种“导师-学徒”综合征。聪明的女性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自认智识不足的年轻女性与一个男人在性和精神上联结到一起,这个男人既是她在政治上的老师和权威,又是她第一个重要的恋人。这个女孩早晚会维护自己智识上的独立和价值,在有的情况里,女孩的成就会远高于自己的“恋人-导师”,逐渐对他摆出一副权威的样子产生憎恶。这种解放可能是一场具有破坏力的长期过程,两人的性关系常常会因此破裂,尽管这不是女孩情愿的。罗莎·卢森堡摆脱了早年对约基希斯的依赖,但二人的性关系以及智力上的合作关系持续了16年。即使到最后二人怀着对彼此很深的怨恨,感情破裂,但他们的政治伙伴关系慢慢恢复了。他们一起工作、斗争直到生命最后。斯巴达克同盟起义在柏林的起义(译注:斯巴达克同盟起义是1919年1月5日至12日在德国柏林发生的总罢工和随之发生的武装起义,是德国十一月革命的一部分)失败后,卢森堡于1919年遭到“自由军团”(译注:“Freikorps”,第⼀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军队退出战场后组成之准军事组织。它是魏玛时代半军事组织之一。部分军团成员为后起之纳粹党要员,包括冲锋队首领恩斯特·罗姆和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杀害。约基希斯也是“自由军团”的目标之一,罗莎遇害之后,他留在柏林寻找凶手,几个月后遇刺身亡。

他们在苏黎世相识,那时罗莎二十岁,约基希斯二十三岁。两人都是流亡者,罗莎生于俄罗斯治下的波兰,列奥来自立陶宛——流亡前的列奥勇敢地反抗沙皇俄国。两人都是犹太人,出身中产阶级家庭,年轻的列奥相对富裕,他父亲在威尔诺的工长为他提供了收入来源。两人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是活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列奥高傲、沉默寡言,有一种冷漠的自信,但流亡生涯的无力感令他备受折磨。罗莎精力充沛,健谈、热情,但起初对自己缺乏信心。“我无法创造‘思想’——富有原创性的、真正的思想,”这位自马恩之后、最富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这样抱怨道。列奥帮了她,介绍各种思想给她,直到她开始创造性地思考。
简而言之,列奥·约基希斯有思考的能力,但悲观地不愿采取行动。两人的合作关系逐渐建立起来,罗莎负责写作,进行政治活动,而她所写或所说的几乎所有内容都要交由列奥来批准、批评和修正。需要强调两点。首先,列奥做这些不是简单地为了让罗莎仰视自己;他的内心有一部分是希望罗莎成为知名思想者的,另外,至少对罗莎而言,列奥是⼀位出色的编辑。第二,两个人的这种伙伴关系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们在二十多岁时组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DKP, Socjaldemokracja Królestwa Polskiego),是后来统治波兰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前身。罗莎担任起《工人事业》(Sprawa Robotnicza)杂志的编辑工作,然后于1898年搬到柏林,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开始了她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生涯。整个过程中,列奥·约基希斯一直都是罗莎的编辑、顾问和恋人。
两人关系里困难的根源是列奥忧郁、悲观的天性。他的流亡和无助就像溃疡⼀般。他冷漠,除非在她强烈地要求下,不愿对她表露任何情感。罗莎很快地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您是个愤怒的人,我终于能理解您了,我非常确信。上帝保佑,我要消除您的愤怒。我有权这样做,因为我是个比您好太多的人,而且因为我意识到这点,我更有权去谴责您身上的这种特质。我会毫不怜悯地恫吓您,直到您变得柔和,变得富有感情,像任何一个简单、正派的人那样对待他人。我爱您胜过爱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同时也毫不宽恕您的错误。
列奥不能向自己索要爱这点使她感到愤怒——“给我写温柔的信吧,谦逊一些,烦您屈尊告诉我,您爱我。今天您给我的爱比昨天我给您的多一点。那又怎样?不要害怕向我表达您的感受,不要感到羞耻。”她从柏林寄生日礼物给列奥,他回信说:“你知道我不喜欢礼物。”她非常无奈:“我什么时候才能让您变得更好,什么时候才能将这该死的愤怒从您身上消除掉呢?”
她搬到柏林以后,列奥留在苏黎世,继续写他那没完没了的博士论文,直到最后也没有完成。在两地分离的几年中,两人只能在共同的假期和出席会议时见面。罗莎说服他离开瑞士,搬来伯林和自己一起生活。他的自尊心,再加上对罗莎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日益增长的荣耀的嫉妒,让他下不了这个决心。罗莎预见到了这一点。“由于您的骄傲和猜疑,我的成功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开始怀疑自己搬到德国这个决定。如果,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要么退出运动,与您随便在什么荒山野岭和睦相处,要么虽然能参与到改变世界的运动中,但是却在与您相处时饱受痛苦,我会选择前者。”罗莎很少会有这种多愁善感的表达。她最终的决定——正如埃廷格女士所说,她唯一能做出的决定——是去改变世界,并努力与列奥·约基希斯和睦相处。
和睦是无法达到的。罗莎在任何情况下都喜欢汪洋恣肆地表达情感,而列奥总是在她热情洋溢地抒发感情时冷漠置之,而他的这种反应令罗莎想要更强烈地表达。列奥着实令人沮丧。他们彼此相爱的内在力量来自一种性与政治伙伴关系的结合,正是这种力量让这对常常彼此激怒的伴侣走过了十六年。罗莎对列奥的方式像母亲对待孩子那样,常常担忧他没有好好吃饭或是没有出门散步,而这⼀定会刺痛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自怜的尊严。(他写给罗莎的信没有保留下来多少。而他则细心地保留了罗莎的所有信件,⼀共近一千封,这本书信集里收入的只是一小部分。)
列奥·约基希斯在让罗莎为自己的成功付出感情上的代价,虽然他并不会承认这⼀点。罗莎备受折磨,她意识到自己变得麻木,好让自己不再受到伤害。她困惑地写道:“我感觉我的内心好像有一部分死了。我不再感到恐惧、苦痛、孤独;我成了⼀具尸体。”列奥担心罗莎不再爱自己,似是写了⼀封绝望的信指责她。她回了一封奇特、直率的信(埃廷格说她写这些信就像是在说话,没有她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里的修改和精细结构), 她在信里说,自己现在的情况是工作造成的,工作让“我的心理状态变得不重要。这些心理状态的存在甚至都让我感到厌恶。”
但是随后她又写道,自己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列奥不在身边。
如果您在这里,如果我们在⼀起生活,我的生活会变得正常。那样的话, 我可能会喜欢上柏林,我们俩在蒂尔加滕公园散个步就能让我快活。坦白说,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让我愉快。无论晴雨,对我来说都⼀样。我走在大街上,完全不会留心看商店的橱窗或路人。在家里的时候,我所能想到的只是要做的事情,要写的信,我漫不经心地睡去,然后再漫不经心地起床。归根结底,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您不在这里。
写着写着,她的情绪变得好了些。她谈起自己最近写的文章,谈到选举前景。她的姐姐要来家里做客,她的弟弟获奖了。她把房间彻底收拾了一番,所有东西变得更好看了。她在信的结尾写道:“你什么时候能见到这一切?!尽快回信!!吻你的鼻子和嘴巴……”

罗莎·卢森堡对她心中的“常态”充满了向往:舒适、亲切、安定的生活,有足够的钱买一顶漂亮的帽子,一本精装版歌德全集,与朋友一起分享的食物和美酒。她的品味并非波西米亚风格,但她也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1904年,她从监狱里写信给“列奥尼亚”(监狱规定禁止与男子通信,故将列奥的名字化为女性名字):
你过着如此孤独的生活,这真疯狂,很不正常,我对此很不欣赏。我现在的心情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讨厌这种“禁欲主义”。在这里,我一直贪婪地抓住生活的每一个火花,每一点微光……我向自己保证,我重获自由以后,一定要充实地度过生命里的每⼀刻,而你,坐拥如此庞大的财富,却像沙漠中的圣安东尼一样,以野生蜂蜜和蝗虫为生!亲爱的姑娘,您会变成一个野蛮人的。等我出狱以后,我的如古希腊人般的热情将会激烈地冲撞您那拿撒拉式的冷酷无情!
罗莎提到列奥的财富是有原因的;列奥一直拿自己的收入补贴罗莎的用度,这是她信里的另一个主题。她对漂亮的帽子喜爱给我们造成了遗憾:她在户外时总是戴着帽子——当时的帽子常装饰着硕大的羽毛,甚至在对工人演讲时也戴,帽子遮住了她的脸孔,她在户外的照片很少有好的。
她对“正常生活”有着坚定信念,她希望自己最终可以和列奥⼀起过正常的生活。她回避婚姻的话题,或者仅仅是回避这个词。但她写道:“属于我们的小公寓,属于我们的漂亮家具,图书馆;安静而有规律的工作,一起散步,时不时去看一场歌剧,一个很小的朋友圈,时不时请他们共进晚餐;每年去乡村度暑假……甚至生个小宝宝?难道这些愿望永远也不能实现?永远不能?”她承认自己有过绑架在公园里碰到的小女孩的冲动。“我们共同努力,我们的生活会是完美的!世界上没有哪⼀对恋人有我们所拥有的机会。只要有⼀点友善,我们就会快乐,我们必须快乐。”
让自己的“导师-恋人”成为恋人,将知识权威变为同志,罗莎妥善处理了这个棘手难题。最后是列奥·约基希斯没有跟得上罗莎的脚步。慢慢地, 罗莎厌倦了他的冷漠和敏感,也厌倦了去阻止他的“精神自杀”。最终,罗莎发出挑战,下了一个个最后通牒。“您的来信清楚表明,您搬来柏林的唯一阻碍是您缺乏意愿,没有其他不可思议的原因。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需要永久的结合,那是因为这个人缺乏内在勇气,无法在远距离或者聚少离多的情况下维持婚姻关系。”她还在信中给了不详的暗示:“在柏林, 我一直能看到这样一类女性,男人膜拜她,屈服于她,而自始至终,我的心里都很清楚您是怎样对待我的。过了这么久,我终于明白,您对我,对我内在的⼀切,都不再敏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在读这些如此热情且常常带着安抚口吻的书信时,可能会忘记,当面对魅力四射的罗莎·卢森堡时,列奥·约基希是革命运动中唯一一个不为所动的人。罗莎当时已经非常有名。她被憎恶,也受人崇敬。运动中的人们热切地阅读她的作品,她的批评让他们战栗。在柏林,有许多这样的男人“膜拜”她,想要拜倒在她脚下。罗莎对于这种膜拜之情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她在与列奥的关系中从未尝过这种滋味。
最后,她离他而去,选择了一个膜拜自己的男人。她有过一次神秘的恋情,之后又与列奥有过短暂的复合。1905到1906年,两人被囚禁在波兰。罗莎先被释放。之后列奥越狱成功,但是当他回到柏林时,发现罗莎和克拉拉·蔡特金22岁的儿子康斯坦丁一起生活在“他们的”公寓里。一场可悲的长达数年的游击战开始了。列奥坚持在公寓的书房里工作,直到晚上才离开。罗莎试图将他拒之门外,但总是徒劳无功,几次异常激烈的争吵之后,罗莎买了一把左轮手枪。最终罗莎与康斯坦丁搬到了另一间公寓。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恢复了政治上的合作关系。几年后,罗莎再次寄手稿给他,征求他的意见。两人的往来书信有时关于债务清算,有时是在讨论罗莎新著《资本积累论》(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中的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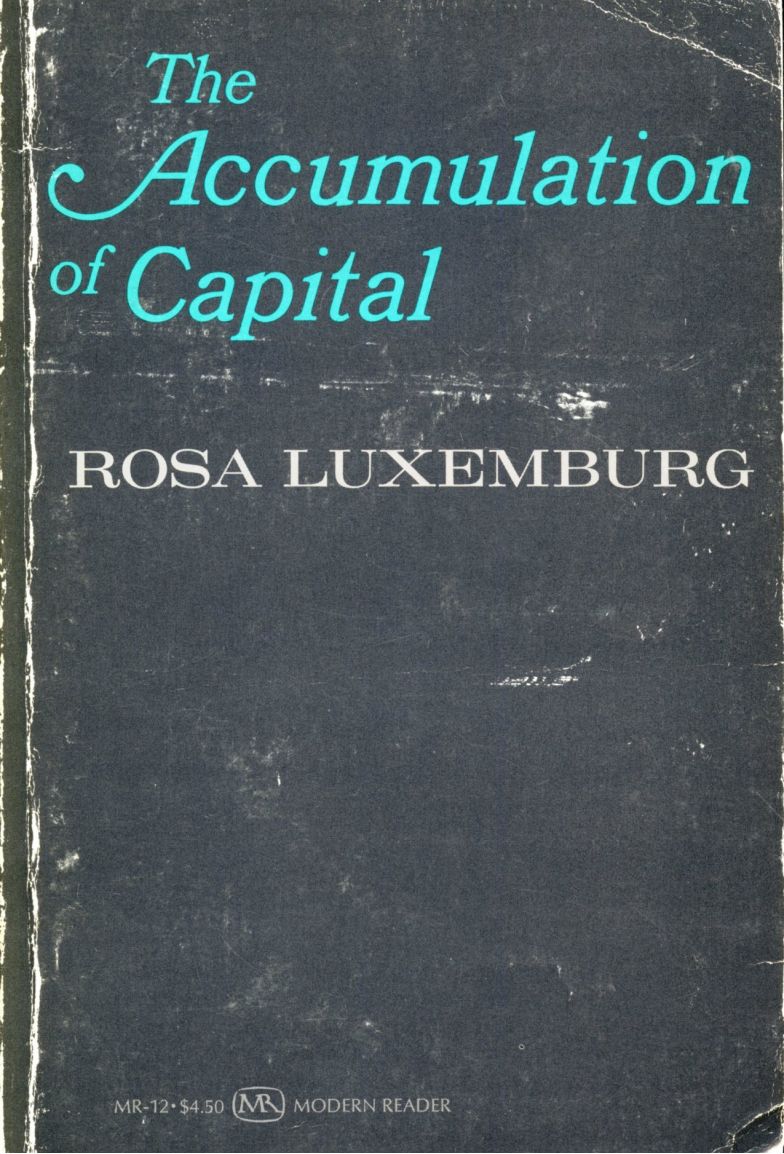
一战爆发,俄国革命爆发,然后,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继而是无望成功的斯巴达克同盟起义。革命和死亡没有将两人分离。有人会说,罗莎和列奥·约基希斯的关系是失败的,我不这么认为;这段关系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它给两人带来如此多的快乐,而且让两人完成了许多英勇而珍贵的工作——两人希望实现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对恋人怀有的激情和个人独立不再相互冲突。罗莎·卢森堡写给列奥·约基希斯的所有信里(埃廷格女士饱含情感地将其从波兰语翻译为英文,我知道这绝非易事),我会一直记住这些话:“我们是那么地相互需要!上帝啊,我们承担的任务是别的恋人都没有的,那就是:让对方成为人。”
尼尔·阿彻森(Neal Ascherson), 苏格兰记者、作家,常年为《伦敦书评》、《纽约书评》撰稿。
本文选自《纽约书评》1980年3月6日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刊发。
原标题:《罗莎·卢森堡的爱情与革命》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