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郁锋 译丨金在权学术访谈:心灵哲学仍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译 / 郁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
金在权(Jaegwon Kim)是国际心灵哲学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著作包括《物理世界中的心灵:论心身问题与心理因果性》、《心灵哲学》和《随附性和心灵:哲学论文选集》等。2000年,金在权在韩国首尔发表了主题为 “走向有限度的物理主义”(Taking Physicalism to the Limit)的系列演讲。其间,他的学生、现任教于美国中央卫里公会大学(Central Methodist University)哲学系的罗伯特·霍威尔(Robert Howell)教授邀请他回顾自己的哲学之路,并评论哲学之走向。本文于2000年秋发表于Ephilosopher网站,此中文版得到了访谈人霍威尔教授独家授权,希望对当下的哲学研究者有所启迪。
”---------------------
Q = 罗伯特·霍威尔(美国中央卫里公会大学哲学系)
A = 金在权(美国布朗大学)
罗伯特·霍威尔:您的求学背景是怎样的?是什么促使您转向哲学并决定将之作为毕生的职业选择呢?
金在权:1955年,在韩国首尔的一所大学学习两年后,我转学到了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在韩国,我的专业是法国文学,到达特茅斯后还继续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法国文学。但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第二个学期转向了法语、数学和哲学的跨专业学习——这源于一件特别的事。在大三寒假,我和另一个哲学高年级的学生同住在一位教授的家里。我们俩经常在一起聊天、争论,尤其是讨论法国存在主义,那时我被像加缪和萨特这样的作家深深吸引。总之,我在和这位朋友讨论存在主义时吃尽了苦头,我说的任何事都立刻被他决然地驳倒,几周后我感到彻底失败了。所以我想,我应该把哲学作为一种可能的专业来了解。在这以前,我仅仅学习了一门哲学导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达特茅斯的哲学系要为我制订一种特殊的跨专业培养方案,以便我能够在接下去的时间里完成学业。我学习了相当比重的数学,因为数学对我来说反倒是“简单”的——我没法用英语写很长的文章!
当我从达特茅斯毕业之际,我的朋友都去申请研究生院,我也一样。我联系了一些(学校),因为卡尔·亨普尔我选择了普林斯顿大学。亨普尔当时在那里教书,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我去普林斯顿学习。我早年在上课时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其清晰和明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实话,我那时并没有准备好去应付研究生的学习,和我的同学们相比,我的准备相当不充分。然而,三年后我还是按时完成了学业。离开普林斯顿后,我在斯沃斯摩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找到一份全职工作。直到我真正拥有一份教授哲学的工作后,我才意识到哲学可能成了我的毕生职业。
罗伯特·霍威尔:如果您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用毕生精力去做另一件事,您会选择做什么?
金在权:我会再次选择哲学。我认为哲学给我们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智识挑战,这些智识挑战是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发现不了的。不仅仅是这些,哲学还给你带来很强的适应性。只要想想看,你们能够从事的工作范围,从量子物理学的解释,到存在个体性的形而上学,再到音乐的美学,所有不同类型的工作无一不在从事着哲学。如果哲学不在这些选择之中,我想我可能会去发掘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有趣价值,理论物理学也非常具有挑战性、非常令人兴奋,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反事实假设是否包括,我会成为一名比在现实世界中的我更为出色的数学家。
罗伯特·霍威尔:您认为对您影响最深的老师是谁?哪位哲学家对您产生了最深的智识影响?(后者不必是您亲身接触的人)
金在权:亨普尔对我产生了格式化的影响。我希望我能学习到他的那种特定的哲学风格:一种强调清晰、可靠的论证,厌恶有意晦涩及故弄玄虚。接下来,我必须提到罗德里克·齐硕姆(Roderick Chisholm)。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我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来到布朗大学时,正好遇上他的哲学高峰期。从他身上我学会了不再惧怕形而上学(毕竟我曾经是一位逻辑实证主义领袖的学生),并且我相信离开了齐硕姆的影响我将不能轻而易举地转向我所从事的心灵的形而上学和哲学——后来我被布朗大学聘去接替韦斯利·萨尔蒙(Wesley Salmon),教授科学哲学和逻辑。亨普尔和齐硕姆在哲学背景和定位上截然不同,但是他们在哲学风格上又十分相似。
罗伯特·霍威尔:是什么吸引您开始研究心灵哲学?
金在权:一些哲学家从心理学,从对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生物学等的最初兴趣到达心灵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从形而上学到达心灵哲学,当然我属于后者。首先,心身问题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另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但在80年代早期,当我开始从事心理因果性(mental causation)问题的研究时,情况改变了。我认为,我所陷入的问题正是对我个人而言最有意义的。我感到这个问题关注的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人类一员的重要方面,这些都是我需要去深入理解的。
罗伯特·霍威尔:您预测心灵哲学的趋势会是怎样的?
金在权:我想,无论在科学还是哲学领域都不会有人愿意与意识研究的繁荣擦肩而过。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繁荣即将到来,可能就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感到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所有有关意识的有效解释或多或少都濒临破灭,并且没有真正的进步浮现出来。在意识研究中存在着大量有趣的东西,并且我确信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只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访同样的地方,并且我们正面临着困扰先辈哲学家,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突现论者(emergentists)和其他许多人的同样困境。
我无法准确描述心灵哲学的前进方向在哪里,但是对我自己而言,我乐意更多地去从事和关注的是一般性的主体性(subjectivity)问题。意识是一个可以归入主体性的问题,但是它并不能穷尽所有的主体性问题。除了意识外,主体性问题还包括主体和行动(agency and action)的问题,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问题和其他那些我有着重大兴趣的问题,并且通过考察这个更为广泛的主体性问题,我们可能在未来意识研究中做出一些真正的推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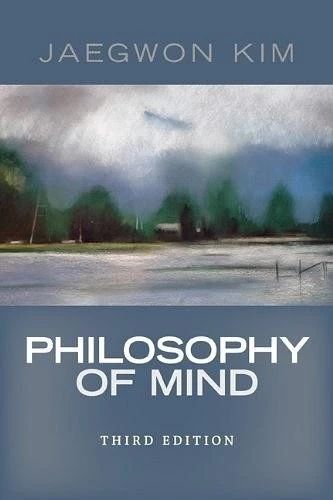
Philosophy of Mind
Jaegwon Kim (Author)
Westview Press,2010-12
罗伯特·霍威尔:您如何描述心灵哲学和更多关于这一主题的经验研究进路(如认知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之间的共同性和关联性?
金在权:我认为并不是很多。在我从事的抽象层面的工作中,实验结果与之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关联。我有时能读到或听到某些有趣的理论的和经验的发现,它们可能会促动哲学的思考,但是我认为,我在心灵哲学中从事的工作与认知及意识的系统科学的结论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
罗伯特·霍威尔:您目前的研究兴趣是什么?有新的研究计划吗?
金在权:此刻,我正在完成五个关于心灵哲学的系列演讲,这些演讲将在首尔报告(作为“大宇Daewoo系列讲座”的就职演讲)。这项工作是围绕“走向有限度的物理主义”的一般主题展开的,它再次与心身问题和心理因果问题相联系,并且和我在大约三年前出版的《物理世界中的心灵》有所重合。我希望这一次我能试着用一种比在早先书中更系统、更全面、解决得更好的方式,确定我关于心身问题和心理因果性的一般观点。我相信在这些问题上,我至少已经达成一种稳定的观点,我感到这一观点是合适的。我的大体结论是:严格说来,物理主义是错误的,但是它又足够接近于正确,目前为止足够接近已经就是足够好!在这之后,我想更加认真地去思考主体性问题。但现在我不能说一定能从中得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罗伯特·霍威尔:金在权教授,您最著名的论证可能就是主张非还原的物理主义(non-reductive physicalism)不能完成它自己的目标,因为心理属性是副现象(epiphenomenal)的,而且不会增加任何东西到它们实现者的因果效力中。这是对您的论证结论的准确表述吗?
金在权:是的,这是准确的表述,即使我把我的观点推及得有点普遍了。也就是说,在非还原物理主义之下是不可能澄清心理因果性问题的——心理事件和状态如何能与物理事件或与其他的心理事件关联进入到因果联系之中。这一困难以何种形式严格展露出来,取决于争论中非还原物理主义的特定形式。戴维森的“无律则”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这一学说认为虽然每个单个的心理事件是一个物理事件,但是在心理的类和物理的类之间不存在似律则(lawlike)的联系。众所周知,戴维森的因果性观点也需要包含“严格”(strict)律则的联系。而且按照他的思路,严格律则只存在于物理域中——他的说法是在“未来的物理学”(developed physics)中。正如许多哲学家所论证的,无律则的一元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无律则一元论之下心理属性是副现象的。当然,戴维森对此并不认同。换句话说,某一特定事件该归入哪一种心理的类的问题,或者什么样的心理描述适用于它的问题,显然与某一特定事件所进入的因果联系是不相关的。
许多物理主义者拒斥无律则一元论中的“无律则”,认为事实上,在心理的和物理的属性/类(properties/kinds)之间存在着似律则的关系。这一群体包括那些相信心身随附性(mind-body supervenience)的哲学家和那些相信心理学是一门特殊科学的哲学家。例如,以下述立场来说,物理主义者广泛认同:心理属性尽管与物理属性不同,但是它们在神经的/生物的系统中物理地实现(可能也在非生物的系统中)。我把这一立场叫作“物理实现主义”(physical realizatonism),我也见过“实现的物理主义”(realization physicalism)的术语,我更喜欢后者。
由于一个我觉得无法避免的原则,非还原的物理实现主义陷入了心理因果性的困境。这就是我称为“因果继承”(causal inheritance)的原则——它认为如果一个属性P在某一特定的情形下由于被属性Q实现而被例示,那么这个P的例示并没有超出它的实现者Q的例示的因果效力。需要记住的是,在实现的物理主义之下表明了不仅仅是心理属性,而且包括在心理属性中的因果关系,都是能够被物理地实现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心理属性就没有超出它们下层物理属性的因果效力。这一结果与非还原物理主义的主张不一致。非还原物理主义主张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明显的不同(如果这里的“不同”意味着任何的不同,它也一定是“因果的不同”),主张特殊科学是从事分析那些处在“高级”层次("higher" levels)上的因果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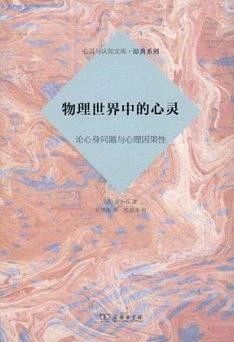
物理世界中的心灵
[美] 金在权 / 著
刘明海 / 译
商务印书馆,2015-06
罗伯特·霍威尔:因果继承原则似乎是直觉性的,许多自认为是非还原物理主义者的人仅仅把它视为一种自然的约定。难道不存在拒斥因果继承原则的人吗?在您近来的一些著作中,您还关注到突现论者。他们拒斥因果继承原则吗?存在一些独立的反驳论证吗?
金在权:是的,有些哲学家——正如你所提到的大多数著名的突现论者——认为,像意识和理性这样的高层属性,它们具有超越下层过程的因果效力,同时这些高层属性又是从下层过程中突现出来或者与它们紧密相关的。这就是突现学说的要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因果继承的原则是用术语“实现者”(realizers)来表述的,而不是用“突现基础”(emergence bases)、“低层相关物”(lower-level correlates)或 “神经基底”(neural substrates)来表述。实现或者作为一个实现者是在下述特定的专业文献中被使用的:只有“二阶的”(second-order)或者“功能的”(functional)属性具有实现者。一种功能的属性就是通常被称作的一种“因果作用”(causalrole)。
聊举一例。疼痛,它是一种功能属性,它处在某种状态中——这种状态典型地由组织的损伤所引起,而且典型地引起像畏缩和呻吟之类的行为。仅仅在这一情形下,当一种状态满足定义疼痛的因果规范,即这种状态典型地由组织的损伤所引起,而且典型地引起像畏缩和呻吟之类的(行为),在这一意义上任何诸如此类的状态或属性都是疼痛的实现者。如果C型神经纤维的刺激具有这类的因果能力(在哺乳动物中),那么它就是疼痛(在哺乳动物中)的一个实现者。因果继承的原则说的是,对于像这样的一个疼痛概念,单个的疼痛的例示(在哺乳动物中)并没有超出C型神经纤维的刺激的因果效力。
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C型神经纤维的刺激仅仅是与疼痛相关——这些属性与和它们彼此相关的属性明显不同,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两类属性在它们的因果效力上必须一致。但是,这并没有使突现论者或其他人完全摆脱困境。在我所理解的突现的普遍意义上,突现的属性能够将新的因果效力带入世界。当然,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对突现论的强有力反驳。
罗伯特·霍威尔:您在论证中所使用的一个关键假定是,物理世界是因果闭合的(causally closed),也就是说所有的物理事件都有物理的原因。您认为物理的因果闭合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吗?或者您假定这样一个论题只是先验的考虑吗?
金在权:对物理主义者来说,它不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论点可能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物理主义包含了物理域的因果闭合,这不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拒斥了物理的因果闭合就等于接受了存在着非物理的因果力把因果影响施加给了物理域,笛卡儿交互主义的二元论(Cartesian interactionists dualism)严格地说就是这样一种立场。相反,相对于某一特定的物理变量(如聚集、能量、旋转等)的集合,物理域是否是因果地闭合的这一问题的确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我们可能会想起这与奎因(Quine)“物理主义”的联系。最后我应该补充一下:尽管,当然物理因果闭合的原则使得困难更加突出和引人注目,但对物理主义者而言,物理因果闭合的一般原则并不是产生心理因果性困惑所必须的。
罗伯特·霍威尔:近来,对于意识或者感受性(qualia)可以还原为物理基质,您表示深深地怀疑。基于您其他的一些论证,这可能暗含了感受性是副现象的。然而这似乎又是相当违反直觉的。处于一种状态中的感受似乎与正在讨论中的这种状态是什么紧密联系,您认为会有哪些独立的考虑,可能减轻某些人对您立场的不适?
金在权:我认为,感受性的副现象主义所引起的不适如果不能完全消除,也是可以充分减轻的。感受的特质(quale)不是功能化的——而且因此,依照我的看法是非还原的——和副现象的,这正是它完全内在性的一面;也即,它是一种绿的可感受特质中的绿色或者一种红的可感受特质中的红色——或是看上去像绿色或者像红色的东西,也就是说不能功能地同一。然而,看上去不同的一种绿的特质和一种红的特质是能被功能化的。你和我都一样地擅长从一堆菜叶中挑出熟了的番茄,这一事实并不依赖于我们共享关于绿色和红色同样的可感受特质;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可靠地区分红色和绿色。因而,尽管可感受性内在的“感受”和“感觉”不是功能化的,不同可感受性之间的区别与相似之处却是能被功能化的,因而也是因果有效的——我认为类似的观点石里克(Schlick)在20世纪20年代早已提出,他说仅仅是经验的形式而非内容能够被描述和交流。我认为,悉尼·休梅克(Sydney Shoemaker)不久前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所有这些都还只是粗略的,但我想你能看清我前进的方向。
罗伯特·霍威尔:上述观点比人们最初认为的要容易接受些。但是,难道就没有一些更严重的担忧存在吗?例如,我们大概知道我们的感受性。只是说大概,因为你知道自己感觉到的那些东西不是功能性的。然而在知识论的讨论中,感受性又存在着因果的差异。
金在权: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的感受性的知识视为感受性和我们(这里的“我们”是指什么呢?)之间因果交互的中介。正如你所知道的,知识的因果论通常是由关于物体和物理事件的知识,特别是知觉的知识、梦的知识等的思考所引发的。我不知道哪个论证表明,或者看似合理地令人相信,我对自己当前疼痛的知晓需要一种知晓和疼痛间的因果联系。如果在这一情形下存在这样一种因果联系,那么我更愿意认为,起到因果作用的正是疼痛的神经基质。当然,我所赞同的这一立场与某些常识看法——如“常识(心理学)”(folk)关于心灵的观点——不一致。绝大多数心身理论都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经典的副现象论可能更糟。但心灵哲学仍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地方,在道德理论中我们有过很多类似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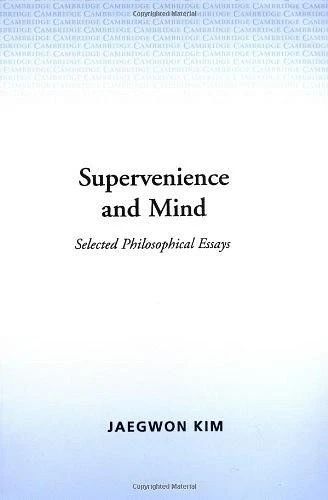
Supervenience and Mind
Jaegwon Kim (Auth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1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9期。本文封面图为金在权教授肖像,摄于2010年,由郁锋提供)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