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公明︱一周书记:医学史与“向死而生”的……哲学与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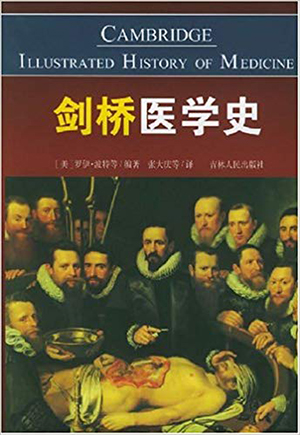
(原书名: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cine,张大庆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与其他侧重和强调专业性“内史”的医学史著作不同,它结合了医学史研究的“内史”与“外史”的研究视角与叙述框架,在论述从古至今西方医学发展历程、重大事件和辉煌成就的同时,不断讨论了医学发展与历史环境、社会制度、文化习俗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与罗伊·波特(Roy Porter)作为伦敦维尔康医史研究所医学社会史教授的专业研究方向当然有关,他的其他著作还有《社会的医生:托马斯·比多斯与启蒙时代晚期英格兰的医疗业》(1991)、《伦敦:社会史》(1994)、《人类最大的福利:人文医学史》(1997)等。这部《剑桥医学史》的主要目的是将医学的发展变化置于历史的情境中来理解,作者认为“对医学历史的理解比高唱赞歌更为重要。本书将试图解释这些现代变化的原由,显示出为什么采取了这一条道路而不是另一条道路,分析普遍趋势和领先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将认真思考我们现在看来是稀奇古怪的和非科学的生理学和治疗体系,以及它们被采用背后的原因。”;“《剑桥医学史》也将试图超越仅仅是简单地讲解医学的发展、医学与科学、社会和公众的关系方面的故事。它的目的是通过历史分析,将医学置于显微镜下,探索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过去几个世纪里医学发生如此巨大变化,而且还将继续变化这一引人入胜的问题。”(第6-7页)今天的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历史上人类身体的健康、疾病、治疗以及预防手段,医学技术的进步、医疗制度的建立、医疗机构的运作以及医学教育的发展,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放在社会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正确的认知和阐释;关于当代医学的发展难题及应对策略,更需要对医学进步的性质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巨大变化的关系有敏锐的思考和跨学科的研究。应该说,该书作者对这两个维度的认识和关注是相当明显的,问题只是因有限的篇幅和适合大众阅读的目标而未能展开全面而又有足够深度的阐述。比如,该书第九章“医学、社会和政府”下的小标题分别是“医学机构与政治——概述”、“启蒙时代欧洲的医学市场”、“法国医学的革命”、“医学、工业与自由主义”、“科学与道德”、“帝国主义与社会福利”、“社会问题的科学解决办法”、“新型医学经济”、“市民的医学(1920—1970)”、“战时医学”、“二战后的卫生服务”和“历史、未来”,都是很重要和诱人的论题,如果充分展开论述,本身就是一部近现代医学社会史的专著。
那么,什么是当代医学的发展难题与困境?作者指出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对西方医学的批评日渐增强,谴责西方医学体系太技术化取向、太非人格化、太体制化、太高技术化、太科学化、太官僚化,谴责它考虑更多的是医学职业的发展而不是病人的利益。(中文版序言,第4页)对于中国的医患关系而言,这“六化”也同样不陌生,只是在其中又有更多的本土因素。还有,“存在的是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可能出现后果的恐惧日益增长。与此同时,由于保健费用不断增高,不堪重负……医学科学的发展将使得许多人负担不起医疗保健吗?医学将屈从于增加费用和精确程度而减少利用的反比定律吗?”;“在富裕国家,贫困者依然得不到足够的医疗;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国际援助,疟疾和其它热带病仍在肆虐。曾被认为已得到有效控制的白喉和结核病,在俄国和其它工业化国家卷土重来。还有艾滋病的流行已摧毁了疾病将被征服的信仰。”(导言,第9页)这些是作者写于九十年代前期的情况。二十多年又过去了,有些问题已然改变,但是新的难题和困境不断出现。一个更大的背景因素使医学与公共卫生面临更严重的挑战,那就是全球化的急剧扩张带来的防疫卫生的全球化需求与国际政治现实格局的尖锐冲突。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跨国传播为此提供了最新的剧情版本,而全球化的生产与消费链条也发出了次生经济灾难的警告,防疫与治疗的责任已经远非一国的医疗部门所能完全承担。
面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困境和越来越诡异的爆发不明原因疫情的风险,人类不能再盲目迷信依靠医疗技术的进步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医学政治学、医学社会学、医学经济学和医学伦理学等论域的研究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从权利和责任的角度全面提升公共卫生和医疗事业在社会运作机制中的地位也是必要的对策。如果说当代医学与公共卫生防疫事业有许多命中注定的新使命的话,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倒逼全球化的公共防疫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否则人类家园将面临共同的灭顶之灾。不应忽视的是,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西方医学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是西方自己的观念、西方宗教传统以及与诸如主观性、自主性、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等价值相关的、更广泛的理性假设的一部分。因此,理解西方医学的基础是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如何在那个“更广泛的理性假设”的基础上思考全球化时代的医疗卫生事业和我们的责任,这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而当我们这样思考的时候,作者似乎是在提醒我们:“在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历史中,医学是其中的一部分。它的未来,也与它的过去一样,不仅在西方国家里,而且在‘第二’或‘第三’世界中,都将取决于财富和权力模式的转换。”(557页)在西方国家,与财富与权力模式直接相关的是税收与国家财政的支出,就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讲的,“医学和治疗学的这些进步不是荒漠上开出的花朵,它们产生于社会对医学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的巨大支持。在英国,国家卫生服务自1948年创立开始就一直处于赤字运转。在英国,国家卫生服务自1948年创立开始就一直处于赤字运转。在世界范围内,大量的社会和私人资源投入医学。目前,在美国和欧盟国家,超过10%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卫生保健。”(第4-5页)很显然,无论是重大疫情或是医疗状况,都可以成为价值反思和政治启蒙的新的契机。
这部《剑桥医学史》使用了大量插图,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珍贵的图像史料。十六世纪末在墨西哥高原流行的天花导致约两百万人死亡,天主教会学者萨哈冈(Sahagun,F.B.1499—1590)编撰的十二卷本《新西班牙通史纲要》(发表于1547—1569年间)中的一幅插图(45页)以多个画面详细地描绘了阿兹特克人被天花感染之后浑身出现斑点最后走向死亡的情状。在这部著作的第三卷,有一幅插图也是以一幅多图的形式描绘阿兹特克人如何以各种方式治病,说明“所有的人群都发展了他们自己特殊的地方化治疗、麻醉药及疗法的知识。”(394—395页,在这里译者把作者名字译为“萨哈格温”)实际上该书217页的那幅彩色植物画《规那树》(或称之为金鸡纳树)也是出自这同一部著作,这种植物在十七世纪从南美引入欧洲,作为治疗发烧的药物和滋补药而大受欢迎。关于地方性的草药,作者介绍了约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一位拜占廷艺术家出版的《文德波内西斯手抄本》(Codex Vindobonensis),内有近400幅彩色植物插图,其中许多插图是临摹公元前一世纪希腊一位内科医生克拉特乌斯(Krateuas)的绘画,有些植物正是今天熟悉的药物(400—401页)。该书402页是公元十二世纪的一部《解毒药书》的彩色插图,描绘的是工人正在耕种草药;403页是一部公元十三世纪手稿中的彩色插图,上半部描绘以热敷治疗一个儿童,下半部描绘医生要一位妇女服用草药。这些插图和资料描述涉及同样的主题:草药与地方性的治疗方法,类似这样的图像史料在医学史研究中当然具有重要的“图像证史”的作用。
从《剑桥医学史》回到现实。疫情在有些地方继续肆虐,寒冷仍然封锁着大地。“向死而生”的哲学与诗歌,所有那些我曾经读过、写过的那些关于生与死以及愤怒诗歌的文字全都喷涌而出。
关于生与死,西哲多有言述。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死是“趋向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 death),也就是说,人活着、生存着的方式就是“向死存在”的方式,即“向死而生”。这不仅仅是说“人固有一死”,更重要的是说人只有积极地面对死亡、思考死亡才能获得生之存在的意义,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畏死”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活在死之中,“向死”而筹划自己,实现自己。用通俗的话说,只有勇敢地思考死亡,才能真正“活个明白”。科耶夫吸收了海德格尔的生死观,承认“人的理想只有通过终有一死和知道自己终有一死的人才能实现”。在哲学、政治学与神学之间,“向死而生”肯定了人的存在价值;也肯定了只有通过“生死斗争”,人才能体现自由的本性,并且更能体验生存的偶然性和特殊性。
匈牙利作家、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哲尔吉·康拉德说,“就算是如此众多的暴力死亡也不能掩盖那些光彩夺目的冬日早晨的美。处于死亡的阴影下,面包变得更像面包,果酱更像果酱。我愉快地将各种各样的家具劈成柴火。”(《客居己乡:一段匈牙利生活》,59页,徐芳园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这是“向死而生”的美学,是康拉德的反抗美学的真实基础。另外,还有读书人的生死观。乔·昆南的《大书特书》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通过读书向天空挥动拳头。只要还有这些史诗般的、无法完成的阅读计划在前头,我们就不能咽下最后一口气:叫死亡天使迟点儿来吧……。坏人会被打败,好人必将胜出。只要还有美好的书等在那儿,我们就有机会调转船头找到安全的港湾。希望还是有的,用福克纳的话说,我们不仅会活下来,我们还会得胜。希望还是有的,我们会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陈丹丹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252页)这可能是关于读书人的希望与生死观最概括、最精彩的表述吧。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研究历史上的死亡现象以及政府、人民如何看待死亡、处理死亡,这是近乎神圣的研究主题。当死亡发生之后,死亡本身并不能为这一页打上句号,而是必须等待对死亡的描述、认定和判断。历史学家熟知死亡曾经被刻意隐瞒、被违心诬蔑的历史,知道意义重大的死亡之页常常要经过漫长的期待、斗争甚至以付出新的死亡为代价,才能完成其书写、才能最终掀翻过去。除了历史学家,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怜悯、正义、公平之神在冥冥之中对死亡的承诺,但这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美国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孙宏哲等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告诉我们美国内战结束后北部与南部的民众如何面对杀戮和死亡的事实、如何埋葬死难者、如何哀悼与纪念、如何帮助死难者的家人,以及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了那些幸存的人。从尸体的物理处理到死亡通知的发放,从死者墓地到新的国家权力,作者以包括有私人日记和通信、宗教文献、新闻报道、文学作品、死亡档案、墓地材料等极其丰富的史料,从多种视角还原出一幅幅汇聚着种族与国家、宗教与政治、历史与现实、记忆与想象等维度的死亡全景图像。福斯特强调死难者的牺牲使作为幸存者的国家必须负起正义的责任,也使人们重新理解国家的实质与命运,这就是南北内战对美国历史的意义,也是死亡缔造了现代美国的含义。
最后要谈的是诗,这几天有几首诗感动了很多人,说明诗歌仍然与苦难和良知同在。我想起以前读过的深圳“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那些在他一跃而去的身影后留下的诗歌,以及在他诗歌中的生产流水线。“我几乎是爬着到达车间……在每个人类沉沉睡去的凌晨,我跟工友都睁开青春的一对伤口 / 这黑色的眼睛啊,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吗。”(《夜班》)最后他的求救让人心悸:“我比谁都渴望站起来 /可是我的腿不答应 ……我只能这样平躺着 /在黑暗里一次次地发出 /无声的求救信号 /再一次次地听到 /绝望的回响。”(《我一生中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