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
问一个问题:到1911年为止,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瘟疫?
根据陈高傭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中不那么精确的统计,总计288次,平均下来差不多每隔7到8年,中国便会发生一次瘟疫。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
很可惜,除了说明瘟疫的发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以外,什么也说明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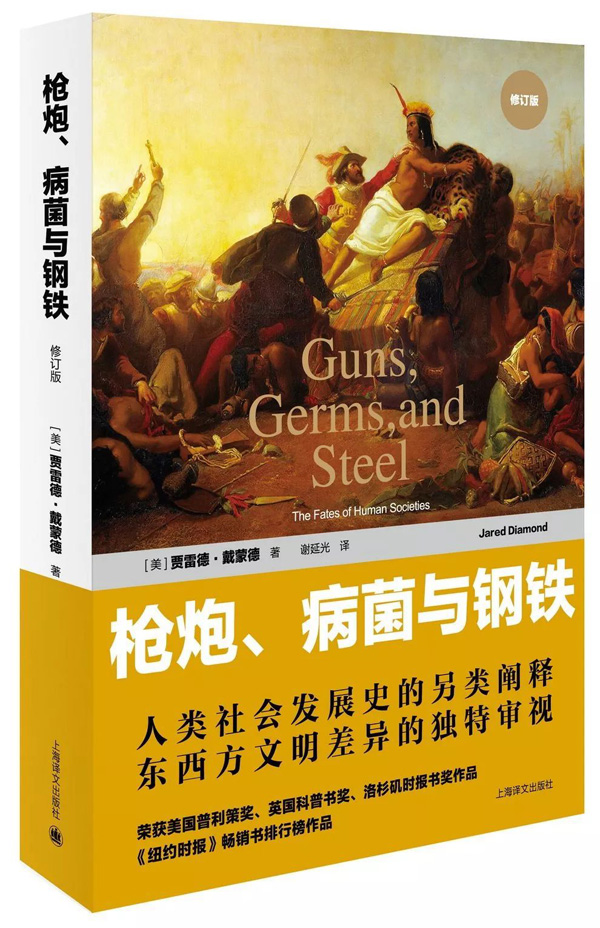
大疫当前,许多经济学家又开始热议那本“明星作品”,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本质上和另一本红得发紫的著作——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一样,他们在展示着韦伯百年前预言:“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空心的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主题,其实是19世纪末以降社会科学界流行的社会进化论的一个变体,并且按照二战以后国际主流学界的“道德标准”,剔除了那些在立场问题上备受质疑的“糟粕”,书中的主要观点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何谓“民族环境的差异”?戴蒙德旁征博引了许多前沿理论,涵盖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地理学、行为生态学、流行病学乃至语言学领域,外加上传统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其实撇开这些花里胡哨的学术外衣,本质上《枪炮、病菌与钢铁》讲述的就是一个地理决定论2.0版本的故事,或者用戴蒙德的话来说:用科学的方式讲述人类社会的历史。
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例如戴蒙德在书名中就明确指出的那个决定性变量——病菌(瘟疫),是否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呢?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借由医学史上那个最为著名的案例之一——1665年的伦敦鼠疫,来简单地审视瘟疫和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1665年至1666年间,伦敦城爆发了一场大瘟疫,后世学者确认当时的疾病就是淋巴腺鼠疫。这场瘟疫造成大约10万人死亡,差不多相当于那时候伦敦城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鼠疫是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最为常见的流行性疾病之一,14世纪时至少夺去了7500万人生命的“黑死病”,普遍认为也是淋巴腺鼠疫。伦敦瘟疫爆发前的数十年间,英国本土就已经出现过两次鼠疫,只不过规模没有那么大而已。1665年瘟疫的来源,多认为是由荷兰人传入的,因为阿姆斯特丹在1663年至1664年间同样也爆发了鼠疫,造成5万人死亡。
伦敦瘟疫最早的病例出现于1665年4月,同年7月,疫病开始无法控制。和现在不同,当时的伦敦城并没有采取封城等隔离措施,大批市民——无论是贵族还是贫民,纷纷逃离伦敦。这样的做法有利有弊:最大的弊端就是瘟疫蔓延到了伦敦之外,比如法国,第二年的冬天也遭受了鼠疫之苦;而好处就是由于一直维持着商业贸易等对外交流活动,伦敦城没有经历严重的物资匮乏之困。与之相比,伦敦附近的小镇艾亚姆的居民则非常前卫地采取了封镇措施,拒绝伦敦商人进入,断绝和外界的一切往来。他们成功地阻止了瘟疫进一步向伦敦以北地区的传播,不过代价也是巨大的,四分之三的小镇居民死于这场瘟疫。
伦敦大疫之时,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携带他的王室内廷,整个搬迁到了牛津。而作为伦敦城主要行政管理的人员——伦敦市政府参事、行政官员,却选择和当时的伦敦市长劳伦斯爵士一起,留驻伦敦。
这样的情形对于国内普通读者可能很难理解。其实一直到18世纪,英国并行两套国家管理机制,一个是王室内廷[King’s Household],主要由世袭贵族组成;另一个则是政府[government],主要由经贵族举荐、经过考核的职员(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公务员)构成。有点类似于我国西周时期的“双轨制”模式:王家和卿事寮。没错,当时伦敦城的科层制官员机构选择坚守岗位,而世袭管理层则选择放弃伦敦城。
除此以外,选择留守的还有神职人员与医生、药剂师,这些不那么专业的人员构成了17世纪的那批“最美逆行者”,每日穿梭于空荡荡的伦敦街道,救助病人,处理尸体,他们被形象地称为“瘟疫医生”(plague doctor)。
那么,这些留守下来的人们遏制住了瘟疫吗?事实是残酷的。在当时的医疗和技术条件下,他们的作用微乎其微。和所有瘟疫爆发之初的恐慌情绪相似,当时的伦敦市政府出台了许多措施,想要控制瘟疫的扩散,但其中大多数只是盲目之举。比如,伦敦市议会下令扑杀所有的猫狗,因为人们认为疾病的来源是这些宠物,结果反而导致真正的病源——老鼠,由于缺乏天敌而疯狂繁殖;又比如,人们普遍相信火能够清除病菌,于是市政府指派大批人员夜以继日地在城内燃烧大火,希望借此扑灭瘟疫;再比如,有人提出有强烈气味的物质可以杀灭病菌,市政府就敦促市民大量吸食烟草。所有这些举措不仅徒劳,甚至现在看起来有些荒唐。
当时伦敦市政府最正确的决定恐怕就是有组织地处理尸体,避免瘟疫进一步扩散。结果瘟疫仅仅在两个月之后就达到了高峰,每周约有7000人死亡,根本无暇处理尸体,最终只能在教堂墓地中匆匆挖坑填埋了事。
1666年初疫病总算得到了控制,但谁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最有可能的原因,或许还是只能归功于欧洲人在生理上的进化——不管戴蒙德或者那些坚持政治正确的学者喜欢与否。因为事实上在差不多同一时期,鼠疫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销声匿迹了。经历了三百年的鼠疫困扰之后,欧洲人自身的免疫系统终于演化出了与疾病抗争的机制。
所以,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究竟激发了英国人的“民族环境”在哪些方面的大变革呢?
恐怕很难说得清楚。
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的进步?每一次瘟疫都会对相应的技术进步产生刺激作用,但技术进步却并非是瘟疫的直接产物。学者们最经常讨论的话题就是瘟疫与现代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发展之间的关系。然而真正让这些近代医学实践获益的,实际上是习俗和军事管理的力量。例如,将牛痘疫苗接种技术推广开来的,不是英国皇家学会、地方卫生委员会,而是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医疗机构。
经济的发展?与其说伦敦瘟疫刺激了英国在近代世界的经济崛起,不如说1666年的伦敦大火发挥的作用可能更重要些,至少这场大火导致伦敦城的重建。
政治的变革?表面上看似乎瘟疫对于英国现代政治进程确实发挥了影响。因为斯图亚特王朝不是毁于查理一世被砍头,不是毁于光荣革命,而是毁于瘟疫。但不是1665年的伦敦鼠疫,而是18世纪席卷欧洲的天花。
其实真正的变革不在于王室,而是经过瘟疫、火灾磨练出来的英国官僚政府和与之相应的公共服务体系,也正是这套体系,是英国近代公共卫生制度真正的幕后推手。但是这批职业化官僚在面对疾疫时的手足无措和效率低下,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当时,后来依然如此。例如1832年英国暴发霍乱,政府随即成立卫生委员会专门处理瘟疫难题,但是一直到1848年再次爆发霍乱,这个卫生委员会都没有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一直要等差不多再一个十年的周期,这个从地方到中央的公共服务机构才开始真正运作起来。不只是英国,全世界的行政机构在公共卫生问题上的处置效率差不多都是如此。一直要等到二战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即便如此,在面对新疾疫时,曾经的恐惶失措又会再度重现。
所以,说瘟疫——也可以包括自然灾害、地理、气候等诸如此类的客观因素——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决定性变量,这是一个既无法证明又无法证否的命题。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瘟疫,但是对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时期,其后果都是难以预料的。黑死病造成的死亡肯定深刻改变了欧洲的人口结构,但是不同的社会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却未必相同:法国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波兰却发生分裂;曾经的海上霸主威尼斯,更是沦为奥斯曼土耳其的附庸。
至于许多经济学者奉为圭臬的案例: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新大陆的原住民不是因为西班牙的军事征服,而是由于天花、麻疹、伤害……这些从旧大陆带来的疾病,才导致了灭顶之灾。不过,多数学者在讲述这个案例时往往忽视了疫病传播的双向性,当旧大陆向新大陆输入疾病时,新大陆同时也向旧大陆输出新疫病——比如流感。但是为何自16世纪以后开始肆虐欧洲的流感所导致的后果与美洲相比要轻微得多呢?是否,并非是美洲的原住民的生理机制,而是阿兹科特帝国和印加帝国的社会组织模式,真正缺乏抵御瘟疫的免疫机制?
瘟疫会对人类社会组织产生冲击,但我们的社会并不一定会因此而改变;真正能够改变人类文明的,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安排如何应对这些强大甚至是毁灭性的外生冲击力量。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
瘟疫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副产品,就像麦克尼尔所言:“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在天灾人祸面前,一个社会制度安排的所有优势和缺陷都会暴露无遗,此时要不要去改变,如何去改变,是变得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糕,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行为,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些外生冲击因素的看法和理解,而并非枪炮、病菌和钢铁的力量。
(作者方钦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