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之后的第一代西方“汉学家”
“中国礼仪之争”爆发后,欧洲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里,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有了较深入的理解。“东学西渐”“西学东渐”,形形色色,林林总总。这一切中间都有耶稣会士的首创之功,很多都与“中国礼仪之争”有关。
“仪礼问题兴起结果,各派传教师皆为拥护己派,详研中国礼俗,其报告论难,大刺激欧洲教界,西人对于中国文物之知识乃见一大见解,此近代欧西东方知识发达史上重要事件也。”
与16、17世纪西方人积极了解中国文化相比,中国人主动而全面研究西方文化要晚得多。基本上都是传教士来学、来教,很少中国人自己往学、往教。在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方面,中国人也十分被动。虽然也有少数几个中国人随耶稣会士到过意大利、英国、法国,传播了中国文化,但是欧洲人了解的中国文化基本上都是由他们自己派来的传教士介绍回去的,尤其是通过“中国礼仪之争”的讨论弄明白的。
作为思想继承者,金尼阁在回国期间,把利玛窦写的意大利文札记原稿用拉丁文增改写成“De Christiana expeditio ne apvd Sinas,svsceptaab societate Iesv”,意为“在中国传教期间的基督教扩张”,陈垣先生翻译为《中国开教史》,近年又被翻译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出了初版,轰动欧洲。此后,1616、1617、1623、1648年又出了四个拉丁文本,1616、1617、1618年有三个法文本,1617年有德文本,1617年有西班牙文本,1621年有意大利文本,1621年有英文摘译本。这本书是第一部深入中国内地,仔细描写中国宗教、文化与习俗的著作。马可波罗之后,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是从这本书开始的。这本书有中华书局1983年中文本,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名改成《利玛窦中国札记》。
金尼阁从自己读过的《尚书》《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中摘录资料,编译了一部拉丁文巨型编年体史书,历朝历代的重要史事均记录在内,书名是《中国历年王朝录》(Annales Regni Sinensis),共四卷。金尼阁号称:为作此书,读了120种书。第一卷在1624年完成,时限上是从三皇五帝到公元前560年。1626年,他完成第二卷,从前560年写到公元元年。1627年,他完成了第三卷,从公元元年写到公元200年。第四卷写作情况不详。这部巨著被分成四卷带回欧洲。在20世纪还有学者见过此书的第一卷,可见当时是出版流行过的。
“中国礼仪之争”爆发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评论在欧洲发表,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1701年,龙华民反对利玛窦赞同中国礼仪的文章在巴黎发表。它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来华教士德西塞(Louis de Cice ,1684年来华,1727年逝世)从西班牙文译成法文,轰动一时,影响很大。该文题为《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龙华民是意大利人,原文应是意大利文。根据钟鸣旦在《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中查证的版本情况,此文的第一个抄本是葡萄牙文,后有拉丁文译稿,最先在西班牙发表。此文先用西班牙文发表,可见这正是方济各会士李安堂在济南从耶稣会士手里获得的那份原稿。李安堂把它译成西班牙文,并由他所派出的同会会士文都辣带回西班牙。因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阎当主教的加入(他是巴黎大学的神学博士),巴黎大学变成了“中国礼仪之争”的论战中心。又因为法国和巴黎大学在欧洲思想文化界的重大影响力,全欧洲都通过争论了解了中国文化。1704年,英国伦敦也翻译了这份报告,收录在《旅行者书录》(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ers)中。
耶稣会士是中西语言文字的沟通者。据说利玛窦和郭居静编了一部《音韵字典》(Vocabularium ordine alphabetieo europaeo concinnatum, et per accentus suos digestum)。
按原文意思,这是一部用西文字母顺序编排,每个字都注明发音的字典。这显然是一部供耶稣会士学习中文用的字书。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后来也编过一些汉西字书,但时间较晚,且多为福建方言。此书在同类书中应该是最早的。费奇规在1604年来中国,马上到北京接受利玛窦指导,利玛窦要他好好学习中文,传授给他许多学习中文的方法。他真的是利玛窦的好学生。在“译名之争”中,他写文章为已故利玛窦的观点辩护。更不负利玛窦期望的是,后来他编了一部《汉葡字典》,让欧洲人学习汉语方便许多。相似的是,第一部《汉法字典》和法语《汉语语法》也是18世纪初年因“中国礼仪之争”而到罗马、巴黎做证的一位中国人黄嘉略帮助作的。
与后来发生的事件相联系,从很多意义上说,来华耶稣会士中积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自然地成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代“汉学家”。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意大利人的汉学就在17世纪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艾儒略、王丰肃、熊三拔、毕方济、郭居静、潘国光、马国贤等都是意大利人。和当代汉学家相比,他们在中国居住了几十年,且大多生活在文人士大夫中间,汉语造诣要好得多。他们的研究成果丰富,社会影响巨大,对欧洲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远过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汉学家”多数是在中国居住日长,回欧洲居住日短,有的终生在中国“留学”,终老于此。
也有中国人在欧洲“留学”的。和19世纪留学运动不同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没有多大的“往学”目的,倒是负有“传学”使命。1681年12月5日,松江府天主教徒沈福宗(Machel Alfonso Chen,?—1692)修士,跟随在江南地区传教的比利时人柏应理神父,到罗马汇报“中国礼仪之争”。作为一个知书达礼的中国人,沈福宗在欧洲许多宫廷、大学、研究院、教会机构,向国王、主教、神父、教授表演祭祖、祀孔的礼仪,向欧洲人解释《礼记》等书在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含义。除了向欧洲人讲解中国礼仪的真实意义外,沈福宗还不得不介绍中国文化的其他内容。他“在罗马吻了教宗陛下的脚”;在凡尔赛宫,他拜谒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并应邀在国王面前表演中国式的餐桌礼仪。目前所知,沈福宗是最早到达欧洲的中国江南学士。他本人被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在欧洲表演、展示。英国宫廷画家奎勒(Godfrey Kueller)为他画了全身的肖像画,广为流传,收藏至今。
在欧洲汉学史上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国贤。马国贤是遣使会士,1710年到中国。当时,“中国礼仪之争”在中国已经结案,康熙把不愿领“红票”、不尊重中国礼仪的传教士驱离中国内地。但是喜欢西方科学和艺术的康熙还是让一些有学问的传教士进到北京,为他服务。马国贤作为当时特许引进的“技巧三人”之一,进到北京,任为宫廷画师。他画过著名的《热河行宫图》。

1723年,他带回了四个年幼的中国学生和他们年长些的中国老师回到家乡那不勒斯。1732年7月,在教宗的特许下,设立了专门培训中国人的“中国学院”(Collegio dei Cinesi),后被意大利政府收管,改称“东方学院”(Istituto Orientale)。他的著作是《中国圣会和中国学院创办记事》(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tione e del collegio dei Cinesi,1832)。该书在1844年翻译出英文本,成为更加著名的汉学名著《京廷十又三年记》(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13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当时,教宗批复成立“中国学院”的条件是:“不得接收除中国人和其他宣誓愿意到中国去当传教士之外的人入校。”这样的办学目的明确地是要为中国留学生建一所专门的大学。当时规定入校学生要作“五项发愿”(five vows):“第一,坚守贫困生活;第二,遵从上级主人;第三,学成后进入圣修会;第四,服从罗马教廷传信部的安排,加入东方传教会;第五,终生为罗马天主教服务,而不再加入其他任何团体。”
这所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的大学真是生不逢时。建立初期,中国内地正处于清朝雍、乾禁教时代,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进入低潮,不单传教士难以进入中国内地,就连一般中国人也因为严厉的禁海令而不得出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困难时期,创办这样的学校,在学生来源和毕业后的去向上都有问题。当时欧洲都传说,马国贤买了五个中国小孩,带回那不勒斯来办“中国学院”。还没有查见这五个中国人的名字,只在《京廷十又三年记》中看到他们的西文姓名,分别译为:谷文耀(Baptist ku)、殷若望(John In)、吴露爵(Lucio U),另外两个还没有发现。很可能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中国学生,“中国学院”从一开始就不是单单招收中国学生。“用基金的花费开销,学校由一批适合于传教任务的年轻的中国人和印度人构成。”
无论如何艰难,名不符实,这个“中国学院”毕竟开创了中西学术交流史上的许多第一。我们大致可以说它是:第一所设在海外的传授中国文化的学校;第一个欧洲人研究中国文化的专门组织,诞生中国第一代留学生的地方;第一个被西方人用来观察中国人的肤色、头发、眼睛和生活习惯及日常礼仪的地方……据开学后人们的参观报道说,当年有八个学生在校,其中六个中国人,两个希腊人。授课用拉丁文,但学生们已经学会了用意大利文和校中的仆人们沟通。他们发现,中国人“脸色是黄的,但并不难看。发亮的黑发,又平又直,盖在低浅的额头。小小的、怪怪的、半睁的眼睛透出黑色大理石般的黑光。……这就是著名的鞑靼民族”。
就欧洲的汉学研究来说,“中国学院”做了许多初创工作。据《意大利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Italiana)“马国贤”条,学院用意大利文翻译了《三字经》、唐宋古文,还有中国各地方言的语法书籍。还有许多作品散布在那不勒斯的图书馆和其他私人手里。马国贤本人编写了一本《中文拉丁文词典》。当“中国学院”难以为继时,意大利政府接管了该校,该校成为意大利的汉学研究中心。学院旧址今天仍然保存着,墙上仍然挂着中国风格的书画。
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从天主教会的神父扩展到世俗学者中。莱布尼兹原来并不是当时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而是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但因为和耶稣会士的著述有密切接触,从而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极大兴趣。换句话说,他对中国文化的倾向完全是受了耶稣会的影响。1697年,莱布尼兹用拉丁文编辑了一本《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 Historium Nostri Temperis Illustratura, in quibus de Christianismo Publica nune primumautoritate propagato missa in Europan relatio exhibetur, deque f vorescientiarum Europacarum ac moribus gentis et ipsius pra sertim Monarchae, tum et de bello Sinensium cum Moscis, ac pacc constituta, multahacteomus, multa hacteomus ignota explicanter),题名甚长,全称为《中国近事:现代历史资料。内容为最近刚获得的有关中国政府特许传教情况的报告,欧洲学术界渴望知道的中国民族和皇帝的情况,以及中国和莫斯科战争与缔约的经过并种种珍闻》。全书分为七个部分:(1)序言;(2)苏霖关于1692年中国传教自由的报告;(3)南怀仁关于康熙谕全国印行天主教书籍的报道;(4)闵明我1693年12月6日从印度果阿给莱布尼兹的书信;(5)安多1695年11月12日从北京给莱布尼兹的书信;(6)1693—1695年,莫斯科使节中国旅行记;(7)张诚1689年9月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过程。
著名学者、理性主义大师纷纷加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他们的宏观建树对“汉学”在欧洲的发展有很大推动。莱布尼兹和笛卡尔、斯宾诺莎一样,是一个“普遍主义”者。他认为世界上有单一的因素,可以构成整个世界的复杂性。由于这样的原因,他对中国儒家宋明理学中的“道”“理”“气”“器”等概念,尤其是《周易》中的阴阳学说,非常感兴趣。莱布尼兹从宋明理学中看到了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元素”(first principle)之类的学说,以为中国儒家也明了世界构成的普遍性。他从“普遍主义”理想出发,对耶稣会士和中国天主教徒们主张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等主张非常同情。他认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能够相互补充,相互沟通,有益于人类。在《中国近事》里,他说:“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为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
莱布尼兹对中西文化的各自优劣做出了比较。他没有到过中国,借助耶稣会士的感性认识和书面描述,因此得出的结论和耶稣会士的观点差不多。他说:“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中国文化重伦理政治,轻哲学和科学理念,这种观点和当时耶稣会士的判断完全一样。或者我们还可以说,把中国文化当作理性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而非宗教神学看待,这种思路和“中国礼仪之争”中耶稣会对中国文化的定性直接相关。

在宗教派别上,莱布尼兹是新教徒。但在“中国礼仪之争”中,莱布尼兹明确地站在天主教的耶稣会一边。他说:“多年来,欧洲人,尤其是耶稣会士以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致力于将上天赐予的这份圣礼传入中华帝国。他们那种投身事业的坚韧不拔精神,甚至使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得不表示赞叹。我知道,我昔日的好友,当代一位杰出的人物安托万·阿尔诺极力反对耶稣会,对它的传教士横加指责。以我的观点看,这类指责在某些情况下言过其实、过分激烈。……推崇孔子,就其本质而言,似乎与宗教崇拜毫不相关。”莱布尼兹摒弃信仰下的“门户之见”,支持耶稣会,推崇中国文化,完全是出于学术上的原因。
1700年,莱布尼兹写下《关于儒家的俗礼》(De cultu Confucii civili),直接参加“中国礼仪之争”。他认为儒家学说只是世俗的礼节,而非宗教。他对争论将导致中西文化交流中断的结局深为忧虑。1714年,莱布尼兹读了龙华民的《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和李安堂的《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为回答这些反对意见,1716年,莱布尼兹写成《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Discourse on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the Chinese)。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化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基于“道”“理”“太极”“太一”的“自然神学”,在此之下有“自然道德”。中国人的人性按照自然规律做“向善”的追求,而不是按照如基督教的绝对律令来“去恶”。这样,人的道德性和世界的物质性就可以统一起来,基于启示的理性和发自人性的理性也可以更加协调。这是符合近代启蒙精神的“人文主义”态度。莱布尼兹认为,中国文化为西方人解决人和宗教的冲突、科学和宗教的冲突、社会和宗教的冲突,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龙华民认为,中国人既把“善”归于“理”,也把“恶”归于“理”,这是思维上的混乱。按基督教神学来看,“上帝”只能是至善至能的,不可能既善又恶,只有人类才是善恶兼备的。因此,中国人的“理”不可能是基督教的“上帝”。
莱布尼兹认为:“他(指龙华民。——引者)完全错了。”莱布尼兹在《性理大全》卷二十八看到过陆九渊的语录——“天体圆如弹丸”,也知道邵雍《太极图说》中的“太极”是一个圆形。所以,他说:“中国人也称他们的‘理’为‘圆体’或‘丸体’。我相信,这如我们(所)说,至高神可比丸体或圆体一样,它的中心无所不在,而它的圆边则并无所在的。他们称它为物之‘性’。我相信这也像我们说至高神是自然之自然(natura naturans)一样。”
这样的“理”,“是至善之中,至善之善,至善之纯,微而无形。它真是纯精神体的,不可洞窥的。它好得不能更好。这句话说出了一切。说了这些话,为什么不能也说中国人的‘理’即是我们拜为至高神的至上实体呢?”
莱布尼兹站在耶稣会一边。在“理”的观念上,他甚至比《天主实义》里的利玛窦走得更远。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只肯定先秦古籍中的“天”和“上帝”,对宋儒谈“理”是持保留态度的,而莱布尼兹则把宋儒的“理”和近代天文学、物理学、神学中的“上帝”一起理解,加以肯定,认为是一种来自东方的自然神学。
莱布尼兹是当时欧洲的著名哲学家,他说的中国之“理”到底是不是中国的原“理”,当作另论。他站在耶稣会一边,毕竟十分有利于耶稣会在欧洲知识分子思想界的地位。但是,他做出中国思想是“自然神学”的结论,是欧洲思想在当时激烈争议的话题,反而给保守的天主教神学界提供了更多口实。神学家据此批评儒家哲学是不同于天主教的异端,实际上也是为了反对欧洲思想界内部以自然神学为特征的理性主义启蒙主张。
(本文摘自李天纲著《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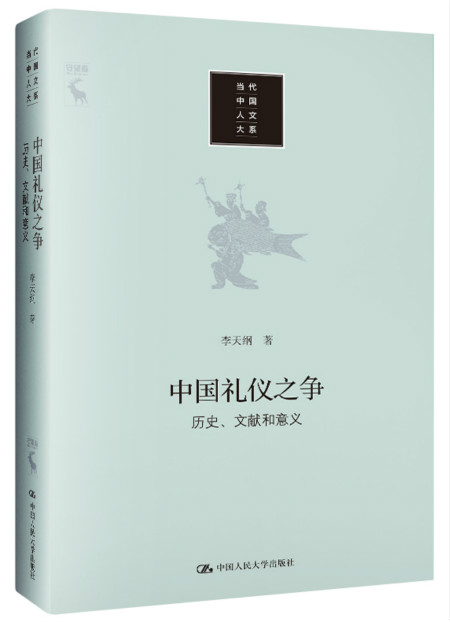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