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谈托克维尔研究

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Françoise Mélonio)为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巴黎四大)教授,主治十九世纪法国思想史。现为《托克维尔全集》主编、《托克维尔杂志》主编、法国托克维尔研究会会长。2019年10月,在她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期间,《上海书评》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肖琦对她进行了采访,谈谈西方学界的托克维尔研究。

您是1970年代的巴黎高师毕业生,硕士论文研究中世纪文学,国家博士论文题目是“法语文献中的托克维尔”。您为何会从文学转向托尔维尔研究?
梅洛尼奥:我读书的时候还是法国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时还没合并成为现在的巴黎高师。我硕士论文研究圣奥古斯丁的政治思想。做博士论文时,导师是米歇尔·赞克(Michel Zink),他曾任法兰西公学教授,现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我当时研究的是中世纪第一份世俗化教育的文本。国家博士论文转向研究1970年代之前法国对托克维尔的接受,即在法语的杂志、书刊中对托克维尔的接受。这其中有一些偶然因素。因为我受邀参加《托克维尔全集》的编辑工作,同时也在从事着别的工作。但我很喜欢这份《全集》的编撰工作,事实上,我当时一直在做的是关于文学与政治社会的研究,关于社会模式与价值的传播问题。我实际上是改变了研究的时间段,但没有完全改变研究的主题。现在看来,当然这个转向确实有一点儿偶然。
我看到您的国家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中有孚雷(François Furet)、勒内·雷蒙(René Raymond)、罗桑瓦龙(Rosanvalon)等,这些都是在二十、二十一世纪的法国甚至国际历史学学界里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样,他们也都可以说是思想史家或思想家。他们是否对您的研究与写作产生过影响?
梅洛尼奥:是的,当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勒内·雷蒙邀请我去巴黎政治学院任教,我读了他的很多书。罗桑瓦龙,我是他的学生,之后我与他一起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合开了很多年的课,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研讨班。他每周都要来上课,讲授的主题是关于十九世纪的民主,也是他已经出版的书的内容。我当时一边授课一边从事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孚雷曾经是《托克维尔全集》编纂委员会的主席,我们曾经一起在“七星文库”中编辑出版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柏林墙倒塌之后,我们一起在中欧和发生剧变的东欧地区组织了一系列会议。我与他一起共事的时间很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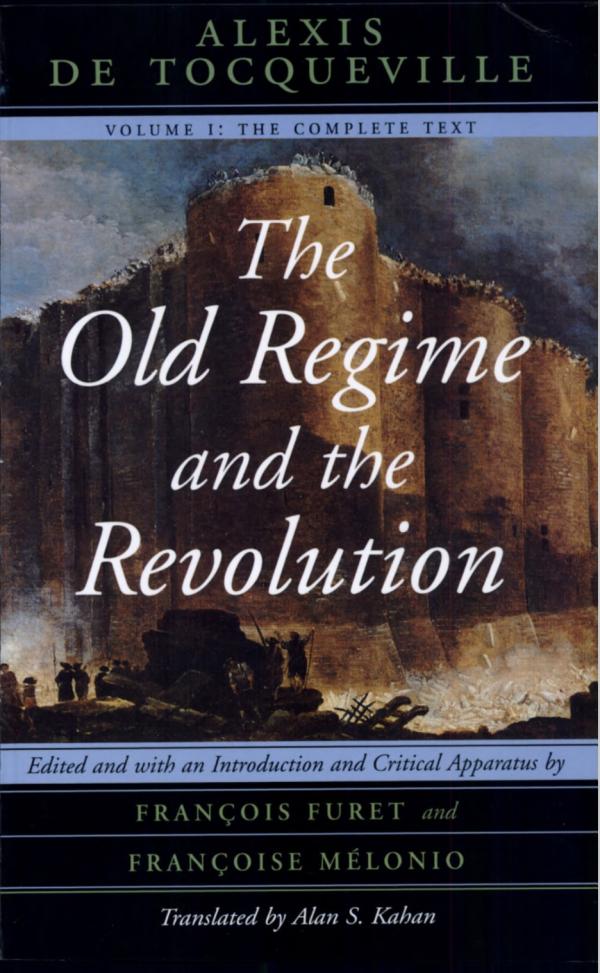
您从1987年起担任《托克维尔全集》编纂委员会的学术秘书,长期从事《全集》的出版工作。目前《托克维尔全集》都已经出版完了吗?
梅洛尼奥:还有最后三卷托克维尔的通信将于2020年初出版。我们之前已经出版过他的一些通信集,包括他与外国人的通信,与非常亲近的朋友们之间的通信。现在即将出版的这些通信中包括那些很早就被我们搜集到的托克维尔写给英国人、美国人的信,尤其是那些写给法国人,当时的政治家,还只是担任部长的基佐的信;写给作家,如拉马丁、夏多布里昂的信;还有写给社会主义者、反革命党人以及一些普通人的信。这三卷通信集涉及托克维尔在法国社会认识的所有人,大概有一千五百封,都是他寄出去的信,我们不出版那些他收到的信。在托克维尔所有寄出的信中,我们也只发表其中一些特别重要的,因为如果全部出版的话,那将会是有数十卷之多。
你们是如何搜集到这些他所寄出去的这些信件的呢?
梅洛尼奥:有些信是他自己保留了草稿或者复件。有些是托克维尔去世后,人们把那些信又寄回来,以期能够立即出版。耶鲁大学购买了一些托克维尔写给他朋友的信件。最后还有些是我查阅了很多目录,联系了许多图书馆查到的,有数百封信来源于他的原始手稿。《全集》的编撰进行了较长的时间,我们所有人都是志愿在做,没有薪酬,进展得也很缓慢。现在我退休了,可以有更多时间来推进一下这些工作。

七星文库《托克维尔选集》三卷
当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决定启动《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梅洛尼奥:编撰工作始于1951年,是由一位移民到英国的德国人迈耶(Jacob-Peter Mayer)开启的。但他不是文献学家,不会编辑文本,所以找了人来帮忙。他自己负责推动,寻找资金支持。编辑工作由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雅尔旦(André Jardin)负责,他几乎一生都在从事这项工作。之后这项工作停滞了,法国政府想要重新启动这项工作,当时的一位政府部长雷蒙·巴尔(Raymond Barr)便让雷蒙·阿隆来负责这项工作。也就是在那时,我被招募到编辑委员会里,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推进地更快了。现在可以说,是雷蒙·阿隆让托克维尔在法国被人所熟知的。
雷蒙·阿隆写过一篇非常经典的论文——《重新发现托克维尔》。
梅洛尼奥:是的,他还教授过相关课程,他的著作《社会学主要思潮》里有一章就是关于托克维尔的。当时托克维尔在法国几乎被遗忘了。在其他的国家,包括意大利、英国等国,人们都在谈论托克维尔。但是在法国,是阿隆重新让人们注意到了托克维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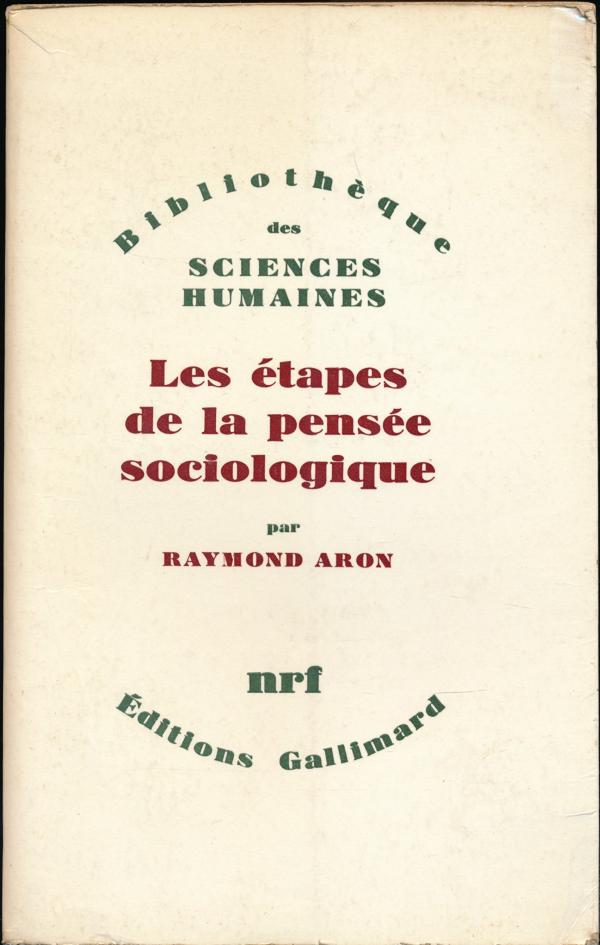
为什么在1950年代前,其他国家都讨论托克维尔,而法国却没有呢?
梅洛尼奥: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人关注的不是托克维尔问题,而是与日益崛起的希特勒斗争。当时人们的想法是,法国的共和体制已经稳固,所以从1880、1890年代法国共和体制建立后,托克维尔也就很少被提及了。但自1945年后,人们开始觉得民主变得很脆弱了,这样托克维尔才重新被人们所关注。所以托克维尔是在二战之后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我曾经统计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托克维尔的书在法国的销售情况,每年仅卖出去一册,甚至有时一年都卖不出去一本。读的人很少,有一些历史学家会读一些,但是公众不读。
您1992年进入《托克维尔杂志》编委会,2007年起任托克维尔研究会主席。您能介绍一下这两个机构吗?
梅洛尼奥:托克维尔研究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会议和主编《托克维尔杂志》,现在还有一个博客——“Tocqueville21”。这个研究会有悠久的历史。杂志是从1970年代开始出版的,它不仅仅是一本托克维尔研究的专门杂志,当然有一部分篇幅是用来专门刊登托克维尔研究相关文章。这是一本社会科学的杂志,聚焦对美国和欧洲所展开的比较研究。我们也有德国、意大利作者的文章,它的特色就是一本双语杂志,法英双语。现在我们试着去把这个比较延伸到亚洲。我们在2017年做过一期亚洲特刊,现在正试着向亚洲开放。杂志不时地会刊登来自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来自拉美国家的作者的文章。但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比较。杂志的作者中有许多知名学者,如阿隆、孚雷等,我们还将一些最重要的文章选编成文集。同时,杂志也试着刊登一些更为年轻的学者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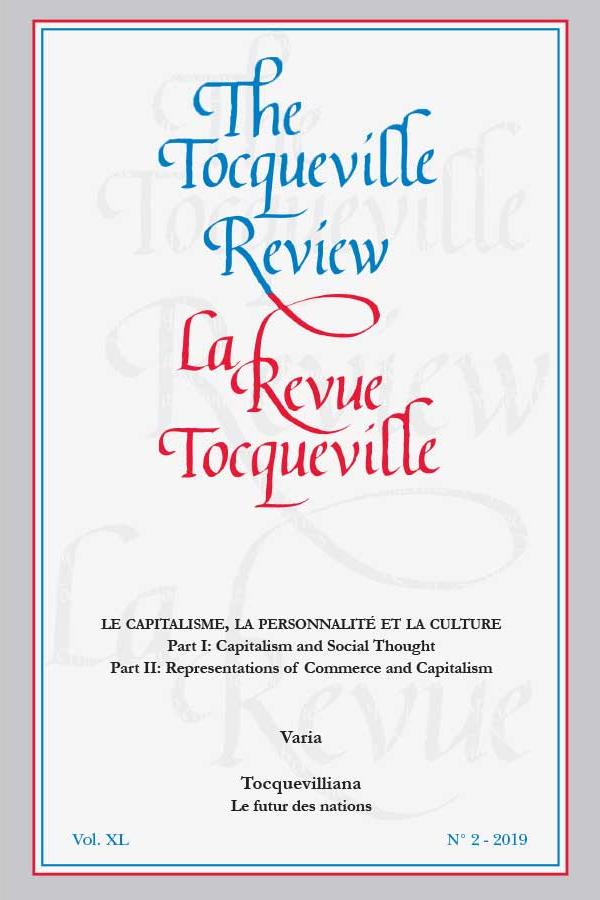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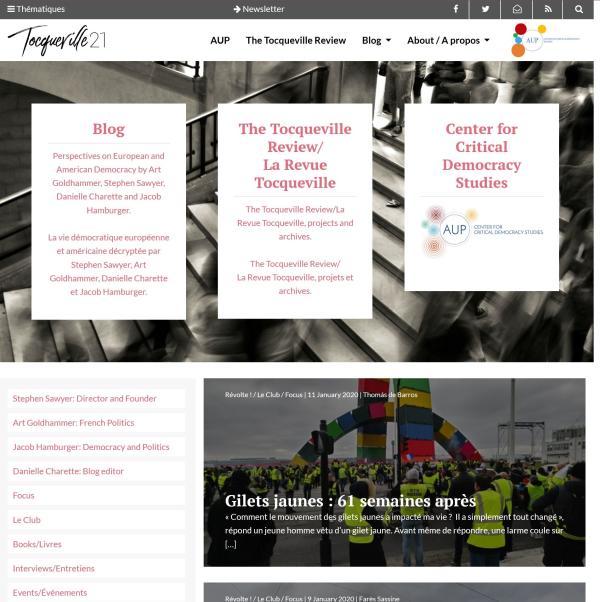
杂志一直都是用双语出版,也同时在美国出版吗?
梅洛尼奥:是的,我们有一些资助,尤其是获得了巴黎美国大学的资助,这得益于一位法美籍的历史学家斯蒂芬·索耶(Stephen Sawyer),他是巴黎美国大学历史学系的负责人。不过杂志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编辑出版的,因为加拿大人擅长于用法英双语编辑出版,这两种语言都是他们的官方语言。事实上,现在杂志的纸质版发行得比较少,只有几百本。更多的是在线上发行,在Erudit上。当然文章要下载都是收费的,否则我们没法出版。
近年来在国际学界,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关于托克维尔的研究呢?
梅洛尼奥:很多学科领域都对托克维尔抱有极大的兴趣。在历史学方面,美国对托克维尔的研究始于1938年,乔治·皮尔逊(George Pierson)出版了《托克维尔与博蒙在美国》一书。1960年代之后有一些研究托克维尔思想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尤其是西摩·德雷舍(Seymour Drescher)与梅尔文·里克特(Melvin Richter)的作品。今天的历史学家如谢里尔·韦尔奇(Cheryl Welch)、奥利维尔·如恩斯(Olivier Zunz)、艾伦·卡亨(Alan Kahan,现在在法国任教)等人的研究特别值得关注。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曾长期在芝加哥大学执教,他在引发美国学界对托克维尔的研究兴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政治科学方面,对托克维尔的研究有着强烈不同的取向,有种分裂的趋势,有一部分托克维尔的研究者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如哈耶克写过一本《通往奴役之路》,该书的题目就是从托克维尔那里借用过来的。还有一个重要的解释取向是社群主义者,政治学家普特南即是属于这一脉。所以在托克维尔的受众之间确实存在有很大的差异性;还有从哲学的角度来阅读和进行研究的。所以在学术研究上一直存在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对托克维尔的阅读理解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英国和法国,可能更多的是从历史学方面展开的研究。在此我还要说的是,那些具有哲学意味的诠释也是非常多样化的。例如,阿兰·布鲁姆的朋友也是他作品的法文译者——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就对民主在法国的演进很悲观。当然也有很多人,包括法国哲学家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与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就主张要对民主的深入发展进行反思。今天在我看来,不管这些解读有多么大的差异性,重要的是要知道托克维尔还对我们说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例如他关于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相似的判断还是对的吗?因为今天在欧洲,很多人都在要求自身的差异性得到承认。这是托克维尔当时所不能想象的。正如罗桑瓦龙所说,托克维尔的思想已经不能让我们去思考今天的法国社会了。身份认同,例如地区性的认同——加泰罗尼亚问题,还有同一性问题、同性恋问题,特别是宗教认同问题,伊斯兰问题,这些都是新的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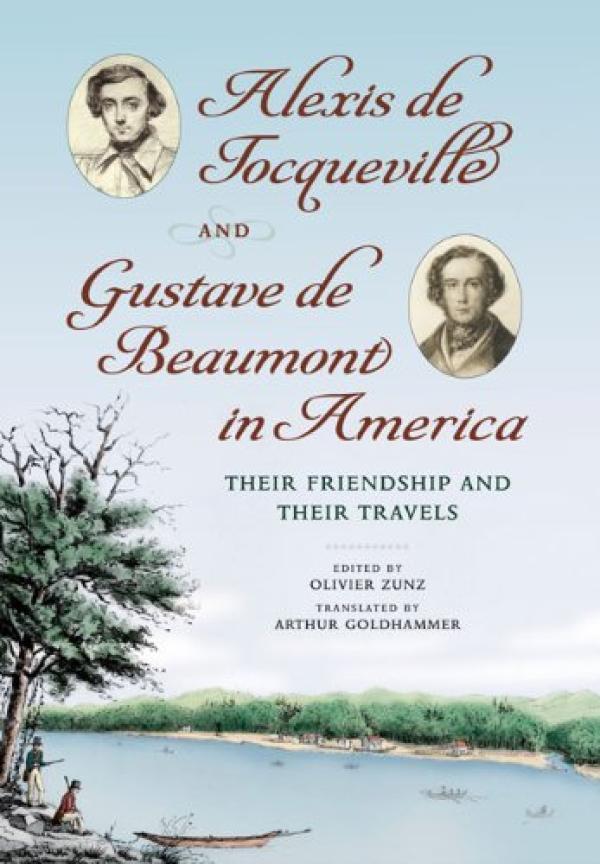

所以在您看来,今天,托克维尔是否不像以前那样值得重视?
梅洛尼奥:确实可能比十年前更少被谈及。在1989年,在中欧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发生剧变之时,托克维尔被视为一位掌握真理的人,因为当时同时面临着美国模式和社会转型过渡期的问题。而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权力都在集中化,几乎到处都如此,人们可能认为我们不再那么需要托克维尔。然而我认为这是错的,我们不再憧憬美国模式,现在美国模式的运行有问题,这抵消了他的部分思想的有效性。但是另一方面,例如困扰我们的民粹主义的问题,托克维尔思考过,当然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思考过。
您认为未来托克维尔的研究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展开?
梅洛尼奥:从编辑的层面来看,我相信我们会找到其他的文献资料。在私人市场上就有,在一些人家中阁楼的角落里都可能藏有一些资料有待我们去发掘。更重要的是,我想每一代政治学学者、历史学家都有不同的问题,人们都是从当下出发去回溯过去。我想我们将来会比现在有更多的研究视角,每一代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去阅读经典。另外有些研究还是有待深入的,例如对政治语汇的研究,因为数字化方式可以让我们对语言进行更多的研究。

近年来欧洲和西方社会一直在讨论民主的危机、代议制的危机。您在演讲中也将这一问题与黄马甲运动进行了对比。您认为托克维尔的思想中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当下的情况?
梅洛尼奥:法国有黄马甲运动,意大利、西班牙、东欧国家也有类似的运动,说到底问题就是掌握权力的精英与大众之间产生了分离,实际上就是国家的代议体制没有能够让公民参与进去。我想托克维尔的思想对理解这个问题,即民粹主义这个问题(这个词很难定义,有点贬义,很宽泛)来说非常重要。托克维尔倡导要让各个阶层的人都参与到政治中来,并且发挥地方的作用。他本人花了很多时间去担任议员、地方议员等公职,这也是他赞扬美国的地方,就是公民能参与到市镇事务的管理中去。所以在国家层面需要重建的同时,在地方层面也需要进行一些改革。对国家的归属感来自于如交通、公务员体系等纽带,它们可以将地方与国家连接起来。托克维尔认为一些政治协会、社会团体的作用很重要。当然他那时没有工会,工会是被禁止的,当时的法律甚至不允许举行超过二十人以上的集会。他非常重视这些东西,而这些也是他在美国所看到并感兴趣,而法国当时所没有的。我认为人们今天所追求的,是如何在更基层的地方层面去考虑到公民的利益,因为所有的运动都是反对权力集中化的。人们的诉求不同,在法国,人们也寻求古希腊的那种抽签的方式,但问题是如何重新让民众参与进来。托克维尔不认为一个威权的政权能够成为一个自由而高效的政权,因为专家们虽然比其他人更为聪明,但他们不懂得民众需要什么。而且所有的公民所能做的比那些掌权的少数人做的要多的多,也会很好,他确信这一点。所以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对我们反思当下是有用的,虽然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城市化、技术化的社会,但要找到一个好的方法也是很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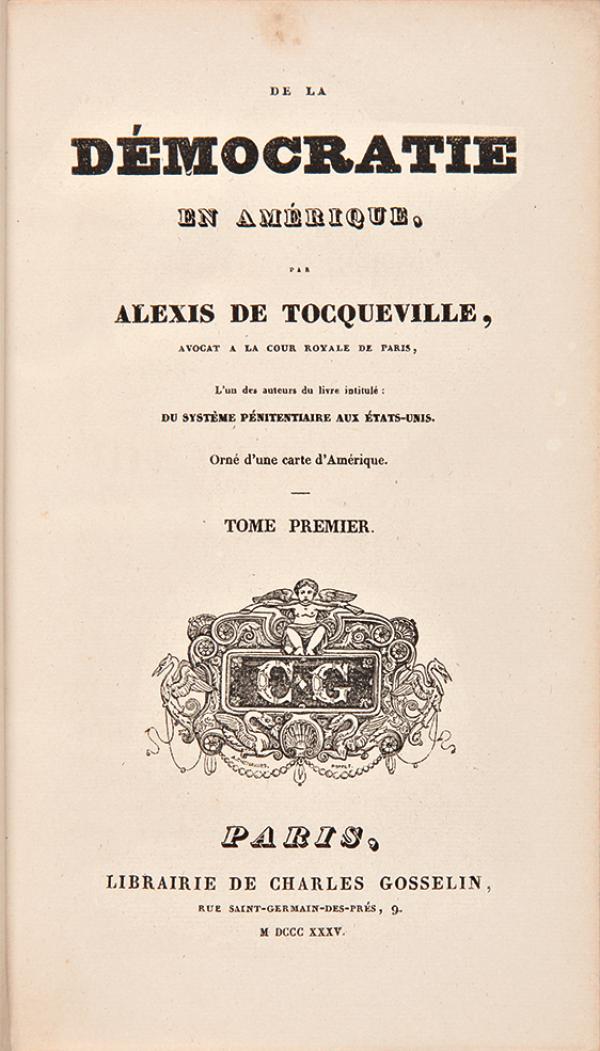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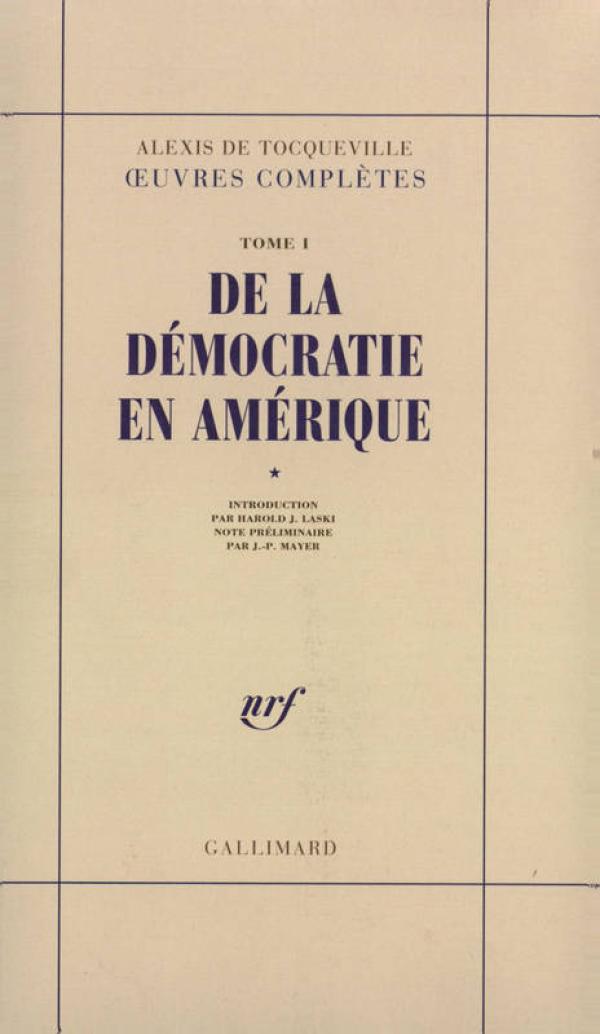
近些年来,托克维尔的思想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回应。您如何看待托克维尔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引发的关注?
梅洛尼奥:我想对美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很不一样。虽然他们面对着个人主义这个问题的困扰(在传统中这个词是褒义的),但他们对托克维尔的阅读与那些具有长时间的中央集权和威权统治历史的国家的人对托克维尔的阅读肯定不同。托克维尔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美国,而是欧洲大陆(英国人有另外一种传统),欧洲大陆指的是德国、俄国、法国,可能没有意大利,意大利当时还没统一,而且他们的政体是很反动的。对所有这些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民主的转型过渡。因为要过渡到民主社会,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著述了。我要说的是,这对于拉丁美洲来说同样如此,因为他们的发展模式是来自于欧洲大陆,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亚洲,我不了解中国,但是对日本,我有一些研究。日本的历史有一点像欧洲。因为日本也是从一个贵族的和威权的旧制度中走出来,他们在明治时期就翻译了托克维尔、基佐等人的作品,他们的问题也是如何从旧制度中走出来。对于中国来说,可能问题有一点不同。因为在西方人看来,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民主的但并不自由的国家。中国也不是一个旧制度的和贵族的体制,它有一段特殊的历史。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许对于部分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复杂之处在于如何将一个中央集权化且经济上高效的体制转化成一个能让更多民众参与进来的体制,因此他们对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特别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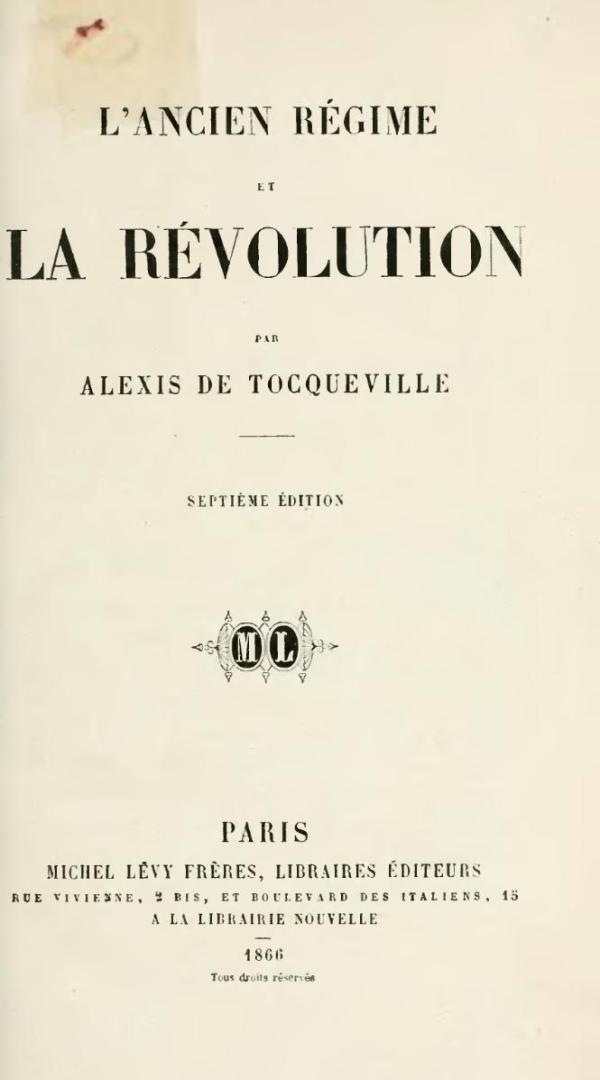
我知道您即将完成一本托克维尔的传记,您能谈谈这部作品吗?
梅洛尼奥:我想在这部传记中呈现的,既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美国的托克维尔,也不是一个天才的、孤独的托克维尔,而是要呈现他如何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内部进行工作的。为此,我描述他的教育经历,他接受的是一个非常古典的教育,他对“旧制度”有着眷恋,同时探究他所想要做的全部事情,例如寻求一种政治与新闻报道上的有效性等。我想把这些新的东西呈现出来,这些新的内容可以表现出他与当时他的同时代人试图去思考的不一样的东西。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本社会网络的传记,这也是我感兴趣的点,因为我开始研究思想家贡斯当的一些思想内容,他是比托克维尔更早的一代人,也是一位比托克维尔更为博学的读者,他使用多种语言进行研究,很哲学化,但他同时也试着去思考思想会对现实世界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一些实用主义的思想,他尝试着去用研究进行思想表达来影响这个世界。我对此很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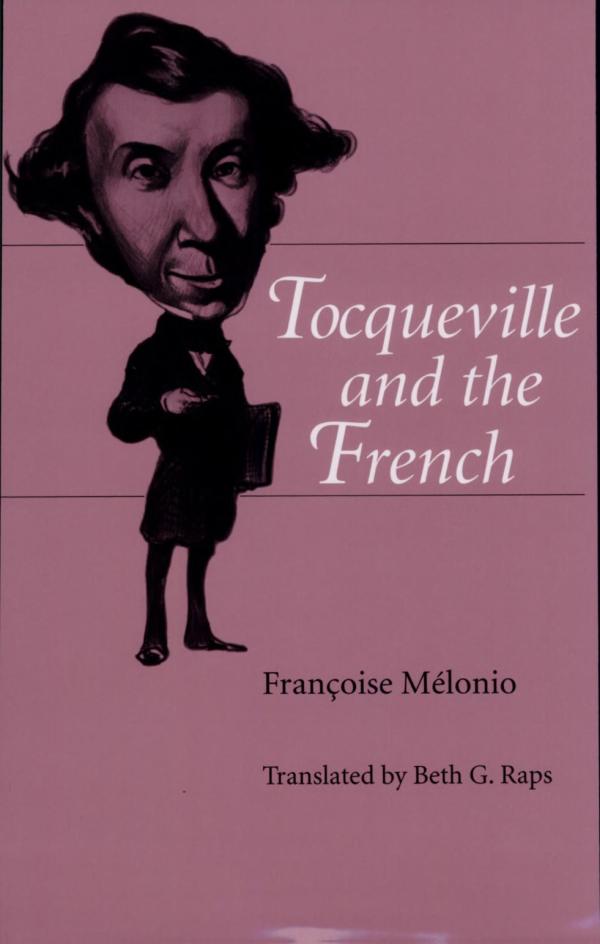
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更为介入政治?
梅洛尼奥:对的,他们的思想更为介入政治,但不是在参与某个党派的意义上的介入,而是说他们更有意愿要去改变现实的世界。十九世纪的法国还没有党派,但他们都是有着强烈的意愿要去改变世界的人,同时,他们也都是在欧洲层面上的思考者。贡斯当与托克维尔不同,他也是位小说作家。他有一本特别著名的小说《阿道尔夫》,里面说到了现代个体的孤独的问题,是本非常有趣的小说。

最后一个问题,您担任过高师的副校长,巴黎政治学院负责学生事务与行政事务的副校长,托克维尔对政治的关切是否在您的职业生涯的选择中产生过一些影响?
梅洛尼奥:当然有。首先,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曾经是法国的较高级别的公务员,所以我来自一个富有行政经验的家庭。我最初参与行政工作也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我在巴黎索邦大学任教的时候,是个年轻的教师,被要求去负责法语系的工作,当时我们有一万余名学生。因为说到底,我是研究托克维尔的,习惯于那些法律性的词汇,对这类东西比较习惯,比较敏感。后来,大概因为做得不错,巴黎高师来找我去,因为他们内部有冲突。巴黎政治学院请我去,我都不是他们那儿毕业的,我是高师毕业的。而且我是法语文学教授,当时巴政是没有这个专业的。当然我同时也是历史学教授,所以我在巴政教的是历史。这两所学校找我去,因为他们需要一位外来的教授去重新规划他们的课程项目,需要一位对他们的学校没有什么野心的人。因为当时我已经是巴黎索邦大学的教授,不想留在那两所学校,所以从事这些岗位的工作是有些偶然性。但是作为一位托克维尔的研究者,我习惯于让大家参与进来,习惯于反思。我想我的研究与这些研究与管理工作也变得无法完全分开了,我现在还在继续为法国政府提供顾问咨询。例如我参加了未来几年科研预算法案的咨询,这项工作目前已经结束。现在,我还是法国高等教育部职业道德委员会的成员。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