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复旦通识·回望传统中国|陈引驰:中国文学的精神世界

大约100多年前,胡适在北京大学开设 “中国哲学史”的课程,课程开始时,他直接从西周的周公开始讲。这种上课方式让学生非常惊讶。学生为什么惊讶呢?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他早年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教“中国哲学史”的老师是从三皇五帝、开天辟地讲起,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同学们问这位老师:您这样讲哲学史要讲到什么时候?老师回答说,哲学真理说起来就是一句话,要说,一句话也就说完了;如果不说完,就可以永远说不完。同学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样的学习氛围里,胡适突然跳过之前的时代都不讲,直接从周公讲起,肯定让学生们目瞪口呆了。大家问理由,胡适就说,西周开始有《诗经》,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历史的了解和历史的把握,这样才可以开始讲哲学;三皇五帝的时代没有这样的历史文献,所以没办法谈哲学。同学们可以看到,胡适的哲学史的课程得依靠《诗经》。《诗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儒家经典,也被认为是一部重要的文学典籍。但胡适之所以提到《诗经》,是因为他把《诗经》作为历史材料来用。这样,《诗经》同时被奉为文、史、哲的经典。
由于时间有限,我今天要讲的“中国文学的精神”,只能简单讲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与我刚才提到的胡适的例子有关,那就是中国文学的现实面向。将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比较,西方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从神、英雄非凡的表现开始的,相比中国最初的文学,它有更多超凡、夸饰的成分。20世纪加拿大著名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用人类学的观念来谈文学,他认为西方文学传统里,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与主人公的关系,从古到今是从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的过程。最开始是神和英雄,19、20世纪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卑微的小人物。
相较而言,中国文学一开始并非没有对神的称颂,但整体而言有很强的现实性,尤其是我们今天还在吟诵的《诗经·国风》,这从刚开始提到的胡适的故事中就可以看到——在“中国哲学史”课上他把《诗经》这部最初的中国文学总集当作历史史料来看,而不是当作文学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常见、悠久的传统,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是把古代的文献都作为史料来看的。
我们读到的中国很多诗、文作品——学者认为这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都以个体的时代经验作为表现对象。以唐诗为例。如果今天有位朋友突然说他要开始做一名诗人,那他是在做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但是在诗歌创作巅峰的唐代,写诗是非常日常的、属于生活经验的事情。遇友、考试、落第、邂逅,都可以写一首诗。我们熟读成诵的很多作品,其实都基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经验。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是个浪漫的诗人,这首诗里也包含很多夸饰、想象的部分,最后他写道:“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有非常浓的《楚辞·九歌》的味道。但是接下来他写道:“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这个梦最终是醒来了。《梦游天姥吟留别》写了许多迷离恍惚、超凡、非人间、充满想象的场景,但是最后李白还是告诉人们——这是在做梦。所以说,他的立场还是现实的。
中国文学的精神,第一要重视的还是面向现实的特点。西方学术界有学者提出,中国文学是非虚构的——这当然有很大的争议,不能说中国文学没有虚构的部分,后来的戏剧小说当然有很多虚构,早期诗文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但是绝大部分呈现出很强的现实性。这种情况不需要做太多解释——因为中国文学和中国传统中尤其以儒家为主导的观念、再具体到儒家的文学观念,有很强的联系,它基本上是一种现实的精神。
第二个方面是美善兼备。这与我前面提到的现实精神、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性、伦理性和政治性,这是它的一种基本关怀。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学观念中所谓的“兴观群怨”——这四个方面都是孔子提到的——基本都是从人群的关系上来讲的,“兴”是兴起,鼓动大家;“观”是可以观察、观风;“群”是让大家团结起来。“怨”当然是抒发怨愤,但是怨愤的是谁呢?一个人很难抒发怨愤,抒发怨愤实际上是在群体中抒发,即使你抒发的是个人怨愤,也是在群体的环境中得到疏导的。汉代的儒生说《诗经》的功能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它们都认为文学有社会的和伦理的意义。
“美善兼备”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论语·八佾篇》里就提到,孔子说《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这就是今天“尽善尽美”这个成语的来历。说《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所以《韶》乐是比《武》乐更高的,《韶》是关于尧舜禹的舜,《武》是关于周武王的。为什么《武》有问题?尽美矣,但未尽善。原因非常简单,在儒家观念中,孔子那个时代的认知非常清晰——武王伐纣,虽然是伐无道,但无论如何有亏于上下秩序。所以伯夷、叔齐要阻拦周武王的军队,在周推翻商以后,不食周粟而饿死了。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把《伯夷叔齐列传》列为第一篇,多少也是这样的一种观念的呈现。但是舜不一样,尧、舜、禹三位是完美无缺的古代圣人。简单地说,中国传统里美和伦理同时达到顶峰才算完美,这才是极致的美的感动和伦理的实现,如果有冲突,就是一种缺憾。孔子之所以会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就是说它在伦理上、在政治秩序上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中国诗人当中,最伟大的诗人当属杜甫,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钱锺书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是《中国诗与中国画》,他讲到中国画的最高标准和中国诗的最高标准是不一样的。中国画的最高标准是从王维开始的文人画的传统,但是中国诗有诗佛、诗仙、诗鬼,其中成就最高的,毫无疑问是诗圣杜甫。杜甫每饭不忘君王、对人间的疾苦有关怀,而他的诗歌艺术也是晚年“渐于诗律细”,成就包孕古今,在伦理和美两方面都达到完美的境界。
但这其中也有片面的地方,如果对善恶或者说所谓世间价值、世间秩序过度尊重和遵守的话,往往会导致诗人“美”“刺”二元简单化的姿态。“美”“刺”是汉儒的说法,用来讲《诗经》作者的态度,“美”当然就是颂美,“刺”当然有一定的讽义。近代梁启超曾说汉儒有时候把诗人都当成蜜蜂,总是在刺……这可能导致一个作家的态度简单化,文学作品也可能类型化、两极化。最典型的例子,《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是智慧的象征,曹操就是奸雄。比较《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前者的人物更丰富一些,后者的人物就更加类型化。很大程度上,可能因为《水浒传》表现的是一个江湖,一个边缘社会,多少和这个社会所制定的价值有距离,它能够将多元性呈现出来;而《三国演义》努力要呈现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推重正统的观念,包括忠孝节义等等,所以显得两极对立。
第三个方面是多元雅俗。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很多都与儒家有关,中国文学的主体精神中,儒家当然是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将这种说法简单化——中国文化传统、包括文学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传统,比如儒家有“美善兼备”的观点,道家、道教的影响也不能忽略。比如说,中国文学传统中很早就出现且延绵不绝的神仙世界,它超越了现实,在现实世界之上另建造了一个境界,于是便有了所谓的“仙”和“凡”的分离,这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道家、道教的“神仙”观念,由空间的维度打开了现实世界外的另一个世界。后来,佛教带来了所谓“三世轮回”的观念,在时间的维度上打破了儒家关注此一生的界限。儒家观念里,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他面对的是此一世。中国人当然也会想象过去和未来,但可能都不是他最关注或者给予较多考虑的方面。但是佛教引入后,讲“三世轮回”,讲前世、来世,就打破了时间的限制。从这个方面来说,道家与道教、佛教其实拓展了整个中国文学的空间。
我讲的多元性,不仅仅是儒、道、释的参与,还有一个重要维度是“雅与俗”的区别。所谓的世俗,不仅指文学呈现的世俗社会的实际状况,而是指那种民间性的、代表了一般历史情感和观念的方面。世俗文学往往非常有活力,但未必有方向性;它蕴含力量,但是四处横溢与冲决,是在非常清楚、有自觉传承意识的大传统之外的小传统。小传统关注的方面与精英传统不尽相同。我们观察中国文学传统时要注意,我们今天所认同的、非常熟悉的古诗文,基本属于精英传统,世俗传统与我们的理解非常不同,需要区别对待与理解。比如《三国》《水浒》,虽然写的似乎是历史,但都是历史的影子,《三国》“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但它最重要的部分是其中那些英雄人物。不过,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每个英雄人物都是定型的,是化身——有的是智慧化身、有的是奸雄化身、有的是中庸化身,这个趣味不是历史的关注,而是对人的关注。《金瓶梅》当然也是市井世情的作品,讲的是西门庆之兴衰,核心就是“财”和“色”。民间的或者我讲的世俗的文学,绝大部分内容实际上不是作者本人创造的,这里面所包含的价值,既是普通的、也是多元的,总体上褒扬忠孝节义,批判贪财、好色。
第四个方面是虚实相应。虽然前面讲中国文学注重现实、强调人间性,但这并不代表它没有深度的关怀。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事理的结合,讲理不是抽象的讲理,而是事中言理、借事表理,事理是相即相容的,在具体文学表达和文学呈现中,在人物故事和整个文学世界中来呈现意义和关怀。
另外我们都爱讲主客浑融(心物交融)的取向与情景交融的诗学。很早,老师就教大家理解诗歌的一个套路是:情景交融,意象生动。“情”是主观的方面, “景”是呈现出来的文学的图景或者文学的表现——所以,寄寓了情意的物象(“意象”)或者物象的世界(“意境”),是诗歌中非常重要的表现方面。中国小说也是这样,中国小说很少脱离人物的具体言行、抽象地挖掘人物内心或思想活动,这都是同样的传统脉络。
比如这首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也非常喜欢的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想,唐代诗人看到陶渊明这首诗,可能会认为最后一句诗是蛇足,“此中有真意”——诗句告诉我们这里面有意思,但又说不出来,或者不想说出来,这不是废话吗?可能后来唐人就不这样想了——诗里表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我形象,表现了“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那样的黄昏时分、倦鸟知归的景象,已经包含了“此中真意”。虽然陶渊明最后又加了这两句诗,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意思也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其中基本的意思很简单:在中古很多诗歌里,鸟是一种自然、自由的象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鸟按照自然节律行动;陶渊明自己则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和鸟的节奏是一样的——通过写鸟的节律、自己的生活,表现了他与自然的感应、与环境的感应,他自己的情、意都已经在诗中表达出来了,这种结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虚-实关系、主-客关系、意-象关系或者情-景关系,相关的两者之间的对应,形成了它们相互间的一个同构关系,它们基本都是在这样的“虚-实”结构中展开的。
前面我提到中国精神传统的多元性,儒家更强调实的方面,在道家的视野中,更突显文学不仅是实的,还有蹈虚的一面,以实映虚,以虚驭实,比如绘画中的“留白”、音乐中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文学理论中的“虚静”说等等。当一个作家进行创作的时候,要宁静自己的心神,要把自己掏空,然后才能够表现。苏轼有一句诗说:“静故了群动,空固纳万有。”只有空,才能把所有的都表达出来。这是中国比较特别的说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虚实结合。从诗人的创作过程到文学作品的表现都强调这样一种关系。
第五个方面是中和之美。总体来说,中国人是平和的,追求中和之美。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里提到,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古诗抒情,从不明说,全凭暗示,不激动,不狂热,很少词藻、形容词和比喻。”又说,我们自己觉得中国诗色彩斑斓、五光十色,但外国人看中国诗都很灰黯,就像暗夜看猫或猫看世界(猫是色盲),都是灰色。中国文学讲求“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情感上强调的是“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文学不能没有感情,但是任凭感情的发泄或者尽情舒展,其实不是中国文学所认为的好的方面。
最后一个方面是赓续传统。中国文学对于传统高度尊重。中国的文人一再回到古典中去寻找灵感,从文学的构思、想象,到精神的源头、开拓的支持,以复古为旗帜的文学运动历来未曾断绝。简单举一个例子,《诗经》是第一部文学总集,历来特别受到重视。第一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请大家注意诗句中提到的“水”,“水”是非常有意思的存在,在很多古诗里都是阻隔的象征。汉代古诗《迢迢牵牛星》讲的天上即后来传说牛郎织女的故事:“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里指的不是地上的隔膜,而是天河的隔膜。宋代李之仪也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词里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这里的“水”也是一种间隔,长江从空间上把我们间隔开来,但是在间隔当中又有一种贯通,“共饮一江水”。可以看到,这是中国文学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传统——“水”在文学中的表现,水对情感的隔碍与沟通。
古代很多形容方式和修辞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语言中,“杨柳依依”就是出自《诗经》。中国成语非常多,这是为什么呢?成语也是一种文学延展的方式,是一种对传统的尊重的表现。此外还有典故。读古典作品典故也许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需要具备有相应知识和了解。
“推重传统”成为中国文学非常重要的特征,甚至形成了中国文学中很重要的一种模式,即关于文学史逐渐下落的一种观照模式。就像鲁迅在《阿Q正传》里提到“九斤老太”的事情,“一代不如一代”,最好的是《诗经》《楚辞》的时代,汉魏古诗其次,之后是唐诗。宋人经常讲宋代是不行的,如果要写好诗,要把盛唐那几家诗好好读一读,不断回到传统当中去。从诗、骚到汉魏古诗,一直到唐诗、宋词,变成一个逐层下降的诗歌历程。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评判这一观念的对或错,而是说这样一种观照和理解模式,实际上是对传统持续关注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种对于历史进程的负面的认知角度。
我前面提到,中国文学复古传统未曾断绝。比如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时,就说古文是好的,晚期、近代的都不好。他们这个方式用过去的讲法是“远交近攻”,隔着远的都是朋友,时代相近的都是要打倒的对象。其实直到现代也还是这样,胡适等人开始“白话运动”时,提到要复古,但是他们视野更宽广,不是要复韩愈、柳宗元之古,而是学欧洲近代的复古——文艺复兴时代,但丁、彼特拉克采用意大利的方言、而不是拉丁文进行创作。中国文学的复古传统,即使是创新,也以复古为目标和途径,这也成为一种延续到今天的基本范式。这也需要我们进行反思:一方面是客观平情地了解这种范式,另一方面是分析它的利弊得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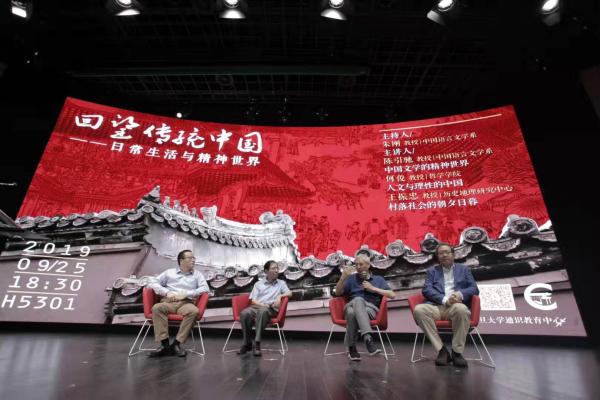
(本文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提供。)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