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爱因斯坦如何摧毁了一颗行星
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在几个世纪的观测中,人们发现水星轨道存在轻微的扰动。这与牛顿理论所预言的行星行为有些许偏差。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法国天文学家勒威耶进行了计算,于1859年提出假设:水星轨道内尚有一颗未被人们发现的行星。他还以罗马神话中火神的名字(Vulcan)为之命名(对应中文译名即“祝融星”)。此后,人们开始疯狂地寻找这颗行星,但除了一位乡间业余天文学家声称目击了它之外,没人能再次证实它的存在。1915 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体系构建完成,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解释水星轨道的扰动现象。自此证实:祝融星并不存在。
被遗忘的祝融星的故事很可能再也不会不为人知了,直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科学写作项目的教授和主任托马斯·利文森(Thomas Levenson)的《追捕祝融星》一书再现了牛顿、爱因斯坦和失踪的祝融星的故事,展现了在决定宇宙命运时观测和计算之间的冲突。利文森在这本小书中告诉我们:祝融星来自哪里,它如何消失,以及,为什么它的神韵在今天仍暗藏其间。这本小书也向读者揭开了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和现在被人们遗忘的祝融星背后的物理学,同时展示了科学在现实世界中是如何发展的。在此过程中,作者还揭示了我们在努力时——即便是经验十足——无法避免自欺欺人对我们的影响。
本文系《追捕祝融星》最后一章节——“后记:‘渴望看到 ……先定的和谐’”。

然而,对于这颗折磨水星的幽灵行星的处理,爱因斯坦还没有完全完成他给自己设定的工作。1915年11月25日,他连续第四次在星期四来到柏林城中心。在科学院里,他展示了自己关于引力的最终理论。没有遗留的错误,没有不必要的假设,没有特殊的观测者。他的工作完成了。讲座结束后,他可能还和同事们讨论了一会儿,然后才离开。
思想的火花还在持续。几天后,他告诉贝索,他感到“满意,但有一点疲惫”。他在写给一位物理学家朋友的信中表现得更多一些。仔细研究这些方程,他写道,因为“它们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发现”。这个发现用最紧凑的形式表现出来,归结为一行简洁的方程,即爱因斯坦方程:

1915年末,几乎全世界都不知道一场智力革命刚刚赢得了胜利。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还有三年更为艰难、残酷的时光,即使那是些真正掌握了广义相对论内涵的人,也无法逃离战争。在东方战线,卡尔·史瓦西( Karl Schwarzschild)在了解了爱因斯坦的讲座内容后,便深深被广义相对论吸引。1916年2月,当卡尔 ·史瓦西还在军队服役时,就计算出了爱因斯坦场方程的第一个精确解——这个结果指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黑洞。爱因斯坦不确信这一怪异的可能性是否具有任何现实物理意义,但他还是作为史瓦西的代理人向科学院提交了这篇论文。
那是史瓦西最后一项有意义的科学成就。在肮脏的战场环境中,疾病的威胁堪比子弹——那个春天,他染上了一种罕见的皮肤疾病,并于两个月之后过世。私下里,爱因斯坦对史瓦西过分的爱国情怀感到惋惜;但在公开场合,他表达的是对失去史瓦西惊人的强大头脑的悼念。
瓦尔特·能斯特( Walther Nernst)是爱因斯坦另一位投身战争的同事。1913年,正是这位化学家的“朝圣之旅”让爱因斯坦离开苏黎世,选择了柏林。1914年8月,他踏上了一场堪比闹剧的旅程。他让妻子以完全军事化的方式训练自己,然后他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向西进发。此时德国军队正在向巴黎行进,他想为德军当情报员。一位50岁、还戴着眼镜的教授在前线并没有多大用处,因此不久后他就返回了柏林。但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进了军队,到1917年,两人都在战争中丧生。爱因斯坦对战争狂热分子的厌恶,本有可能使他蔑视这些遭受如此折磨的朋友们,但有些灾难实在是过于惨烈,即使是他,也无法超然的用一句“我告诉过你”而置之不理。在听说能斯特两个儿子的事情之后,他说, “我已经忘了如何去憎恨”。
数百万人在战争中丧生,欧洲变成了停尸房,科学界已经没有多余的智慧头脑思考时空的几何问题了。这使广义相对论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水星轨道问题的解决强有力地说明了这个新理论是正确的,但对任何新结论的最终证实都要看预测结果:它能否揭示一些尚未发现的现象,并经由观察或实验进行证实或反驳。广义相对论做了一些类似的预测,其中一个已经可以利用当时的技术检验:太阳的质量使光发生弯曲的程度是牛顿理论预测值的2倍,即1.7角秒而非0.87角秒。因此,对这项物理声明的决定性检验又一次落到了对日全食的观测上。
由于欧洲依然陷落在战争的深渊里,组织一次远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战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1917年年末,少数英国科学家开始计划下一次可观测的日食,那将是在1919年5月29日,日食带跨越南大西洋。那是战后和平的第一年,两个二人小组在春天出发了,一队去往巴西本土的索布拉尔(Sobral);另一队前往普林西比岛( Principe),这是西非沿岸的一个小岛屿。去往普林西比岛的观测队于4月23日抵达目的地,成员是天体物理学家阿瑟 ·爱丁顿( Arthur Eddington)和他的助手。他们拍摄了控制图像,也就是夜空中的星空照片,以便在日食发生时与观察到的相同星星做比较。无论是根据牛顿还是爱因斯坦的理论,这些控制照片上的星星位置在日食照片上都将有所变化。问题是,这个变化有多大。
5月29日,观察者们遭遇了日食观测中常见的灾难:猛烈的暴风雨,伴随着黎明而来。雨势在中午时分减小了,但直到1时30分天文学家们才第一次看到太阳,此时日食已经开始了。云层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变厚,但在全食临近时又消散了。爱丁顿回忆时说: “我们必须执行拍摄计划。”他们曝光了16次,但只有最后6次看起来比较有希望。6张照片中,有4张必须回到英格兰才可以冲洗,而余下两张中只有1张拍到了足够清晰的天空,可以在野外进行初步分析。4天之后,也就是在6月3日,爱丁顿第一次对星星位置进行了比较。
他找到了想要的答案:偏折角是(1.61±0.3)角秒——与爱因斯坦的预测足够接近,可以证明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尽管他后来回忆,那一刻是他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但当时对外发布的时候他要谨慎得多。他从普林西比岛发回英国的电报非常简单:“透过云层。有希望。爱丁顿。”
爱因斯坦本人从未怀疑过这个结果。他的两位朋友,保罗·奥本海姆(Paul Oppenheim)和他的妻子安娜·奥本海姆-费拉拉( Anna Oppenheim-Errara),在那个夏天前去探望他。爱因斯坦当时身体不舒服,于是就在床上招呼客人。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洛伦兹的一封电报带来了尽管还没有完全证实,但充满了希望的消息。75年之后,安娜·奥本海姆依然记得那个场景。爱因斯坦穿着睡衣,袜子露在外面。当电报被拿进来以后,他打开了电报,然后说: “我知道我是对的。”奥本海姆-费拉拉强调,不是他觉得或者相信他是对的。 “他说, ‘我知道。’”
到如今,在我们这个扭曲的宇宙里,即使是作为对考古的兴趣,人们也几乎不再提及祝融星了。只有一小部分人对这个故事有模糊的记忆——大多是对历史怀有特殊兴趣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对他们来说,祝融星是一个警示故事:要得到一个人想要的或者期望得到的结果简直太简单了。在这些描述中,勒威耶本人表现得尤其差劲,他如此确定自己对水星的研究结果,如此急切地想要再一次品尝发现海王星的荣誉,以至于他将一个普通、业余的乡村医生捧成了半吊子专家。其他人,比如沃森,认为自己看到了长久以来遗失的行星,并带着这样的信念躺进了坟墓。他们都警醒人们,在严密、理性、完全实证性的科学世界里, “渴望”没有一丝用处。人们常常以为,过去就是过去了,现在要比过去更加聪明理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以现在的眼光看来,相信祝融星的人多少有些滑稽。就像爱迪生和他的长耳大野兔,待他们回过头,发现其他人都伸长了脖子在看笑话。
不过,爱丁顿那张具有决定性的照片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故事。这些结果的公布使爱因斯坦闻名全世界,即使在他过世60年后依然享有盛誉。这一名声的获得是因为爱丁顿和他的同事确信,他们并没有自欺欺人地寻找他们期望看到的结果。还记得去索布拉尔观测日食的那支队伍吗?那里的天气很好,那一队拍摄的有用照片比爱丁顿这一队多几张。当他们进行分析时,他们似乎展示了普林西比岛这支队伍所得结果的一半:牛顿的答案,而不是爱因斯坦的。爱丁顿确信在索布拉尔的那支队伍拍摄的图像有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如果真是个错误,很难被发现。在9月份的时候,除了说观测到的偏折值在两个预测值之间,他不再做任何表态。
这只是暂时的。第二个月,爱丁顿和他的同事们确认索布拉尔队的主要仪器有一处光学缺陷,这造成了结果上的系统性错误。他们找到了另一台位于巴西的设备所拍摄的另外 7张图像,结果与爱因斯坦的计算值相一致,证实普林西比岛队得到的数据为最佳结果。有了这些证据之后,爱丁顿才认为忽略那些矛盾的图像是合理的,并且向皇家学会发出了警示。

当然,爱丁顿是正确的,这就是所需的全部证据。索布拉尔队的主要仪器有缺陷,而爱丁顿最好的图像最接近正确结果。当然,更重要的是,广义相对论经受住了每一次考验:从宇宙的诞生和演化一直到你手机里GPS的精确性,黑洞,引力透镜和引力波,宇宙膨胀,甚至对于时间旅行的设想(虽然几乎不可能,但并非完全无法实现)——这些都存在于广义相对论的“故事集”中。而且,这个理论不仅充分地解释了很多事物,它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事物的新方法——不仅仅局限于物理学,同时也在更广义的文化之中,科学是其中一部分。
要记住人类的这个事实:19世纪中期,那些带着渴望凝视太阳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以及对此感兴趣的普通人们,得出了一些相似的宇宙理论,所有这一切都暗示了祝融星的现实性。
那么,我们应该从这颗距太阳最近的并不存在的行星,以及广义相对论的全面胜利中学到什么呢?
至少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人类的认知中,科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可以自校正。每一个结论都是暂时性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结论都在一些小的方面,甚至偶尔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不完善的。但在争论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清楚地知道已有的知识和自然之间的差异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知道了祝融星从来都没有存在过,是因为爱因斯坦告诉了我们这个结果。但对于勒威耶和他的追随者来说,在他的时代及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并没有像这样的确定方法。他们缺少的不是事实,而是一个框架,一个从另外的角度解释祝融星并不存在的思路。
这种洞察力并不会因为命令就产生。在洞察力出现之前,我们只能通过已知的事实来解释发现。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人们固执地认为祝融星存在,说明了要人类放弃过去的幻影是多么的困难,建立牛顿引力理论及其继承者——广义相对论,是多么伟大的成就。
最后再说一下爱因斯坦。1918年,他在德国物理学会发表演说。在这次演讲中,他尝试着描述了一个在已知的边缘试图探寻未知自然的人的想法。他并没有谈逻辑、严谨性,或一些特殊的脑力天赋。相反,他提到了伟大工作背后的驱动力来自“渴望看到 ……先定的和谐”。要达到这一目标,当然需要研究者的日常工作,他们要学习数学,进行计算,与想法和实验中的错误进行没完没了的猫鼠游戏。这些都是必须去做的。但是日复一日地进行这些工作,还须以某种方式,那就是“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他说: “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两个多世纪以来,人类都生活在牛顿发现的宇宙里。祝融星的不存在并没有推翻这个居所,相反,它成了承载历史的标志。
现在,尽管一度看上去十分奇特,但我们就生活在爱因斯坦的美丽宇宙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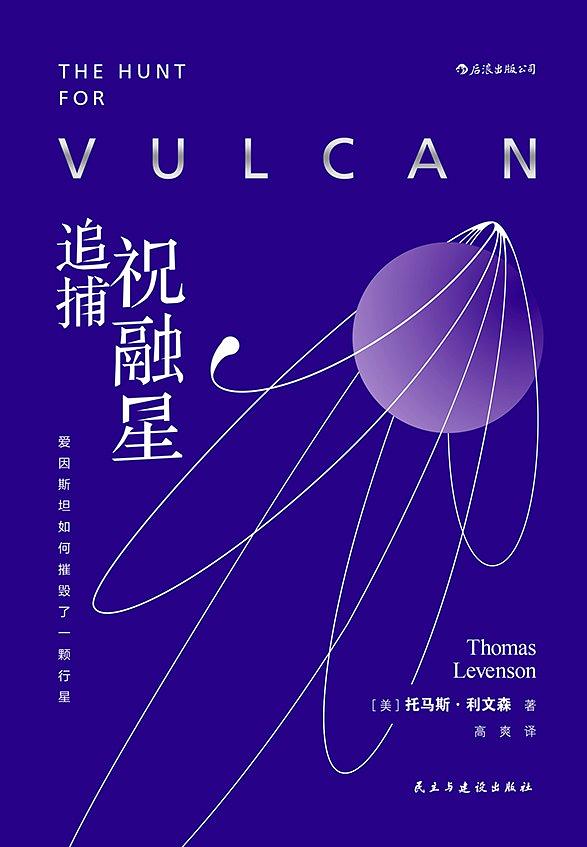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