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讲座︱赵庆云: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十七年”档案与旧人摭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赵庆云研究员于2019年11月21日主讲复旦大学历史系第15期“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携其新著《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以“史学史(学术史)研究中的‘学’与‘行’”为题,和到场师生分享了自己研究的经历和体会。本次读书班由复旦大学戴海斌副教授主持。本次读书活动还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叶毅均特聘研究员与主讲者对谈。得益于专业领域相邻,两位与谈人为在场者道出了主讲者研究背后的甘苦,也拓展了既有的学术议题。本文系赵庆云研究员演讲整理稿,末附两位与谈者发言的简要整理稿,发表文字均经发言者审定。

机缘:近代史所“十七年”档案与旧人摭忆
《创榛辟莽》这本书,我酝酿了很久。写作的机缘,是2008年刚进入近代史所的时候,所里派下任务,要为所庆60周年整理大事纪。借着这个机会,我看到了所里封存的一些资料,包括“十七年”(1949-1966)时期遗留下来的档案。所里的老先生,都惊讶于这批档案的存世——他们一度以为这些档案在“文革”中早已佚失殆尽了。但事实上这些档案被保留了下来,而且种类还比较丰富,比如整风的文件、互相之间提的意见、会议记录、计划、总结。就是这样一批意外发现的资料让我决定,以它们为基础,再进一步搜集其他的史料,以近代史所这个学术机构为中心,来写一本书。
但根据个人研究的经验来说,这些档案虽然珍贵,也不可偏信。尤其是1949年之后那些整风的档案、计划总结,其实都必须拿去与其他资料对照。计划总结每年都有很多,里面构想也很多,但最后能够落到实处的,可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又像整风的材料、自我检查这一类档案,夸张失实的地方,也不在少数。
我用来研究“十七年”史学另一些重要的资料,就是私人文献和口述访谈。所里仍健在的老先生们对此提供了不少支持,有几位老先生就提供了自己当年的日记供我参考。另外,做口述访谈亦花了不少心思。这项工作也带有抢救史料的性质:现在一些将及暮齿的老先生,其实都还是当时1960年代才进所的年轻人;真正1950年代初进所的,现在已经寥寥无几。而且有好几位,访谈后不久便故世了。
我总的构想,就是从近代史所的筹设、人才集聚、科研组织、机构的运作——尤其是党组织在一个学术机构中具体的运作方式——这些方面来叙述。同时也会涉及学科建设,研究理念诸方面。另外,当时近代史所的地位高,而且因为权力集中,强调自上而下地推动,所以很多事情可以影响到全国史学界。一些大的史学活动,我也挖掘了一些资料,尽可能地呈现出来。
另外一点,当时的史学不是纯粹的史学,它是文化斗争的武器。所以近代史所确实和民国时期史语所那种纯粹的书斋学问不同,它更强调革命性、实践性。就学论学,不仅显得呆板,也往往会导致缺少历史感。所以这本书,主要是把“学”和“行”结合起来探讨,挖掘动态史实,以“见之于行事”,进而由“行”观“学”,以“行”论“学”,力图拓展史学史的研究视野,展现十七年史学丰富复杂的面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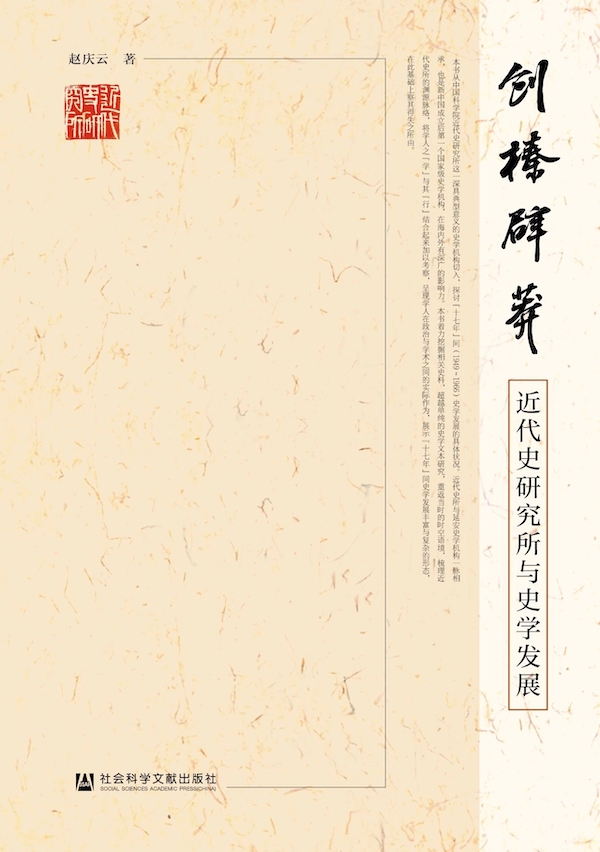
为什么先成立一个近代史所?
为什么1950年代中科院率先成立的是一个近代史研究所这个问题,书中单独写了一小节。我总体的论述是说,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强调“厚今薄古”,说史学要为现实服务——这确实是让范文澜将研究重心转到近代史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为什么到1950年代中共建政之初,要在中科院率先成立一个近代史所,而不是一个涵盖更广的历史所呢?
这牵涉到一些个人的考虑和选择。范文澜个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我考察得出的判断是,这主要是基于人事方面的考虑。范文澜的基本想法,就是近代史积累薄弱,研究的人不多,而那些著名学者基本上是研究古代史的,那么先成立一个近代史所,就可以把那些从事古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名正言顺地排除在外面。其实当时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还是倾向于先成立一个综合的历史研究所,在1950年还让陶孟和写信,有意把陈寅恪延请过去。但陈寅恪也没有积极回应。之后高层很快便敲定,要成立的是一个近代史所。从《竺可桢日记》看,竺可桢对此也表示很不理解,还对郭沫若很有意见,说中科院是大家的,不是你郭某一个人的——他以为是郭沫若做的主张。其实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范文澜。
范文澜的考虑是,民国过来的那些著名学者,有的甚至比他还年长,资历比他老,若同在一个研究所怎么相处,怎么领导,是比较伤脑筋的。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陈垣、向达、杨树达等人对这此举措很是失望。陈垣在1950年春节团拜会上就指着范文澜,当面批评说,为什么先成立一个近代史所,让我们这些人都不能进入中科院系统?向达就说得更挖苦了,1957年“鸣放”的时候他讲:“史学界为什么奄奄一息?那就是因为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宗派主义的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先是成立一个近代史所,把他们都排除在外。
这件事情到1953年有了变化。到1953年最高领袖看到史学没有繁荣起来,近代史所重在培养新人,成果产出不太令人满意,所以由最高层介入,成立了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让陈伯达领导,明确说中国历史很长,最好是分三个时段:上古、中古、近代,三时段各设一所,同时三个所合办一个权威杂志——也就是《历史研究》。所以近代史所筹设,前前后后,其实牵涉到新旧史学界不少微妙的关系。

难以钩沉的语境
在考察学者学术研究的同时,我将相当笔墨放在钩稽学人的具体学术活动和人脉关系,通过结合时代政治、社会语境来窥探文本的背面,力求对这些学者有了解之同情,不做批评与苛求。
其实一些史学学术观点的争论,又和背后的人际关系纠结在一起。有时候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表面上是学术观点的争论,其实后面牵扯到人事关系、人际矛盾。比如范文澜、黎澍、刘大年对人民大学尚钺的批评,既有学术上的见解不同,也有此前的人际关系牵扯其中。至于范文澜与尹达的矛盾,更直接影响到近代史所与历史所两所间的关系。
这些学界人物之间的关联,有时候很微妙,很难把握。而十七年的材料中呢,恰恰有一些相关材料:整风的档案、党小组会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它会涉及到个人的恩怨。像这样的材料,怎么在书里呈现出来,也比较费脑筋,所以最后还是做了取舍。
1950年代去今虽然不久,然而对当时的时代语境,又实在很难真正做到了解之同情。比如1950年代党小组的会议上党员之间的相互批评。其实今天党组织里也有这种互相批评,但大家顾及和气,批评就比较形式主义,或者明贬实褒,或者兜兜圈子。但当时牟安世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年轻,还是范老招进近代史所的,范文澜则德高望重,而牟安世在党组织会上对范文澜的批评,就非常尖锐,涉及工作方法、待人的方方面面,而范文澜也只得态度认真地回应了九点。在今天这是不好理解的。再如当时非党员面对党员的那种惧怕心理,以及一位学者在政治运动中冲击别人,却觉得自己承受了很大心理压力,以致于患上神经性疾病等种种事情,都是现在很难体会到的。

“十七年”的全国性史学活动
另外书里面也写到几次涉及到全国史学界的一些活动。这个面就远远超出了近代史所本身,而且因为涉及到整个国家,牵涉到成千上万的人。比如社会历史调查,“四史运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史学反修,它们都和政治相纠结,同时又确实有学术的成分,也结出了一些成果。口述史要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社会历史调查与当今的田野调查确实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时的人调查做得很认真,去农村就同吃同住同劳动,交上朋友之后,再做访谈。
我手头也有一些特别的资料。当时一个后来很有名的人物,沈元,那时候本来因为翻译赫鲁晓夫的报告被打成右派,后来因为写了《<急就篇>研究》发在《历史研究》上,引起轰动,郭沫若、范文澜看了都大为嘉许,然后就调他到近代史所工作。沈元在当时也深受写“四史”、做调查的风气影响。他和张振鹍两人到山东黄县下丁家大队口子村劳动,历时八个月,两人一个一个访谈,留下一包记录的手稿。这些手稿由张振鹍先生提供给我。他们当时想写一个村史,但后来没有写成;因为写“四史”的基本要求是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但是从他一一收集的材料来看,和这个总体要求还有距离,所以就放弃了。而这个材料还是留了下来。
还有史学反修正主义。当时把30至50岁之间不少做学问做得不错的学者都召集到北京,成立了一个史学反修正主义的小组,让他们到全国收集苏俄侵华的史料,收集来了几万册。然后也做了一些翻译工作,写了一些文章,要从历史学方面来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这和后来近代史所的中俄关系史学科、及《沙俄侵华史》的撰写,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时候很多史学著作,其实往往起始于某项政治任务。
再一个是中国史学会。1949年有一个新史学筹备会,然后1951年正式成立史学会。成立之后第二年秘书长向达就发牢骚,他说:范文澜和胡绳,应该思索一下自己的功过,史学会刚一成立就被他们搞得奄奄一息,没有实际的活动。这其实很难怪哪一个人。事实上,范文澜利用这个史学会作为号召,还是做了不少实际的事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我们说它编得很好,背后其实是范文澜整合了全国多个方面的力量,他给一档馆写信就有十几封,同时柴德赓、陈垣这些旧派学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当然这后面最核心的,还是近代史所自身的编辑组,关键人物就是聂崇岐。编这套丛刊,聂崇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政治运动的影响是本书目前研究未尽的一部分。就近代史所这一学术机构而言,政治运动连绵不断,不同背景的知识人在运动中如何因应,如何自处?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史学史,也是知识分子史、政治史。史学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有必要与政治史、党史、革命史结合起来探讨。
比如这本书初稿写到的1953年“反小圈子”运动。原本行政上一件小事,被上纲上线到一个政治问题,最后把荣孟源、漆侠、沈自敏、何重仁被打成一个反党小集团,漆侠本来很受器重,这时也只能被迫调离。李瑚、张振鵾两位先生都回忆说,当时这个“反小圈子”的政治运动,对他们这些年轻人震撼很大。从相关资料来看,“反小圈子”本来当然是莫须有的事情,但背后牵涉到复杂的人际矛盾,也有权衡博弈。据我研究,事情后面其实有范老的影子。这也涉及到范文澜书生形象之外的另一面。政治运动在一个研究所内部具体如何进行,如何影响到学者的心态及学术机构的长远发展,如何影响到史学研究的生态环境,都值得进行具体而微的探讨。
另外再可研究的是当时的劳动锻炼制度和学习制度。这直接影响到当时学术研究的环境,也可以看到老先生们诉苦说不能长期潜心研究学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很多的学习要求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就是所谓的“滚泥巴”。而劳动锻炼的安排,条文是一回事,实际运作起来,就有很多蹊跷。比如党员、积极分子可能就锻炼得少一点,而政治方面有包袱的人员,所有的锻炼他都得不折不扣地完成。还有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从李瑚先生的日记来看,内容是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主,通过学习毛著来学习马列理论。不过后期政治学习的情况就有点疲沓,尤其时事学习往往成为闲聊,借此机会大家还会传播一些敏感的信息。总的来看,虽然1957年说强调要保证研究人员5/6的研究时间,1959年说要保证有4/6的研究时间,但根据他们年终总结的清算来看,实际上用于研究的时间往往无法保证,有人甚至只有1/6的时间在做研究。
再者,集体研究是近代史所的一大特点,这也导致了一些著作署名方面的微妙问题。聂崇岐自己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最后他自己署名第三作者,第一范文澜,第二翦伯赞,聂崇岐他也心里也愤愤不平,所以还是留下文字把这个事情记了一笔。当时很多人对集体协作模式有不少批评和反思。所以到1980年代以后,集体研究就难以为继了。1980年代那个集体项目《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原来的《中国近代史稿》进行得相当艰难,后面也就不了了之,未竟其功。

李孝迁教授发言:庆云兄很自谦,说这本书只是解决了一些“是什么”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这本书的优势,而不是它的局限,毕竟任何一项历史研究首要的工作总是史实重建。这本书在史实重建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采用了大量一手档案文件、书信日记、私人访谈,呈现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为了重建史实,书中颇多大段引述一手资料,一般读者或觉得累赘,甚或认为是凑篇幅的,但我认为这是庆云兄在材料处理方面的匠心独运之处。这些史料大多为作者独家所有,在其他地方不易寻见,整段披露史料,才有可能完整透露历史信息,读者可从中体会把玩,以检验作者的判断。就我来说,读他的书最大的乐趣,就是读这些整段资料,“断章取义”式裁剪史料,倒不是我最想看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较特殊,要找到公开发表的学术论著之外的材料,有相当大的难度。他们的书信或日记,通常很难见,公开整理出版的部分很少。赵老师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披露很多外人没办法看到的资料,是相当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庆云兄分寸拿捏得很好,不轻易褒贬、批评——就把事实摆出来,让读者自己来评判。
与其他史学领域相比较,“马史”研究进展相对缓慢,研究思路过于陈旧,除了受研究者视野局限之外,与相关文献的局限也有很大关系。有时候不是研究者不努力,而是研究者没法努力,没有抓手,使不上力气。像延安时期的马史文献留存的就很少,抗战时期在重庆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相关材料也很零散,这种史料状况跟胡适、傅斯年之类人物研究很不一样,前者所凭借的文献太少,难免捉襟见肘,不易施展拳脚,会影响研究进一步的拓展。像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研究,虽然均有评传,有的还出版多种,但总体来说,读来“不过瘾”,所依托的文献大多是公开出版物,不容易看到这些出版物之外的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就是说“文外之意”大多无法呈现。研究“马史”经常会碰到一些回忆性质的文献,很多是门生故旧回忆写的,有的则是晚年建构式的记忆,删除了太多历史细节,史料价值大打折扣。
做学术机构的研究,近来也有不少。比如陈以爱对北大国学门的研究、尚小明老师写北大史学系等等。研究各个高校的历史系,包括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也陆续都有人去填补空白。但是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局限——都比较关注1949年之前,而1949年之后的,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人做过。所以像赵老师这本书是很有突破的。几十年来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民国这个时段,其实大可以把战线往后拉一拉,1949年到改革开放这个时段的史学史、学术史,空白点很多,有价值的题目也多,大有可为,大家不必都挤在民国,赵老师这本书的成功,就给我们很好的指引。
叶毅均研究员发言:庆云兄书里讲学术机构中的党组织那一节,写了应该有四十几页,篇幅相当长,对我们生长在台湾地区的人来说,党组织当然很遥远、很陌生,但这本书把其中的门道讲得很清楚,所以我读那一节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但庆云兄这本书的副标题,“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就我的感觉,其中或许还缺少了一小块“遗失的环节”。因为除了大陆,台北也是有自己的“近代史研究所”的。
其实我们可以拿台北的“中研院”近史所,和大陆的中科院近代史所做一个对照。如果要说“中研院近史所的十七年”,那可以从1954年开始筹备算起。郭廷以先生1955年当筹备处主任,正式设所后任所长,到1969年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被迫离开台湾,把自己一手创立的近史所拱手让人,一年之后正式辞去职务,到1971年正式办理退休。那这个1954到1971年,就是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十七年。比起中科院近代史所的“十七年”(1949-1966),仅仅晚了五年左右才开始。此后双方平行发展,但仍不时或虚或实地有所交集,甚至带有某种“竞争的焦虑”。
台湾地区的这个小十七年,借用近史所成立40周年所庆出的那个回忆录的名字来说,就是“走过忧患的岁月”。忆及近史所的这段岁月,他们也是一肚子苦水。不但一开始筹备设所时受到来自史语所的强大阻力——这一点和中科院近代史所率先创设所遭遇的史学界反弹异曲同工——就连郭廷以所长筚路蓝缕创办了这个所,外面的人还说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因为美国的费正清是中共的同路人,郭廷以又是费正清的同路人。甚至最后被指责勾结外人,出卖档案;在白色恐怖的那个年代,台湾的情治人员直接进到院里来抓人,问郭廷以所长,你为什么没有处理手下的人?你是不是“庇护匪谍”?除了“外患”还有“内忧”。郭廷以嘱意李国祁来接他的班,但是他的大弟子王聿均等“三公”(王聿均、李毓澍、黄嘉谟)就不满意,极力杯葛。这不像范文澜可以根据党组织主导的原则找刘大年来接班,同时又不会产生异议;台北没有党组织,在郭氏二代弟子中就会有接班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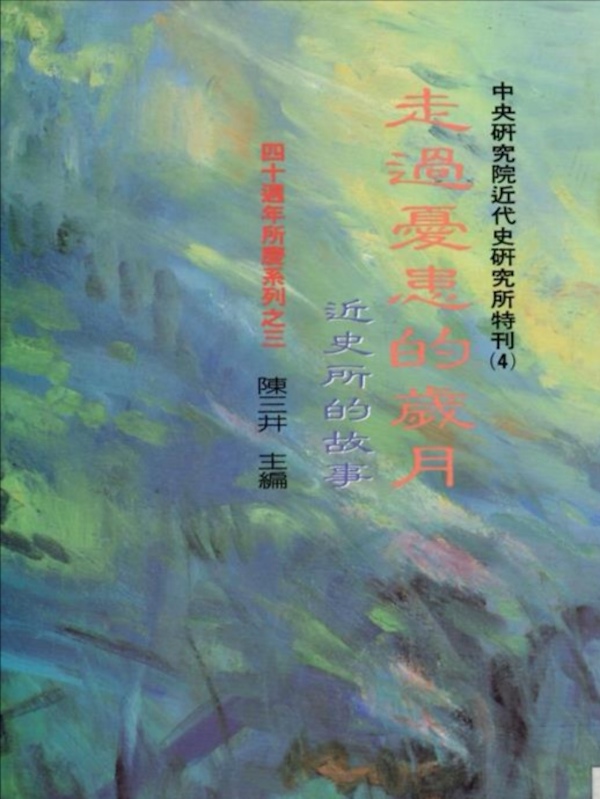
台北的小十七年里,学术和广义的政治,也有产生龃龉的时候。沈云龙在近史所出一本专刊《黎元洪评传》,因为把黎元洪抬到太高的位置,就有在台湾报刊的读者投书说,“黎元洪哪有那么重要,我们的总理孙中山才是最重要的人,建议应该查禁这本书!”。又比如张存武,那时候他原本要研究清季的反美运动,但是当时情治单位找到他的书稿,就要去抓人。怎么可以反美呢!相较于当时大陆“怎么可以亲美”,当时在台湾是“怎么可以反美”——反美就是中共“煽动”的嘛。所以原先的书名《清末中国反美运动》,郭廷以教他改成《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这样子一改就没问题了。
我常常在想,以后可以做的进一步工作,就是去思考两岸史学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在冷战隔绝对峙的大局势之下,同样是政治对学术的影响,两岸史学有着怎样不同、以及雷同的表现方式。而且我们大可以把战后美国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建立,放进来一起比较。因为就是为了要理解1949年之后大陆为什么会“赤化”,为什么会“沦入共产党之手”,所以美国才要花这么多的钱,包括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去建立这个研究。也是因为政治,才会有所谓从汉学到中国学的这个转变,才会让费正清等人有机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而台湾地区在各方角力之中,扮演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一方面是“军事反共”的基地,一方面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实验室(借用已故台大教授陈绍馨语)。把“中研院”近史所这个基地建立好了,美国人就可以把它新一代的汉学家送到中国台湾去训练,再加上台湾地区自己近史所能够掌握的档案,它就可以成为学术冷战对抗的最前线。多年前张朋园先生的专著《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廷: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一书,对于此一问题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言简意赅的示范研究,在比较小的范围里或许可以和庆云兄此书对读,未来应该是我们可以综合地去研究的一个课题。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青年学者读书班”不定期邀请海内外学者发布新作、分享新知,澎湃新闻将陆续刊载这一系列讲座纪要。)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