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
郁喆隽 译丨哈贝马斯与讨论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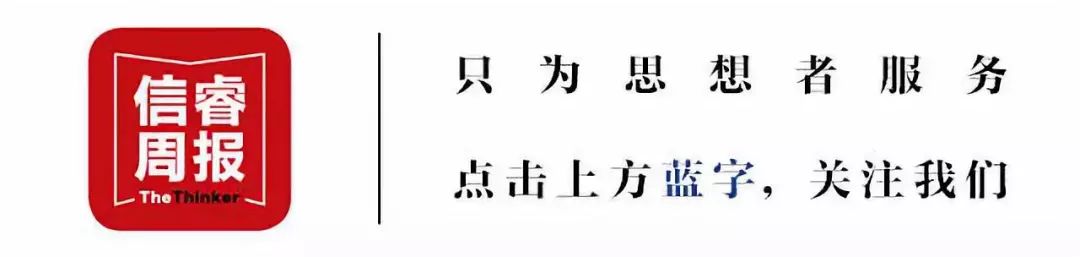

文 / 雷蒙德·盖伊斯(剑桥大学哲学系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
译 / 郁喆隽(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编 / 者 / 按
2019年,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继承人、被誉为当代世界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的德国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迎来了他的90岁生日,与此同时,一场围绕其哲学遗产的激烈争论也就此在西方思想界展开。剑桥大学哲学系教授雷蒙德·盖伊斯(Raymond Geuss)6月在在线杂志Soziopolis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讨论共和国”(Eine Republik der Diskussion)的文章,批评哈贝马斯对公共议论的理解实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这篇文章引发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教授马丁·杰伊(Martin Jay)、耶鲁大学政治学与哲学系教授塞拉·本哈比(Seylia Benhabib)等学者的回应与反驳。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的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宗教学与社会理论,他翻译的哈贝马斯晚年对国际局势观察和反思的作品集《分裂的西方》于2019年3月出版。《信睿周报》邀请他将盖伊斯的文章译为中文,以期读者了解这次论战的起始。除德文版外,盖伊斯还以“讨论共和国”(A Republicof Discussion)为题在《观点杂志》(The Point Magazine)网站刊发了英文版文章。在郁喆隽看来,两篇文章虽极为相似,但在行文、结构和措辞方面均有所差异。其在翻译时参考了英文版的内容,但最终以德文版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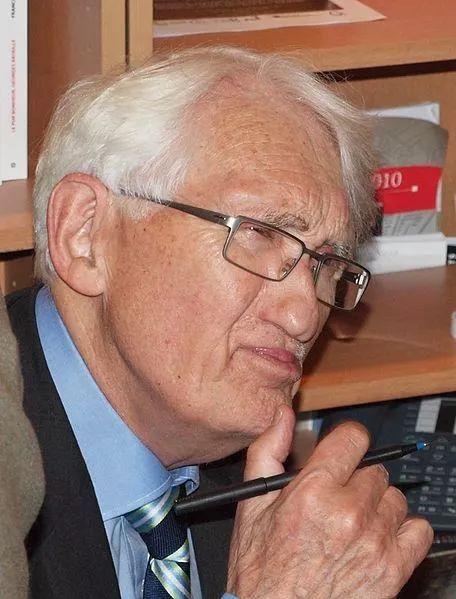
Jürgen Habermas(1929 — )(图片来自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Ziel 摄)
当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其《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表达出对“每一种思想的任意、一般的可交往性(Kommunizierbarkeit)的自由幻想”[1]的顾虑时,他想要针对的是政治自由主义和哲学的关键概念“交往”(Kommunikation)。然而,他的两线作战方案——一方面反对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反对迷恋那种无边界的可交往性——并没有在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的下一代中得以延续。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阿多诺的非官方继任者尤尔根·哈贝马斯更多地致力于以下工作:用新康德主义的方式来为自由主义平反,并且要依赖于一个充满规范性的概念——“话语”(Diskurs)[2],这意味着要以一种“交往行动理论”(instrumentellem Handeln)[3]为中介。基于以下三个理由,这一工作可以被称为 “新康德主义式的”:首先,它将对“合法化”(Legitimation)的追问置于核心位置;其次,它关注那些假想的,但又是无法改变、产生规范性的结构;最后,它对理论进行了二分,也即把“话语”和“工具行动”截然对立起来。阿多诺诊断了那种一般可交往性的自由主义幻想,但哈贝马斯并没有对此提出批评,而是严肃对待,并将之提升为合法性(Legitimität)的一个标准。自由主义应当在一种先验的交往理论中找到其规范性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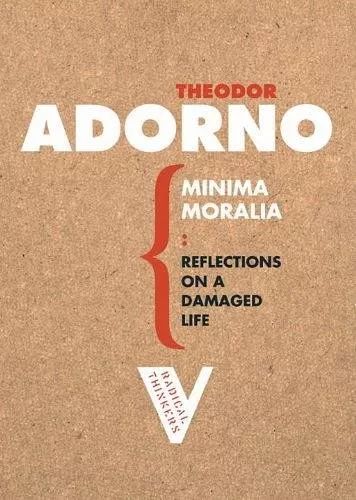
Minima moralia
Theodor Adorno (Author)
E. F. N. Jephcott (Translator)
Verso, 2006-01
“交往”对哈贝马斯而言不仅是个经验过程,它还具有一种双重结构,这一双重结构对西方的整个意识形态建构,对自由、民主或法律的理解都是独具特色的:一方面“交往”指向一种在日常语境中经验的、自明的和毫无问题的用法——它引发了一种假象,即交往关乎人类共同生活的普遍基础事态;另一方面,交往结构的单纯存在——哈贝马斯称之为“和解关系”(Verständigungsverhältnissen)——已经要求理想化的规范性。因此严格地讲,只有满足了这一要求和与之关联预期的和解,才能被称为完整意义上的“交往”。交往一方面是准经验性的,另一方面则是规范性的。在两者之间就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扭曲。悖论的是,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我们社会中的交往经常不是交往。哈贝马斯曾经穷尽了德语的日常用法,在一次表述中谈到了“扭曲的”交往,即当和解实践不符合其内在的规范性规则时。因此,正如康德所做的那样——他严格区分了倾向和义务,或者说要区分“经验上的驱动力”和绝对命令,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分在社会强制条件下的伪交往和真正的、不含支配的话语。
“自由讨论”的理念和理想在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那里,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样一种理论建议和自由主义的某种意向之间的选择亲缘性(Wahlverwandtschaft)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然而,哈贝马斯也不得不处理那一种理论的标准问题。传统自由主义的一个明显弱点在于,这样一个在原则上并不特别明确,但又非常具有传染性的观点:讨论总是可能的,也总是好的——唯一的前提是,人们并不处在急切的危难或者例外状态中,也没有受到相应的威胁和对身体和生命的危险。这也假定了,一场尽可能不受到管制的讨论,必定有助于澄清状况;而且如果意见交流通畅的话,讨论者之间可以达成共识,这至少“在原则上”是可能的。约翰·穆勒(John Mill)声称,对“低等民族”而言,自由主义一无是处。他当时关注的是大英帝国里被压迫的印度人民。但是,公开且明确地反对“讨论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理想,即便是穆勒也会对此感到为难。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即便当讨论自身处在“理想”条件下时,认为它在根本上能够建立共识,这一点在经验上仍是错误的。事实上,讨论经常是更为极端化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一场讨论不仅徒劳无获,而且还导致了比原本更大的混乱,或者意见交换(时间)越长、越深入,各方越坚持己见。正是这样的经历,要求将交往行动理论纳入“理想言语情景”当中。一个参与了言语行动的人,果真会认定通过来回地表达最终会达成共识?
我们来看看英国的例子:关于脱欧的公共讨论在过去三年里,给我的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也是多余的痛苦。不言而喻的是,在脱欧公投之前的“讨论条件”绝非“理想的”。关于这一发现,我们无须多言,但事实是,10年前,除了一小撮头脑发热的人之外,没有人对归属欧盟这件事感兴趣。一直到慢慢展开的讨论过程中,很多公民开始关注这一话题。同时,强硬的欧洲反对派——大约占英国人口的10%——又增长了10%,他们展现出对欧盟的潜在敌意,并公开表达出来。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历史的偶然因素也掺和了进来,这样又有17%的选民投票支持脱欧。由于投票机制的结构属性,37%有投票权的选民投票支持脱欧,成为了有效“多数”,换言之,占52%的实际选票。结果就众所周知了。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历史结果导致了现在30%到40%的英国公民真的是反欧的。而且没有一场在如此理想条件下进行的讨论,在中期可能改变这一状况。在讨论中公开其立场的人,后来(在可能进行的第二次公投中)承认自己错了,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心理原因,这是很困难的。对很多脱欧派选民而言,拒绝欧盟变成了一个绝对的生存机会。对他们来说,脱欧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关乎“认同”(Identität)问题。如果我和这样的脱欧人士交谈,我绝对不会使用“更好论证的权力”。我甚至不会假定,在理想条件下时间无限的讨论会消除混乱并最终形成共识。这一状况和类似局势的麻烦之处恰恰在于,那些关乎“认同”的论证是无法或者极少奏效的。“我们绝对不想在任何状况下,和被我们所鄙视的‘欧洲佬’交换。”你对此要说什么?只有明显的长期社会变革,即社会——经济过程,以及干预世界历史事件和有远见的政治实践才能在这里发挥作用。对此凯恩斯(Keynes)早就知道,并且说得很好:长远来看,我们毋庸置疑都已经死了。[4]
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也提出过一套“交往”理论。但是和哈贝马斯不同的是,他毫不含糊地将“交往”视为一个“自然过程”(naturalistischer Prozess)。此外,杜威强调,在有问题的实践情景中,提供澄清(Klärung)的主要是人类的行动。每一种“澄清”首先都是回应;澄清处在一种给定的环境中,并且在原则上指向这一环境。只有通过额外的和进一步的行动,包括抽象和传播行为,它才能获得更“一般”但总是有问题的有效性。在某些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解决问题的行动当然也可以采取讨论的形式。然而,不存在先验预定形式的理想讨论。如果讨论无济于事,就必须脚踏实地,以改变实际的环境——毋庸置疑的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动手。有些人觉得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启齿甚至亵渎神灵的口号。但在必要时,坦诚的“自由主义者们”从不犹豫不决,这似乎并不陌生,他们只是不愿承认罢了。
奎因(Quine)的著名说法“根本的翻译始于家中”(radical translation begins at home)[5],在分析哲学中相当于兰波(Rimbaud)的声明“我是另一个人”(Jeest unAutre)。这句话提出,我即使在最私密的自说自话时,在与我自己的内心独白时,也遇到了一个对话伙伴,他所使用的语言对他和我而言,并不是完全透明的。这种语言也必须加以“翻译”。因此作为原材料的尚待翻译的过程,只能基于他(和我)的行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如果我甚至没有和我自己达成透明的规范性一致,并且按照奎因的判断,这种状态的观念无疑是前后矛盾的,那么由哈贝马斯对规范性调节的理解和对真正共识的狂热,能得出什么呢?
在“交往”这一自然现象中,人们从未如此努力地要划定一个领域,该领域将超出可能的支配(Herrschaft)[6]范围——或者在乌托邦式的期盼中,也就是说在思想上——旨在悬置或者说制约支配。正如哈贝马斯建议的那样,即使“支配无涉”(Herrschaftsfreiheit)被确定为理解的规范性内部逻辑的涵义,但与历史和实际的交流经验无关的理论却超出了“支配无涉”的交往,而把我们当下处境的偶然因素绝对化了。当代哲学的首要问题是消除社会合法性之欠缺,并且可以通过诉诸上述的交往理论来实现,这一论断在很多方面都是可疑的。将“合法性”视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至少是近代的核心哲学问题,这是一种新康德主义的偏见。首先,声称理据(Rechtfertigung)才是现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可能是错误的。其次,哈贝马斯关于“无涉支配的话语”的想法是荒谬的——“交往”没有稳定和不变的结构,交往尤其也没有相应的结构,可以为辨识和批判“支配”提供具有一般约束力的标准。换言之,不存在以下意义上的“交往”:它是符合规则的言语行为——它必然要以普遍规范为目标,并且该规范建立在交往结构之中,始终服从于交往参与者的相互期望。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 著
曹卫东 /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10月
早期自由主义的神学基础(斯宾诺莎、洛克)在18世纪下半叶丧失了公信力,此后人们已经进行了近200年的尝试(从康斯坦特和洪堡到穆勒,还有霍布豪斯),不采用上帝的观念和与之相关的一切。独立的、缺乏了神学支持的自由主义——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表现为一个漫长而广泛的实验,正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的那样,它的短暂成功依赖于欧洲殖民大国、大英帝国及其模仿者的庇护。如果殖民帝国足够大、强大和自信,那么它当然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不仅允许宽容、言论和表达自由,而且还可以保护构成其法律前提的主体权利。一战时欧洲出现了精神崩溃,二战的开始意味着旧有帝国秩序的瓦解,此后只有美利坚帝国内部在一段时间里,对多种多样的“自由人”(homo liberalis)而言,成了一个露天饲养场[7]般的大陆。从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9月的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美国内部也在逐渐崩溃,而且日益明显。
晚期自由主义的温和精神,带着一种怀旧气息渗透到哈贝马斯的著作中,表达出了一个历史时代的声音。1945年以后,特别是在中欧,重建政治、经济和社会新秩序的问题尤为紧迫。粗略地说,另一个问题是向西或向东整合。人们还没有考虑到更激进的社会变革。毫无疑问,联邦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早已融入西方,然而这个重大的政治计划为1981年出版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Theorie deskommunikativen Handelns)提供了当代史的框架。众所周知,事后性(Nachträglichkeit)[8]是哲学反思的一个特征。因此,一种准先验的哲学将话语作为公共理性使用的一种媒介,它一方面允许西方在整合过程中在美国、法国、英国和荷兰重拾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传统;另一方面要求特别处理有效性主张(Geltungsansprüchen),该整合一直带有德国康德主义传统的全部风格。
人们几乎不关注杜威的“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us)——他有时将自己的立场称为“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或“实验主义”——它在旧联邦共和国[9]的形成阶段几乎无法立足。人民中的大部分确实很害怕政治和社会实验——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因为他们担心东方的“法西斯主义”实验死灰复燃,也反对参加东方的“伟大文化实验”。“不要实验!”是基督教民主联盟(CDU)[10]在50年代末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口号。由于铁幕另一边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并不小,甚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变大了,所以虽然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实验”,但完全可以将其从讨论中抽离。例如,按照波普(Popper)所说,过于激进和大规模的“实验”违反了“研究的逻辑”,或者如哈贝马斯所说,交往理性的那种先天的界限,将某种“工具性的”政治干预变得不容置疑了。此外,先验论(Transzendentalismus)不仅是装饰物,而且是用来限定可讨论内容边界的不可放弃的工具,必须尽可能确定牢固的、不容动摇的边界。这样一种努力并非纯粹的德国现象,而是地区性现象。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甚至是美国的罗尔斯,几乎都被迫进入康德学派,以追求“美国生活方式”。换言之,那里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抵制那些被认为过于激进的替代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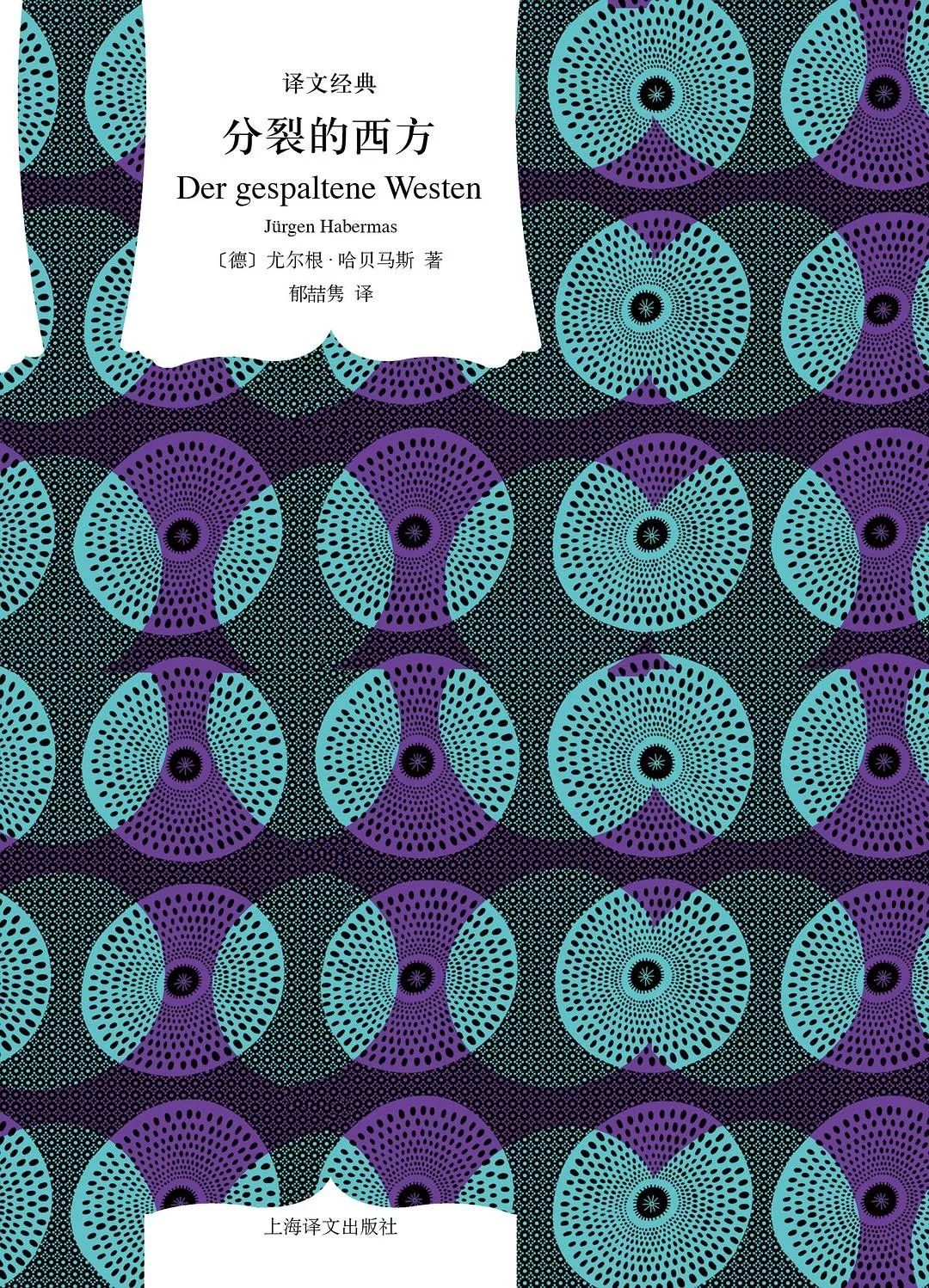
《分裂的西方》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 著
郁喆隽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3月
我们“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生活”这样的愚蠢断言,绝对不是对现状的特别有说服力的辩护。如果确定了给定的关系和基本结构,干预将更为有效。通过提供各种可能性的范围,来批评个别的滥用,它将从中获益。一种宣扬话语批评的意识形态,越是具有情感逻辑的优势,就越能实现自身。这种意识形态,通过将不适感转变为对既定社会体制的特定缺陷按照其本质加以改良的小规模批判,可能可以吸收和引导过度能量的破坏性——这一点要感谢康德。
预言并不在哲学家的能力范围内。不过,反思和推测未来是人们在其同时代的社会中几乎无法避免的。由此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下一代人是否还会和从1950年到2000年之间的青年人一样,关注讨论或者话语。他们不仅应该有所不同,而且还愿意有所不同。有什么理由去指责他们背叛了自由讨论的理念呢?谁能指责他们呢?
[1] 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德文版),第50节,此处为第43页。——原注
[2] 德语Diskurs(英语为discourse)在汉语中有几个不同的翻译,如商谈、协商和话语。——译注
[3] 以往一般被翻译为“交往行为”。德国社会学传统自马克斯·韦伯以下一直严格区分行为(Verhalten/behavior)和行动(Handeln/action),后者带有行动者的主观意涵。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kommunikativesHandeln)显然指后者而非前者,因此需要改译为“交往行动”。——译注
[4] 语出《币值改革论》(The Tract on MonetaryReform,1923)。——译注
[5] 这一观点是奎因1969年在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一书的《本体论的相对性》一文中提出的。——译注
[6] 英文版在此处混用了force和domination,令人费解。德语中的Herrschaft一词含义更丰富。从马克斯·韦伯以来,“支配”(又被翻译为“统治”)一直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译注
[7] 原文如此,带有较强的贬义,英语版使用了open-air zoo。——译注
[8] 在英文版中作者将这一概念归功于黑格尔,可能指哲学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这一比喻。精神分析的传统将该词归功于弗洛伊德,翻译为英语的afterwardness,汉语称为记仇或怀恨。——译注
[9] 指两德统一之前的西德。——译注
[10] 德国的重要政治党派,也是现在德国联合执政政府中的主导政党,常年是德国联邦议会第一大党。——译注
(中译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5期,德文版原题为Eine Republik der Diskussion,载于Soziopolis,2019年6月18日)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中方出手连环反制
- 中方连环反制,美指期货应声下跌
- 10位在韩志愿军烈士寻亲线索公布

- 美股继续暴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入熊市
- 美媒:美国国税局将裁员2万人

- 被誉为“活化石”的中国特有树种是
- 被誉为地球之肺,位于南美洲亚马逊盆地的雨林是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