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专访|费正清中心主任宋怡明:了解百姓日常才能了解中国
凡是国家,必有军队,用以保卫国土、攘外安内。由于军事制度普遍存在,从此处入手进行历史研究,管中窥豹往往卓有成效。不仅能通过军事制度来了解国家如何运作、如何分配资源,而且能以之探索国家与百姓如何互相作用与影响。而在中国大一统的王朝体制中,民间社会也形成了灵活多样的应对机制。
近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的新作《被统治的艺术》中文版面世,该书以明代沿海卫所为背景,剖析在明朝世袭军户制度下军户家庭与官府的互动,着重描述和总结了承担兵役义务的军户如何趋利避害,制订出种种策略以优化自身处境。他们既未公然蔑视权威,亦非俯首帖耳,而是在反抗与服从的“中间地带”运作,以期将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同时使利益最大化。

“我喜欢从小历史见大历史,由百姓小故事讨论时代大问题。从明代军役制度及军户的因应策略入手,再现政策与人性的博弈,反思明朝治国得失,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是好制度。”近日,宋怡明来到上海,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宋怡明普通话流利,熟知福建风土人情,有近三十年田野调查经验。他作为以历史人类学研究为标志的“华南学派”第三代学者翘楚,经常引用他口中的“祖师爷”傅衣凌先生的话:历史研究不可以在图书馆做,要去跑田野。
在《被统治的艺术》中,宋怡明运用了大量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等民间资料,讲述了许多发生在军户生活中有趣的故事。真实而鲜活的案例,辅以严谨、细致的考辨,构成了这本讲述百姓自身历史的社会史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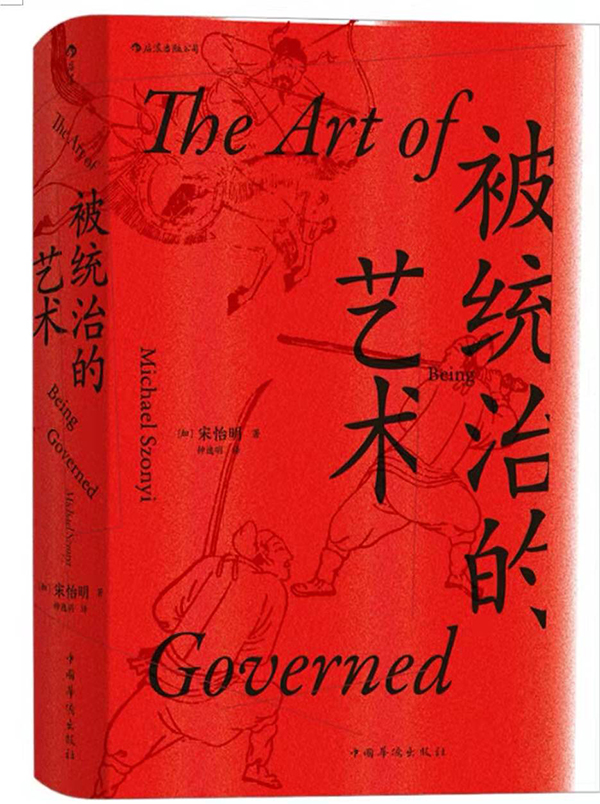
澎湃新闻:你在2008年入职费正清中心时就提到要做明代军户制度研究,为什么选择了这个方向?
宋怡明:这和我的博士论文有关,当时我做了一个历史人类学的课程,接触到了福建的福州地区。福州是一个家族组织非常发达的地区,我想了解它的历史,想了解当地百姓是从哪里迁徙过来的,然后发现在中国整个宗族发展的历史上,明代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是很关键的时期。
为了研究宗族历史,我开始重视明代。之后做了大量田野调查,收集了很多族谱,发现军户的族谱非常特别,其中讲述、隐藏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因而决定做这样一个研究。
澎湃新闻:明代军户制度是怎么样?
宋怡明:根据明代的军户制度,每个军户有义务出一男丁去卫所当兵,只要你登记为军户,这个家庭就得永远送男丁去当兵,军户是世袭的。在朱元璋的设计下,国家需要多少兵丁,就设多少军户,这样就有足够的兵源。这是个很聪明的办法,责任下沉给老百姓了,只要你是军户,你世世代代为朝廷出兵,让谁来当兵你们自己决定。
但这样就出现了很多悲剧家庭,比如万历年间生活在泉州近郊的颜家,颜氏家长先是选择了让第四个儿子出丁,但这个只有十四岁的孩子入伍后不久就因病身故,颜家随后又派出另一名幼子接替,但这个孩子没服役多久就当了逃兵不知所终。颜氏家长改变策略让大儿子应役,大儿子被调往西南边疆,终身服役再未回乡直至去世。勾军官吏第四次登门时,颜氏家长都已经风烛残年,却不得不再次择子顶补,但这个儿子连驻地都没到,就在长途跋涉中病故。
澎湃新闻:这本书虽然在讲军户制度,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话题,而是百姓与政府打交道的艺术,你在书中频繁提到了两个词“日常政治”和“制度套利”。
宋怡明:“日常政治”简单些说,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对权威规范、制度等。很多政治行为往往只是一种平凡而日常的互动,介于被动服从和主动反抗之间,在这个中间地带,百姓间接地与国家机构、管理制度及国家代理人打交道。
“制度套利”是近代财政学上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可以非常准确地描述我观察到的现象。对明代百姓来说,日常政治意味着不计其数的权衡斟酌,包括掂量顺从或不顺从的后果、评估各自的代价及潜在的益处。百姓为何要这么做、动用了哪些资源、和体制的博弈如何重塑了他们的社会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研究的,换而言之,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中国历史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被统治,而是怎么“在被统治的状态下中优化自身处境”的艺术。

宋怡明在讲解他在福建沿海所作的研究
澎湃新闻:百姓博弈、腾挪的空间在哪里?你在族谱中读到了哪些故事?
宋怡明:明代百姓想尽种种办法来应对,既能完成国家的义务,又不至于让家庭遭受太大打击。朱元璋的这个设计,在长期的执行下,我想多多少少促使了宗族的发展。为了应对征兵,百姓想到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轮换,让几个儿子轮流去,或者是只让一个承担义务,其他几个通过支付钱财作为补偿,这样的话,事实上是把国家的义务合同化、货币化了,把劳动的义务变成了财政义务。在很多族谱中能看到这样的家族协定。
第二个办法就是分家,比如我看到泉州某一个家族族谱的记载是这样的:军户的父亲去世了,有两个儿子,那么他们如何承担兵役的义务?他们采取了分家的办法,即老二分得家产的绝大部分,老大分得小部分,但是老二家从此承担兵役的义务,而此事与老大家再无关系。然而,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老二家又有三个孩子,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财产补偿给服兵役的一方,那么还有什么办法来处理义务承袭?这时他们想到祠堂牌位——以在家族中的牌位作为回报,承诺给去服兵役的儿子及其后代,祭祖时牌位排在第一位,以此作为承担兵役义务的回报。而对于政府而言,它不管谁去,只管有没有人去。
此外,军户们也发现,其实没必要让自己家族的人去,完全可以雇人去做兵丁。我找到一份温州英桥王氏的族谱,是万历年间编的。这个王氏家族有一个父亲和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不想当兵,因此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和尚去,以给他买块田地作为报酬,让和尚去当兵,这块地则由双方轮流管理。族谱里还写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和尚从此由原来的陈姓改姓王,兵役义务由他的后代负责。但是和尚怎么也有后代?他可能是个假和尚吧,我们不得而知,非常有趣。
通过这些族谱故事,你可以看出,百姓发明了一些很复杂也很简单的策略来应对日常政治中的风险。作为军户,如果你的亲戚在外战死或失踪了,第二天就会有人来抓你去当兵,这是不可预测的。百姓通过上述三种办法将这个风险控制到了最小。

澎湃新闻:所以明代的卫所跟海上贸易已经有了密切关系?
宋怡明:是这样的,《明实录》也记录了许多类似的故事,很多海军从事海上贸易、国际贸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方国珍,方国珍在向朱元璋投降前已经是海上一霸,后来他的部下被编入明代国军,自然保留了一定的海上传统。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例子,沿海地区有一群人被称作蜑家或蜑民,意思是生活在船上的人。有大量的蜑家在洪武初期被编入海军,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海军的海上技术,另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那些不容易受控制的人。更重要的是,当时实行禁海政策,不允许民间造船,唯一能造船的地方就是卫所和军户。所以他们的竞争优势之一是对海上科技的垄断;还有一个更有意义的优势,这也是《明实录》的记载——海警队(海巡)都是他们的亲戚。从事非法海上贸易最危险的事情就是碰到海警队,但是如果你知道海警队某天在哪里巡逻,你就去别处贸易,跟没有关系的人比,当然有了优势。
澎湃新闻:这是更复杂的一种关系,用官方的制度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宋怡明:是的,蒋继实能这么顺利地从事海上贸易,主要是因为他是海军军官,他利用了他在海防领域的特权在商业领域套取利益。还有一点,他作为海军需要负责荡平倭寇,但他自己也是倭寇,我刚刚讲的故事里的行为都是倭寇的行为。明代沿海地区的研究让我们早已经认识到,很多倭寇不是日本人,而是本地人。但是我可以进一步说,不只是本地人,实际上负责海防的军队,也是倭寇的一部分。我也发现了不少案例,其中显示早期的华侨和早期去台湾的人,也是当时、当地的海军成员。
澎湃新闻:你认为从知识分子角度看中国和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不一样的,从百姓在军户制度下的生活来理解中国文化会更直接?
宋怡明:没错,我经常问学生为什么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视家族、亲戚关系,他们会说是因为孔子、儒家的关系。但是在古代大部分百姓是不识字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孔子。所以你不能单独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文化注重宗族关系。
有一次我来中国参加一个社科类的会议,学者们通过探讨中国哲学和孔孟等哲学家来试图阐释现在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但这就好比你想了解西方社会的内在逻辑,但我只给你讲圣经。如果你想了解我个人、我的行为和内心想法,你根本不能只用圣经来讨论说明。当然哲学文化有它的高度,圣经对我会有一些影响,但它不是一切。
所以我认为要真正理解某一个社会、某个文化的运作,还是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比如老百姓对他们的利益是怎么理解的?他们寻求一些什么?他们心里想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寻求了什么方法和资源去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
澎湃新闻:你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在收集族谱的过程中,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
宋怡明:我学术的老祖宗傅衣凌(1911—1988)说,历史研究不可以在图书馆做,要去跑田野。所以,我们需要去民间收集(民间)文献、族谱等,有时候你跑好几天才拿到一个族谱,有时候一天就能拿到好几个。
首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中国百姓很擅长占据理论高地,用非常漂亮的话来修饰他们的策略。在族谱上,往往都会写“我们都是一家人,家族繁盛绵延世代”等等,然后紧接着写上一份合同。从来不会有写“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所以现在想出一个解决方法”之类的。
还有的家族,会出现两份表述截然不同的族谱,比如其中一个说他们祖上是读书人,另一份族谱说祖上是渔客,我不在乎哪个真哪个假,我在乎的是他们讨论的家族迁徙史。后来到村子里,和一个老人聊天,老人说“文革”的时候祠堂被拆掉了,牌位砸断了后露出了字条,字条上写某个祖先其实是海盗,杀了人后逃到了这个地方。祖先是海盗不光彩嘛,就变成了读书人。但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家族的迁徙路径。
在田野调查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有一次,我下到一个非常偏僻的村子,那里没有什么招待所或者旅馆,村里的乡亲就安排我睡在戏台。结果到了清晨,我发现我身边围绕着大概有500匹马。原来当地有还愿的习俗,向城隍神许愿后要牵着一匹马来还愿。因为戏台有围墙,大家就都把马牵到这里,不会丢。
澎湃新闻:你担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四年多了,从你的角度看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变化?你如何看待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化?
宋怡明: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来中国,后来也在武汉教过书,也见证了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巨大成就。尤其中国近几年在科技、人文、经济上的进步,非常了不起。中国人又有着很强烈的乡土情结,我这次来中国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他是河南的,来上海十多年,而且以后也会继续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但他告诉我,他要花掉所有的积蓄在农村老家盖房子。中国农村问题又是另一个很大的话题,这会是我下一个十年研究的重点。
中美两国这几年关系的变化是我们也没有料到的,而且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就更不能只呆在图书馆做研究,大家都要尽力去想种种办法来处理好这个关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美国的学术界已经很有权威了,所以我和我的同事更有责任参与公共舆论,让美国的政客和民众更理解中国,这对两国关系非常重要。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