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读︱《穆斯林发现欧洲》:“发现”还是“相遇”
伯纳德·刘易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伊斯兰和中东研究学者,曾师承于东方学家马西农,具备深厚的东方学研究基础,对于伊斯兰教的律法和神学理论,以及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现实政治皆有着极深的造诣。刘易斯也被誉为中东研究最伟大的“圣人”、“战后关于伊斯兰和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等。《穆斯林发现欧洲:天下大国的视野转换》是刘易斯晚年的一部著作,其主题属于“东方学”的范畴,简单来说,“东方学”起源于两个世界宗教的相遇和碰撞,此后才开始拓展到更为辽阔的地域,因此伊斯兰研究在东方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刘易斯在书中所写:“由于二者的斗争由来已久,历经数个世纪乃至上千年,两者间的亲缘关系反而常遭忽略。当中有许多共通点,双方共有的希腊和犹太因素,以及在更为古老的中东文明中,都具有共同的根源。就希腊的哲学和科学,以及犹太教的预言和启示而言,两大文明都为他们增添了其他的异质因素:两者的信徒怀抱着坚定信仰,自视为神的终极真理的唯一拥有者,因为有着以各种方式向全人类传播这一真理的使命。”因此,两者就如同“异卵双生子”般难解难分,对二者互动交往的研究颇具意义。而本书关注的就是两个世界接触以及交流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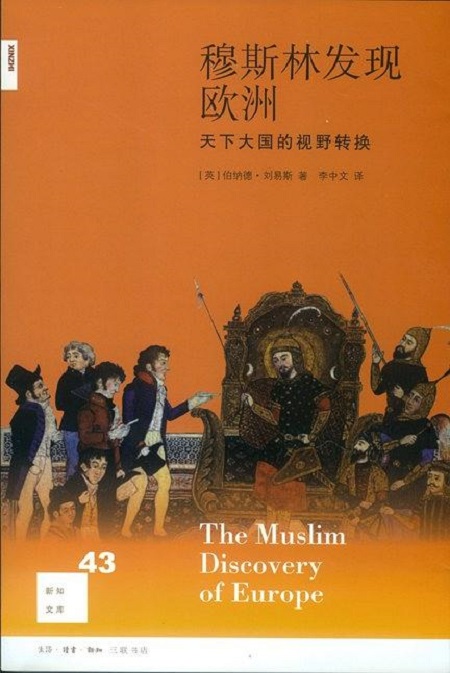
在近现代历史叙述之中,“发现”一词通常是用于描述欧洲人由15世纪开始对世界的探索。但本书“发现”一词所蕴含的意义则有所不同。这个所谓的“发现”,开始时间早,时间跨度长。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已不再是发现新世界的探险家,而是本身是受到伊斯兰世界发现与观察的“战争园地”的“蛮夷”。7世纪伊斯兰崛起之后侵入欧洲,两个世界由此产生了激烈对抗;接着,穆斯林的征伐活动逐渐停歇,并逐渐同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国家恢复了经贸往来;中古时期奥斯曼土耳其的大规模扩张之时,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徒总是恐惧并注意着穆斯林的威胁。此后,西欧社会内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开始对伊斯兰世界产生巨大冲击,时间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并由此开启了新的时代,此时的“发现”,可以说伊斯兰世界是在“被迫”和“自愿”中度过的。
在内容上,本书共由12个章节组成,总体上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欧交流与碰撞的总体回顾,对从两个世界的互动交流进行了梳理。包括阿拉伯穆斯林发起“圣战”、十字军东征、蒙古西征、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苏莱曼大帝围攻维也纳、勒班陀海战、法军占领埃及等历史事件。这一部分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以穆斯林的视角去解读了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件。例如,公元732年的普瓦提埃战役,查理·马特率领法兰克军队成功阻击阿拉伯军队,这场被欧洲人视为挽救西欧基督教世界命运的战役。但是,在穆斯林史家那里,对此却鲜有提及,不过是“圣战”中的一个小小挫折罢了。二是介绍了穆斯林的世界观:穆斯林将世界分为“和平之地”和“战争园地”两部分,前者即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后者则是除此之外的地方,对于民族、国家、种族等划分标准则不置可否;此外,在对待异教徒方面,相对于基督教世界对于异教徒的残酷迫害,伊斯兰教的处理办法颇具“民主”之风,对待居住于伊斯兰国家的异教徒,只要“纳贡”和“承认伊斯兰的宗主权”,就可以保留自己的信仰、文化、社群,由此衍生出了影响深远的“米勒特制”。为何伊斯兰世界会出现这种做法呢?通过对伊斯兰史料的发掘,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真主派遣过许多先知,预告人类将收到一部天启的经典,而穆罕默德是先知的封印,古兰经是最终、最完全的启示。先前所有重要的启示也都蕴含在其中。只要没有涵盖到的,都是由于先前降世经文的讹传和曲解等。”由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伊斯兰世界的做法。
第二部分介绍了交往中各类活动的发展,主要有翻译、语言文字和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活动。首先,最为重要的是文字和语言,穆斯林大多认为“要是学了异教徒的文字,就会沾染到所谓的不虔诚,甚至玷污的成分,除非是改宗者所带来的其他语言的知识,否则非伊斯兰教的语言和文字是乏人问津的。”即便是著名的“大规模翻译运动”,从事翻译工作的学者多为改宗者和异教徒。因此,“中间人”在双方的交流活动中应运而生,在奥斯曼帝国后期,出于外交的需要,更是出现“通译员”一职,此时“中间人”就作为一种职业和阶层固定下来,多由帝国境内的异教徒担任。在学者和官员之中,也只有极少数学习过西方的语言,大部分人,“在说到这些野蛮的、不重要的语言时,他们的口吻,显然就像后来欧洲探险家在提到非洲土著的方言时那样不屑”,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语言知识已然是一项重要的工具,而翻译机构则成为了进入军队和宫廷以获取荣华富贵的康庄大道”。其次,在学术研究层面,相对于欧洲学者对伊斯兰世界的深入了解,穆斯林学者对西方的认知大多“执著于信仰、教法,而成为谎言和童话”。直到奥斯曼帝国在对外战争节节败退之后,才开始注重对西欧事务的研究,了解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军事科学上的兴趣,另一方面是政治和军事情报上的需求,对于西欧各国的内部事务还是不加关心。
第三部分刘易斯则从一些较为具体的领域来进行叙述,从宗教、经济往来、科学技术、文化和社交等不同角度入手,生动具体的呈现出两个世界的交流与互动。在宗教上,穆斯林“以宗教做首要的认同和分别”,宗教就是自我认同和认同他人的核心价值。例如奥斯曼帝国海关通常规定了三种关税费率,但这三种费率不是取决于商品,而是决定于商人的信仰。在信仰上,由于早年对欧战争的不断胜利和深信伊斯兰教的“最终真理”地位,穆斯林普遍认为,基督教对伊斯兰不会构成宗教上的威胁,穆斯林史上首次感到其信仰受到西方的威胁,是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大革命所倡导的“唯俗论”威胁到了穆斯林的教法和社会的根基,但是一些穆斯林精英也开始在这种“哲学”中寻找西方成功的秘诀。经贸往来是双方交流与接触的重要媒介,早期的西欧商品并不能吸引穆斯林的眼球,甚至由于中东地区发达的转运贸易,使得伊斯兰在双方的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是到了18世纪,贸易优势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西欧。刘易斯在书中列举了一个有趣实例:“咖啡和糖,原先是由中东引进欧洲的,18世纪末,在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喝的咖啡里,咖啡和砂糖都是源自中美洲,并由法国和英国商人进口,现在只剩下开水是当地土产”。在商业交往的带动下,两个世界在艺术方面也有很多交流与互动。首先是绘画,尽管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但是早在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就已出现了詹蒂利·贝利尼为其所作的肖像画;17至18世纪初,奥斯曼上层贵族都乐于留下西洋画像;到了18世纪末,土耳其绘画基本上都受到西洋画法的影响,“只有到了20世纪初,土耳其的画家才一步步重新找到算得上是他们自己的表现方式”。(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其次是音乐,西方的音乐很难在伊斯兰世界得到认同,刘易斯这样描述:“在土耳其的西化运动中,音乐之落后于文学,也正如科学之落后于学术。因为音乐,也像科学一样,是西方文化的内部堡垒,那些向往着它的后来者必须设法打破这最后的秘密之一不可”。(同上)关于政治体制的认知上,在伊斯兰世界,“人是没有立法的权能的,真主是法律的唯一来源”,“人世的权威所能做的,只是加以诠释、调整和执行”,西方议会所拥有的立法、司法权力是难以理解、甚至荒谬的。随着帝国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家们开始深入考察西欧各国的立法和司法程序,愈发关注各国的宪政和议会制度,并将其当作“打开西方先进国家的密室”。在科技领域,曾屹立在世界科技之巅的伊斯兰世界,为何会逐渐走向封闭保守呢?刘易斯借助伊斯兰教经典,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在初期伊斯兰里头,穆斯林有所谓‘ijtihad’的原则,即独立判断的行使,穆斯林学者便得以在‘天经’未提供明确答案之处,解决神学和教法的疑难。在穆斯林的神学和法学中,有很多部分就是这么形成的,不过一旦问题得到解答,这个过程也就告一段落。根据传统的说法,这就是‘ijtihad’的大门关上了。穆斯林科学的发展中,确实也有类似的平行现象,造就了大规模的科学活动和发现,后来‘ijtihad’的大门关上时,伊斯兰学者认为自己已达到至善至美之境,穆斯林科学因此也就进入了一段漫长的、几乎只有编纂和重复的时期。”在社会交往的描绘中,由于两个世界缺乏足够的交流,存在着许多偏见和趣闻,例如,在穆斯林的印象中,西欧人总是不卫生的;对于法国人所谓的时尚,认为“欧洲人的复杂的穿着是可笑并浪费时间的”。诸如此类,都反映了接触与交流的匮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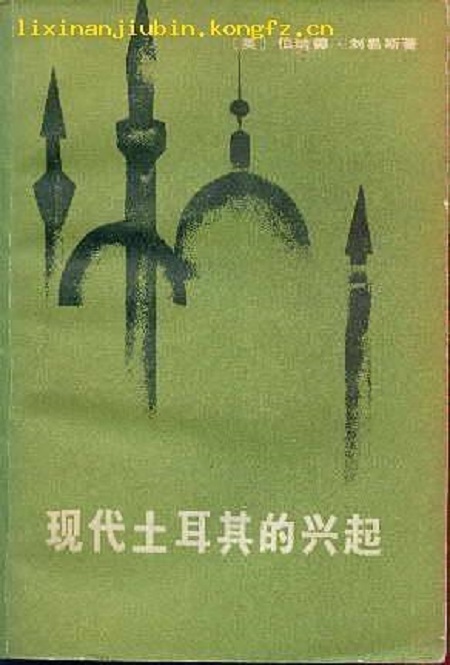
如同刘易斯的其他作品一样,此书参考了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英语、法语等在内的大量文献。因此,刘易斯没有仅仅根据“东方学”研究来呈现这一段交往史,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东西方两个角度考察这段千余年的东西方交往史。但是,也正因为这种细致入微的刻画,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忍俊不禁的细节。在二者交流的过程中,双方都对对方进行着夸张的描述和记载,真实的反映了两个世界在一定时期之内的相互认知。
针对刘易斯在书中的一些表述和看法,我有着一些不同的理解。
第一、根据前文所述,伊斯兰教在穆斯林认同的建构层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将伊斯兰教视作阻碍穆斯林获取知识的最主要障碍,这种说法本身恐怕站不住脚。圣训中极为著名的一章就是“求知,哪怕远在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去获取真理和知识,尤其是早期的远行游历,早在先知时代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值得倡导和鼓励的善举。在广袤的伊斯兰世界中艰难跋涉并寻求和编辑圣训,这种以“求知”为目的游历活动,被认为是崇高的虔信行为。因此,仅仅将伊斯兰教作为伊斯兰世界衰落的主要原因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第二、赛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表达了其对刘易斯及其著作的批评,认为刘易斯的著作加固了人们对伊斯兰世界封闭、落后的负面印象,而非尝试去消除,加深了世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欧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隔阂,而且刘易斯的结论本身,也是“文辞优美但缺少说服力的”(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事实上,我们在本书中就可以为赛义德的观点找到依据。帝国后期的处境已十分危险,无论在宗教上有多么不满和不舍,都不得不为现实让步和妥协。但是在刘易斯笔下的穆斯林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麻木不仁:“穆斯林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其中展现出来的种种进步因素无动于衷,看到的只有混乱和牺牲,并且仍然在基督教内部事务的范畴之中加以理解和审视。只要穆斯林自身生活在安稳的环境之中,那他们周遭的世界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故,都是同他们无关的。穆斯林只有在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时才会考虑同欧洲进行接触,谋求革新。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连危险都意识不到——正是法国、俄国用武力进驻穆斯林的心脏地带,才迫使他们对现存的实际威胁加以反思并寻求出路。”用外部刺激来解释实行变革的原因,这也许是种可行的思路(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拒绝了伊斯兰世界内部任何潜在的进步可能,若进步的动力全都来自于外部刺激的话,实际上无异于承认,穆斯林世界内部只是一潭死水,没有任何改变。北京大学吴冰冰教授曾在其著作《学术与偏见》中这样写道:“刘易斯将穆斯林的衰落归结到他们缺少好奇心和冷漠,而这种观点是强行将学术层面的研究探讨同现实政治之间建立联系,忽视了欧洲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变化,而只片面强调穆斯林好奇心的匮乏。归根结底,将结论引向伊斯兰世界可以被外界力量(西欧)所控制的结论。”而这也正是赛义德批判刘易斯和东方学的原因之一。
第三、如前文所述,在近代历史上,“发现”一次多用来指向西欧世界对新大陆、对世界的发现。而作为一部旨在描述两个文明互动与交流的作品,“相遇”可能比“发现”更为适合,但是刘易斯可能有意为之的使用“发现”一词,相比于西欧探险家“发现”美洲,细读本书之后,我们会发现伊斯兰世界对西欧真正意义上的“发现”,可以说并非是自愿、主动式的“发现”。事实上,我们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本书主要描述的是伊斯兰世界从顶峰跌落、开始去重新认知西欧基督教世界的艰辛之旅,从开始的漠视乃至蔑视西欧,到衰弱之后被迫主动的去关注西欧,并在军事、教育、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等方面重识西欧、学习西欧的过程。尽管刘易斯一再表明其目的是要显示在与西欧的交流中,二者一直存在着双向的对话。但不置可否的是,在近代以来只是伊斯兰世界对西欧的模仿。因而,这并不是一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式的“凯歌”,而是一曲文明从顶峰跌落到低谷的悲鸣,是一部跌落后不得不向曾经的手下败将学习的历史。此外,对于如今的西欧世界来说,伊斯兰不仅仅是作为“东方学”的一个研究对象,二者一直是朝夕相处的邻里,或是在边境积聚的难民。“阿拉伯之春”之后,伊斯兰世界的民众流离失所,而西欧已成为难民心中最为向往的“天堂”,难民问题也成为当今西欧各国面对的一大难题。因此,如今的西欧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所要面对的不再是相互“发现”,而是如何改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穆斯林发现欧洲:天下大国的视野转换》一书使我们了解到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千年以来的交流史,对今天发生在西欧和伊斯兰世界的种种乱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如果把这段历史和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史进行比照,或许会带来更多的启发和思考。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