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茅海建论清朝的宗藩关系③︱跨越千年的异文,迟滞百年的研究
故阙特勤之碑的故事
从现在已发现的缅甸表文、暹罗表文、苏禄咨复文来看,缅甸语、暹罗语、苏禄语原本与汉文译本相差极大,虽说李光涛教授提供了暹罗“自译汉表文”,但相关的研究尚未完全完成。而南掌表文被“翻译”的过程,很可能说明了异文发生的原因。所有这些异文的出现,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唐代的故阙特勤之碑。
我最近去蒙古国考察,意外地看到了故阙特勤之碑。它位于蒙古国中部哈拉和林附近,鄂尔浑河旧河道。我对唐代的历史是不太了解的,因为去了缅甸,对“骠国”的历史记载感兴趣,因此也对这个碑发生了兴趣。我们知道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碑(Rosetta Stone),是该馆的镇馆之宝,制作于公元前196年,上面有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古希腊文,意思完全相同。由此,古文字学家可以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故阙特勤之碑制作于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从外形来看,就是唐的风格。西面是汉文,南、东、北面是突厥文,但两种文字表达的是不同的意思。
唐代文献记录了突厥要求唐朝帮助建庙立碑之事,说明了这个碑是可靠的。1889年,俄国考古学家雅德林采夫(N. M. Yadrintsev)发现了这个碑,但还不能解读。这位俄国考古学家猜测称,如果一面是汉字的话,将是解读另一种文字的钥匙。他想到的,大约是罗塞塔碑。该碑突厥文的解读开始于1893年,当然汉文字的解读似乎更早一些。此后,突厥碑文的解读与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之点。

阙特勤(公元684或685-731或732年),突厥毗伽可汗(公元?-734年)的弟弟,也是毗伽可汗最重要的助手。从唐代文献来看,唐朝与东突厥交战,东突厥虽占有一时的军事优势,但惧于唐朝的国力,主动向唐朝称臣,结为父子关系。吐蕃曾欲联合突厥攻唐,被毗伽可汗、阙特勤所拒,两人被认为是“亲唐派”。阙特勤死后,毗伽可汗十分伤心,要求唐朝派工匠为其立庙建碑。故阙特勤之碑汉文由唐玄宗李隆基所撰,对“亲唐”的阙特勤十分赞赏,碑文中有动人的句子:
……且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犹朕之子也。父子之义,既在敦崇,兄弟之亲,得无连类,俱为子爱,再感深情。是用故制作丰碑,发挥遐檄,使千古之下,休光日新。词曰:沙塞之国,丁零之乡,雄武郁起,于尔先王,尔君克长,载赫殊方,尔道克顺,谋亲我唐,孰谓若人,网保延长,高碑山立,垂裕无疆。
其中最重要的句子是“尔道克顺,谋亲我唐”。有意思的是,毗伽可汗自己也写了碑文,并让唐代工匠把他的碑文刻在同一座碑上。从毗伽可汗所撰文字来看,他和阙特勤都不是什么“亲唐”派,而是对唐朝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住在这里,我同唐人建立了关系。他们慷慨地给了〔我们〕这么多金、银、粮食、丝绸。唐人的话语甜蜜,宝物华丽(原文:柔软)。他们用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宝物诱惑,使得远处的人民靠近〔他们〕,当住近了以后,他们就心怀恶意,他们不让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为。一人有错,连其族人、人民、后辈都不饶恕。由于受到他们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宝物的诱惑。突厥人民,你们死了许多人。突厥人民,当你们一部分不仅要右面(南面)住在总材(Chughay)山(阴山),并要住在平原时,于是恶人就这样教唆部分突厥人民道:“凡住远处的给坏的礼物,凡住近处的给好的礼物。”他们就这样教唆了。无知的人听信了那些话,走近了〔他们〕,于是你们死了许多人。如去那个地方,突厥人民你们就将死亡;如你们住在于都斤山地方,〔从这里〕派去商队,那就没有忧虑。如住在于都斤山,你们将永保国家。
由于其诸官和人民的不忠,由于唐人的奸诈和欺骗,由于他们的引诱,由于他们使兄弟相仇,由于他们使官民不和,突厥人民丧失了成为国家的国家,失去了成为可汗的可汗,高贵的男儿成为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姑娘成了女婢。突厥诸官舍弃了突厥称号,亲唐朝的诸官采用唐朝称号,臣属于唐朝皇帝,〔并为他们〕出力五十年,前面,在日出之方,一直打到莫离可汗那里,在西方,一直打到铁门〔关〕,把其国家和法制交给了唐朝皇帝。突厥所有普通的人民这样说道:“我曾是有国家的人民,现在我的国家在哪里?我在为谁获取国家?”——他们说。“我曾是有可汗的人民,〔现在〕我的可汗在哪里?我为哪家可汗出力?”——他们说。这样说着,他们就成为唐朝皇帝的敌人。成为敌人后,〔但〕他们未能自立,重又内属了。〔唐朝皇帝〕并不考虑〔突厥人民〕曾出了这样多的力,他们说:“我要灭掉突厥人民,并使其断绝后代。”他们〔突厥〕在灭亡。(耿世民译)
唐玄宗李隆基肯定不知道毗伽可汗的内心想法,而在鄂尔浑河刻石的唐代工匠也不知道他们所刻的内容。我这么说,当然有着历史的证据,就当毗伽可汗为阙特勤建庙立碑后不久,被其大臣毒死。唐太宗李隆基得此消息,于公元735年(开元二十三年)再派工匠到鄂尔浑河畔,为毗伽可汗建庙立碑,于是又有了毗伽可汗碑。这也是世界著名的石碑。两座庙当然早已不存在了,两座碑却经千余年而留存至今,相距约一公里。

突厥古代历史资料是很少的,最主要的文献应该是中文的。在蒙古鄂尔浑河畔发现的古突厥文石碑,当然引起了土耳其的关注。上世纪末,土耳其考古学家也来到这里,并为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援建了一座博物馆,修建了专门的公路。据说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土耳其馆就有故阙特勤之碑的复制品。这些土耳其历史学家可能汉语不太好,不太知道这座碑的全部历史;或者说欺负中国人,反正你也看不懂古突厥文。
从唐玄宗李隆基到清世宗胤禛(雍正皇帝)、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时间上正好是一千年。他们都是伟大的君主,盛世的创造者。从故阙特勤之碑之异文到南掌表文之翻译,再到郑昭的表文之异文,是否又有着相似性?如果有相似性,这连接一千多年的这些伟大君主的思想底蕴又是什么?左右这些君王思想的儒家天下学说又起了什么作用?

使用汉文字的朝鲜、越南、琉球三国宗藩关系的解读方式
由此再来看龚自珍的《主客司述略》和嘉庆朝《大清会典》,谈到了朝鲜、越南、南掌、缅甸、苏禄、暹罗、荷兰、琉球、博尔都嘉利亚、意达利亚、博尔都噶尔、英吉利,一共是十二个国名,十一个国家。按照清朝的主观观念,清朝与这十一个国家建立了宗藩关系。我以上的演讲,去掉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葡萄牙、罗马教廷和英国,剩下了七个亚洲国家。我以上的演讲,引用了白诗薇、庄吉发、增田えりか、三王昌代、李坤睿等人的研究论文,说明了缅甸、暹罗的宗藩关系不太像,苏禄、南掌的宗藩关系可能不太像;剩下的只有朝鲜、越南、琉球。也就是说,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能真正确定宗藩关系的,只是使用汉文字的朝鲜、越南、琉球三个国家。而这三个国家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朝鲜王国是宗藩关系的“模范国”。现在的人谈清朝的宗藩关系,往往是清朝与朝鲜王国宗藩关系的扩大化,用朝鲜的事例来说明其它国家。这是错误的。曾经有一位政治学教授问我,什么是宗藩关系?让我下个定义,而我却无法下一个统一的定义——十一国是十一种情况,亚洲七国是七种情况,差异非常之大,决不可以混为一谈。
使用汉文字的朝鲜、越南、琉球,同时也尊崇儒家学说。当然这三个国家儒学程度是有差别的,朝鲜最高,越南次之,琉球更次之。朝鲜和越南皆开科取士,考的就是儒学。琉球派人去北京国子监入学,即琉球学馆。宗藩关系是与儒学相联系的。藩属国朝贡、册封等事务由礼部主客清吏司来管理,也与儒学的教义有关。
那么,这三个使用汉文字的国家,宗藩关系又是怎么样的?
先来看越南。我曾经去过越南阮朝的都城顺化,看到了铸九鼎、看到了王城的城门从外面看是三个从里面看是五个,外三内五,即外王内帝。阮朝的君主对清朝自称越南国王,而在国内自称为皇帝。在阮朝的官方文献《大南实录》中,阮朝君主对清朝皇帝的态度不是那么毕恭毕敬的,而是经常要算计算计宗主国的。

再来看琉球。琉球王国的历史文献保存下来的是不多的,其中最重要的官方文献《历代宝案》,记录了1424至1867年的外交文件,其保存至今也是一个奇迹,最好的抄本现藏于台湾大学图书馆。从《历代宝案》来看,琉球国王对清朝皇帝的态度与琉球表文的言辞还是有差别的,更何况琉球王国与日本萨摩藩又有着特殊关系。
作为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朝鲜,也最重视历史。其历史文献最多,保留的也比较好。满洲人入主中原后,朝鲜王国的儒学者一度认为,他们才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甲午战争后,朝鲜王国改国号,其中一个提议便是“大华”。在这个宗藩关系的模范国中,从表文到官方的《实录》,都充满了“事大字小”的儒学精神。那么,清朝与朝鲜王国宗藩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由此而定性了吗?我觉得还不可以。朝鲜王国重儒学、重历史,他们的朝贡使节还留下了许多记录,即号称多达五百多部的《燕行录》,现在已经选印了三十多部。他们的这类记录似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两国关系的本质。这些前来朝贡的使节,私下里对宗主国是不太尊重的,经常说坏话,批评大于歌颂,甚至不尊重清朝的皇帝,尽管他们的国王是清朝的皇帝册封的。
如果要真正理解并说明清朝与朝鲜、越南、琉球三国的宗藩关系,还需要多看三国本身的文献,了解三国内部的情况,了解三国君主与宫廷对清朝的看法,了解三国贡使本身的观感,并了解儒学在三国的意义,绝不能只看清朝的官方文献。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到三地去学习、生活一个时期,学习他们的语言与历史,了解其情感,尽管其官方文献当时使用汉文字。只有从双方的角度来观察、来解读,才能得出正确结论。王元崇教授批评道:“有些人抄着《大清会典》写历史!”《大清会典》自然要详细阅看,但光看《会典》无法写出真实的历史。我在前面讲过,这只是清朝官方的主观看法。

现有的研究状况——学习语言的重要性
根据清朝的官方记录:苏禄最后派使入贡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南掌最后派使入贡为咸丰三年(1853),因贡道受阻,未入京;暹罗最后派使入贡亦为咸丰三年(1853);缅甸最后派出贡使到京时为光绪元年(1875);琉球在日本并吞之前,于光绪三年(1877)派出求救使;越南最后派出贡使到京时为光绪七年(1881);朝鲜最后派出贡使为光绪二十年(1894)。也就是说,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1895),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管辖的封贡体系完全被打破,除了前面提到的、作为特例的喜马拉雅山地国家外,清朝已经没有藩属国了。
《大清会典》最后一次修订,始于光绪十二年(1886),成书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然在光绪《大清会典》中,仍然沿续了过去的说法:
主客清吏司,郎中满洲一人、蒙古一人、汉一人;员外郎宗室一人、满洲一人;主事满洲一人,汉一人。掌四裔职贡封赉之事……凡四裔朝贡之国,曰朝鲜、曰琉球、曰越南、曰南掌、曰暹罗、曰苏禄、曰缅甸。余国则通互市焉。凡入贡各定其期,与其道,使各辨其数。凡贡使至则以闻,乃进其表奏,达其贡物,叙其朝仪,给其例赏。贡使往来皆护……
朝贡国仍为七个,只是不再有“荷兰”与“西洋诸国”。直至此时,礼部主客清吏司的官员数额未变,职能未变,尽管七国的贡使已不再来。光绪《大清会典》如此叙事,也说明清朝此时的尴尬。修订《会典》者都是清朝的官员,一方面他们想维系清朝原来的封贡体制,另一方面他们所占有的资料、所掌握的语言以及他们的思想观念,都不支持他们能够得出新的结论来。总理衙门虽已成立多年,但其官员多为科举出身,疏于近代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知识,大多不懂外国语,更没有缅甸语、暹罗语、老挝语、苏禄语的知识。京师大学堂刚刚开办,对于各国的研究,尤其是亚洲七国的研究,尚未开始。
清朝灭亡后,1914年(民国三年),北洋政府成立清史馆,编纂《清史》,参加者多为前清的遗老。他们的旧学功力极其深厚,对清朝的掌故、典章十分熟谙,但毕竟缺少相应的近代政治学、近代国际关系和外国语的知识。《清史》的编纂是打破旧体例的,新设了《邦交志》,共八卷,分别叙述了清朝与俄、英、法、美、德、日本以及瑞典挪威、丹墨(麦)、和(荷)兰、日斯巴尼亚(西班牙)、比利时、义(意)大利、奥斯马加(奥地利)、秘鲁、巴西、葡萄牙、墨西哥、刚果等国的交往;但仍有传统的《属国传》,共四卷,前三卷分别是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南掌、苏禄七国,内容仍以清朝官方史料为主。《清史》的编纂当时未能完成,今以《清史稿》存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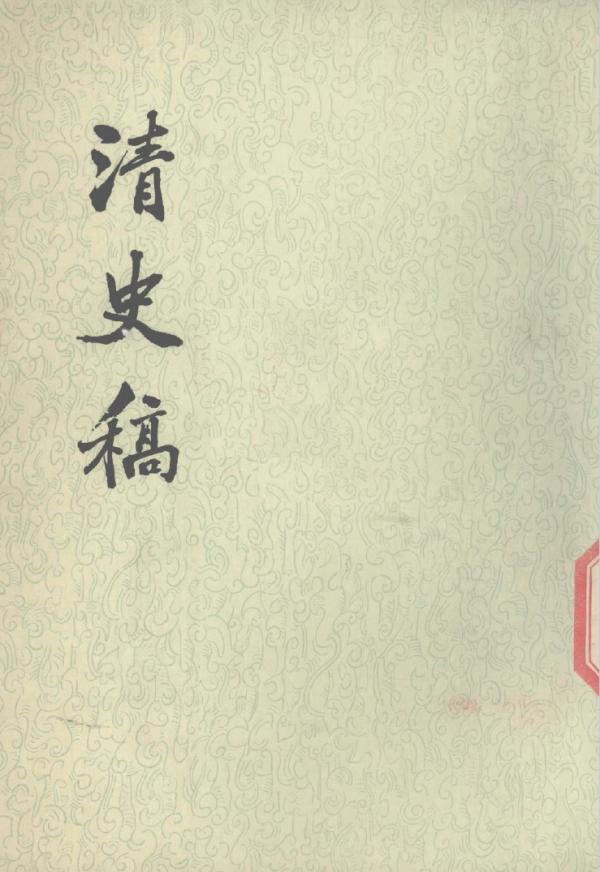
北洋政府清史馆编纂《清史》时,中国已经有了多所大学,但外交史、东亚史的研究尚无大的进展。此后,清华大学历史系蒋廷黻教授以筚路蓝缕之精神,以启“山林”——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开展起来了,然关注点仍是欧美日本等大国。也有一些学者关注于东南亚史,但所使用的仍是中文材料。战争与革命引发了重大社会动荡,也阻碍了研究的进展。此后的学术史,也为大家所熟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研究者忌言“宗藩”,似乎是一种不好的名词。由于长期缺乏深入的研究,中国学术界曾一度对“清朝的宗藩关系”变得十分生疏,有些人甚至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相混淆。
我在前面一再强调,一项好的研究必须看到看懂双方的材料,了解双方的企图。这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语言能力,尤其是多种语言,然后是在地生活经验,才能得到真正的进展,得出中肯的结论。以龚自珍和嘉庆《大清会典》所提到的十一国而言,以目前中国的学术研究状况而言——清朝与英国、葡萄牙、罗马教廷的关系,我们是有所了解;而清朝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关系,我们基本不了解;清朝与朝鲜、琉球的关系,我们有所了解;清朝与越南的关系,我们了解的不多;清朝与缅甸、暹罗的关系,我们不怎么了解;清朝与苏禄、南掌的关系,我们基本不了解。也就是说,自1895年甲午战后清朝封贡体系被打破,至今已经一百二十四年了,中国学术界还说不清楚“清朝的宗藩关系”。

我们作为宗主国说不清楚,藩属国能说清楚吗?
英国、葡萄牙、罗马教廷、荷属东印度公司可以排除在外。作为朝鲜王国,韩国学术界大约还比较清楚,北朝鲜恐怕不是很清楚;作为琉球王国,日本学术界大约还比较清楚;作为苏禄王国,菲律宾学术界大约不很清楚;作为越南王国,越南学术界恐怕不清楚;作为南掌王国,老挝学术界恐怕不清楚;作为缅甸王国,缅甸学术界大约不太清楚;作为暹罗王国,泰国学术界大约不很清楚。也就是说,由于史料的保存情况,由于书面语言的变换,由于国家形态的变化,由于各国的学术研究水准差异,当年的藩属国也说不太清楚了。我在这里还需要强调文化背景的因素。日本吞并琉球王国时,曾向清朝提出了两分法,即以宫古海峡为界,以北归日本,以南归清朝。清朝提出了三分法,宫古海峡以南归中国,奄美大岛等归日本,琉球王国保留冲绳本岛及附近各小岛。从表面上看,这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但清朝的目的是让琉球王国继续承在,宗庙有所承祀,即儒学“兴灭国”之义。李鸿章甚至还考虑过让琉球王国在宫古海峡以南的宫古岛、石垣岛复国,但琉球官员再三陈述两岛太贫瘠,无法生存。如果不从儒学精神上去理解清朝的意图,也不能说明真相。

宗主国说不太清楚,藩属国也说不太清楚,谁能说得更清楚呢?
我们特别要注意日本学术界。以目前的研究水平来看,清朝与朝鲜王国的关系,京都府立大学冈本隆司教授的研究最深刻(《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现在美国特拉华大学王元崇教授是后起之秀(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shu-Korean Relation 1616-1911),他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清朝与暹罗王国的关系、清朝与苏禄王国的关系,东京大学的增田えりか、三王昌代完成了博士论文。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今天也在会场,他是外交史的专家,他的许多学生今天也在场。法国学术界的情况也值得注意,前面提到的白诗薇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的东南亚研究是相当出色的。他们都是我们学术上的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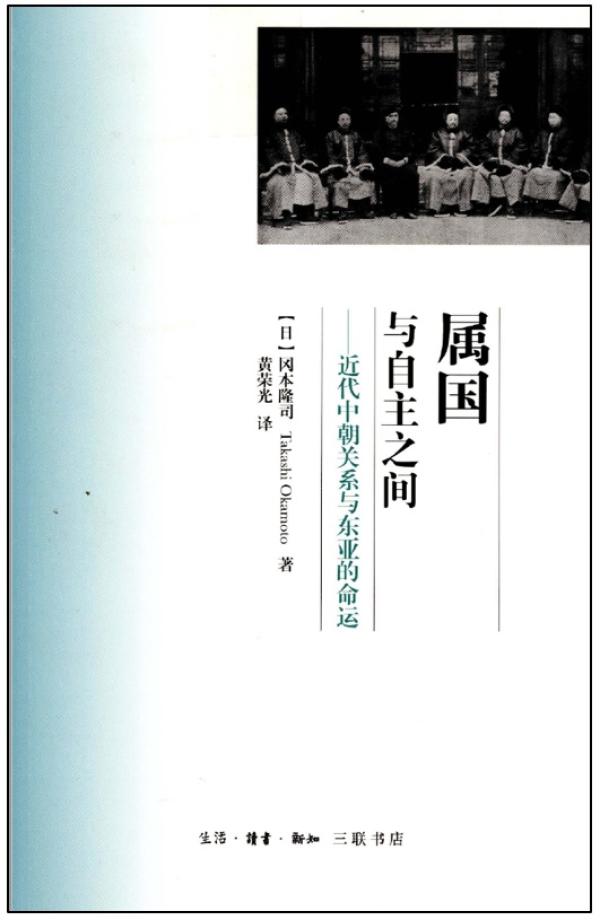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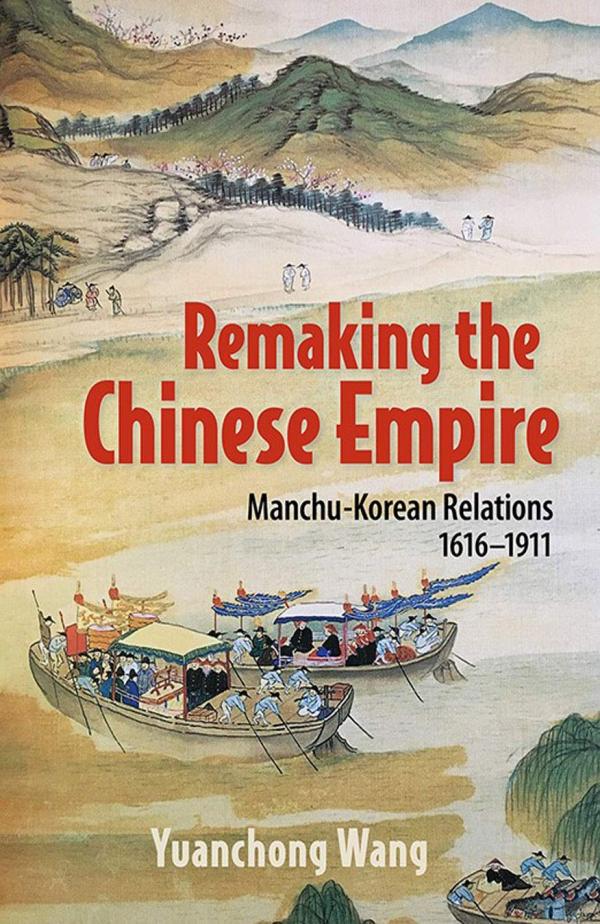
王元崇著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shu-Korean Relation 1616-1911
我今天到上海交通大学“海洋视野下的东亚国际关系暑期班”,来讲我自己并不研究的“清朝的宗藩关系”,目的就是鼓动优秀的年轻人加入到这项研究中来。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它是一个文化大国吗?是一个研究大国吗?我们能不能在研究方面超过日本、法国或其他国家?也就在这个月(2019年7月)初,我到蒙古国访问,与蒙古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奥云吉日嘎拉进行交流。她研究清朝喀尔喀蒙古史,在日本东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于我的学生刚学蒙古语,还不能翻译,我请另一个懂日本语的学生进行翻译,结果是日本语成了中国人与蒙古国人之间交流的中介。奥云说,她的老师冈洋树教授懂汉文、蒙文(老蒙文与新蒙文)、满文、俄文和英文……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年轻学者若要做出出色的研究,让国际学术界知道他们的水准,第一项是学习语言,第二项是学习语言,第三项还是学习语言……
最后我再来讲一个故事。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首位历史学教习屠寄(1856-1921),清朝的进士,也是研究蒙元史的著名学者,著有《蒙兀儿史记》。1915年(民国四年)春,屠寄在常州家中写信给在上海的赵凤昌:
……拙著告竣,尚未有期,西人文学家必兼希腊、罗马及近代法、德诸文,方足遍观群籍,而折中一心。寄不解西文,至为阙憾。儿辈仅通英文,虽稍足相助,然蒙兀史之外籍,法、德、俄、阿剌比(阿拉伯)、突儿厥文居多。近代记蒙兀事,西书以朵逊书最完善,往年张菊生同年幸为我购得诸荷兰。其书法文,成于道光间,凡四巨册。惜儿辈中无通法文者。若倩人译,须四千元(每千字二元计),无此闲钱。拟俟三儿孝实毕业后,补习法文二年后,为我译之。已与预约矣。(《赵凤昌藏札》,第七册)
“张菊生”,张元济,也是清朝的进士,总理衙门章京,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和主持人。朵逊,即多桑(Abraham Constantin Mouradgea d’Ohsson,1779-1851),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人,曾任瑞典驻法国等国公使,懂多种欧洲语言及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文,并通过德文、法文、俄文的翻译作品接触中国文献。多桑的《蒙古史》是一部世界级的史学名著,价值极大。屠寄的三儿子屠孝实,此时在日本留学,要等他留学回来,再学习法语,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是边写边刻的,到他死的时候都没有写完。该书一百六十卷,其中二十卷只有存目。他的三儿子屠孝实确实提供了帮助,做了一些翻译工作,但不是法语。多桑《蒙古史》的部分内容是屠寄请他的朋友周秉清帮助翻译的,但译者非为蒙元史的专家,错误颇多,影响了屠寄著作的准确性。在屠寄死后十五年,1936年,多桑的著作由冯承钧教授翻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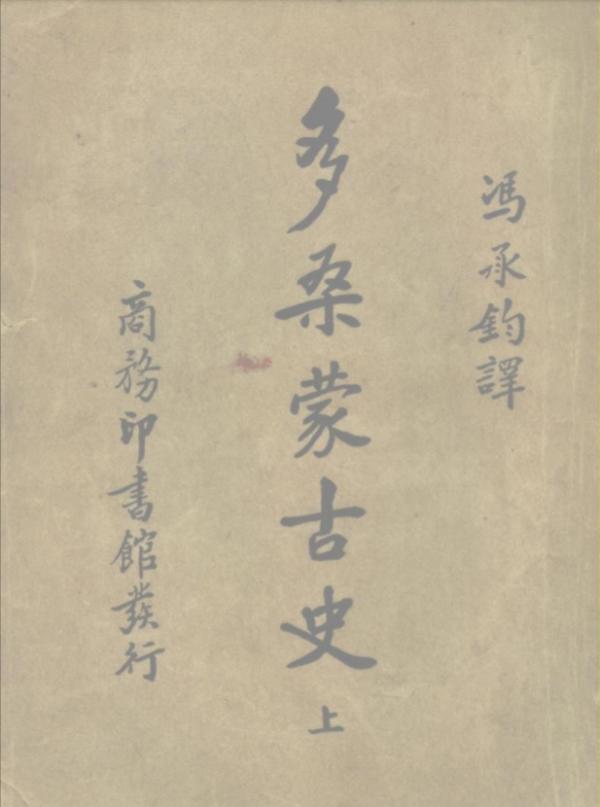
然而,若从国际学术界的标准来看,如果没有多种语言的阅读能力,仅仅靠着冯承钧的翻译,就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最优秀的研究成果来吗?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