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韦森评《观念与制度》︱经济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缺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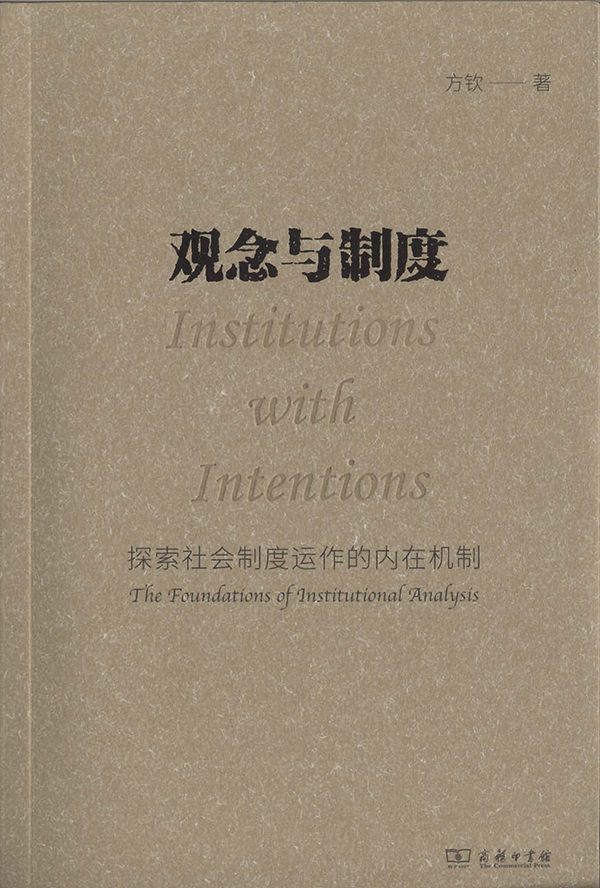
由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这本《观念与制度》,是复旦经济学院青年学者方钦博士经过十余年艰苦思考而反复修订出来的一本学术专著,原改自他十年前在复旦大学师从张军教授所作的博士论文。我虽然不是方钦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但是从他2002年来复旦大学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开始,我就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学习、研究和思想的成长,对他的博士论文的整体思路和理论框架,乃至每一章的写作都很熟悉。在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方钦留校在复旦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经济思想史课程。在他留校执教的这十多年中,我对方钦的学术研究和思想进展也知根知底。近两年,方钦又和我一起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为研究生合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课程。因此,他现在出版第一本学术专著,邀请我这个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老兵”作序,对我们二人来说都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事情。
自二十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托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约翰·R.康芒斯(John R. Commons)注重研究人类社会中的“social institutions”开始,制度经济学在近百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慢慢发展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尤其是自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教授的两篇经典文章《企业的性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发表以及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教授的数本专著出版以来,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亦常常被称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经济学的这一研究领域中,已经有数位经济学家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英文、西方其他文字和中文中,近些年来都有许多制度经济学的专著乃至教科书出版。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如制度变迁的最终原因和变迁的路径上,仍有不同看法。甚至在什么是“institutions”的理解上也实际上仍存在许多争议。譬如,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的文著中,他一直是从“生产的建制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的角度所理解的“institution”的。而在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教授的诸多著作中,他始终是把“institutions”视作为社会中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约束,而正式的规则包括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规则和契约,非正式的约束他认为则包括惯例、行为规范、行动准则乃至道德伦理规范,等等。在哈耶克的许多著作中,他尽量不用“institutions”一词,而把他后期的经济与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确定作为“社会秩序”(social orders)。值得注意的是,一生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研究不同社会的“institutions”和“institutional changes”的诺思教授,在晚年也和他的合作者约翰·R. 瓦利斯(John J. Wallis)和巴里·R. 温格斯特(Barry R. Weingast)等学者一起重新使用了“社会秩序”的概念,提出在人类历史上曾存在过(着)三种社会秩序:“原始社会秩序”(the primitive social order)“受限进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s)“开放进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s)。他们还认为,理解人类社会在近现代进步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弄清从“受限进入秩序”向“开放进入秩序”的转型(见North, Wallis & Weingast,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自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历史以来,不同国家和社会总是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制度也不断发生演化和变迁。在现代和当代社会,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有共同的地方,也实际上各有差异。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是如何形成、维系、演化和变迁的?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最终动因是什么?如果问这种元问题,那最终的回答应该是这要取决于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的大多数人信什么,人们的观念和认识是什么。因为人是有理性、有自由意志和能进行个人和集体选择的一种动物,人类要生活、生存、交往和延存下去,就要组织成社会和国家,就要通过结合成一定的社会与经济组织,并制定和遵从一定社会规则来进行生产、生活、交往和交易。生活在不同疆域上的人类群体要组织成国家以及国家要采取什么样的制度,那就要取决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们相信什么、认为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于是,在人类社会漫长历史演变中,在不同的疆域上形成了不同的族群和国家,也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中慢慢形成了这些观念,也同时演化生成了各国的不同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在世界各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整个西方思想界开始讨论一些人类当如何生活和生存的问题,一些思想家也创生出了人类当如何生活、如何生活会更幸福的理论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慢慢被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于是就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制度变迁,在西方各国慢慢建立起了现代的政治、法律和市场经济制度。当然,作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副产品,在西方思想界也曾出现一些思想家设想了如何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非同于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1689-1755)等启蒙思想家的一套理念或言“ideology”,并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和世界其他各国进行过各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实验。这包括1871年在法国短暂出现的巴黎公社,以及自二十世纪初开始从俄罗斯到苏联,从东欧和中国在1978年前所进行的世界范围的计划经济国家模式实验。在经过几十年的社会经济体制实验后,发生了苏联的转制和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转制。如果大范围的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在生活在不同疆域上的人们的共同认识和信念,尤其是夺取和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和集团所提出的一套信念,决定了一定时期的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不同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其制度的变迁,从根本上来看取决于一定时期为大多数人尤其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所信奉和制造出的一些理论信念。当社会的大多数的信念发生了变化,那个社会的制度变革也就会到来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通往奴役之路》这部二十世纪的世界名著一开始,哈耶克就曾指出:“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见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ed. By Bruce Caldwell, Chicago: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4/2007, p. 66)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撰写的《法、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也曾说过,“每一种社会秩序(social order)都建立在一种ideology之上”(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Every social order rests on an ideology”,见F.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6, p. 54)。哈耶克的这一见解无疑是对的。正是在一个疆域上的人群在其社会的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国家如何管理、经济如何运行、人们如何生活和生存,乃至发生社会冲突后该用什么样的社会规则和约束来保证该社会运行的一套“理念”“观念”和“信念”——这套相互关联着的理念在十九世纪后被一个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安托万·德斯蒂·德·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1754-1836)统称为“ideology”(这个英文词在中国大陆之前通常被翻译为“意识形态”,哈耶克的关门弟子林毓生先生则主张用“意蒂牢结”来对译这个概念),人们才按照某一套“ideology”来构建了由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所构成的社会秩序(在近些年的著作中我称它为“社会制序”)。尤其是自中世纪开始,西方各国逐渐形成了一套人类社会当如何生活和生存一套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信念,才发生了世界各国的现代社会制序转型。这正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尤其是美国这个现代最发达的国家,最初也是由有一些有着共同信念和信仰的清教徒在一块人口稀少的印第安人的居住地上依照他们的共同理念而建构出来一个现代国家,建立起由民选总统、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联邦制的政治制度,以及依据英国普通法为主体并吸收欧洲大陆制定法而构建起来的法律制度,并采取了保护个人权利、私有产权、自由企业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制度。甚至连二十世纪初从俄罗斯十月革命后所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几十亿人口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验,不也是是按一整套ideology而构建出来一种社会制序实验?今天回过头来看,前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或斯大林模式、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匈牙利模式以及东欧各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与社会体制,无疑也是按照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铁托等革命领袖人物所创生和演变出来的一套观念和信念体系而构建出来的一整套的政治、经济乃至法律的形态有同也有异的社会制序。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人类社会和世界各国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存在的社会制序,主要是根据一定的理念而建构出来。当然,在人类历史的演变史上,一些按一些意识形态创造型的思想家和统治者个人的理念所构建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在实际建构时可能会走样,在现实的制度变迁中一些错误的理念所导致的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实行而不断修正和变异,即使能按照一定的社会理想模式将其付诸实施并建构出来一定的制度,但因为这些政治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制度并不符合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而导致经济衰败、官员腐败、社会衰朽而最后整个社会制序的解体。这就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开始非常强大的帝国或国家灭亡或解体。在人类历史上,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元帝国的最后分裂和解体,都是些例子。

不但在整个社会体制上人们的信念尤其是夺取并掌握政权的统治者和“ideology”的创造者的信念会影响乃至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法律制度的整体式样,甚至在一个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一些社会的、宗教组织的乃至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的一些信念,也会直接影响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演变,最后也会决定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路径。方钦在这部著作第三章,就探讨了远古社会中的礼物交换与产权的关系,发现“产权观念就是伴随着原始宗教的思维模式而起源的。正是由于物品上携带着人的本质的一部分——这是比任何世俗力量都更为强大的超自然力量,产生了对于所有权观念的朴素理解”。方钦还发现,法国学者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曾认为,“私产的观念出自宗教本身”,土地是以宗教的名义而成为了家庭的私产,进而“大多数远古社会所有权的建立,都是由于宗教的原因”。在第四章,方钦则探讨了传统中国社会中产权问题。由于自西周开始在华夏社会中就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传统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的私有制。侯外庐先生在1954就提出了一种“王有制”的观点,认为“君王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后来,王家范先生则认为,过去我国史学界所认识到的那种传统社会的“私产”现象,实际上只是“私人占有”,因为在皇权之下,没有任何个人——豪强地主或自耕农——能够防止权力对权利的掠夺。缺乏制度保障的“私产”不能称为“私有制”,其实质仍然是“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程念祺在一些著作中也持相似的观点。实际上,在1987年发表在《东岳论丛》上一篇文章中,我当时也提出过:“在两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中国就曾出现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有经济’及其与之相适应的财产归属观念,在西周之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屡屡出现社会的大动乱和王朝更替,经济政治制度也发生了一定的演变,但总的来看,王朝官僚政治机器一直对经济过程有着超强的一体化的控制力量。以至近代工业在中国萌生出现时,其主体形式也基本上是官办和官商合办经济。民国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更主要以官僚资本占主导地位并为其基本特征。因此,除了从理论上说我们今天的国有是劳动人民的公有从而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皇亲国戚、官僚地主的私有有着本质区别外,仅就形式而论,‘国有’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从这一点上来看,建国后我国之所以能从国外移植来一套高度集权的统制经济运行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相适应的国有制这种虚所有制的潜构架,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中都有它的遗传模板。”(见李维森,《“硬化”企业的财产关系是建立完备的市场机制的先决条件》,《东岳论丛》1987年,第1期,45页)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方钦则探讨了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中世纪后期到近代在西方国家中观念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回顾了从中世纪罗马教廷反对和禁止高利贷到十三世纪之后近代商业活动从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意大利城市国家开始兴起这一段时间里的观念史和制度史的变迁过程,并随后在第六章讨论了韦伯命题,即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念基础之间的关系。第七章及其附录则讨论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文化观念尤其是宗教与制度的问题。虽然这些探讨从很大程度上还是思想史的回顾和分析,但却得出“当宗教表达了社会中个人普遍遵循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共同的直觉上的伦理要求的时候,宗教与制度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必然的同构性:每一种社会制度,都需要有一种因与其意见一致而相互结合的宗教信仰。因此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宗教,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见本书《附录二》)。这一判断有点过强。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和认识不同的“宗教”,以及在不同社会的历史时期中某种宗教的地位及其为民众所信仰的范围和程度,还取决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某种宗教为国家的统治者所接受的程度。但整体而论,不理解不同社会文明中的“主流”或言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就很难能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种种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这确实是有道理的。
研究观念与制度的关系,不但在研究大范围的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上是不可或缺的,在具体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中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且不可或缺的一环。研究宗教信仰与不同社会和文化中制度实存之间的关系,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方钦的这部《观念与制度》,正是朝着这一方向所做的初步理论努力。就全世界范围来看,这种研究到目前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尽管哈耶克、诺思、马科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以及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等等经济和社会思想家在他们的一些著作中在某些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其中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自由的构成》(1960)和《致命的自负》(1988),诺思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2005)、诺思、瓦利斯和温加斯特的《暴力与社会秩序》(2013)、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1915)、《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1917)、《古犹太教》(1919),以及桑巴特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1896)、《现代资本主义》(1902)、《犹太人与经济生活》(1911)、《资本主义》(1930)和《新社会哲学》(1934),等等。当然,这里也毋庸讳言,方钦的这本《观念与制度》,还没有像当代思想史上的一些大家那样提出一个整全的理论框架,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部著作还像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有些章节还是以一些理论思考的片段形式发表的。尽管如此,这部学术专著的每一章都包含着作者这些年的艰苦思考,无疑已经提出了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洞见。尤其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思想史的文献回顾和梳理上,这本专著给出了诸多之前著作所没有给出的理论发现。因此,我相信,这本《观念与制度》定能为社会制度的经济与社会理论分析做出它自己的“边际”理论贡献。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in der ganzen Ideologie)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马克思还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它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9-30页)熟悉马克思的经济与社会思想的我们都知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史观,这一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有了其理论雏形。尽管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一开篇,马克思就指出:“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为何物或应该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物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中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象、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我们要起来反抗这些思想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15页)马克思的这些话是在十九世纪中期(1845-1846年)说的。现在,人类社会都走到二十一世纪了,在一些国家和社会中,人们与某些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否还是如此?正因为因此,研究观念与制度的关系,以及探究什么样的观念和什么的制度才是正义的和最能增进人类福祉的,就变得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了。
方钦这本《观念与制度》给出了前所未有的理论解释与深入思考,启发人们更多地从这些方面去探索文化观念和理论信念与人类社会制度生成和变迁的过程和机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