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孙歌: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的亚洲论述
在日本思想史的脉络里,一提到亚洲问题,立刻会浮现出一个“定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分子是依照两个方向思考亚洲问题的。一个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所谓“脱亚入欧”论,另一个是以冈仓天心为代表的“亚洲一体论”。前者主张摆脱亚洲的“恶友”以迅速进入欧美列强的行列,后者则认为亚洲为世界提供了欧洲文明所无法提供的“爱”和“美”的文明,在这一意义上,它具有欧洲文明无法企及的价值。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发表于1885年,它有自己的上下文;冈仓天心发表于1903年、用英语写作的《东洋的理想》也有自己的背景,其实这两种思考在各自的语境里并不是相互针对的。但是,当后世的日本知识分子建构日本思想史的时候,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却变成了相互对立的两种文明论的代言人,这完全是出自后人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日本现代史中的所谓如何对待西方文明的立场设定问题。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明治日本面临着一个表面单纯但内里复杂的问题,即它试图以直接呼应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方式摆脱几千年来它在东亚所处的臣服于中国而竞争于朝鲜的位置,重新排列东亚的国际关系秩序。但是同时,它也必须面临西方占据优势的人种对抗局面,作为有色人种,日本人不可能真正进入欧美的国际联盟,它不能不以亚洲的面孔进入世界舞台。早在日本开国之前,被视为日本近代准备期的封建幕府时代,日本人就开始了对于中国文化宗主国地位的反叛,而当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不得不面向西方敞开大门的时候,如何处理东亚三国间的关系就无法仅仅在东亚的圈域内考虑了,它必须被纳入世界范围内(准确地说,是欧美和东亚的国际政治结构之间)去加以重新思考。于是,在思想史领域里出现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出现了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历史认识方式。在这种认识论的基础上,弱肉强食得到了正当化,而西方文明则被视为进化史观逻辑上的成果。另一方面,对于这种进化史观的怀疑也在逐步增长,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的批判和在东方传统中寻找超越优胜劣汰逻辑的原理成为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之献身的工作,他们的文化立场更具有美学性质;但是在如何对待西方文明这一点上,尽管着眼点和思路完全不同,其实在明治时代,这种表面上的对立却源于同样的危机意识,那就是没有“亚洲”这样一个与欧美相对应的空间,没有东亚三国乃至更多有色人种的联盟,就没有可能真正战胜步步进逼的西方列强。而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被建构为两种文明观念的代言人,那是二战之后、经历了日本亚细亚主义恶性膨胀为“大东亚共荣圈”之后的历史反思意识造成的,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被视为日本亚细亚主义内在骨架的两个支撑点,是因为战后日本面对着如何清理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和批判这两部分遗产的问题。
在发表《脱亚论》之前,福泽谕吉其实主张的是“东洋连带论”。但是,他的“东洋连带论”具有二重性结构,即强调东洋各国首先要进行国内改革旧体制的革命,推翻守旧派的权力,然后才可能摆脱西洋列强的压力。换言之,福泽谕吉的“连带”观不以国界为前提,而以“文明”为前提,他不认为只要是有色人种就可能联合起来抵制列强。所以,主张连带的福泽谕吉,也同样主张对邻国的革新派给予实际支持,加入他们推翻本国保守派政府的政变,输出“文明”。

在福泽谕吉的时期,所谓“大亚细亚主义”不是一个理论命题,而是一个实践的口号。它的载体是被笼统地称为“志士”或“浪人”的活动家在东亚邻国的颠覆性活动。朝鲜1884年发生的甲申事变就与日本的志士密不可分,而中国的辛亥革命更隐藏了介入极深的日本人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上个世纪之交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包含了连带感和扩张欲的悖论关系,也包含了真实的危机意识和对于欧美列强的现实对抗心情。在这样一个脉络之上,可以列出这样一些与亚细亚主义相关的政治家、活动家和知识分子:近卫笃麿(贵族院议长,东亚同文会首任会长),他以人种区分为前提强烈主张介入中国的事务以使它免遭被白种人殖民的厄运;樽井藤吉(不得志的民间政治活动家),他在1893年出版《大东合邦论》,提出日本与朝鲜合并以抗御欧洲列强的主张。宫崎滔天(终生支援中国革命的活动家),他在《三十三年之梦》中倾吐着对中国革命的抱负和感情;北一辉(具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并对昭和青年将校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活动家),他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者而思考着大亚细亚主义。
事实上,福泽谕吉完全可以列入这一串名单之内,因为他的脱亚论是以东洋一体论为基础的。《脱亚论》发表之时,包含了福泽谕吉对于时政的感情性介入。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带有非常强烈的具体针对性,它体现着福泽谕吉对特定事情的特定反应方式,不能看作他思考中的原理性成分。但是,在福泽谕吉这篇短文之中,其实非常强烈地表现着他思考中的原理性成分,这就是福泽谕吉在思考文明问题时的相对主义原则。
《脱亚论》是一篇短文,通篇充满了福泽谕吉特有的紧迫感。开篇说道:“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但是,在福泽谕吉眼里,这东渐之西洋文明并不仅仅是个安琪儿,它的魅力之中亦埋伏着杀机:“文明又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治愈)其术。有害无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挡其势,何况利害相伴且常以利为主之文明乎!”把文明比喻为麻疹,且认为智者的选择当为“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体现了福泽谕吉对于同时代世界大势的判断:他认为西方文明对于全球的征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东方民族不具有抵抗的能力,正如东京人不能够抵抗从长崎传来的麻疹一样。既然文明利大于弊,那么,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接受它。当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自有其详细的内涵,《脱亚论》只不过暗示了他理解近代文明的视角;但是这麻疹的比喻却使福泽谕吉得以与他的后代中那些缺少内在紧张感的西方文明崇拜者相区别,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历史解读前提。
在表明了对于西方文明的基本判断之后,福泽谕吉表明了他对东亚近邻的失望,他大声疾呼与东方的邻国绝交,理由在于他认定了这些邻国必定亡国;而福泽谕吉最害怕的,是日本被西方视为与必定亡国的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脱亚论》传达的首先是他的民族生存危机感,其次才是他对于亚洲邻国的失望和由此而来的视亚洲为野蛮的价值观。对于这篇“绝交书”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但一个基本事实是不能否定的,那就是福泽谕吉这位日本近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完全是在“优胜劣汰”方向上思考亚洲价值的,为此福泽不惜无视日本的地理位置,打算把日本在理念上挪出亚洲,这表明他早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考虑亚洲这一地域概念的相对性问题了。在将地域概念相对化的同时,福泽谕吉显然也要使文明的概念相对化,尽管他强调的是“入欧”,但是他明显不打算把文明视为欧洲人的专利,因为他认为日本同样可以加入欧洲的文明行列。
稍知日本近世思想史的人都了解,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中存在着一种“华夷秩序观”。这本来是中国古代在地理概念之外辅以文化判断的思维方式,如认为善行可以使“狄”上升为“狄人”,体现了把华与夷狄的区分机能化的思维方式;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疆土的不断扩展,“化外之民”被同化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中国的“内部事务”(尽管中国历史上“华”与“夷狄”的交互融合过程绝非“同化”一词可以概括),这种思维方式甚至一直持续到清朝处理西方不平等要求的时代,连割让香港岛都被视为“华”对“夷”的怀柔策略;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国土疆界的这种弹性感觉,华夷的范畴基本上是一个实体性的政治地理范畴,“华”的中心位置是不可取代的。而在日本,华和夷被作为两种判断政治文化的标准,它被视之为“仁”“德”“道”之有无的标志,而不再仅仅是地理上的中央与边境的关系。例如著名的儒者荻生徂徕,就在他的《谖园十笔》中谈道:如果夷进而为夏,就该视其为华;如果夏退而为夷,就该视其为夷。要点在于是否遵循先王礼教。太宰春台也在《经济录》中谈道,如果具备礼仪,四夷之人也与中华人无异;反之,中华之人也可因为失去了礼仪而等同于夷狄。所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华”与“夷”的位置可以互换,不能互换的仅仅是它作为王道礼教的等级秩序。自从中国明清之际改朝换代伊始,日本上层社会便逐渐形成了所谓“华夷变态”看法。所谓“华夷变态”,是指日本人否定清朝代表“华”的正统性,它的逻辑结果便是日本取而代之,以“华”自居。这暗含着日本人对于中国有史以来从未动摇过的恩师地位的一次意识形态反动,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同等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近世日本人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动,采取的是把符号和它所指称的实体相分离的方法,“中华”可以成为一个指称任意实体的符号,不必顾忌它与中国的地界有无关系。这就奠定了一个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思维前提,那就是所谓“文化认同”与文化所由产生的地域之间,可以存在相对独立的关系。幕府末期的日本人以华夷秩序观面对世界的时候,便产生了另一个相关的口号:尊王攘夷,这是针对西方要求日本开国所作出的反应;但是,这个口号也同样具有符号化的性质,稍后的史实证明,攘夷口号喊得最响的两个藩,正是其后最为有力的开国派。事实上,当明治维新造就了日本全面向世界开放的基础之后,近代日本人一直是沿用这一思维方式来面对世界文明的。在明治时代,日本人坦然地将西方文明视之为“中华”,认为更正统的中华不是自己,而是比自己更先进的西方,这就把“华夷变态”又推进了一步,使它世界化了。
福泽谕吉无疑在相反的方向上沿用了这一思维方式。所谓“脱亚入欧”,实际上就是把日本这一亚洲国家从它所在的地域位置上抽离出来,符号化为可以移动的文明载体,使它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近代强国发生一体性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地理位置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世界”这一新的格局中,日本人重新排列了他们在历史上以“中华”和“大和”的关系为轴心的时代所试图排列的那种“华夷变态”的秩序。
“脱亚入欧”与西方世界“中华化”的同时并行,体现的是19世纪80年代日本知识界和上层社会的文化危机感与民族危机感。它与同时代中国同类危机感的指向性是非常不同的。中国的所有危机感都集中地指向了文化的内部调整,而日本的危机感却驱使它向外寻找可以摆脱危机的、新的世界关系。当福泽谕吉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相对脱离它的地理位置的符号时,他必须给它一个新的位置,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位置并不在欧洲。所以,福泽谕吉的处境比江户时代的“华夷变态”论者更为险恶,因为后者至少仅仅试图把日本的地位与中华对调,并且符号化的重点在于中华,还不至于把日本弄得无家可归。而福泽谕吉把日本符号化并且试图使它与亚洲决裂的时候,问题就变得不那么一厢情愿了:你想入欧,欧洲要你么?你想脱亚,亚洲同意么?
在19世纪80年代,福泽谕吉尚且无法顾及这个困境,逼到眼前的问题,是两次鸦片战争已经拉开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帷幕,日本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潜在危险,而同时也看到了对中国伸手的机会。这是一个道地的实体性问题,没有任何符号化余地。福泽谕吉相对主义认识论的两难之境不会成为今人议论的首要话题,就是因为它不能从它所处的特定情境中抽离出来,而当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与那个时代的危机意识结合的时候,尤其是当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强国幻觉的时候,日本的“无家可归”很难成为问题,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福泽谕吉却留下了一个“后患”,那就是其后在日本思想史上反复出现的“脱亚”与“兴亚”更替的思潮。日本是不是亚洲国家,直到今日仍然时时成为问题,福泽谕吉这种把日本符号化的做法要负部分责任。后人之所以必须去寻找能够与福泽谕吉文明观相抗衡的文明观以使日本得以在亚洲立足,原因也在于由福泽所强化的这个符号化模式,只能以另一种符号化的模式取而代之。
比福泽谕吉晚二十年左右,冈仓天心发表了他的《东洋的理想》,这是一个在文明观上强调亚洲一体性的文本,但是其上下文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完全不同,它所针对的问题不是日本如何在弱肉强食的现代世界中生存,而是日本如何为现代世界提供新的文明价值观。冈仓天心对于东西方文明的思考,始终是在“精神活动”的领域中进行的;他对于亚洲一体论的阐述,建立在他对于西方文明的保留性态度之上,这是因为他与福泽谕吉不同,对世界大势取的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立场。当冈仓天心在伦敦出版这部著作时,他面对的是大半个世纪之后萨义德所面对的问题,那就是西方人对东方的了解完全是建立在自我中心和想当然的基点上,因而东方文明没有作为独立价值体系,而是作为西方文明的投影被纳入世界格局。冈仓天心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谈道:“如果东洋须攻克对于西洋的未知,则西洋不是须放弃对于东洋的既知吗?西洋人一方面拥有着庞大的知识网络,而另一方面又至今还抱着何等众多的偏见!”在这个意义上,冈仓天心对于亚洲一体的论述,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体现了与福泽谕吉脱亚论一致的内在张力—它们都是试图回应西方近代入侵的产物。

《东洋的理想》有一个著名的开头,冈仓天心论述的基本视角就隐藏在开篇这段浪漫的陈述里:“亚细亚是一体。喜马拉雅山脉只不过是为了强调,而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分割开来;它们是拥有着孔子的共同体社会主义的中国文明和拥有着韦陀式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但是,就连这披着冰雪的壁障,也从未有过哪一个瞬间能够切断那寻求着终极普遍之物的爱的扩展,而恰恰是这爱,是亚细亚所有民族的共通性思想遗产,使得他们得以造就世界上的所有大宗教,而且,特别要加以注意的是,这也是把他们从不顾人生目的而一味偏好寻找其手段的地中海与波罗的海沿岸的诸民族中区分出来的标志。”由于亚洲的所有民族具有西欧文明所欠缺的对于终极普遍性的爱的追求,所以亚洲文明远远胜过沉湎于技术手段的西欧文明。冈仓天心不忘记在对亚洲文明的阐述中强调日本的特殊作用,这就是它作为亚洲文明博物馆的功能;比起福泽谕吉的“日本情结”来,冈仓天心的日本情结显然更具有弹性,尽管他的这些论述在后来被利用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舆论工具,但是这不是冈仓天心本人关心的问题。假如把《东洋的理想》看作历史或美术史的叙述,它处理知识的方式以及那些知识本身是很可以质疑的;但是当冈仓天心面对西方做这种叙述的时候,他的独特立场却为这种论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价值。这就是,在20世纪初期,冈仓天心使西方人了解到,东方存在着与他们的亚洲观念完全不同的另一套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的方式,而且这种来自东方的亚洲观,在文明的层面对西方中心的文明观的确具有挑战性。
冈仓天心的个人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他早年被派往欧美研究西方艺术的历史,但是这反而强化了他对亚细亚艺术的信念;同时,冈仓是一个具有现实政治兴趣的人,他的个性导致了他在仕途上屡遭惨败,但不妨碍他始终在艺术领域内关注现代政治思想与文化的基本问题,这使得他有可能在日本日益关注西方价值的时代里提出相反的命题,即亚细亚的价值。按照冈仓天心的思路,判断世界基本问题的尺度应该来自亚细亚,而不是欧美。在当时的日本,这种看法其实并不背时,因为它暗合着日本政府与上层社会在新的华夷秩序中确定自己优越位置的欲望;如果把冈仓天心的亚细亚一体论视为当时日本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一个变奏,其实倒是更为合适的。
假如把这段话与福泽谕吉《脱亚论》的论述方式对照起来看,可以看到的不仅仅是它们在价值观念上的对立;其实,把西洋文明看成比麻疹更具有益处的传染病的福泽谕吉,与把其视为不顾目标只看手段的“劣等文明”的冈仓天心,在深层意义上是一致的。这就是说,他们都面对着东西方对立的模式,也都面对着一个既定的亚洲。更重要的一致是,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使亚洲符号化了。不同的仅仅是,这个既定的亚洲,在福泽谕吉眼里是即将灭亡的野蛮的符号,而在冈仓天心眼里是诞生了世界三大宗教的爱的符号而已。在脱亚还是兴亚这个层面上,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的确可以作为历史中的两个原点,围绕着他们构成了一个日本近代史运动的椭圆形轨迹。
脱亚还是兴亚,换言之,日本是不是亚洲国家、是否对亚洲负有责任和义务的问题,成为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一首挥之不去的二重变奏,的确是由于这个椭圆并存着两个圆心,并且不断放射出至今仍未衰竭的能量。但是,假如我们对日本近代史上亚洲问题的思考仅仅停留在这一椭圆之内,那么将会遗漏掉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思考线索。为了全面地考察亚洲问题的意义,必须从竹内好与桥川文三的图式中走出来,并且暂时搁置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的对立,从更高层面上发现他们之间的一致性,并且寻找与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相对的另一条思考线索。这样,我们会发现,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的亚洲论述同样具有强烈的理念性功能,并且同样地对于亚洲与西方这一划分方式的疏漏之处有意地忽略不计。
(本文摘自孙歌著《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一頁folio |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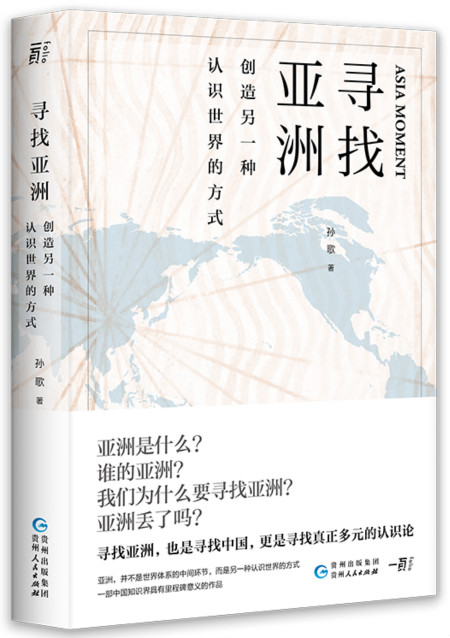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