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杨照:为什么要读《史记》
司马迁的历史态度
我们今天要读《史记》,首先会遇到两个问题:为什么读?用什么方式读?
和所有中国传统经典一样,《史记》是在与我们不一样的环境及时代中产生的。经典最简单的定义是“经过时间淘洗后存留下来的古书”,久远之前的人们面对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和课题,将他们思索的内容写成文字,然后一代一代传留下来,成为经典。较之同时代的书籍,传统经典可以使我们离开有限的视野和熟悉的现实,感受不一样的人类经验。当然,能够留下来的经典不仅在时间上古远,还包含了一些经过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反复检验的共同价值。这些可能是人类共同的遭遇或命运,也可能是不同世代累积下来的共同智慧。
此外,今天我们读《史记》,还可以学习司马迁看待历史的态度,以及书写历史的方式。在一般的教育体制下,从课本里学到的往往是一堆固定的事实,往往让人以为历史就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用这种方式学习历史会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我们以为历史都是拿来背诵的,而为了应付考试背下的这些事实,绝大部分都会在考后迅速遗忘;第二,我们很难去思考究竟可以在历史中学到什么,尤其是与现实相关的智慧。
司马迁不是用这种方式看待历史的。在读《史记》时,我们首先要了解司马迁的“史识”。单纯看数字,《史记》有一百三十篇,多达五十二万余字,是一部很庞大的书。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史记》横跨几乎三千年的时间,把中国发生过的所有事情、曾经存在的人、累积下的经验,只用这五十二万余字来记录,可以说是极为精简。司马迁在处理三千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在用一种清楚的意识,一个衡量历史轻重厚薄的标准,去判断到底应该把什么写进来,把什么排除在外。这样的选择标准用我们的观念来说就叫“史识”。
“史识”与“史观”密不可分。当我们认为历史就是一些固定的事实时,就没有史观存在的空间,即不管什么样的人来写,历史总是那堆东西,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来写,都不会写出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历史如果真是如此,就没有史学存在的必要,也不可能比较什么历史书是好的,什么样的历史学家比较杰出。
历史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或者进一步说,是解释“如何”及“为何”,这是与我们当下学习历史的态度差异最大的地方。按司马迁的态度,历史不是一堆“What”,重要的是“How and Why”。在个人层次上,一个人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讲话做事?作为一个群体,彼此行为之间的互动会产生什么模式,他们为何如此?某些事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又选择何种手段?这些都在历史里,也是我们理解、研究史学时最重要的挑战。
当我们以这样的视野和方式去整理丰富庞杂的史实,就会对人类行为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而碰触到普遍的人类经验,真正做到以古鉴今,让历史对当下现实有所帮助。司马迁在著作中清楚地展现了这种历史态度。他用了几个重要的观念解释《史记》的目的。
首先是“究天人之际”。简单来说,在解释历史上人的行为、判断是非善恶时,必须区分这是不是意志可控的事情,有些东西人再怎么样努力也无法改变,比如说像命运般庞大的东西,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限制。要公平地评价一个人,从他的行为因果中得到智慧,就一定要区分“天”与“人”。司马迁讲的“天”指庞大的背景,是与个人努力无关的部分,而“人”就是一个人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作为,在最后如何承担责任。
司马迁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在历史中学习,就要“通古今之变”,即在时间之流中,不仅要看单一事件的来源、发生、变化,还要把眼光拉高,看长时段里的人在集体行为中如何运用权力,组构社会,进行交易。这类集体的行为,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就必然有一种特别的模式,在司马迁的语言里,这个模式就叫作“通古今之变”。这个概念的重点在于“通”,即它不是个别事件的解释,而是能够归纳的、更明确的模式。我们掌握之后,不管是看待古人还是分析今人,都能够有一种超越时间的眼光。
能够在历史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彰显出司马迁另一个巨大的野心,即“成一家之言”。这仍然与我们的历史观念不一样,历史怎么会是每个人说来都一样呢?对司马迁来说,如果你说不出“一家之言”,提不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比如周代怎么瓦解、秦始皇如何统一六国、汉武帝如何改造汉朝,就根本不配做历史学家。写历史就要写到“成一家之言”,不能人云亦云。
所以,我们今天读《史记》,就是学习如何解释历史,如何在其中区分出命运与人的意志,在历史里看到更加庞大或长远的模式。这些与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观念差距太大,必然会给予我们很多刺激。
《史记》的地位
认识《史记》有若干种方式,包括如何理解它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史学和文学上的特殊地位。
从史学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在早期就已经很发达了。中国的历史在周代发生重要转折,直到20世纪我们才比较仔细地掌握了周之前的商代文化。从文献或考古资料上看,商代的文化非常奇特,它背后有着一个神鬼交错的世界。在商代人的意识中,现世活人所在的世界与死人或者灵魂所在的世界交错。我们看不到、触摸不到后者,但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灵媒或动物,跟它来往。那个世界就在生者身边,与生者没有截然的差异。所以我们会在商代文化里看到很多沟通天地的精巧描绘。
不过,自从西边的周人崛起后,这种文化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之间,周人剪商成功,建立了新的政权,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新的政治制度叫作封建制度,新的文化就依附封建制度而成立。封建制度来自亲族系统,换句话说,它的核心概念与精神最看重自然的亲族关系,作为父亲、儿子、叔伯、侄子外甥,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一般的生活礼仪乃至政治权力上就做相应的行为。由此,我们认识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才真正浮现出来。
周人这种价值观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即必须保留宗族系统的记录,使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久之后的人们仍能清楚每个人与其他人的亲族关系,这就要依赖记忆,而人的记忆没有那么可靠,自然必须依赖记录了。
在中国上古的考古资料、金石资料里面,青铜器的用法在商代到周代之间明显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商人那种鬼神世界中,青铜器是人与非人世界的交流工具,所以铸刻了以动物为主的各种纹饰。我们可以想见,在仪式中,鼎或者其他青铜器里焚煮东西的香气、烟往上传,商人相信这样就可以与住在上面超越现实世界的祖先进行沟通。
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甚至应该说“偷”来铸造青铜器的方法,但是他们铸造的青铜器的重点特征改变了。商人青铜器表面华丽复杂的艺术性纹饰,或者说功能性的神鬼交会的纹饰慢慢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铭文,即把文字刻铸在青铜器上。为什么要在青铜器上写字呢?我们要看到青铜器铭文的固定形式。青铜器铭文和周人发展出的其他记录方法,都是为了让这种关系,以及围绕这种关系所需要的经验永久保留下来。在此开始诞生中国非常强大的意识传统,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在世界各种文明中,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最发达,历史记录最完整,这部分来自周人在建立封建制度过程中,功能性地保留了这些资料。
但是这种意识在功能性作用之后发生了各种深化、变形,其中最重要的阶段在春秋时代,这时出现了《左传》。原来只是为了把人与人的关系、与礼仪有关的部分记录下来,现在则进一步出现了特殊面向,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教训。换句话说,从《左传》开始,如果不学历史,不去继承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经验,生活就会变得危险而艰难。不知道前人遇到了哪些事情,他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又如何解决,与懂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相比自然远远不如。从这里开始,东周历史的记录进入王官学的系统里,变成了贵族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从这个脉络看下来,到了汉朝,我们才能够了解,司马迁的《史记》是这种传统的集大成者。《史记》是一部通史,也就意味着是人类有意识、有经验以来的总和。通史是时间的完整呈现,司马迁要从开天辟地、人怎么来、人的社会怎么来、人的历史怎么来开始写起。通史不会有真正的终点,因为时间要继续流下去,不过在现实上,司马迁只能把历史写到自己那个时代。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是中国历史意识的一次提升与突破。在这个时候,历史取得了一种整体性,不再是一块块、一段段的。一个人一辈子发生了什么事,或者稍微长一点,一朝一帝或者从一个家族的建立到灭亡,这都是一段一段的历史。我们有看待这些片段的眼光,但司马迁用他的著作让我们认识到,当我们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时,所看到的历史、从里面学到的内容,以及因此认识到的世界与道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历史有不同的意义,最浅显的诸如昨天的事情教会我们今天怎么面对现实,而深邃的哲学性意义则要把历史作为总体来掌握和理解。从这个意义来说,司马迁在中国历史意识的深化上厥功至伟。在《史记》之前与之后,如何看待历史、历史包括什么、历史可以给我们什么,是彻底不同的。至少从这一角度,司马迁不但写了一本书,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他的方式直接建立在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一个面向,即如何看待历史上。这个态度是由司马迁建立的,此后无论谁进入中国文化、进入中国历史,都无法遗忘。
(本文摘自杨照著《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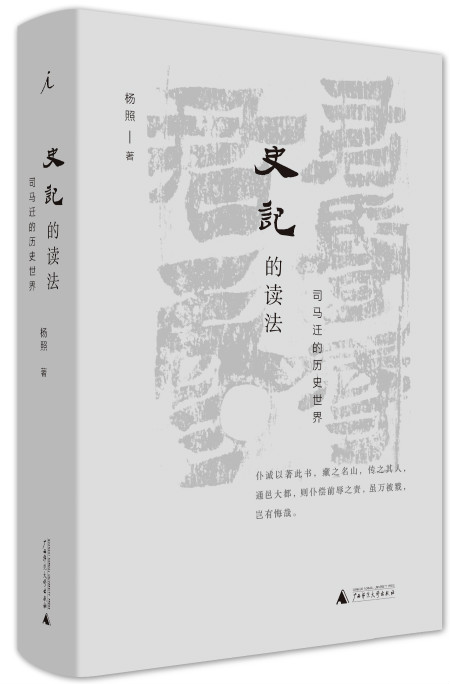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