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都市青年,正在被迫成为“游牧民族”


有一种现代爱情是——明明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两个相爱的人却选择分居两处。
日本公开宣称不婚的国民女王天海祐希,每逢上综艺节目,十有八九会被问及感情问题,早前,在某次节目的半玩笑半逼问中,她描述了一番自己理想中的相处状态:
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是住在步行3分钟距离的临近两个住处的话,那倒可以考虑结婚。


天海祐希只好再解释,大意是:住在一起难免会介意很多事,或者自己介意,或者对方介意,哪怕是端茶送水这种细碎的琐事都可能会想很多,如此一来,“做什么都没关系”这样自在的氛围就不会有了,两个即使最亲密的人,相处起来也会变得费神费力。
“找一个人,在一起,不住一起”,这是一种很值得玩味的新型亲密相处之道,说值得玩味,一是它很难符合现实,所以奉为“理想”,所以很多憧憬这种亲密关系的人干脆独善其身,既是因为自己怕麻烦,更是因为找一个同样讨厌麻烦又合拍的人,是一件更麻烦的事。
二是虽说憧憬这种状态的人也认为它遥不可及,可是生活又最善于制造惊喜,许多人正在走向这种亲密关系,以一种意想不到又心不甘情不愿的方式。
三是从历史的脉络来看,你会觉得人类真是善变,明明是种群居动物,究竟是怎么发展到连伴侣都不愿意待在同一片屋檐下的?如果要描绘一个人类睡眠极简史,它大致会是这样的:
很久很久以前,由于没有空调暖气,也没有屋瓦保护,一大家子睡觉需要“抱团取暖”,中世纪以前,连客人也热情招呼加入,一字排开睡大通铺。
后来,人们就一直在分开,先是有了分开的卧室和床,为了卫生和隐私,再后来,连夫妻双双也把床分,为了各自有更好的睡眠质量。
在欧洲,上世纪一度还有过睡觉时间性革命,妻子们主张在卧室里摆两张床,意味着自己有权利拒绝丈夫。

再往后过了几十年,分床意识又开始大行其道,特别是越来越多年轻伴侣的加入,在日本,这被称为“无性症候群”、“冷恋”,在美国,这被称为“睡眠离婚”(Sleep Divorce),除了祝彼此好梦之外,更是为了尊重彼此的个人空间。
——这就是我们所身处的时代了。
冷恋、睡眠离婚这些新词的出现,不过是去年和今年的事,哪怕早些的无性症候群,往前能翻到的最早报道,也是2013年的,虽然年头不多,然而就是这几年,分开睡觉这件事可以说已经分流出了两条“小路”,但两条路都有点难走。
一条“小路”是,一小部分更注重自我空间的人所发展出的,如天海祐希般的“理想相处”与独身主义,可参考昨日文章《一个人住,你选择的是自由还是寂寞》。
另一条“小路”是,在“理想相处”的另一面,一部分情侣,出于种种原因,虽然待在同一个地方,却正在被迫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张床、一个房间。
或者说,人们开始被迫同城分居了。
这两者,就好像是一件事走向了正反两个极端,被迫分居的人们,也算是半实现了天海祐希的理想相处状态,除了距离稍远了些。
这也就是前面说的“意想不到”了。
2.十年前的“半糖主义”,成了现在的“缺糖主义”
2012年的夏天,有一对香港年轻人在迪士尼乐园陷入了爱情,三年后,两人结婚了,并且有了一个孩子。
听起来是一段顺遂的缘分,唯一不寻常的地方在于,两人于婚后,仍然分住在同一个城市的两端、相距遥远的两间卧室里。
女方骆(化名)31岁,与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位于香港东边的北角,男方周(化名)35岁,住在香港青衣,同样是在父母家里,两地往返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而两人的孩子、一个如今已经3岁的小女孩,星期一到星期四会和妈妈在一起,周末就去爸爸家。
每个星期,周都是尽量挤出时间陪着骆和女儿走回家,然后再搭地铁回自己的另一个家,出去约会、旅行,只能等着父母有空照看女儿的时候抓紧机会。
这种“一结婚就分居”的婚姻生活,夫妻俩一开始也受不了,甚至对所谓婚姻也产生了诸多怀疑,仿佛自己并未结婚,至于爱情的结晶,那需要投入巨大时间与精力的孩子,也就意味着说,两个人作为父母,总是不能同时分担抚养的重任,也不能一起看着孩子长大。
“我们花了一年多时间才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骆在采访中如此说。
这看起来反常的个例,事实是,它是相当常见的“正常”现象,尤其对于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来说,谈论起来,身边都有几个这样的人,或者自己就是。
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此普遍,却鲜见公众关心、媒体讨论,是大家都司空见惯了?还是大家都已经被生活驯服得相当吃苦耐劳,以至于两个相爱的人在一个城市里需要抽出时间来回跑,也觉得理所当然、毫无怨言?

今天如此嘈杂的社交网络,对此倒很少关心,反倒是12年前,一度热议过这个话题。
那时还流行起一个词叫做“半糖夫妻”,被教育部列入2007年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这个如今早已被遗忘的旧词,指的就是同城分居、过着“五加二”生活的夫妻。
隔了十余年,区别在于,当年人们还把半糖主义视为一种“距离产生美”、“情感保鲜”的主动选择,是少数高学历、高收入人群的非主流选择。
而今天,主动选择变迁成了被动接受,少数“双高人群”的非主流生活模式,“下沉”为了广大普通群众的某种常态。
倒不能说“半糖”就降为“无糖”了,还是会有人觉得这种方式有利情感保鲜,只是就大多数而言,因为被迫而将就的“半糖”,就始终会为那少了的一半耿耿于怀,所以不如说今天是降为“缺糖主义”了。
当然会有人问,为什么不搬到一起?
骆女士说,一间卧室对两个成人和一个孩子来说,实在太小了。言下之意,两个人加在一起,可能也就只能负担一个拘谨的小卧室。
今年发布的一份住房负担能力对比调查中,香港排在倒数,中等价位的房子,相当于中等收入家庭的年收入x21,而在相对更昂贵的欧洲伦敦,中等价位的房子也只需要中等收入家庭的年收入x8。

公屋,也就是由香港政府或公营机构为低收入市民而兴建的、可出租公共屋邨,现在香港约有三分一居民住在公屋里,然而一个市民要得到一套公屋,靠的不是证明自己有多穷,而是运气女神和自己坚强的生命年岁。
公屋需要申请、轮候,幸运的人平均也要两三年才轮候到一套公屋。
可不幸的人永远占大多数。今年还有媒体在Youtube上发布视频报道,称一对夫妻申请公屋,轮候了8年,从最初的两个人等成了四口之家,终于等到一套100多平米的住宅,房龄虽然超过40年,怎么也强过没有,于是也就欣欣然搬进去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住不起同一套房的痛苦,不会只限香港。
3.单身青年只要一张床就够了,城市欢迎你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来泰克拉的旅人所看到的,除了木板围墙、帆布屏障,就是脚手架、钢筋骨架、绳子吊着的或架子撑着的木浮桥、梯子和桁架。你会问:“为什么泰克拉的建设会持续如此之久?”居民们会继续提着一个个水桶,垂下一条条水平锤坠线,上下挥动着长刷,回答说:“为了不让毁灭开始。”你若问他们是否害怕一旦拆除脚手架,城市就会倒塌,垮成碎块,他们会连忙低声说:“不只是城市呢!”
如果对这些回答还不满意,有人会透过木板围墙的缝隙窥视,看到起重机吊起其他起重机,支架支着其他支架,梁柱架着其他梁柱。他会问:“你们的建设有什么意义呢?一座建设中的城市的目的如果不是一座城市,那又是什么呢?你们执行的规划、蓝图又在哪里?”
被迫同城分居这事,说是因为大家过得很窘迫,因为负担不起城市生活成本,其实根本原因是,一个城市看重自己的长久发展,甚于为它的发展而卖力的这些人。
一辆超载的公交车,其乘客互相挤压的龇牙咧嘴,其车身鲁莽笨重的前行拐弯,基本就是一个对“发展”如饥似渴的大城市之形象。这样的城市,无不面临用地紧张、平价房源紧缺等等的问题,但人口依然在增长。
于是这两年,逐渐催生了一种新型建筑,被称为“寄生建筑”(parasitic architecture),小而轻巧,有时还可自由移动,最重要的是,可以依附在已有的建筑上,无须自己再占用一块土地。
例如美国犹他州的圣胡安,今年出现了一些仅12平方米的格子屋,就“驻扎”在旧建筑的屋顶上。
又比如世界上最高楼之一,加拿大多伦多553米高的CN电视塔,在一份概念图中,被设计成吸附了一堆木制“像素块”,这些“像素块”还有不同的大小、布局可供选择,被认为既开发了资源,又增添了景点特色,而且就视野和地理位置而言,实在是难得的绝佳房源。

寄生建筑的最理想租客,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这种人说出来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很在意租房成本,大多还不愿意(或者愿意也还没有能力)在一个地方定居,也大多还不愿意被一份工作所限,所以短期内或者很频繁地,会从一地迁往另一地。
于是这样的寄生建筑,就正好做了他们的“临时帐篷”。
料想得到,城市里的“游牧民族”,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单身青年,而且寄生建筑的应时而生,从实用性和美观性来说,也很符合城市单身青年的期望。
可是另一面,寄生建筑所投下的黑色阴影,远比它所提供的舒适空间,要更大更深。
寄生建筑之所以出现,大背景是无数密密麻麻的青年们,在不断求发展的城市里不断贡献着驱动发展的能量,为了这些能量源源不断,为了发展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城市当然十万分地欢迎单身青年,但城市并不关心这些单身青年自己的长久发展。
换句话说,组建家庭、抚养孩子这些事,都正在被城市有意无意地,放弃考虑。
难道有家庭的人就不能为发展做贡献吗?
不妨做一个夸张化的简单对比——
一个单身者往往可以贡献超过8小时的工作,有时甚至24小时、一周七天也在所不惜;而一个有家庭、有孩子的人,就必须分配出一部分的精力和时间给家庭和孩子。
要满足一个单身者的生活需求,极端地说,只要有一张床就够了;可是换做一个带有孩子的家庭,就需要一套房子,需要有支持教育的学校,最好附近还要有公园,有游乐场所,城市需要付出的成本自然就大大增加了。

显然对于效率至上、利益至上的城市来说,单身奋斗者可比拖家带口的人有利用价值多了。
这在全球诸多城市都有事实为证。以美国为例,在100个全美最大的城市中,平均的儿童人口比例为23%,其中有着最小儿童比例的是旧金山,创业者的聚集中心,儿童人口比例仅占13%。

一些美国城市会选择把日渐破败的市区,例如旧的公共学校,改建成适合中产阶级的居住区,是为“乡绅化”举措。而在芬兰,2014年政府关掉了三分之一的公共游乐场,这样就省了一笔资金去维护它们符合安全规定。
美国、芬兰尚且如此,那些稍微欠发达又力求上进的地方,提供给儿童的娱乐基础设施基本不存在,也就十分正常了,更遑论仅有的那些设施安不安全了。我们大概都见过孩子们在工地废墟、工厂、污染的河流、垃圾场附近嬉戏的场景。
所以今天世界人民都在忧愁生育率下降,多少也不能全怪年轻人过于崇尚个人主义,毕竟大环境也很不友好。
想象一下,当城市中的青年们都无法保证自己的以后,甚至根本不愿意有下一代的情况下,当所有城市又不约而同地都在不断向外扩张面积、不断向上建起更高的大楼、不断涌入更多的单身青年时,城市,真的会有未来吗?
4.人们在一块金钱的聚散地上来来去去,谁来保存城市的记忆?
一个不友好的大城市经过一番淘洗,来了又走了的,一部分是无法积累财富的人,一部分是无法负担在此定居的人,留下来的,多半是与他们相反的人,于是贫富两极化、人口构成单一化,进一步,经济形式的单一化,诸如此类的问题会像墨水滴一样慢慢渗进来,再慢慢晕开。
这样一个不友好的大城市,它如何能确定,自己求得的发展,多过它所失去的呢?
康奈尔大学曾经做过一份报告,叫做《论有孩子的家庭的经济重要性》,它的结论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城市,就需要纳入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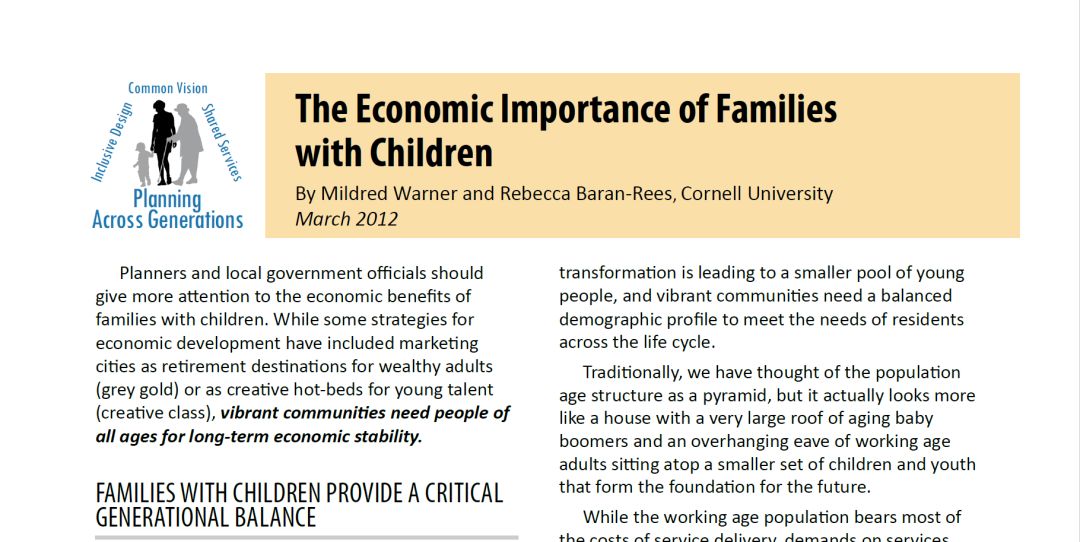
除了年龄阶段,同样关系到所谓稳定与发展的,还有性别平等、老年劳动力对年轻人的隐形支持,以及其他此类难以定义的、与经济或许有或许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所有这些融合在一起,才使得一个地方之所以成为“城市”,而不是一块金钱聚散地而已。
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理由——谁来保存一个城市的记忆?
每个城市都有她的故事,这些故事,唯有那些生根立足的人,那些在一个地方长大、在一个地方安居、在一个地方老去的人,才讲得出来,或俗世烟火,或浮世繁华。
说来也奇怪,人类的情感,总是附着在经历过的事物上,而事物在时间长河里走过的痕迹,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看得见。一个城市的喜怒哀乐,也只能靠有血有肉的人来见证、述说、传承。
反过来,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一个忘记此时此刻自身正在存在的地方,它真的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去往哪里吗?
5.看不见的城市
最后说说另一个小故事,关于一对毫不起眼的老夫妇,隐身在毫不起眼的角落里。

一个仅仅只有5.5平方米的小房间,不带窗户,蜗居着已经69岁的老马(化名)和他的妻子,每个月,老马领到的补助金里,三分之二要用作小房间的租金。
老马曾在澳门赌场打工,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自己的妻子,如今妻子身体抱恙,每隔几个月就要回家乡杭州调养一段时间,一部分健康问题,就是因为久居在这样一个狭窄简陋、没有空气流通的小房间里。
老马同样也申请了公屋,已经等待了三年。
当初尽管知道前面有许多难处,两人还是结婚了,现在果然挣扎在最困窘的环境里,可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老马的妻子还是说,“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很开心。”
回到《看不见的城市》里那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一座建设中的城市的目的如果不是一座城市,那又是什么呢?你们执行的规划、蓝图又在哪里呢?”
你知道卡尔维诺怎么回答吗?
“今天的工作一结束,我们就给你看,现在我们不能停手。”他们回答。
日落时分,工作结束了。工地上笼罩着一片夜色。天空繁星点点。“喏,蓝图就是它。”他们说。
你看,现实极尽辛劳,所幸,人的内心总也还有另一个看不见的城市,卑微活着的人们,也并不卑微。
参考来源:
The married couples in Hong Kong who live apart | BBC
The major cities being designed without children in mind | BBC
The 'parasitic' homes that could change cities | BBC
It's time to embrace the sleep divorce | Medium
撰文:陈皮
编辑:猫爷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