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非虚构工作坊 | 罗新:我们该怎样与过去对话?
编者按:2019年10月18日至20日,第二期“澎湃·复旦”非虚构工作坊在上海举办。本次工作坊由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发起,建投书局参与主办。98名学员在罗新、庄永志、周浩、李宗陶、郭玉洁、叶伟民六位导师的引领下,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学习,共同探索非虚构创作的魅力。
10月18日上午,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以“历史非虚构的探索——我们该怎样与过去对话?”为主题,从他的非虚构著作《从大都到上都》出发,分享了自己用探索历史的眼光重新发现中国、在旅行文学中发现世界的体会,并就历史非虚构写作中史料的引用、合理想象的边界等问题与学员深入探讨。以下为讲座内容精选,以飨读者。
整理 | 罗炜熠 俞诗逸

罗新在讲座中,邹佳雯 供图
我想自己被叫到这里来跟大家交流,是因为我写了《从大都到上都》。我的历史同行看到这本书,说这不是学术书,但专业圈以外的朋友觉得这本书还挺“历史”的。这就处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专业同行觉得我不务正业,专业外的读者觉得书里还有这么多的历史。所以这书就归类到非虚构之列。我到这里,就是出于这样一个机缘。说到非虚构写作,大家懂的肯定比我多,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那么,我就跟大家聊两点:第一,我为什么以及如何写了这本书;第二,怎么看待非学院派研究者所写的历史作品?
写这本书不是偶然。我一向爱读旅行书,算是travel writing或travel literature,读了不少,读多了难免“见猎心喜”,也想写。我读这类书时关注的是作者怎么观察、怎么理解他所到的地方,跟我的观察与理解比起来有什么不同?我本科读的是北大中文系,当然是有写作志愿的,不过大学毕业以后,也就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时代有了变化,文学热让位于文化热。那时,我跟着文化讨论的时代潮流读了一些历史书,兴趣逐渐转到学术领域。没有想到的是,我五十岁以后,当年那种创作的冲动突然出现了。当然,小说我是写不来的,我可以写一个旅行的书。以前我读的旅行书都是国外的,没有国内的,似乎国内不大见这类作品,当然也许是我读得太少。
2015年初,我在书店买到罗瑞·斯图尔特(Rory Stewart)的《寻路阿富汗》(The Places in Between),讲的是2002年阿富汗战争之后,他去阿富汗走中央山地的经历。仔细一读,我被他的写作和他的旅行本身所吸引。我研究了一下作者,发现他还真是个人物,那时他已经成为英国的国会议员。《纽约客》曾刊出对他的长篇人物特写,并提出一个问题:“罗瑞·斯图尔特步行穿越了阿富汗,他能一直走到唐宁街10号吗?”《纽约客》那时就对他未来的政治前景做了这么大胆的预测。总之,我读得特别上瘾,以至到后来,我决定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写了一篇长篇书评。

《寻路阿富汗: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版
在《寻路阿富汗》刺激下,我也有了写作冲动。说到旅行,我也旅行过一些,可是没有哪一次值得写一本书。罗瑞·斯图尔特这本书的看点是作者的行走本身,只把这件事说一遍就挺吓人。很多旅行作品之所以动人,不一定是因为写作,而是故事本身,作者的经历本身就足够震撼。我没有这样的经历,要从事这样的旅行写作,需要有新的旅行经历。2016年春天,我偶然想到了从大都走辇路到上都这个题目。我十多年前和朋友在网上讨论过元代两都之间的辇路路线问题,那时就想过,应该自己走一遍,走一遍就大致上明白沿途情况了。我的目的很明确,走这一趟就是为了写一本旅行书。有人当过总统以后回头写个回忆录,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我这个案例里,我是为了写回忆录才去当总统的。对于旅行文学的写作者来说,他们是为了写作才去旅行的。计划既定,我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读史料、写笔记,为旅行、为旅行之后的写作做准备。
美国著名的生态保育学者约翰·缪尔(John Muir)写过很多书,译成中文的有《夏日走过山间》,还有不少佳作没有翻译,比如我特别喜欢的《走一千英里到墨西哥湾》(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这本书全都是他的旅行日记,每天所见所闻,就那么几行。这种写作不需要文学技巧,而缪尔也全无创作的动机,他只是记下自己的行走与观察。那么为什么这本书能吸引读者呢?因为他的行走、他的故事本身就挺吓人:内战刚刚结束,硝烟还未散尽,他从印第安纳一直走到佛罗里达,行李主要是笔记本和植物标本,身上几乎没有钱。他每天的日记就只写那么几句,今天到了哪里,路上看见了什么植物,遇到了什么人,如何乞食,如何过夜。平平淡淡,但读来惊心动魄。当然,我可不能像他那样写,我的旅行过于稀松平常,我吃的住的都挺好,只写这个恐怕要被人笑死。怎么办呢?我也算学过文学,知道一本有特点的书,需要一定的写作策略。前面说过,我之所以产生旅行写作的冲动,原因之一是我觉得中文旅行写作中,没有我特别满意的作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写,应该怎么写?
走完从北京到上都这点路之后不久,我就开始写了。我当作范本的,也就是我认为可以学习其写作策略的,是马克·亚当斯(Mark Adams)的《到马丘比丘右转》(Turn Right at Machu Picchu)。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户外杂志的编辑,不过他完全没有户外经验,他说自己仅有的野营实践就是在自家门前的草地上搭帐篷陪孩子玩。在马丘比丘被宾厄姆( Hiram Bingham)“发现”将近100周年之际,亚当斯决定去重走发现之路,目的显然主要是为了写书。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安第斯高山深谷走印加古道,之前之后又在不同图书馆阅读了大量档案材料。写作不是偶然,要有非常充分的准备,还要吃很多苦,吃别人想不到、吃不了的苦。他这本书的写作难度其实非常大,因为“重新发现”这种题材毫不新鲜,很多书都以“再发现”为主题,要写出新意是很难的。然而他却写出了新意,写出了一本足以列入旅行文学经典书目的好书。
在我看来,亚当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写作策略,比如,他简洁地呈现出至少三条平行并列的时间线,三条时间线之间相互呼应,既有历史深度,又有阅读趣闻。一条时间线是宾厄姆在印加古迹中的探索,他如何偶然发现了马丘比丘,亚当斯要对宾厄姆这个人和他的时代进行研究和发掘。另一条是作者自己的时间线,他如何重新发现当年的发现。第三条时间线是印加帝国覆亡的历史本身,加上了这条时间线,印加的梯田石墙荒弃古城才焕发出生命。显而易见,三条线之间天然地存在着断裂。单独写其中任何一条,大家都做得到,然而要同时写三条,散而不乱,让它们之间有紧密关联,抓得住读者,难度相当大。作者成功做到了把这三条线都写出来,缜密有致,一点也不散漫。我的旅行当然比不上他,但在写作技巧上,在结构布局上,我可以学他,可以把简单的旅行写得复杂一点,让文字比行走本身显得有趣一点。
要学习这种写作,就得发挥我的长处。我的长处是,我是研究历史的。至少表面上,我讲起历史来,容易比非专业人士显得可信些,我想这是身份优势。当然我也有一定的知识优势,或者说是获取专业知识的方法优势,我知道该看什么书,知道到哪里找这些书。但单单凭这个优势,还不够写一本我期待中的旅行书。我的旅行本身很有限,一共才半个月时间,经不起一写。我必须加一些内容进去。加什么呢?没办法,我只好从我的阅读中选一些,要么与徒步有关,要么与途中所经各地的历史有关。
比如,我走了450公里,其间大约300公里是走在所谓的长城地带,主要是明长城,所以我就把明朝的长城写了进去。说起来我走的是元朝的辇路,但我读的资料主要是明代的,就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对于长城,普通读者都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我不能写别人都知道的。我想表达一些想法,把想法隐含在叙事里。长城不是,或不止是一条非此即彼、敌我分明的军政分界线,实际上它还是把长城内外南北联系在一起的一条线。我强调有许多汉人越过长城,跑到草原上,也有很多蒙古牧人从草原上跑进长城里边来。来来去去,都是为了逃离不堪忍受的政治和经济压迫。我想把这两者都表达出来,使我们对长城的认识更丰富、更符合历史实际。
写的时候,我希望把线索变得更复杂一些。如果说这次写作有什么值得回味之处,我觉得主要在于形式探索。旅行写作最容易平铺直叙,因为时间线索过于清晰,难免会按照旅行的时空次序简简单单说下去。我为了让文字多一点层次感,经常在平面的叙述中加进一些别的文字、别的线索,只希望把平淡的徒步变得不那么平淡。我的写作策略就是让内容更丰富一点。似乎过去中文的旅行写作里不太追求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我觉得形式还是重要的,无论是非虚构还是虚构,形式永远都是重要的。好的写作者总在探索新的表达方式、新的结构。如果说我这本小书有什么新意,我希望是能够展示,有时候可以把乱七八糟的事情混杂在一起写,旅行写作的文体可以有多种形式。
旅行文学一定要容纳多层次的时间。比如我们现在看窗外的黄浦江,它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我们要写出它的这个样子,但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要写出它是现在的样子,更要了解它昨天、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是一百年前的样子。有深度的时间才是历史,对于写作者来说,置身历史中你的资源就一下子变多了。当然,关注时间深度跟我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关,这本来也是历史学学科一个特点。我们观察现实、思考问题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单一的一个点,而是奔流不息的时间河流。

罗新在讲座中,邹佳雯 供图
关于旅行文学,我推荐一个写作范本,休·汤姆森(Hugh Thomson)的《龙舌兰油:迷失在墨西哥》(Tequila Oil: Getting Lost in Mexico)。刚看到书名,我很疑惑,以为龙舌兰也可以做油。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不存在龙舌兰油,作者用这个词是一个隐喻,因为书里写他18岁时开一辆旧车自北而南纵贯墨西哥,一路上喝了不少酒,对他的冒险来说,龙舌兰酒是比汽油更重要的燃料。汤姆森第一次美洲探险的30年之后,写这本书时,他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和考古学家,他回首往事,凭记忆写出了这本有趣的旅行书。这么多年之后,写30年前自己才18岁时的经历,哪些细节是可靠的,哪些是有意无意添加的,很难说。其中很多细节都过于personal,不大好说就是非虚构。但我觉得这本书的美妙之处,在于作者把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解释,解释自己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建议读一读,从中可以学习一点写作技巧,或至少,是看到某类旅行的趣味。
现在讲第二点,就是非虚构写作中的历史作品。
我关注这个话题也很长时间了。我读的不多,就我所读过的来说,非虚构历史作品中最成功的作者几乎都不是学院派,有业余爱好者,也有记者和编辑。也许是因为专业历史学家通常写不好通俗文字。职业历史学家接受的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写作的训练,按照那种训练,写作者并不在乎圈外人看不看得懂,一个好的学术写作只是提供给为数有限的同行们看的。有些冷僻领域的专业论著甚至连领域隔得稍远的同行也看不明白。这样的学术人生使得专业工作者习惯于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友好的文字,对圈子以外的普通读者不友好。这种环境、这种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的写作者,通常不适合写大众读物,我自己对此有很深的体会。
国外的同行们也是这样。一个学者从博士生到获得博士学位找到助理教授职位,再辛辛苦苦到教授,总有二十多年吧,这么长的时间里,他沉浸在学术写作里,他对文字的评判标准早已凝固。两种不同的思维和写作方式——学术与通俗,他只能集中精力做学术。当然他们中会有人设想,等哪天当上教授,再开始写一点通俗文字,写点不带注释的文章,那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都是理想,等你当上教授,哪怕你真的不在乎评估、不在乎考核了,你也早已养成什么都写成学术论著的习惯。
国外的畅销历史读物通常都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写的,作者往往是一些记者或编辑。这里我说两本书——《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和《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作者查尔斯·曼恩(Charles C. Mann)就是一个记者,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是他却写出了这两本广受欢迎的、讨论全球史的著作。作者写这两本书,几乎参考了相关领域所有的重要论著,从专业研究者那里汲取了全部养分。比如,作者讲发现美洲所导致的物种大交换,以及这种大交换所引发的世界史新发展,最重要的养分来自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 Jr)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比较一下会发现,克罗斯比的书把最核心最基本的观念、概念和思路都写好了,但因为表达的方式是学术的,他对话的对象是历史学同行,一般读者读的时候还是可能常常抓不住要点。而查尔斯·曼恩能用更具体更鲜活的事例,更平易更浅显的文字,把同样的历史写得广阔而生动,普通读者因为更关注具体的故事及其因果联系,他会觉得对他来说内容也变得更深刻了。虽然查尔斯·曼恩的书在学术贡献和思想原创力上远远达不到克罗斯比的水平,可是从让读者更多了解学术世界这个角度说,他成功地将专业研究者的学术成果转变为大众社会文化常识的一部分,所以他对历史学也有了贡献。

史景迁的作品以丰富的历史叙事著称,在海内外享有声誉。
很多年前我还在读博士时,系里邀请许倬云先生来做讲座,我参与接待,有机会跟他聊天。有一次许先生感慨说,他很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知识?我听了触动很大。我们不应满足于自己搞懂了,自己明白了,也需要让别人觉得你的理解有意思。这一点是非常难的,需要写成可读性很强的著作将历史思考表达出来。学术思考的严肃性使得历史学家容易对某些通俗文字的写作者产生蔑视。历史学当然不是讲故事,但历史学在一个很高的层面毕竟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或许多个故事,而思索和探究故事背后的意义,才是历史学的大关怀。但是如何把意义表达出来让非专业的大众读者也明白、也感兴趣?这是个难题。专业历史学家中,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多、最成功的是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比如,在《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中,他利用了各种资料将王氏的生活环境,她所处的社会与时代,精细地、生动地描摹出来。他写的只是一个小地方的故事,但读者能够感受到很大范围内的历史流动。
好的通俗的历史作品的标准之一,恐怕是要让专业工作者不对作品的历史观及历史知识猛烈批评,当然前提是专业工作者愿意去翻看一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由专业历史学家来写这类作品。事实上,我相信在中文世界里,这个类型的写作主要不能依靠专业历史学家。目前阶段,似乎好的通俗历史作品还不多。将来一定会多起来,但多半不会出自学院派。我并不是贬低我们这些专业研究者的能力,只是因为一来长期的专业训练所造成的写作习惯,二来也有个分工需要。潜在的写作者们在哪里?他们必须是历史爱好者,能够及时消化专业研究者的工作,同时又擅长写作。令人高兴的是,现在中文世界里出现了规模很大的、高质量的读者群。这说明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读者对于读物质量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写作者所可以提供的,至少目前阶段是这样。学术资源空前开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空前庞大,许多奇奇怪怪的人才广布深藏,或许再过几年,大批优秀的写作者就出现了。靠了这些写作者,中文也会脱胎换骨,能够发展成人类最好的表达工具之一。希望是这样。
回到历史的非虚构写作上,我相信历史学术圈之外的人将来会扮演主要角色,发挥主要作用。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做学术研究的人继续安静地、并且骄傲地继续做自己熟悉和习惯的工作。专业工作有自己的意义,非专业的写作者会尊重专业研究者,他们为了自己的写作,会读专业的历史研究论著。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专业论著增加了读者,对学术来说这也是很好的。
Q&A
问:现在很多读者要看人的故事,但是历史素材上,除非正好有一个比如像您说的某个人的日记留下来。否则就像您刚才举的《王氏之死》,史景迁需要重建康熙内心。描写一个历史上的人物,我们写作的界限在哪里?哪些东西是我们根据史料可以走到那一步的,哪些是不能夸张的?
答:从历史学来看,某些细节的想象,如果不影响所表达问题的历史学价值的话,部分地是许可的。如果写作者的推测变成了对重要结论有影响的因素,那就是不好的。在中间环节加入一点想象,不影响其他因素的话,大概是可行的,因为要给读者足够的空间。
问:我喜欢历史所以也写过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在历史写作中,看档案材料、回忆录等是一个必备的条件,但是如果材料很多的话,我们怎么取舍这些材料?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很多史料可能是当事人或者后人的认识或者看法,并不一定能够代表真实本身。那么,当我们写作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重构真实,还是写一个虚假的东西?
第三个问题,您的《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是按照历史专业的写法来写的。如果用非虚构的写法重写一遍,我会写那个大汗被勒脖子窒息的场面。这个场景肯定是设想出来的,你在书里面做了详细论证。那么,我在写这样的东西时,是否要把论证的东西写进去?怎么加入这些论证过程,才能使它还是一个非虚构作品,而不会变成专业的历史论文?
答: 在研究过程中,大家会发现自己不停地被意外的线索拉走,总有一种力量把我们拉到另外一条线、另外一个问题上去。大家可以“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也可以盯着原来计划好的那条线不放。都是可行的。无论如何,最终写作不能太乱,只能选择写一个主题。写作是有边界的,不能把全部材料和问题都放进去,不然就不是一个好的写作,只会是一团乱麻。写作必须要有清晰的线索。我写《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的时候,已经有意识地想让更多的人可以读,我把注释减少到了最低程度。论证不是很多,把论证放在叙述里,让人感觉到自己不是在论证,更像是在叙述,但实际上这仍然是一个学术写作。对于非学术的历史写作来说,恐怕论证不能太多,但是不能没有论证。只要是历史,就必须有论证。论证不一定要像传统的清代考据那样,也可以是逻辑性的。西方历史书乍一读似乎考证不多,但却始终在进行逻辑性、叙述性的论证。我们现在中文历史写作里,这种形式的论证做得还不好。这是非虚构历史写作要借鉴的,隐藏论证,但不能没有论证。
关于历史认识的问题,我觉得历史写作要有对历史掌握的深度。我能理解,非历史研究者处理历史问题时,不像专业工作者有宏大的时代把握。这个时候,就得花点精力看看那些专业工作者怎么说历史,不然只能处理小题材,不仅显得写作的说服力不够,而且意义也不大。要想变得有意义,得跟上学术的高度。要理解为什么专业工作者在强调某些话题,为什么他们不在乎另一些话题,你的非虚构历史写作放在这样的视野下,一下子就升华了。
问: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平时会看社会新闻吗?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解读?
答:这个问题常有人问我,你学历史的,怎么看现实中的事。我觉得专业的历史工作者,一定要关注现实,因为只有通过关注现实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我们离过去太遥远了,历史资料都是被一挑再挑、一删再删,说法单一,证据单一。理解现实,对理解过去有很大的帮助。反过来,学历史是否有助于理解现实?从我个人来说,没这个体会。
问:我是新闻系的一名在读学生。作为一个历史专业的学者,您如何看待口述史?同时您刚才提到说,非虚构写作中的一些细节可能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它涉及一些非常私人化的范畴。那么,在处理这些细节的过程中,是否需要再对它做进一步的考证?
答:我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口述史的工作。关于真实性、可靠性,我觉得并不是口述史史料独有的问题。我们读的那些历史资料、历史著作、甚至“二十四史”,不能说一切都是可靠的、真实的。没关系,历史学有足够多的方法处理史料,谎言也是值得分析的史料,比如撒谎的动机,想掩盖什么,想让听众相信什么。要做的是比对各种历史资料,观察历史资料之间的关系,从中认识和理解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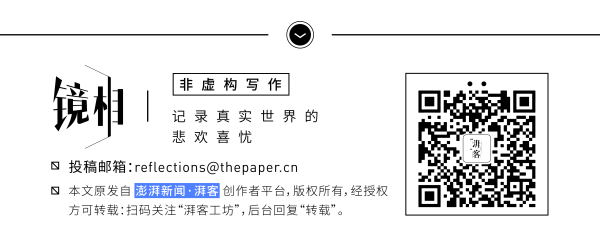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