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隐藏的伊比利亚 | 拉斯乌尔德斯,没有面包的土地
田野
西班牙语专业毕业后,我二十多年的工作和游历大多集中在拉丁美洲:在国际广播电台用西班牙语对拉美广播、去墨西哥学院做访问学者、就连主持央视和凤凰卫视的电视节目,也是从南极纵贯南北美洲去北极,总与伊比利亚无缘。而这次,我终于得闲开始一次穿越西班牙、葡萄牙的大旅行。
一路上,我的目的地总在随时调整,早餐时读到的新闻、路上新结识的朋友、忽然袭上心头的两行诗句、或者一个好玩儿的地名,都让我改变原有的行程。
这些偶得之喜,让我发现一个隐藏在浓艳的旅游推介与褪色记忆之间的伊比利亚。

路易斯·布努埃尔启发的旅程
在马德里最奇妙的体验,莫过于穿行阿托查火车站内的五百多种雨林植物之间,然后,趁水雾留在皮肤上的温润尚未消散,一头扎进索非亚王后艺术中心,沉浸于那些比热带植物更加肆意的现代艺术品中。
根据1995年颁布的皇家敕令,以毕加索出生的年份1881年为界,之前的艺术品藏于普拉多博物馆,其后的一万八千多件现代和当代作品则归入索非亚王后艺术中心。
参观索非亚王后艺术中心就像是一场行为艺术,一场现代和后现代的马拉松。即使是最痴迷的朝圣者,在面对满墙的米罗、达利、塔皮埃斯,和满走廊的达达、超现实和立体主义,也会从最初的狂喜和震惊,慢慢坠入麻木和淡定。
各种折叠倒置的空间、错乱的色彩和难以理喻的想象,轮番肆虐着我的感官。当我站在二楼6号厅的镇馆之宝、毕加索的《格尔尼卡》面前时,已经恍惚得只想休息片刻。
展室尽头的放映间灯光黯淡,沙发柔软。本来只想稍歇片刻,我却渐渐被银幕上正循环播放的一部纪录片所吸引,把《格尔尼卡》全然抛在了脑后。
屏幕上放映的原来是西班牙国宝级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的一部纪录片。这部时长为27分钟的《拉斯乌尔德斯,没有面包的土地》,是他继《一条安达卢西亚狗》和《黄金年代》后的第三部作品。因为前两部影片在法国被禁演,还耗干了他母亲的积蓄和与达利的友谊,因此,布努埃尔对这部人文纪录片充满了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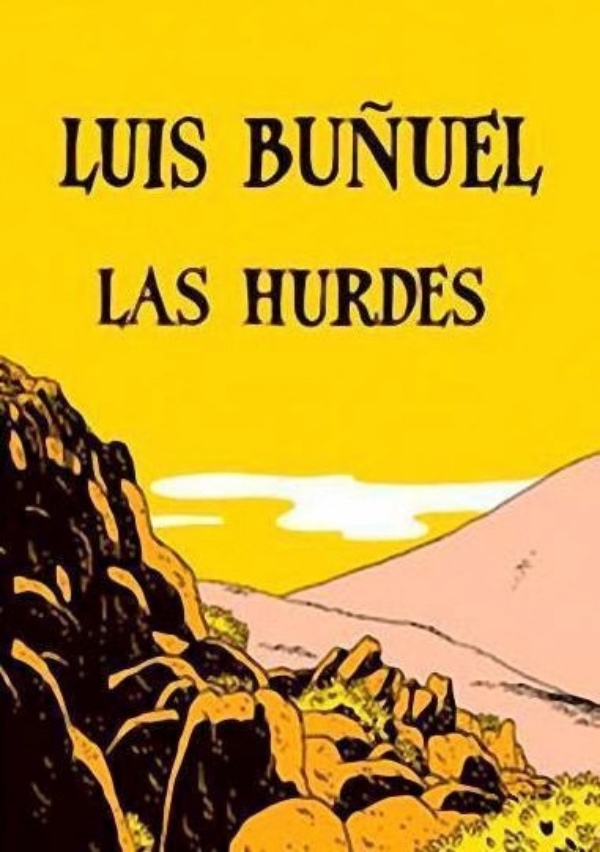
它的拍摄过程颇为传奇。布努埃尔当时在巴黎穷困潦倒,有拍摄计划,却筹不到资金。他的朋友拉蒙·阿欣开玩笑安慰说,要是自己买彩票中了奖,就资助他。没想到话音未落,阿欣真的中了西班牙的圣诞彩票大奖,而他也真的履诺,承担了布努埃尔全部的拍摄费用。
不过,布努埃尔想要拍摄的拉斯乌尔德斯地区(Las Hurdes),在当时的西班牙却是个不愿示人的痛处。它位于埃斯特雷马杜拉大区北部的群山中,风景壮丽,却极度贫穷。
据说在1922年,西班牙国王阿尔方索十三世曾经骑马巡游此地。当他需要牛奶来调咖啡的时候,当地人端来的却是一杯人奶,并抱歉说整个地区连一头牛都没有。这让国王惊愕不已。他几乎是流着泪离开此地。疾病、贫穷、中世纪般的停滞、阴郁和荒蛮,被布努埃尔所纪录的拉斯乌尔德斯,正是当时西班牙在其他欧洲强国眼中的形象,这极大刺激了西班牙人的自尊心。
在1933年春天为期一个月的拍摄中,布努埃尔按捺不住的超现实主义冲动也给这部纪录片带来更多争鸣。为了表现严酷的自然条件,他让助手开枪射杀一头山羊,佯装它是失足跌落悬崖,不过,火药燃烧的硝烟却不慎入画。这些痕迹明显的夸张和失实,成为反对者的口实,影片最终在西班牙和法国都被禁演。
布努埃尔一贯在选题和表现手法上只重艺术、毫不顾忌他人的感受。西班牙内战之后,他流亡墨西哥,拿着墨西哥政府的投资拍了一部反映社会底层小流氓生活的影片《被忘记的人》,引得墨西哥全国上下对他口诛笔伐,骂他忘恩负义。最后还是帕斯等一干知识分子奋力为他的创作自由辩护,才渡过了风波。
姑且不论艺术,对于即将出发去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的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预兆。我决定调整行程,直奔拉斯乌尔德斯地区,去看看这片当年的“没有面包的土地”,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阿尔贝尔卡,腹地与边疆
阿尔贝尔卡是拉斯乌尔德斯地区的门户,距离葡萄牙一步之遥。虽然身处伊比利亚半岛的腹地,却是不折不扣的边疆。
公路在贝哈尔和法兰西山脉之间一连串隐秘、破碎的山谷中穿行。这里地貌崎岖,难得见到平整广阔的农田。路边除了孤直的橡树与叶冠低垂的核桃树,就是花期刚过的欧洲甜樱桃林。在树下层积的落花和恣意盛放的野花之间,整齐地摆放着蜂箱。飞舞的蜂群会被车辆经过时的尾流带得忽聚忽散。
一路行至蜂箱尽处,小城阿尔贝尔卡也就到了。
拉斯乌尔德斯出产的蜂蜜醇厚清亮,在西班牙堪称极品。过去,当地人赶驴运蜂蜜到阿尔贝尔卡,再转卖到山外去。不过,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旅程。盛满蜂蜜的陶罐很容易在山岩上撞碎,如果溅到驴和赶驴人的身上,会引来漫山遍野的蜜蜂。布努埃尔为了在纪录片中展现这一幕,在一头驴身上涂满了蜜,让它在被蜜蜂蜇了一天后死亡。今天看来,这是标准的虐杀动物,但在当时却没人在意。
我在大广场石头十字架附近的小摊子上买了一小袋琥珀杏仁,凝固的蜜糖包裹着一颗颗完整的熟杏仁,爽脆的芳香与粘牙的甜蜜完美地纠缠在一起。
杏仁和这道传统小甜食的作法,都是摩尔人带到这里的。他们也是这个城市的命名者。“Alberca”源自“Al Birkah”,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有水的地方”,特指有蓄水作用的长方形人工池塘。
在摩尔人用刀枪征服的每一个地方,都会一锄一镐地修建以这种池塘为核心的水利系统。源自波斯-阿拉伯地区的绿洲式灌溉农业与半干旱的西班牙,简直是天作之合。这是摩尔人能够在半岛立足八百年的真正根基。阿尔贝尔卡也因此成为了一座繁荣的城市。
几个世纪后,卷土重来的基督徒勒令城市中的穆斯林居民改宗皈依天主教,消灭了一切摩尔时代的痕迹。不过,他们的这番努力,却给这里留下了有趣的印记。老城中几乎每家每户的门楣上都刻着十字架、宗教祈祷词或者箴言,比如:“万福玛利亚,未染原罪的清净受胎者”之类的。这恰恰表明,这里曾经的居民都是改宗者,需要随时坚固他们的信仰。



街巷狭窄曲折,房屋大都是三层:第一层是安稳的石砌结构,门窗狭小以便承重,有些房屋干脆就借用天然的巨石作为地基和墙体。上面两层采用更加轻盈的土木结构,阳台宽敞、窗户密布,可以最大限度地接纳阳光,外立面墙壁则裸露出暗色木质梁柱。这种房屋看起来与阳光酷烈的伊比利亚并不太相宜,倒是更适合阴沉多雨的北方。
其实,从城外环绕的法兰西山脉的名称就可以发现端倪:老城的建造者来自法国。十三世纪初,莱昂国王阿方索九世向自己的大女婿、勃艮第的雷蒙德求助,引入一批勃艮第移民定居阿尔贝尔卡。自此,伊比利亚人、摩尔人与法兰克人在此交融生息,衍生了这座小城的独特气质和诸多奇异的节日和风俗。
布努埃尔在这里拍摄过一个非常奇怪的节日,透着一股中世纪的狂野和阴郁。市民们将一只公鸡倒吊在一根悬架在街道上空的绳索上。 一身骑手打扮的六位新婚男子,必须在骑马飞驰而过,并用手去撸一下公鸡头,最后甚至将鸡头一把拧下来,在广场上巡行展示。随后,这个充满了性隐喻和血腥暴力的仪式画风突转,变成了真正的节日。几名新婚者要请所有居民喝葡萄酒,全城沉浸在一片欢笑中。这个说不清来由的古怪节日,并没能延续至今。不过,阿尔贝尔卡还保留着不少颇具古风的传统。
如果说摩尔人引入了杏仁,勃艮第人建造了房屋,那么伊比利亚基督徒们则贡献了火腿。
阿尔贝尔卡的火腿属于西班牙四大火腿产区之一的萨拉曼卡产区。山区的野生橡实和泉水赋予它一股山野的清香。本地人对猪有着特别的情感。在教区本堂门口的广场上,有一座憨态可掬的猪雕像。


每年6月13号-圣安东尼·德·帕多瓦的圣徒日,市政府都会在这里放生一只小猪。这只猪每天在城里四处游荡,走到谁家门口,居民们就要向它提供吃食。它的快乐生活将持续到来年的1月17日-圣安东尼长老的圣徒日。届时,这头已经吃得身肥体壮的猪将被拍卖,款项用来做慈善。至于它的命运,看看街上土特产店前悬挂的火腿和香肠就可想而知了。
在小橄榄村,土地是人类的女儿
Aceitunilla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小橄榄”,但这个小山坳中多是柏树、柳树和粗硬的灌木,只是村庄里有寥寥几株橄榄树,未免有些名不副实。
布努埃尔在这里拍摄了当时村民的生活和一所新开办的小学校。小学生们在溪水中把学校分发的面包泡软,异常享受地几口吃掉,因为他们从来没吃过面包。这也是片名“拉斯乌尔德斯,没有面包的土地”的由来。
这个在册人口116人的村落时至今日,恐怕仍然是西班牙最贫穷的地方。在村口,86岁的佩德罗和他的妻子、84岁的玛利亚正相对无言地晒太阳。他们正在等待每周一次的汽车商店来到村子。除了自己种的一点儿蔬菜,这里什么都不出产,连面包都要从外面运来。
“我们这儿除了玉米别的都种不活。”佩德罗指了指小溪边人工堆砌的几块梯田。纪录片中,曾经详细介绍了当地人如何耕作:首先,用几周时间在溪水边平整出一块土地,靠水的一侧用石墙围起来;然后爬到高山上的树林中挖土,背回来铺在梯田里。每年地力耗尽,又要重新上山背土。真是用汗水在浇灌贫瘠的土地。


难怪西班牙著名思想家乌纳穆诺会感慨道:“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人类是土地的儿子;而在拉斯乌尔德斯,土地是人类的女儿。”
村子的大多数住房还保持了旧日模样,屋顶用薄石板层叠铺就,远远看去像是怪兽身上的鳞甲。许多房屋已经人去楼空,只剩下嶙峋的梁柱和倾颓的夯土墙。我发现还能住人的房屋门上都斜插着一束半干的橄榄枝,想找人询问,敲了几户都没人响应。终于,我等来了年近六十的奥尔登萨。她刚从附近山上下来,打算把几株野花移种到窗边的花盆里。她说这些橄榄枝是在圣周期间接受过祝福的,可以对抗暴风、冰雹、雷电、骤雨等极端天气。山村最怕的就是会引发山洪的暴风雨。
奥尔登萨的几个孩子都在潘普洛纳生活。最早村里的某人在那里立住了脚,同乡们也就认准了潘普洛纳,虽然距离很远,却形成了移居传统。如今,年轻人都走光了,她在村子里都算是岁数小的了。刚要告别,奥尔登萨让我稍等一下。她从家里拿了一盒甜食让我带着路上吃,说这是孙子回来探亲带给她的,一共两盒,她自己留了一盒,叫我千万不要客气。
一时间,我感觉自己回到了华盛顿·欧文笔下那个质朴热情的西班牙。

手捧着几块存放得已经有些发硬的甜点,我沿着石板路走过这个半是废墟的村落。老夫妇还在晒着太阳等候今天的面包。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我依稀听到玛利亚口齿含混地唱着一首谣曲:“我的所有记忆都停留在那个你爱着我的夜晚…”那一瞬间,我忽然很想对布努埃尔说一句:“你错了!”因为他在片子的结尾说:“在这个贫穷的地方,你永远不会听到人们会歌唱。”
拉斯乌尔德斯,这片没有面包的土地,反而比精致的美术馆和后现代的大师们更贴近我心中的西班牙,一个即便被时代抛在身后、即便困顿于贫穷,却依然严守自尊、古道热肠的古老西班牙。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